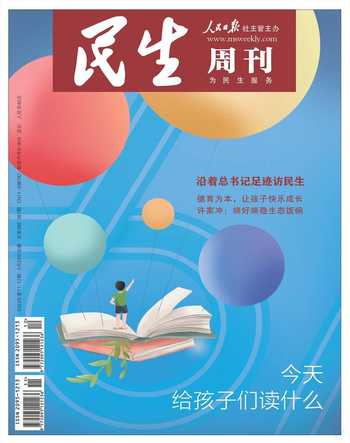大汗淋漓童書熱
郭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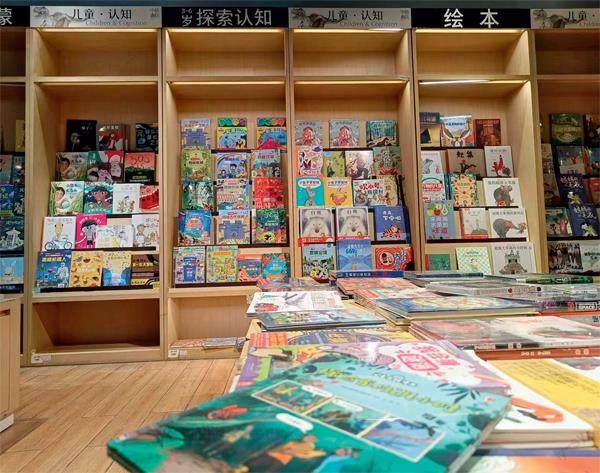
琳瑯滿目的童書貨架,代表的是童書市場的火熱。
林沫是個不愛讀書的中年人,一年到頭也讀不了三四本。但她又是個愛買書的年輕媽媽,自打孩子會說話,家里的童書就越來越多。如今,家里的書已經堆得像“小山”一般高,7歲的兒子哆哆也像玩積木一般,經常會把五顏六色的書弄得滿地都是,然后再規規矩矩地擺放整齊。
“只要孩子想買,我就會滿足他,買書總比買玩具和零食好吧!”林沫覺得,買書是很高級的消費,而且還是隱性的投資。
趕上周末,只要有時間,她就會帶著哆哆去實體書店逛上一圈。她發現,在大型書店的兒童專區里,人流密度并不比游樂園低。年輕的家長們大多坐在一旁盯著手機,孩子要么四處走動說笑,要么拿起書安靜地閱讀。“臨走時,部分家長還會買上一兩本孩子說喜歡看的書。”
事實上,林沫身上發生的,和她在書店所看見的,正是我國目前許多家庭都真實存在的現象,以至于有網友說:“耐人尋味的是,在國人的讀書時間不足經常被拿來說事的今天,我國童書卻賣得很火。”
那么,童書熱現象的背后是什么?
在浙江大學民生保障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何文炯看來,如今的年輕家長普遍重視兒童教育,并將購買童書作為一種重要的人力資本投入,他們希望通過閱讀提高子女的素質和能力,為今后的發展奠定基礎。
“政府通過提倡素質教育,尤其是‘雙減政策出臺后,學生和家長都希望有更多的閱讀,因而對課外圖書需求增加。同時,隨著經濟發展,普通百姓家庭收入提高,總體上說,他們購買童書的能力逐步增強。”何文炯在接受《民生周刊》記者采訪時說。
童書發展黃金期
目前,我國的童書出版市場到底有多熱?
有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說明問題。據出版商務網報道,2000年,我國少兒圖書占整體圖書零售市場的比重還不到10%,而2021年其占比已增長至29%。在2022年1—9月,占據60%市場份額的“金品種”圖書中,少兒品類占比最高,達到32.59%;品種數最多,有10076種。
另據《2022年圖書零售市場年度報告》顯示,2022年我國圖書零售市場碼洋(“碼洋”是圖書出版發行部門專指全部圖書定價總額的詞語)規模為871億元,“從2022年各類圖書的碼洋構成看,少兒類是碼洋比重最大的類別,且碼洋比重進一步上升”。
林沫說,她眼看著小區附近一家書店的兒童專區面積越擴越大,售賣童書的數量也越來越多。
而我國童書市場的發展,也如兒童專區一般,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記者梳理發現,最初,我國圖書市場并沒有將童書和成人書進行區分,“小人書”連環畫成了幾代人的童年閱讀記憶。但大部分的連環畫并非專為兒童出版,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也使得這一階段的童書市場相對空白。
2000年初,隨著在西方已經發展了百余年的圖畫書這種兒童出版物,經由日本,以“繪本”的名稱引薦進中國后,圖畫書因其天然承載的兒童性、圖文結合的獨特形式,及其背后隱藏的科學而先進的親子教育觀,逐漸為國內市場所認可和接受。
“新穎的形式和理念與當當網的電商業務發展撞了個滿懷,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推動下,2005—2015年,中國童書市場正式進入第一個黃金十年。”資深童書出版人、奇想國童書創始人黃曉燕告訴記者,除了傳統的兒童出版社外,市場還涌現出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童書品牌,并帶動了大量海外優秀童書的引進。
值得強調的是,有報道稱,截至2018年,我國580家出版社中超過95%的出版社參與了童書出版。
內卷
隨著書架上琳瑯滿目的圖書越來越多,林沫近幾年還觀察到一個有意思的變化,“雖然童書裝幀愈加精美,但是由于購買童書的渠道增多,購書成本反而降了下來。”她清楚地記得,大約在2018年前后,她一度不舍得花錢給兒子買繪本,就是因為“太貴了”。
“隨便一本薄薄的繪本,定價都在三四十元,甚至是五六十元。”起初她覺得貴點也沒什么,畢竟買書不像買菜,但是給孩子買書會“上癮”,她總想讓孩子接受不同領域的知識,時間長了,買繪本的支出有時會占當月生活支出的“大頭”。有一次,朋友送了她幾本二手繪本,林沫如獲至寶,感覺像是撿到了大便宜。
記者在北京、河北、安徽等地采訪發現,不少有孩子的家庭,家里童書少則十幾本,多的甚至有幾百本。北京市民王曉倩的孩子沒到6歲,家里的書架和抽屜里都是孩子的書。王曉倩數了數,僅書架一層就擺著100多本童書。
眼下,包括林沫和王曉倩在內的大部分家長,購買童書的首選途徑還是網購。近一段時間,通過小紅書、抖音主播推薦而購入童書則成為主要方式。“算上各種購物券和贈品,網絡購書要比去實體書店便宜很多。”
盡管購書成本相對降低,但是對林沫和王曉倩來說,卻越來越不會給孩子買書了,“有時候被推薦一本書,上網一搜,有好多相似的版本,實在不知道該買哪個。”
“比如《我為什么不能》《我為什么不行》《我們的身體》《認識我們的身體》,算上朋友送的和自己買的,我家的書柜里竟然有3個版本的《十萬個為什么》。”林沫正打算把其中一套送給樓下的鄰居或者掛在二手交易平臺交易。
她還發現,很多關于情緒管理類和道理類的童書,雖然版本和書名不同,外觀設計也精致,但是里面內容大同小異,“這本的主人公是阿貓,那本的換成了阿狗,故事也都相似”。
王曉倩也表示,有些童書雖然知識多,但缺乏故事性、趣味性,“有時自己看了都犯困。家里買的科普書,大多在書架上吃灰,孩子翻幾頁就放下了”。
以上種種,都意味著童書市場正在“內卷”起來。
“家長在童書購買方面處于決策者地位,因此,兒童家長對童書的認知十分重要。”
原創能力的冷思考? ??
針對部分家長在選擇童書上遇到的諸多情況,浙江大學民生保障與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何文炯分析認為,從童書的供給側看,這些問題值得重視。
“一是從整體上看,已出版童書的質量不高,原創性弱,對兒童成長的啟迪性不強。二是某些童書粗制濫造,甚至出現明顯的差錯,甚至是政治性錯誤。三是從統計數據看,童書的銷售額持續增長,但究竟是童書的品種和銷售數量增加還是童書價格上漲?四是某些童書被編成‘大部頭,過度系統、完整;某些童書裝幀過于考究,浪費社會資源,增加家長經濟負擔。”何文炯說。
資深童書出版人、奇想國童書創始人黃曉燕也指出,相比多達一億多的適齡兒童人口基數,我國每年出版的童書新品數量和種類不夠豐富,內容仍缺乏原創性、獨特性和多樣性。
更有觀點指出,我國目前一邊是不斷擴大的市場和對好書的饑渴需求,另一邊則是原創內容供給能力瓶頸,這已經成為我國童書市場發展的主要矛盾。
何解?
何文炯建議實行綜合治理,在加強童書編寫研究方面,他認為一方面要考慮童書內容的研究,即選擇什么樣的內容作為兒童的讀物,這里的關鍵是要基于人性和兒童的長遠發展,以經典著作為基礎,結合時代進步并面向未來,來確定可以編入兒童讀物的內容;另一方面是童書的表達方式,即采用便于各年齡段兒童理解、喜聞樂見的方式,將兒童讀物內容用文字或圖像表達出來。這就需要有一支專業性的隊伍持續地加以研究。

童書的種類多了,但質量高的讀物卻并不好選擇。
“家長在童書購買方面處于決策者地位,因此,兒童家長對童書的認知十分重要。但目前部分家長對童書的重要性理解不到位,有的家長是盲目跟風,也有相當一部分缺乏財力。”所以,何文炯認為政府和社會需要通過有效的渠道對家長進行引導。
在出版業深耕多年的黃曉燕觀察到,大量競爭者的涌入和粗放式的發展,讓童書行業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也讓市場形成了兩極分化的局面。
她將如今的童書出版企業分為兩種:一種做品牌,其生產的書都有著“非常清晰的面目”,有思想性、藝術性,幫助孩子在精神和審美能力上有所成長;而另一種出版商則專注于掙快錢,書雖然粗糙但售價低廉,薄利多銷,靠銷售數量取勝。
在黃曉燕眼中,出版業雖然本質上是一種商業行為,但一家出版機構安身立命的根本,還是其所深具的文化屬性,應該以出版穿越時空的經典為追求。“堅持做優秀原創、堅持長期主義無疑是困難的,需要更多定力,但也因此而更凸顯其重要性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