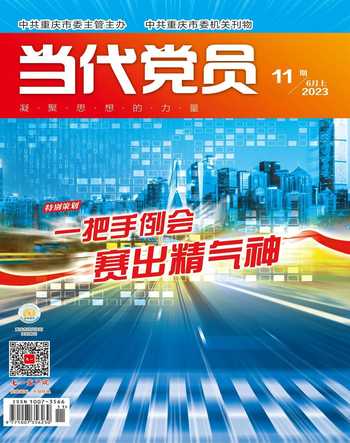花田四季圖
彭鑫

人間四月,春水如魚。
海拔一千多米的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菖蒲蓋上,一股股春水漲起,涌向何家巖。它們晶瑩靈動,恰似一條條美麗的魚。它們從虬勁的古松下游過,從青青水草旁游過,從孩童的指縫間游過,從農夫的夢中游過……然后,它們輕巧地繞過一座一座木樓,帶著李花白、桃瓣紅、櫻桃香,青菜的根莖、牛羊的輕吻、山村的心愿,游向希望的田野。沒幾天,萬畝梯田就幻化了,波光閃閃的,仿佛千萬面鏡子拼嵌而成。
這個時節,草很肥嫩了。太陽帶著露水,剛從東方的青山間露出半個頭來。農夫就牽著耕牛走出牛欄,走過田埂,走向小河。那里水草豐茂。農夫知道,吃了一冬干稻草的牛,饞那一口。耕牛貪婪地張著大嘴,舌頭一卷,一大把青草就落了肚。草間的露水,把牛唇、牛鼻,滋潤得清亮亮的。清冽的霧氣,不時地涌向農夫的口鼻。農夫的心也清亮亮的。
梯田蓄水好些天了,泥土松軟如膏。
一蓑衣,一斗笠,一耕牛,開犁了。耕牛健壯,犁口鋒利,泥土一行行地翻轉,農夫一邊吆著牛,一邊吹起了口哨。山鳥聚過來了,在春泥中一蹦一跳,啄食蟲子。一只陽雀,吃飽了,竟站在牛背上,嘰嘰喳喳。農夫看著鳥兒,好像看著自己八歲的兒子。他們都愛在大人做事時,圍著大人“聒噪”個不停。
小滿一過,“開秧門”了。
花田鄉海拔高,氣溫上升得緩,所以插秧的時間稍晚。寨子沸騰了。老漢們吹牛角、吹嗩吶。孩子們蹦蹦跳跳,喜鵲一般鬧喳喳。
農夫一仰頭,干了插秧酒,走下水田。泥土很軟很涼。他握著碧綠的秧苗,內心充實寧靜,仿佛美好的日子已經攥在手中。插一行秧,退一步;又插一行,再退一步……一步一步后退,一步一步把秧苗插滿稻田。
一周后,萬畝梯田已經寫滿萬千行“綠色文字”。它們是大地上最動人的詩行。它們將拔節、分蘗、抽穗、結實,最后變成金色的詩句。農夫站在田埂上,敞開衣衫,吹著微風,愜意地望著這片深愛的土地。他感覺雙手仿佛已經能撫摸到那沉甸甸的稻穗了。“人勤地生寶,人懶地生草。”農夫揉了揉腰說。
稻田間看夏星,別有一種詩意。
水稻正是青蔥時節,宛如人生的青春歲月。農夫在星光下,看水稻的長勢,看田里的水多水少。有的要放水,有的還得繼續蓄水。夜里稻田的空氣與白天不同,似乎洋溢著一種淡淡的香味,很純正。水稻是草木之秀,自然如此。
忙完了,農夫徜徉在田埂上,欣賞兩種星空。一種星空在天上,一顆顆星星,碩大,晶瑩。晶瑩到感覺一碰即碎。一種星空在梯田里,一塊梯田就是一塊星空,一塊塊星空從山腳蜿蜒到山腰。星星們躲在禾苗下,躲閃著,亮晶晶的,帶著一絲絲清涼的水汽。農夫常常很晚才睡,但第二天起來,依然神清氣爽。許是田野之氣養人。
秋姑娘伶俐,萬畝梯田幾天就織金鋪錦了。
一顆顆稻粒,金黃飽滿,閃爍著金屬的光澤,仿佛是從大地深處掏出來的金子。農夫看著看著,就陷入沉思。他想到了美味的米豆腐,想到了先輩們開墾梯田的艱辛,想到了妻子的新手機,想到了兒女的新衣服。
稻穗一日沉似一日,終于開鐮了。農夫一彎下腰,就一定要割到田的另一頭才抬腰。所以,農夫總是割得很快。秋陽如虎如火,汗水濕透了農夫的前胸后背。一陣山風吹來,汗水全收。山歌常常在此時響起,隨風飄到寨子里,飄到鄉鎮上,飄到有些人的心間。
農夫有時也會停下來,站在金色稻浪間發會呆,感覺自己好像站在大地的心臟上。他的心情也被稻浪染成了金色。他覺得世間的美好,都有著成熟稻谷的金黃,比如童年,比如幸福,比如鄉村振興。
冬至了,大雪鋪天蓋地。
一夜,門前的溪水就被凍住了,起了一層層魚鱗似的冰凌。一家人圍著火鋪而坐,農夫捧著本書看,妻子織著毛衣,女兒在做作業,兒子在玩棕編的蛐蛐。紅炭煨著的紅薯,散發著焦香。燉著臘排骨的鼎罐,也在咕咕作響。農夫望著窗外,黛瓦白雪,令他恍惚,仿佛看到了唐詩宋詞里的一個自己。農夫愛土地,也愛詩詞。《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兩本書的護套,已經換了好幾回了。
天要黑了,他走到牛欄邊給牛添草。金黃的稻草垛,戴了頂大白帽。農夫回頭望了望屋后的青山,笑了笑:“嘿,你也戴了頂大白帽。”雪又下了起來,給一層層的梯田仔仔細細地蓋上了棉被,沒有一寸土地是漏風的。豐年好大雪!
這時,寨子里的燈火都亮了起來,仿佛是花田睜開了幾百只眼睛,在和農夫一起欣賞花田雪夜詩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