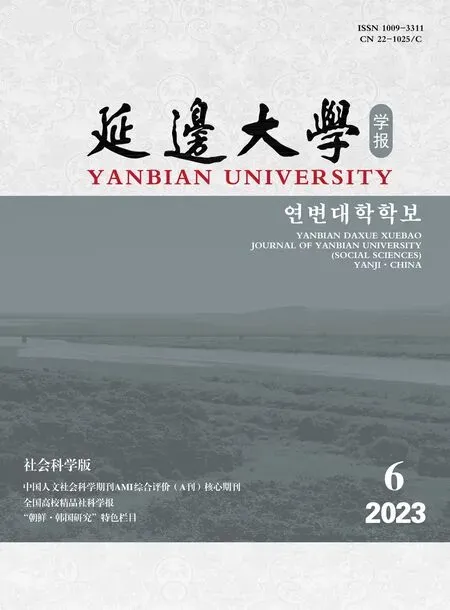“筮法”與“經旨”之間:試論朝鮮丁茶山的易學
廖 海 華
丁若鏞(1762—1836年),字美鏞,號茶山、與猶堂,是李氏朝鮮后期實學派思想的集大成者。(1)邢麗菊:《韓國儒學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5頁。茶山遍注群經,著有《周易四箋》《喪禮四箋》《中庸講義》《論語古今注》《梅氏書評》《春秋考徵》等,卷帙宏富。其治學方法兼顧漢宋,旁采西學,具有強烈的實學精神。在易學方面,茶山的《周易四箋》對《周易》經傳作了體系性的重新解釋,而《易學緒言》則對中國易學史上的諸多名著作了細致的學術評論。此兩書置諸整個近世東亞易學史中,也堪稱上乘之作。
由于茶山易學在朝鮮乃至東亞易學史上的重要性,近年來相關研究頗多。這些研究主要涉及兩個話題。其一,茶山的易學解釋體系包含諸多象數體例,如被他稱為“四法”的推移、物象、互體、爻變,關于這些體例有許多專題性研究。其二,茶山對易學史頗為注意,對前人的引用和評論在著作中隨處可見。因此,茶山與易學史諸名家(如朱熹、朱震、來知德、毛奇齡、李星湖等)的學術史關系也頗受注意。(2)國內研究者中,林忠軍先生具有代表性,他對丁若鏞的“推移說”“爻變說”“太極說”分別有專題論文,并且從象數易學發展史的宏觀視野出發,指明了茶山這些學說與中國漢宋易學之間的密切關聯及其特色所在。韓國研究者中,方仁先生較有代表性,他是《定本與猶堂全書》所收標點本《周易四箋》《易學緒言》的整理者,其茶山易學研究既涉及《周易四箋》版本考證這類文獻學問題,也涉及茶山與歷代易學之關系、茶山易學的“記號學”解讀等理論性問題。這些專題性考察豐富了對茶山易學的認識,但也留下不少疑問:人們誠然可以對茶山易著中的各條象數體例進行細致研究,但這些體例究竟是在一種怎樣的解釋思想下被統一起來的?這一問題仍顯得含混不清。同時,如果我們不搞清楚茶山易學的根本性原理,則即使將他與中韓易學史上的諸家進行比對,也只能得到細節上的異同,而無法看清其學脈的來源。一個明顯例證是,茶山在《周易四箋》卷首“四箋小引”中強調其易學“四法”都承自朱子,但若對比朱子《周易本義》與《周易四箋》,則兩者在象數體例和卦爻辭解釋上異遠多于同,那么,是否茶山的自述乃是無意義的虛言?(3)[韓]方仁:《丁若鏞的〈朱子本義發微〉研究》,《茶山學》2011年總第19期,第6-8頁。
對于上述問題,目前常見的象數體例考察和易學史源流考索似都略顯不足。有鑒于此,本文由“筮法”觀念在茶山易學解釋中的基礎地位出發,考察“筮法”如何貫通其易學體系,并為此體系中的諸種解釋體例賦予意義。在此基礎上,才能充分理解茶山易學的內在統一性,而其與朱子易學之間的相互呼應關系也可順理成章地得到闡明。
一、茶山《周易》新解與朱子易學
茶山易學最令人印象深刻之處,是其試圖對《周易》進行全盤新解的雄心和努力。這可通過《周易四箋》解釋學面貌與傳統易學義理、象數兩派的不同來加以簡略說明。首先,茶山主張“一字一文,皆取物象”,(4)[朝鮮朝]丁若鏞:《周易四箋》卷一《括例表上》,《定本與猶堂全書15》,首爾:茶山文化財團,2012年,第34頁。下引《周易四箋》皆為此本,僅隨文標注書名、篇名、頁碼。并且將此最嚴格的“象辭相應”觀念作為解釋所有卦爻辭乃至《易傳》的原則,這就導致茶山易學與王弼以來的義理派面貌全然不同。其次,茶山對象數學說的運用有其自身獨特的體例,這包括對爻辭和《小象》的解釋充分運用爻變說,對卦辭與《彖傳》的解釋完全不用爻變說等,這使其與一般象數派易學也相當不同。其中,爻變說的運用尤為關鍵。所謂“爻變”,是指占筮中凡遇老陽之數(九)或老陰之數(六),則發生陰陽交易,即老陽變為陰,老陰變為陽。《周易四箋》以“初九”和“初六”為例云:“其曰初九者,謂初畫動而為陰也;其曰初六者,謂初畫動而為陽也。”(5)《周易四箋》卷一《括例表上》,第50頁。因此,乾卦初九就是乾卦初畫“動而為陰”,也就是乾卦變為姤卦。《左傳》記載蔡墨將乾卦初九稱為“乾之姤”,正是爻變說的關鍵證據。茶山認為:“周公撰詞之初,原主既變之體而用其物象。不知爻變,則不可以讀周公之詞也。”(6)《周易四箋》卷一《括例表上》,第50頁。也就是說,《周易》爻辭必須基于爻變才能得到正解,然而“自漢以來,爻變之說,絕無師承”,(7)《周易四箋》卷一《括例表上》,第51頁。因此《周易》也就長期不得其解。對于爻變說能善加運用,這無疑是茶山在易學上高度自信的關鍵所在。當然,茶山《周易四箋》最后定本著成于戊辰年(1808年),其時他對中國易學史的研究尚未完成。到了十幾年后的嘉慶庚辰(1820年),當茶山寫作《易學緒言·茶山問答》時,已注意到宋代易學史中爻變說的存在:“《文獻通考·經籍考》載《周易變體》十六卷,宋都潔所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專論之卦為主。恨未得此書見之也”。(8)[朝鮮朝]丁若鏞:《易學緒言》卷四《茶山問答》,《定本與猶堂全書17》,首爾:茶山文化財團,2012年,第315頁。下引《易學緒言》皆為此本,僅隨文標注書名、篇名、頁碼。又按,都氏之書,《文獻通考》確著錄為“《周易變體》十六卷,都潔撰”,而《四庫全書總目》則據《永樂大典》輯本著錄為“《易變體義》十二卷,都絜撰”。也就是說,茶山后來通過《文獻通考》間接得知宋代都潔以爻變解《易》,因而知曉爻變說至近世仍不絕如縷。以后見之明觀之,在東亞易學史中,全面運用爻變說來解釋《周易》者固然并非僅丁茶山一人,但確實為數甚少,且應以茶山的解釋最為靈活巧妙、最具體系性。可見,即使僅就爻變說一點來看,茶山易學已經足以自成一家。更何況,茶山“四法”中除“爻變”之外的“物象”“互體”“推移”,雖然與傳統象數派之間共通點較多,但仍有極強的茶山個人特色。例如,易學史上講“推移”一般均就十二消息卦講,而茶山則以十二消息卦對應十二月,并以中孚、小過兩卦對應“五歲再閏”,以此十四卦為“辟卦”而推衍出其余五十個卦,并由此解釋“大衍五十”之義,其學說確實頗具巧思。
茶山的《周易》新解并非無源之水,從易學史的演變來看,可將之追溯至朱子易學。在《周易四箋》卷首的“四箋小引”中,茶山也提出,其易學“四法”均來源于朱子。以爻變為例,“四箋小引”云:
朱子曰:“遇一爻變,以本卦之變爻辭占。”【見《啟蒙》】占法既然,經旨宜同。爻變者,朱子之義也。(9)《周易四箋》卷首,第32頁。
所引朱子之語,見于其《易學啟蒙·考變占》。(10)朱熹:《易學啟蒙·考變占》,《朱子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8頁。由這一條我們可以看到茶山對于朱子學說的轉化。這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朱子《考變占》中列舉了一爻變、二爻變、三爻變乃至六爻皆變的種種情況,而茶山則認為《周易》筮法僅有一爻變,因此將《考變占》涉及多爻變的內容都略去不提。其二,朱子《考變占》雖然明確了上古筮法主要以變爻為占,但《周易本義》解釋爻辭的根據卻仍然只是此爻在本卦中的爻位、爻性,完全不考慮爻變的問題。而茶山則以“占法既然,經旨宜同”為理由,將筮法中的“以變爻為占”應用于《周易》爻辭解釋而成為爻變說。
茶山這種由“占法”而推“經旨”的思想,對于朱子易學是一項非常關鍵的推進。眾所周知,朱子在易學方面的最大創見就是提出“《易》本卜筮之書”。此說對于易學解釋有著根本性的沖擊,意味著《易傳》以來的中國易學解釋傳統有偏離《周易》“本義”的危險,對“本義”之探尋需要回到“卜筮書”這一原點重新出發。基于這種洞見,朱子在具體的《周易》文本詮釋方面做了很多開創性工作,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成果豐碩的體系。(11)如張克賓所說,“《易》乃卜筮之書”是朱熹易學的“基源問題”。參考張克賓:《朱熹易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頁。然而,此體系也遺留了一些問題,其中關鍵的一項是,朱子雖然認為卦爻辭皆卜筮之辭,但在解釋卦爻辭與卜筮之關系時,卻只及其“用”而不及其“體”。以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為例,朱子解釋的重點在于占筮者遇此爻時應如何將爻辭運用到自身處境中去,如言:“若揣自己有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圣人作而萬物咸睹。自己無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彼之大人”。(12)《朱子語類》卷六十八《易四》,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696頁。這無疑是對卜筮過程中此爻辭之“用”的精彩詮釋。然而,在卜筮語境中此條爻辭本身究竟是以何為根據被創作出來的,為何要取“飛龍”“大人”之象而非其他?這種涉及卦爻辭之“體”的問題,朱子并未能基于“《易》本卜筮之書”命題而作出較好解答。與此相關聯的是,朱子雖然認為卦爻辭必有象數根據,但在解釋具體卦爻辭時,常言其取象方式大多“不可曉”“今不可穿鑿”,(13)《朱子語類》卷七十《易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774頁。因此其《周易本義》實際上延續了王弼、伊川等人的解釋風格,并未真正深入卦爻辭的象數根據。
可見,朱子雖云“《易》本卜筮之書”,但其易學解釋中卜筮與《周易》大體上仍處于相互外在的關系。因此,發展朱子易學的關鍵就是澄清《周易》與卜筮之間的內在關系,為《周易》解釋找到一個堅實地基。茶山論證爻變說時以“占法”推“經旨”的做法,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在茶山看來,《周易》是從上古筮法傳統中孕育出來的,卦爻畫和卦爻辭的內在結構都需基于筮法傳統才能得到確切理解。其易學解釋的整體思路不妨總結為:由“筮法”而推“經旨”。(14)茶山易學中“卜”與“筮”的區分具有關鍵意義(詳見下文),因此不用“卜筮”一詞。同時,“占法”乃從屬于“筮法”的子概念,因此也不用“占法”一詞。對此整體思路的澄清,就是茶山易學最重要的價值所在,也是其易學解釋得以成立的根基和前提。其中主要涉及兩個問題:其一,“筮法”的基本邏輯是什么;其二,如何由“筮法”的基本邏輯推導《周易》之“經旨”。以下對此兩個方面分別加以說明。
二、“筮法”的基本邏輯
關于“筮法”的本質,茶山在《易論》一文中有較系統的說明。(15)此文既收錄于《周易四箋》卷四,也見于茶山《詩文集》卷十一。《易論》試圖探索《易》之起源,其開篇即云:
《易》何為而作也?圣人所以請天之命而順其旨者也。(16)《周易四箋》卷四《易論》,第328頁。
《易》的功用在于“請天之命”,也就是在具體的行事上首先知道“天命”的意旨,并以其為行動依據。如果“天”乃是其他文明中那種人格神形態,則“請天之命”就意味著直接聽取神諭或啟示,但在中華文明體系中“天”不取此種形態,因而如何“請天之命”變成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雖然,圣人能切切然請之,天不能諄諄然命之。則天雖欲告之成而勸之使行,末由也。又雖欲告之敗而沮之使勿行,亦末由也。(17)《周易四箋》卷四《易論》,第328頁。
如孟子所說,“天不言”,不能對人“諄諄然命之”(《孟子·萬章上》)。雖然“圣人”有“請天之命”的誠意,但“天命”如何傳達給“人”卻仍舊是一個難題。在孟子那里,這一難題是通過《尚書·泰誓》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來解決的,由此闡發了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而茶山借用此語,卻是要說明筮法起源于此天人如何相接的難題:
圣人是憫,蚤夜以思,仰而觀乎天,俯而察乎地,思有以紹天之明而請其命者。一朝欣然,拍案而起,曰:“予有術矣。”于是以手畫地,為奇偶剛柔之形,曰:“此天地水火變化生物之象也。”【此八卦。】因而為之進退消長之勢,曰:“此四時之象也。”【此十二辟卦。】又取之為升降往來之狀,曰:“此萬物之象也。”【此五十衍卦。】于是取其所畫地為奇偶剛柔之勢者,玩其象,憶其似,若得其仿佛者,而命之名曰:“此馬也,彼牛也。此車也,彼宮室也。此戈兵也,彼弓矢也。”著之為法式,冀天之因其名而用之。雖人立之名,非天之所以為實,然天茍欲鑒吾誠而告之故,則亦庶幾因吾之所為名,而遂以是用之也。(18)《周易四箋》卷四《易論》,第328-329頁。
上古“圣人”用以實現天人相接的“術”就是筮法。筮法首先需要一個用以進行占筮的卦象系統。這又可分為兩步:第一步是“畫卦”,即相繼畫出八卦、十二辟卦(實際上有十四卦)、五十衍卦,以象征天道生成萬物的過程;(19)茶山云:“《周易》推移之法,全侔造化”(《周易四箋》卷八《系辭上傳》,第280頁)。林忠軍說:“(茶山的)十二辟卦推移生衍別卦模擬了天地日月變化及其生成萬物的過程。”林忠軍:《論丁若鏞“推移說”與漢宋易學——兼論朱熹、毛奇齡推移說對丁若鏞的影響》,《周易研究》2015年第3期,第7頁。第二步是“命名”,使得每一卦都有一套象征對象,如此卦象征馬、彼卦象征牛之類。如此得到的卦象系統,其本質仍然是某種人為創作的符號系統,并非“天之所以為實”。但是,在“天不能諄諄然命之”的限定之下,我們所能合理期待的天人相接方式就是“天”能“庶幾因吾所為之名”,通過此卦象系統而對人有所指示。
有了卦象系統,就為天人相接、請天之命奠定了可能性的基礎。接下來就需要對此系統加以恰當運用。這也可以分為兩步:第一步是在卦象系統中隨機擇取某個具體的卦爻,此即揲蓍之法;第二步是就所擇取的卦爻解讀其中所蘊含的“天命”,此即占斷之法。關于揲蓍之法,茶山《易論》云:
于是出于野,取芳草若干莖,與其所為升降往來者,合其數以相應,敬以藏之于室而待之也。【此蓍策五十。】每有事,出而握之,既又為之劈而四之,曰:“此四時之象也。”又于是散之聚之,參伍之,變通之,曰:“此萬物之象也。”既已算其數而著其形,形成而體立。【此筮得一卦。】(20)《周易四箋》卷四《易論》,第329頁。
揲蓍之法與上述“畫卦”過程有著平行對應關系。據茶山《蓍卦傳》之解釋,其“蓍策五十”象征天道一源,“劈而四之”象征四時,“參伍變通”象征萬物,相當于重新演繹了一次天道生成萬物的路線。“筮得一卦”之后,需從中解讀“天命”之所指,此即占斷之法:
于是取所謂馬、牛、車、宮室、戈兵、弓矢,仿佛之象,察其所升降往來之跡,而其形之或全或虧,或相與或相背,其情之或舒或蹙,或可悅,或可憂,可恃、可懼、可安、可危者,無不以其仿佛者而玩之。【此占其吉兇。】(21)《周易四箋》卷四《易論》,第329頁。
占斷之法與上述的“命名”也是相互對應的。其不同在于,“命名”是在卦畫與物象之間建立一套靜態的聯結關系,而占斷的重點則是“察其所升降往來之跡”,在“變”中觀“象”。變中觀象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最初畫卦過程中,五十衍卦是由十二辟卦“推移”而來;同時,六十四卦之間又通過“爻變”而具有彼此轉換的可能性。因此在茶山看來,升降往來、變動不息本就是卦象系統的主要屬性,也是筮法區別于卜法的本質特征。卜、筮兩者都是通過一套符號象征系統來“請天之命”,但筮法基于數的演算,不同卦象之間自然有一套相變相通關系,而卜法所得的“兆體”都是通過燒灼龜甲形成的自然裂紋,所謂“卜之兆也,方、功、義、弓,各有定體”,這些“兆體”彼此之間不可能形成易卦那種規整的相變相通關系。(22)《周易四箋》卷四《易論》,第329頁。正因為筮法蘊含了豐富的“變”之形式,才能發展出內涵極為豐富的“易辭”并形成《周易》經典,而更為古老的卜法系統反而湮沒無聞。茶山此種“卜筮之辨”,與王夫之“龜之見兆,但有鬼謀,而無人謀”的說法所見略同,(23)王夫之:《周易內傳·系辭下傳》,《船山全書》第一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615頁。與現代易學研究者的見解更有不謀而合之處。(24)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第7頁。
在茶山易學的筮法邏輯中,天人之間是充滿張力的,因為人的理性在此為自己設置了一個難題:“人”雖然相信“天”的超越地位與權威,但其理性已經無法相信一個“諄諄然命之”的“天”了,因此天人之間如何相接才顯得煞費思量。如上文所述,正是由此困境才逼出了一套筮法程序。這套程序要有效,其關鍵無疑在于卦象系統連接天人的功能。關于這一點,茶山有兩種論述。首先,如上引《易論》所言,卦象系統的設計與運用都小心翼翼地模擬天道,最大程度地體現了人的敬天之誠。因此,雖然此卦象系統不過是“人立之名”,但仍可期待“天”能“鑒吾誠而告之故”。其次,關于卦象系統連接天人的功能,茶山偶爾亦有更激進而神秘化的表述,認為八卦物象乃是“伏羲畫卦之初”“與神明約契者也”。(25)《周易四箋》卷一《括例表上》,第42頁。這就不是將卦象系統定位為簡單的“人立之名”,而是將其來源追溯于“神明”,作為其神圣性和有效性的根據。從中,我們無疑可以看到茶山思想受西學(天主教)影響的痕跡。(26)茶山周圍天主教相關人士頗多,如其妹夫李承熏(1756-1801年)曾在出使中國期間在北京接受洗禮。參見邢麗菊:《韓國儒學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6頁。然而,只要“天不能諄諄然命之”這一前提不變,則所謂“與神明約契”,仍舊只能理解為“人”對于“神明”的合理期待。總的來說,茶山對于卦象系統溝通天人的功能雖然偶有加以神秘化的傾向,但此種神秘化始終是被嚴格限制的。更進一步,在茶山易學中,不管卦象系統是“人立之名”還是“與神明約契”,其連接天人的功用都被限制于“敬事神明”的上古時代。對于秦漢以后,茶山則反復強調“宜廢卜筮”。(27)茶山云:“古人事天地神明,以事上帝,故卜筮以聽命。今人平居既不事神,若唯臨事卜筮,則慢天瀆神甚矣。……今人守正者,宜廢卜筮。”(《易學緒言》卷四《卜筮通義》,第280頁)由此可知,茶山對于筮法所涉及的“天人關系”,持有某種歷史演變觀念。
三、由“筮法”而推“經旨”
理解茶山易學的筮法邏輯之后,可以進而考察茶山如何由筮法而推經旨,即如何根據筮法邏輯而確定《周易》的解釋原理。首先可以通過兩個例子來觀其大略。其一,茶山最為重視并據以將其著作命名為《周易四箋》的“四法”,其實全部根源于筮法邏輯。如上所述,在卦象系統的設計過程中,“畫卦”包含了由十二辟卦到五十衍卦的“升降往來”,這就是“推移”的由來;“畫卦”之后的“命名”使得所畫之卦成為一套象征系統,這就是“物象”的由來。到了運用卦象系統進行占斷時,又要求“變”中觀象,此“變”就包括“推移”和“爻變”。所謂“互體”,則是對“物象”的一種補充,以增加取象方式的豐富性。由此可見,茶山易學中的諸多象數體例并不是雜然并陳的,它們互相聯系為一個整體,而其共同的根源就是筮法。其二,關于經名之“易”字,自《周易正義》承易緯《乾鑿度》之說,提出“易一名而含三義”即“簡易、變易、不易”(28)于天寶點校:《宋本周易注疏》卷首,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8頁。以來,其說頗為流行。但茶山則云:“若所謂簡易、不易者,緯家之謬說,不足述也。”(29)《易學緒言》卷一《漢魏遺義論》,第82頁。其解“易”字,主要取“變”之義:“六十四卦,無不受變于他卦,此之謂‘易’”。(30)《周易四箋》卷一《括例表上》,第40頁。如上文所述,六十四卦的相變相通關系乃是筮法的本質特征,茶山正是據此解釋經名。
然而,更為重要的是,筮法并不僅僅在茶山個人易學中起著奠基的作用,而且也可以一般性地為《周易》解釋提供重要視角。筆者擬從如下角度說明這一點:對于易學史上不少爭論不休、各執一詞的重大難題,茶山所澄清的筮法邏輯往往可以起到破局之效。以下圍繞象辭關系這一易學史上的關鍵問題進行考察。
《周易》文本由卦爻象和卦爻辭兩個部分組成,這兩個部分之間的關系,即所謂“象辭關系”乃是歷代易學家探索不息的一個重要問題。傳統易學一般都主張“象辭相應”,但關于“象”與“辭”之間究竟如何相應,其聯系緊密到何種程度,不同學派之間仍有極大的區別。(31)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第11頁。關于此,可以看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所云:
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征。義茍在健,何必馬乎?類茍在順,何必牛乎?爻茍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茍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于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32)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609頁。
這是對漢代象數易學的著名批判。在王弼看來,卦爻辭中的“牛”“馬”等物象,是為了表達作者心中的“順”“健”之義而設置的比喻之辭,與卦爻畫之間并無必然關系。由此可知,易學史中義理派與象數派所講的“象辭相應之理”有著相當明顯的寬嚴之別。如王弼所說,漢代象數易學傾向于“案文責卦”,對卦爻辭中任何字詞都要求找到卦爻象根據,如果卦爻辭有“馬”而卦爻畫無“乾”,則通過卦爻畫的各種組合與變換來求得根據,所謂“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與之相比,王弼以來的義理派則更關注卦爻辭所表達的“卦義”與“爻義”的卦爻畫根據,至于卦爻辭中包含的種種具體名物,則往往被視為由卦義、爻義引申出來的比喻之辭,并不需要直接的卦爻畫根據。(33)劉大鈞:《周易概論》,成都:巴蜀書社,2016年,第109-110頁。這種對于象辭關系的不同看法,是易學史上義理派與象數派產生分歧的關鍵之一。在這一問題上,茶山的立場相當鮮明:
物象者,何也?《說卦傳》所云乾馬、坤牛、坎豕、離雉之類是也。文王、周公之撰次《易》詞,其一字一文,皆取物象。舍《說卦》而求解《易》,猶舍六律而求制樂。(34)《周易四箋》卷一《括例表上》,第34頁。
可見,茶山主張的是最為嚴格的“象辭相應”論。從《周易四箋》對經傳的實際注釋來看,茶山的上述觀點并非虛說,而是確實嚴格貫徹于其易學著作中。根據其解釋,不僅卦爻辭中的“一字一文,皆取物象”,而且《易傳》十翼中的內容,也基本上都是有卦爻象根據的。那么,茶山為何要采用如此嚴格的“象辭相應”論?關于這一點,聯系上節所分析的茶山筮法邏輯就可以自然領會。如茶山所說,筮法的根本目的在于“請天之命”,為此首先必須有一套卦象系統,其中卦畫與物象的聯結雖為“圣人所立之名”,卻是“天命”傳達于“人”的基礎保障。可見,《說卦》所列的“乾馬、坤牛、坎豕、離雉”等“物象”,乃是筮法得以進行的根本條件,并非可有可無的“比喻之辭”。在具體的占筮過程中,通過揲蓍之法而得到某個卦畫之后,占筮者應當對此卦畫所蘊含的“象”反復進行觀察揣摩,祈盼能從中解讀出“天命”來。“請天之命”這一根本目標,決定了上述這種占筮過程必須盡可能地排除“人意”因素,將卦象的意涵客觀地呈現出來,由此才能明了“天命”所指。作為筮法之最終產物的占辭,從原則上必須保證其“一字一文,皆取物象”。《周易》作為一部卜筮書,當然必須遵循筮法的這種內在要求。因此,最嚴格的“象辭相應”論才是卦爻辭解釋最為自然而正當的原則。
理解茶山的思路之后,可以將之與易學史上的一般情況稍加比較。在傳統易學中,象數派指責義理派的解釋過于空疏,使得卦爻辭中的諸多具體內容都淪為隨意的比喻之辭;反過來,義理派則指責象數派所提出的種種卦爻變化模式太過迂曲,且對于闡明“圣人”之“義”并無作用。(35)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二卷,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第1-4頁。推敲起來,此兩派之所以互不相下,是因為《周易》文本確實包含某種“二元性”。《周易》由卦爻畫和卦爻辭兩個部分組成,此二者無論作何種組合都存在問題。具體來說,“象”與“辭”組合的緊密度與解釋細節的簡潔度成反比關系。“象”與“辭”組合得越緊密,解釋細節就越繁瑣迂曲;反之,解釋細節越簡潔明了,“象”與“辭”之間的組合就越松散。也就是說,想要為卦爻辭提供充分的象數根據,就難免迂曲;想要如王弼那樣“掃象”,就難免空疏輕浮之譏。象數派和義理派無非是在此種內在張力中各執一端,因此誰也無法說服誰。進一步言之,傳統易學一般將《周易》文本視為一個圓滿自足的論域,試圖在《周易》文本的范圍內找出此文本的根本原理,如此一來,上述由于文本二元性而來的兩難困局也就很難避免。與之不同,在茶山易學中筮法才是易學思考的起點,《周易》作為一部卜筮書,其解釋必須遵從筮法的內在要求。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才能堅決主張“一字一文,皆取物象”這種最嚴格的“象辭相應”論,并給予義理派致命一擊。試想一下,如果真如王弼所說,“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征”,可以為了表達“義”而自由選取比喻之辭,那么《周易》就成為一部純粹發揮“圣人之義”的書籍,而筮法原有的“請天之命”的內涵則完全喪失了。可見,在由筮法而推經旨的視域中,義理派的錯誤并不只是解釋方式空疏、象辭關系松散的問題,而是從根本上誤解了《周易》文本的性質。反之,象數派的解釋方式或許容易流于繁瑣迂曲,但那只是較次要的弱點,其對“象辭相應”的嚴格主張在大方向上仍是正確的。由象辭關系論的例子可以看到,茶山由筮法而推經旨的思路對于易學而言確實頗具獨特價值。
四、余論
究其原始,茶山由筮法而推經旨的嘗試無疑源自朱子“《易》本卜筮之書”命題。茶山澄清筮法邏輯并著力闡明筮法與《周易》文本的內在關聯,將朱子命題所蘊含的理論能量進一步釋放出來,可說是朱子易學在異域的一大發展。不過,朱子此命題也留下許多難題,除上述卦爻辭象數根據等問題之外,還有一項對后世影響極大:既然說“《易》本卜筮之書”,那么《周易》與其他雜多的占卜書如何區分開來,從而保證其“經”之地位?由這一難題稍一轉手,就可能導向現代易學中那種對《周易》經學觀念的全盤拋棄。對此作出妥當的回應,確立《周易》超越一般筮法之上的“經典性”,也是茶山《周易》新解的重要任務之一。茶山為此做了不少努力,如辨析《周易》筮法相對于“夏商舊法”的優越性、將卦爻辭詮釋為“為筮人立例”而非實際占筮記錄等。這些工作的易學內涵也極為豐富,此處限于篇幅無法展開,筆者擬另文闡明。
在古代經典中,《周易》被尊為“群經之首”,地位至高,影響最廣。然而,現代學術興起之后,《周易》的“經”之地位所受沖擊也最嚴重,卦爻辭被視為古代占筮記錄的“累積”或“編纂”,其中雖寄寓了原始哲學思想,但其主體內容仍不過是古代巫術思維的遺存。(36)李鏡池:《周易探源》,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154-159頁。以筆者所見,茶山將《周易》置于上古筮法傳統中,同時著力闡明《周易》在此傳統中的“經典”地位,這種易學觀可以最有效地回應現代批判,且與現代學術的求真精神相得益彰,因而有助于綜攝傳統易學與現代學術的有益成分,是今日《周易》研究不可或缺的寶貴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