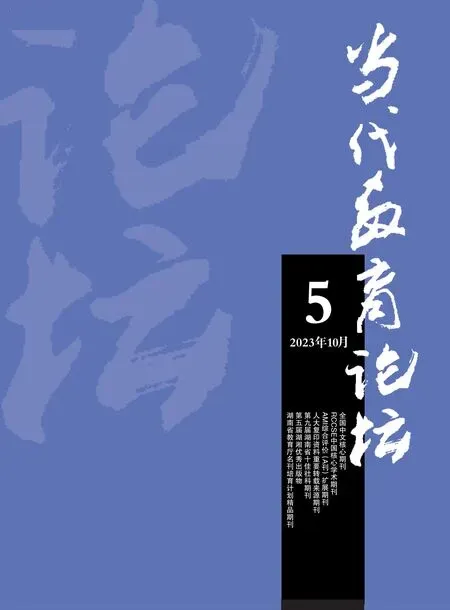孔子教學批評藝術及當代觀照*
謝 計 李如密
從字面意義解,“批評”可理解為對事物加以客觀分析、比較,又可理解為專對錯誤和缺點的指摘。在教育教學語境中,批評是指教育者基于為學生成長負責的目的,針對學生所表現出的錯誤或缺點,借以一定的方法手段,施以恰當的刺激,從而幫助學生知錯改錯。批評作為一種常規教學手段,同表揚相輔相成,協同保持著教育張力,促進著學生的健康發展。然而,相比于表揚、賞識在教學過程中至少能獲得師生和氣的報償,從性質上說,教學批評畢竟還是一種帶有消極情緒色彩的教學手段,在教學實踐中常常遭受偏見。譬如教師施以教學批評易被視作其教學能力不足、教學方式不理智、對學生不尊重的表現。緣此,何以適時、適度、巧妙地施以教學批評,考驗著教師的教育智慧,呼喚著教師的教學批評藝術。
作為“萬世師表”的孔子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教育家,其對門下弟子的教學方法手段多樣且精湛。教學批評是孔門教學中常用的教學手段之一,《論語》中所載孔子對門下弟子施以教學批評就達28 次[1]。從《論語》《孔子家語》等所載的孔門“問對”“侍側”“游歷”等教學實踐中可以窺見,孔子教學批評藝術意指出于仁愛的目的,針對門下弟子表現出的過錯和缺點,孔子通過適合的教學情景活動,遵循不同對象的個性與不同過錯的程度,巧妙運用批評指導門下弟子知錯改錯,進而獲得顯著的教育成效,達到了藝術化的教學境界。概言之,孔子教學批評藝術主體表現為以關愛學生成長發展為旨歸,以和諧親密的師生關系為基調,以改過復禮的思想觀念為底蘊,以藝術化的言行教導為手段,針對學生過錯和缺點施以關懷性、教育性與層次性的指導。從教學藝術視角出發,回顧孔門經典教學片段,品味孔子教學批評藝術,以期在理論層面發掘原汁原味的孔子教育教學智慧,使對孔子教學批評思想的認識不再停留于簡單的抽象概括;在實踐層面幫助教師在領略孔子教學批評藝術魅力的同時,探索教學批評藝術的現代轉化。
一、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的底色
以火光為喻,藝術火光的真正意義在于其蘊藏著的熱,即藝術創作者之個性、理念、情感等獨屬個人意義世界的屬性的寄予,構筑成其藝術表達的底色。基于教學藝術視角理解教學批評,教育者的先賦個性、守持理念與原則等構筑成其教學批評行為的底色,影響其教學批評藝術的呈現。因此,澄清孔子的教學批評藝術,當從孔子的個人性格及其守持的教學批評思想理念與原則等起始。
(一)“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個性底色
相比于表揚、賞識在教學過程中至少能獲得師生和氣的報償,批評往往更容易招致負面、消極的影響,由此引發的常見現象是教師避用批評甚至不敢批評。更糟糕的局面是,當批評異化為個性不穩定的教師情緒宣泄的手段時,則極大地損害了批評在教學中的正當價值。這帶來的實踐反思是教師需要具備強烈的、適配的個性魅力來駕馭批評。換言之,教學批評藝術需要適配的教師個性底色。孔子具有高超的教學批評藝術,也是得益于其極具魅力的個性色彩。有關孔子個性最直接的描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論語·述而》),意即孔子溫和而嚴厲,有威儀而不兇猛,莊嚴而安詳[2]111。在孔門弟子心中,孔子首先是溫和的、安詳的師者形象。孔子溫和、安詳的性格不僅體現在與眾弟子如親如友的日常生活交往中,更體現為教育教學過程中對學生真誠的、毫無保留的仁愛。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論語·述而》)“我沒有一點不向你們公開”的表白不禁拉近了孔子與弟子間的心靈距離,使得學生感受到滿滿的溫情。在教師地位與“天”“地”“君”“親”并舉,極致推崇師道尊嚴的文化語境中,孔子在教育教學中所表現的溫和與安詳的性格無疑打破了師生間的隔閡,為其教學批評的出場構建了融洽的關系氛圍。同時,“厲”“威”“恭”是孔子個性的另一面,這表明在教育教學中孔子的溫和、安詳并不意味著對學生無限度地退讓、縱容,這為孔子施以教學批評保留了可能性,作出了個性上的預設。在此基礎上,孔子有威儀但并不兇猛,表明他不是一個脾性暴躁、蠻橫粗暴的老師,這消除了批評作為孔子泄憤工具出場的嫌疑。綜合看來,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個性與批評相適配,構成了其教學批評藝術的個性“底色”。
(二)“過,則勿憚改”的理念底色
教育教學中的批評旨在幫助學生認識過錯并改正過錯,它指向學生的錯誤和缺點,不是對學生生理、人格等方面的歧視和侮辱,這強調教師需要正確認識批評,才能有效實施批評。進一步而言,教師教學批評藝術是在正確的教學理念指導下生發的。孔子教學批評藝術背后的重要指導理念無疑是其深刻的改過思想。其一,如何看待犯錯或有缺點的學生?子曰:“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論語·里仁》)在孔子看來,因為人是各式各樣的,所以人犯的錯誤或缺點也就是各式各樣的。什么樣的錯誤就是由什么樣的人犯的[2]51。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面對犯錯或存在缺點的各類學生,難道要對此置之不理,放棄教育?這顯然與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相悖,對犯了過錯或存在缺點的學生同樣施以教育是其“有教無類”教育理念的應有之義,批評則是孔子幫助稟賦各異的學生知錯改錯且“不貳過”的重要手段。其二,如何看待學生犯的過錯和缺點本身?在孔子看來,一個人有了過錯或存在缺點并不打緊,“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孔子家語·執轡》)。如果有了過錯卻不加改正,那么這個過錯便就真正成了錯誤,即“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靈公》),主張“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因此,孔子非常重視改過在個人修養中的作用,認為個體對待過錯的不同態度,可以反映出其修養水平的高低[3]。在孔門教育教學中,一方面,孔子始終要求學生自身注重自省自察、見賢思齊,鼓勵學生正視過錯,注重提升學生“過則內自訟”和“聞過則喜”的修養;另一方面,作為老師,孔子也經常善用教學批評幫助學生知過改過,使其“不貳過”。可以說,“過,則勿憚改”的改過思想構成了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的理念底色。
(三)“子之四憂”的規則底色
批評是對過錯的指摘,則應當先確認過錯,尤其在敏感、復雜的教育教學情境中,能否合理地確認學生的過錯,是能否恰當地實施批評的根本[4]。而確認過錯則必然離不開一定的參考標準。那么,標準從何而來?這便是批評者內心所信奉的某種規則,任何批評,無不是批評者對其內心信奉的某種規則的捍衛與宣揚[5]。如若教育者心中沒有其堅持的規則,那么批評在教育教學中則缺乏相應的出場閾值,往往會被濫用無度。在孔門教育教學中,眾弟子的過錯觸及了哪些方面,孔子才會施以批評呢?整體看來,孔子授業基本上屬于“君子之教”,圍繞“孝”“悌”“忠”“信”“仁”之類的議題,是反復從不同案例中,揭示某種價值觀念的真諦,以“禮”“樂”衡量弟子的精神狀態、行為表現與治學態度,為其指明行動的方向[6]。其中孔子突出強調了“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孔子直言不修養品德、不講習學問、不追求仁義、不改正缺點都是他非常憂慮的事情,如若孔門弟子在這些方面有所逾矩或不求精進的話,孔子都會施以批評。比如,在德行修養方面,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又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論語·子路》),表明孔子主張要注重內在修養,戒驕戒傲。而當某一次子路盛服見孔子,且擺出神色傲慢的樣子,顯然觸犯了孔子所信奉的規則,孔子對其施以了批評,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孔子家語·三恕》)在學問講習方面,子曰:“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君子不可以不學……”(《孔子家語·致思》)而當看到宰予晝寢時,孔子直接批評道:“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論語·公冶長》)在聞義則徙方面,當樊遲請學稼與為圃,孔子表示不滿,待樊遲走后,孔子批評道:“小人哉,樊須也!”(《論語·子路》)因為在孔子看來,“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樊遲請教農學技能,追求物質利益的提升不符合“君子”的追求,沒有做到徙義,不符合“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的原則。在知錯改過方面,一次孔子批評了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的舉動,子路對此不接受并與孔子辯駁,孔子則更為直接地批評道:“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由此觀之,在教育教學中,孔子對弟子施以批評,主要都是針對學習態度、品德修養等重大的原則性問題,其批評教學藝術具有核心的規則底色。
二、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的手法
藝術創作者之個性、理念、情感等獨屬個人意義世界的屬性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手法來向外界表達。同樣的,孔子教學批評藝術不僅具有其獨特的個性底色、理念底色以及規則底色,其教學批評的手法也表現出高超的藝術性。
(一)言語式批評
所謂言語式批評,即孔子在與弟子的對話交談中,通過言語表達的形式指出弟子的不當和過錯,用詞常伴有明顯的、強烈的情緒色彩,比如否定、不滿、憤怒等,區別于孔門一般的“子曰”“問對”等師生間的言語對話。言語式批評是孔子常用的批評手法,體現了孔子精湛的教學語言藝術,主要體現為以下幾種類型。
其一,直言不諱。這類表現為孔子在話語中直接表達自己的不認同,指出弟子的過錯。如《論語·先進》載,當知道子路叫子羔去做費縣縣長,孔子就直接表達了不認同:“賊夫人之子。”認為子路這樣做是害了人家。子路不服氣,便與孔子辯駁,而孔子又直接地批評道:“是故惡夫佞者。”以此警示子路反思自己的過錯。當得知冉求執意為富于周公的季氏增賦斂財時,孔子非常氣憤地批評道:“非吾徒也。”斥責冉有過分剝削人民的主張。又如《孔子家語·致思》載,魯國法律規定,如果有人能從其他諸侯國贖回做奴隸的魯國人,就可以從魯國的府庫里領取一定的錢財。然而子貢贖回了人卻拒絕去領取錢財。孔子知道后直接批評子貢:“賜失之矣。”指出子貢的行為破壞了禮法規矩,不能有效地引領平民大眾。
其二,嚴肅反詰。這類表現為孔子通過嚴肅的反問、責問來指出弟子的過錯。典型的案例如《論語·子罕》載,一次孔子援引《詩經》中一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夸贊了子路,子路聽到老師的夸贊后不禁沾沾自喜,嘴上一直念叨著這兩句詩,不料孔子轉而嚴肅地反問道:“是道也,何足以臧?”對子路予以批評警示。如《論語·八佾》載,魯國大夫季氏僭禮去祭祀泰山,孔子先是質問在季氏手下為臣的冉有為何不加以制止,在冉有回答“不能”后,孔子嚴肅地反問道:“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批評冉有未能擔起維護禮的責任的過失。當宰予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孔子則以“何為其然也”(《論語·雍也》)的反問指出宰予對“仁”的錯誤理解。當宰予認為父母去世,為此守孝三年,為期太久了,應當縮減期限,孔子以“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論語·陽貨》)的反詰表達了對宰予錯誤想法的反對。沒想到宰予對這一反問的回答是“安”,令孔子非常不滿。待宰予退去,孔子直言:“予之不仁也!”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先前的反問意在批評宰予仁愛不足的錯誤想法。
其三,對比暗示。這類表現為孔子通過比較的話語體系來表達自己的不認同,暗示弟子去認識自己的過錯。或以自己作比,婉轉地批評弟子的過錯。如《論語·子路》載樊遲請學稼和為圃,孔子就只回答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看似表達自己在農學技能方面不如老農老圃,實則在委婉地批評樊遲志向不足、舍本逐末的傾向[7]。在《論語·八佾》中,當“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時,孔子以自己可惜“禮”與子貢可惜“羊”作比,委婉地批評子貢“去羊”的不當做法。在《論語·憲問》中,孔子以“夫我則不暇”作比,委婉地批評子貢譏評別人的不當行為。或以物作隱喻,批評弟子的不當。如《論語·公冶長》載,當看到宰予白天睡大覺,不用功讀書,孔子則以“朽木不可雕”“糞土之墻不可杇”的比喻,表達對宰予這一行為的不滿。
其四,引例說理。這類表現為孔子通過援引事例、陳述應然的道理的方式來分析弟子的過錯。如《孔子家語·三恕》中,子貢將“孝”單純地理解為“子從父命”,將“忠”單純地理解為“臣從君命”,孔子聽完先直言“汝不識也”以表否定,爾后依次列舉“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為例深刻分析了“孝”“忠”的應有之義,幫助子貢糾正先有的不當理解。又如《孔子家語·困誓》中,子貢因生厭學情緒向孔子提出休學去事君、事父母、事兄弟以及耕田的申請,這顯然與孔子“學而不厭”(《論語·述而》)、“學而不已”(《韓詩外傳》卷八)的主張相悖,孔子對此依次援引《詩經》上的道理,一一駁斥子貢的休學申請,申明了“焉可以息哉”的立場,勸誡子貢打消厭學休學的錯誤想法。
(二)行動式批評
所謂行動式批評,即孔子借以某些行動舉止來表達自己不滿意、不合作的態度,以此使有過錯的弟子自己知錯改錯。此類手法的批評更為高級,更耐人尋味,主要體現為以下幾種類型。
其一,不咎。這一行動式批評見于《論語·八佾》中,魯哀公問宰予作社主要用什么木。宰予回答夏代用松、商代用柏、周代用栗,并強調“使民戰栗”的意涵,這顯然不符合孔子德政仁治的一貫主張,孔子聽聞后自然不滿。但宰予畢竟是自己的弟子,也不能對其過錯置若罔聞。因此孔子對此表示過去的事情就隨它過去吧,不再追究了。其實在此教育情境中,孔子“既往不咎”的行為代表著一種寬容,本身就顯示出一種批評的教育力量和教育藝術,相信宰予一定能領會孔子“不咎”的批評之意吧[8]。
其二,勿內。這一行動式批評主要表現為孔子拒絕與犯錯的弟子會面,屬不教之教。據《孔子家語·六本》載,曾參在地里耕瓜,誤斬其根,招致父親曾皙的一頓棒打,倒地不省人事。曾參醒來后不但不記恨,反而第一時間安慰父親的情緒,并回房援琴而歌,以此向父親表示自己并無大礙。“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以此嚴肅地表達了對曾參“愚孝”行為的批評之意。在曾參托人來求教時,孔子才轉達了其中的道理,“勿內”的批評使曾參認識到“罪大矣”。又如《論語·陽貨》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雖然不能明確孔子拒絕見孺悲的真正原因,但是可以推測的是孔子拒見孺悲的行為有批評之意,不免讓孺悲獨自反省。
其三,哂笑。這一行動式批評見于《論語·先進》中,子路、曾皙、冉有與公西華侍坐在孔子邊,孔子拋出“言志”的主題后,性格伉直的子路率先答道:“千乘之國……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孔子聽完后只是“哂之”,未作任何言語評判。而當事后曾皙問孔子對子路微笑的緣由時,孔子直言治理國家應該講究禮讓,但是子路剛說的話卻一點都不謙虛,所以笑笑他。由此可見,此前孔子的“哂之”,實則帶有批評的意味。
其四,叩擊。這一行動式批評見于《論語·憲問》中,原壤兩腿像八字一樣張開坐在地上,等著孔子[2]226。孔子見到后,先是嚴厲地斥責了原壤,并用拐杖敲了敲他的小腿。因為原壤“夷俟”是極其無禮的舉動,孔子“以杖叩其脛”的行為表達了對原壤強烈的批評、警示之意。
三、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的特征
正如藝術作品所呈現出的某些能帶給個人強烈藝術感受的特征一樣,孔子教學批評藝術所表現出動之以情的關懷性、曉之以理的教育性以及因勢利導的層次性等特征,可謂耐人尋味,顯示出燦爛的教學智慧。
(一)動之以情的關懷性
關懷是孔子對門下弟子施以教學批評的情感起點,是其“仁”思想在教育教學中的具體顯現。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在教育教學中,孔子批評弟子的過程包含著濃濃的師愛,表現出強烈的關懷性。
從批評的目的考察,孔子批評弟子則完全出于其對眾弟子生命成長發展的關懷。比如《孔子家語·致思》中,子路在蒲地做地方長官時,率領當地百姓修建溝渠來防備水患,看到百姓們勞動辛苦,善良的子路就發給每人一籃子食物和一壺水。孔子聽聞,則急忙地叫子貢去阻止子路這么做,子路感到生氣與委屈,跑來找孔子理論,又招致孔子的反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其實子路擅自與民簞食壺漿,雖彰顯了自己的品德高尚,但暴露了國君對百姓的不恩惠。孔子批評、阻止子路,正是出于害怕子路因此被治罪的擔憂呀。又如《孔子家語·辯樂解》中,子路喜歡彈奏粗俗、有亡國之意的琴樂,孔子聽到后直言:“甚矣!由之不才也。”因為子路不注重先王之制,卻喜歡彈奏亡國之音,很容易招來殺身之禍。孔子批評他,也是出于對子路生命安危的擔憂呀。可見,正因為出于“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論語·憲問》)的毫無保留的關懷,所以孔子會時刻關注諸位弟子的每一步發展,不會任其犯錯而不管;正因為出于“吾無隱乎爾”(《論語·述而》)的毫無遮掩的關懷,所以在弟子犯錯時孔子會敢于及時地施以批評,不做永遠“好脾氣”的老師;正因為對于門下弟子愛之深,所以當看到他們有了過錯,才會責之切。
從批評的后續效應考察,眾弟子并沒有因為受到孔子的批評而心生怨恨,師生間的情感非但沒有因此受損,反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比如,子路可能是受孔子批評最多的弟子,但他對待孔子極其尊重并且傾力維護。孔子也曾直言:“自吾得由,惡言不聞于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比如,善問樂評的子貢也在與孔子交流中挨了不少批評,但子貢始終非常孝敬愛戴老師,甚至在孔子去世后,“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于墓六年”(《孔子家語·終記解》)。孔子在批評中始終抱以關懷,眾弟子也從內心深處接受了孔子這份濃烈的關懷,師生間完整的關懷關系得以建立。
(二)曉之以理的教育性
孔子施以的教學批評始終是針對門下弟子的道德修養、學習態度、行為實踐等關乎其個體成長發展類的重大問題,是出于對弟子成長發展的教育責任。因此,教育性始終是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的重要特征之一。
從孔子批評的教育機制來看,主要是激發并利用了人道德情感中的羞恥感發揮教育作用[9]。孔門教育強調以“君子”為最高的追求目標,而鄙棄相對的“小人”之行,幫助弟子們明晰應以什么為志、什么為恥。如在言行方面,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正是基于日常諸多方面的恥感教育,當弟子有了過錯時,孔子恰當地施以批評,激發弟子內心中的羞恥感,使其知恥而后勇,遷善改過。比如,子路彈奏粗鄙的亡國之音,孔子嚴厲地批評了這一行為。子路聽到孔子的批評后,“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家語·辯樂解》),這恰是羞恥感作用的顯現。
從孔子批評的教育過程來看,孔子從來都不是一味地追究已成定局的錯誤結果而喋喋不休,而是注重闡明其中的道理,教導弟子真正認識到錯誤所在,集中體現了批評之教育性的核心要義。比如,孔子批評子路不該穿著華麗的衣服且擺出神色傲慢的樣子,子路聽了后,立馬跑出去換了身衣服,且神情自然地再來拜見孔子。孔子也并沒有再追究他先前的行為,而是借此向子路闡述君子之行的道理(《孔子家語·三恕》)。
從孔子批評的教育效果來看,一方面,挨過孔子批評的諸位弟子都切實地認識到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與過錯,并在實際的行動中不斷改正,后續所取得的進步也證明了孔子批評的優良教育效果。比如,經常挨批評的子路、冉有,后來成為孔門政事科的翹楚,宰我與子貢成了言語科的高才生。又如,因“愚孝”的行為被孔子嚴厲批評過的曾參,則成長為孔門私學中孝行突出、修養精進的弟子;另一方面,在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的熏陶下,其門下弟子也承接并發展了孔子的“改過”思想,同樣強調對過錯的正視與改正。如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可見,從孔子教學批評的機制、過程與結果來考察,無不顯現著教育性的核心特征。
(三)因勢利導的層次性
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的層次性主要在于其對待有了過錯的弟子施以批評的方式不是固定模式、一成不變的,而是會根據批評的對象、問題以及情境等不同施以不同的批評。孔子倡導克己復禮,將禮的錯誤視為原則性錯誤,而將學生由于性格上的特點(如“性鄙”)而帶來的錯誤視為非原則性錯誤[10],隨之施以的教學批評也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教學批評藝術具有顯著的層次性。
其一,根據弟子的性格、稟賦不同,施以不同方式的批評。子路是孔門私學中個性非常鮮明的弟子,身上缺點也不少,“行行如也”“由也果”“由也喭”是對其個性最集中的描述。用現在的話說,子路是個性格伉直、勇猛果敢、直率魯莽、大大咧咧的學生。如此性格的子路對于批評自然有著相當強的心理承受力,因此孔子對于子路常采用直言不諱、嚴肅反詰甚至斥責等批評方式予以教育。而對于活潑、圓活且能言善辯(“賜也達”)的子貢以及同樣擅長言辭的宰予這兩位弟子,孔子在施以批評時常常采用引例說理、對比暗示、反問等方式,通過深入的對話、言辭引導、層層分析來幫助他們認識過錯。
其二,根據弟子的過錯不同,施以不同程度的批評。對于有了過錯的弟子,孔子向來都是嚴格的,但對于不同層次大小的過錯,孔子施以的批評程度也會相應不同。對于“言志”教育中子路的不謙虛行為,孔子“哂之”;對于門下眾弟子厚葬顏淵一事,孔子雖不認同眾弟子的做法,但也只自責地喟嘆:“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論語·先進》)隱晦地表達批評之意。而對于冉有執意幫助季氏增賦斂財、宰予晝寢、曾參“愚孝”等此類重大的原則性錯誤,孔子批評程度極為嚴厲、強烈,宣布冉有“非吾徒也”,斥責宰予同“朽木”“糞土之墻”一樣,氣憤地決定“參來,勿內”等,可謂程度分明。由此可見,孔子因學生個性稟賦不同而批評方式不同,因過錯大小不同而批評程度不同的教學批評藝術顯示出鮮明的層次性。
四、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的當代觀照
千古風云,時過境遷,客觀的孔子已經逝去,主觀的孔子卻在歷代研究者的個體解讀中挨次出現。盡管孔子的教學批評實踐帶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其教學批評所顯現出的藝術性與智慧性是恒常的,給予后續教育者們常思常新的啟迪。
(一)孔子教學批評藝術觀照下當代教學批評的實踐困境
品味經典的孔門教學片段發現,孔子獨特的個性魅力、守持的改過復禮思想觀念構筑了其教學批評藝術的意蘊底色,多樣精湛的言語式批評和行動式批評突顯了其教學批評的能力機智,指向知錯改錯的教學活動流露出濃烈的仁愛之情,實現了教學批評的藝術化境界。以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為鏡,當前教學實踐中,教師施以教學批評主要存在教學批評觀念文化異化、教學批評能力機智缺失與教學批評情感基礎薄弱等現實困境。
其一,教學批評觀念文化的異化。所謂教學批評觀念文化,即作為批評者的教師對教學批評及其價值所具有的科學認識,從而外顯為正當的教學批評行為。從孔門教學實踐來看,懷以仁愛之心,具有“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個性的孔子始終將批評視作正當的教學手段,并敢于施以教學批評,其守持的改過復禮的思想原則牽引其善用批評,不至濫用無度。在此比照下,當前教師教學批評觀念文化的異化主要表現為教師在主觀認識上避用教學批評與濫用教學批評兩種極端傾向。一方面,在倡導尊重學生主體性,鼓勵實施賞識教育的背景下,或是出于對學生身心健康的顧慮,或是迫于社會輿論對教師教學監控的壓力,教師就直接忽視或否定教學批評之于保持教育張力的正當價值,在本應運用教學批評的時候卻選擇回避甚至放棄施以教學批評;另一方面,教師往往將教學批評視作宣泄個人情緒、滿足一己私欲的工具。在日常教育教學中,他們披著教學批評的外衣,遷怒于學生,借以宣泄私人的消極情緒。或是綁架教學批評為個人實施語言暴力甚至是行為懲罰的強暴手段,極大地損害了批評在現今學校教育教學中的正當價值。
其二,教學批評能力機智的缺失。教學批評的能力機智是教師對教學批評的對象、時機與情境等準確把握后做出的機敏反應,表現出獨特的教學技巧和創造性。在孔門教學活動中,面對犯錯的弟子,孔子深諳弟子的個性差異和過錯的程度差異,并據此善用各類言語式與行動式的教學批評手段予以精確的指導,顯示出高超的教學批評能力機智。在此比照下,當前不少教師缺乏教學批評的能力機智,常常誤用了教學批評,主要表現為部分教師在不明晰批評事件的緣由,或是不區分批評對象的個性差異,或是不注重教學批評的時機與情境,或是不把握教學批評的程度等情況下,盲目地施以教學批評,導致未能實現預期的教育效果。
其三,教學批評情感基礎的薄弱。教學批評的效果獲得與藝術化的實現有賴于批評者與批評對象之間深厚的情感關系基礎。從關懷倫理學的角度來理解,作為施教者的教師出于關愛學生成長發展的目的,針對學生的過錯和缺點施以教學批評,學生理解并接受教師這一關懷行動,雙方建立并深化了完整、親密的情感關系,保障了教學批評的實施。孔門師生關系十分和諧融洽,既體現為孔子對眾弟子的深入關切和毫無保留的仁愛,也體現為眾弟子對孔子發自內心、見諸行動的尊崇與愛戴。這濃厚的師門情感離不開孔子與弟子間頻繁的“問對”“侍側”“從游”之類的活動,也為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情感基調。在此比照下,由于教育文化的變遷,現今的學校教育已然極大地淡化了傳統師生共讀、共處的意味,同時以分數和升學率來測量“好教育”的趨向,使得傳統相知相交的師生關系逐漸走向了功利化、工具化的合作關系。在此關系背景下,教師實施教學批評的風險性加劇,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教學批評效果的實現。
(二)孔子教學批評藝術觀照下當代教學批評的實施路徑
教師施以恰當的教學批評對犯錯的學生予以指導是教育教學中常見的文化現象,但何以保證這一教育文化現象不至于異變,則考驗著教師的教育智慧和教學藝術。以孔子教學批評藝術為觀照,探索教學批評的實施路徑,需要圍繞教師教學批評觀念文化異化、教學批評能力機智缺失以及教學批評情感基礎薄弱等現實困境著手。
首先,反求諸己,形塑教學批評的觀念文化。教育教學實踐中存在的教師避用教學批評、誤用教學批評甚至濫用教學批評等現象,首要問題在于教師未能在主觀層面形成對教學批評的正確認識,從而阻礙了教學批評預期效果的獲得。儒家有言“反求諸己”,強調行事未能取得成功,需要反省自身的不足,并予以修正。于此,教師需要反省自身對教學批評的主觀認識,形塑教學批評的觀念文化。一方面,教師需要摒除對教學批評的偏見,加強對教學批評內涵與價值的認識。教學批評是教師通過對學生的不當或錯誤言行予以否定性評價,幫助其知錯改錯,提高認識,進而使學生克服影響自身健康發展的消極因素,完全是一種正當且有效的教學手段。從人的發展歷程和教育實踐來看,教學批評對于人的發展過程中難以規避的犯錯改錯的導向、警示與矯正等價值功能,是表揚所不能替代的[11]。因此,教師需要主動隔絕外界不良輿論對教學批評的污名化偏見,激發自身教學勇氣,規避怕用、避用教學批評的傾向。同時,教師還需摒除批評與表揚相對立沖突的偏見,要認識到同為常規教學手段的表揚與批評向來不是割裂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協同保持著教育張力。另一方面,教師需要在觀念層面確立教學批評的行事原則,包括明確施以教學批評的實事求是原則、公平公正原則與賞罰協同原則等,以此規避誤用、濫用教學批評的傾向。
其次,敏以求之,提升教學批評的能力機智。紓解教師教學批評能力機智缺失的現實問題,無他,唯教師在教育教學實踐中積極主動地對此加以學習與探索。儒家有言“敏以求之”,傳達了一種積極的探索態度。它強調個體要積極學習,不斷地追求探索,如此才有益于個體的成長和提升。面對自身教學批評能力機智的不足,教師需要激發個體自覺,敏以求索。一方面,教師可以通過挖掘教育名家教學批評思想,譬如孔子的教學藝術思想,分析優秀典型的教學批評案例,參與教學批評相關主題研修活動,交互總結教學批評經驗等方式,積累有關教學批評藝術的知識,端正有關教學批評藝術的態度和掌握有關教學批評藝術的方法等;另一方面,教師需要在日常真實的教學實踐中保持對犯錯學生的“教育學意向”,不斷探索和掌握教學批評的機智,包括何以精確識別學生錯誤的機智、何以創設適切的批評情境的機智、何以澄清相關道理和提出改過建議的機智,以及何以有效觀測教學批評后續效應的機智等,錘煉出科學巧妙且行之有效的教學批評行動機制,以期更好地對犯錯的學生做出機敏的反應。
最后,以友輔仁,構建教學批評的情感基礎。親密融洽的師生關系是有效實施教學批評的情感基礎。儒家有言“以友輔仁”,強調君子之間良好關系的建立在于以互相幫助來培養仁德。這給予教學實踐的啟示在于,良好的師生關系使得學生更易于接受老師的批評教誨,有利于教學批評的實施,同時在教師幫助學生知錯改錯、培養仁德的教學批評行動中,也促進了良好師生情感關系的建立。于教師而言,為教學批評構建良好的基礎,教師首先要注重發揮“以身立教”的示范效應,獲得學生的情感認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無不強調正人先正己、身教勝于言傳的道理。因此,教師自身要自覺加強個人師德修養,在做人、治學、任職等實際行動表現上為學生樹立優良的示范,同時在學生面前要勇于開展自我批評,拉近與學生的距離,獲取學生內心的高認可度,保障教學批評的效力。另外,教師需要主動增進對班級學生個性稟賦的了解,留心考察他們的成長狀態,做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論語·為政》)。同時,教師需要積極創設班級交流互動的機緣平臺,在實際的交往環節中升溫彼此關系,為偶爾出場的教學批評打造仁愛的情感關系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