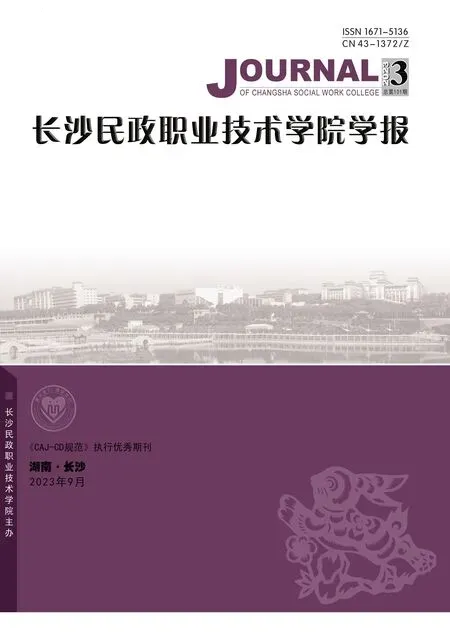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長沙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重點方向、制約因素與推進策略研究
張 蕾
(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4)
建國以來,我國公共管理經歷了“行政管理”“社會管理”“社會治理”三個歷史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社會治理”新概念,并且明確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目標。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體現了我黨執政理念的重大跨越,標志著中國社會由管理范式向治理范式邁進。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1]。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未來五年“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提高市域社會治理能力”;未來十五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近些年來,學界圍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產生了一大批理論研究成果,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實踐路徑研究方面也受到某些學者關注,但鮮有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發展對策的研究。本文從中國式現代化語境視角切入長沙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問題研究,具有戰略前瞻性、現實針對性和對策可行性,有助于拓展長沙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廣度和深度,優化長沙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環境,充分發揮長沙市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提高長沙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規范化、制度化、現代化水平,推動長沙市社會組織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發展。
1 中國式現代化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含義及其相互關系
“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出發,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將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偉大征程。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滿足規模巨大人口的美好生活需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美麗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2]。社會治理是在黨委領導下,由政府主導,吸納社會組織等多方面力量共同參與,對社會公共事務與公共問題進行合作共治,以此實現公眾需要的更好滿足及公共利益的最大化[3]。社會治理現代化體現為治理觀念、治理內容、治理制度、治理方法與技術、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多元主體綜合運用制度、程序、標準、方法和技術在重點方向和焦點領域協同共治,通過社會治理的社會化、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智能化、專業化,回應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和現實需求,有效解決人口規模巨大的社會問題與矛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發展問題、精神文明需求的供給問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生問題[4]。社會治理現代化內含于中國式現代化之中,是中國式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式現代化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指明方向、明確目標,提供理論支撐,提出原則要求。
2 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重點方向
在我國官方話語中,社會組織一詞經歷了從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到社會組織的嬗變,彰顯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組織的重要性。社會學領域中的社會組織是指人們為了實現某種共同目標,將其行為彼此協調與聯合起來所形成的社會群體[5]。組織成員運用知識、規則、技術和經驗開展組織活動,完成組織規定的目標和任務。社會組織具有民間性、非營利性、自愿性等特征。社會組織類型與社會分化程度緊密相關。社會分化程度越高,社會組織的類型也越復雜。如以機構編制為標準,可將社會組織分為國家機關、群眾團體、企業單位、事業單位、新社會組織等;以組織發揮的功能為標準,可分為政治類、經濟類、教育類、科技類、文化類、衛生類、環保類、社交類、社區服務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等;以登記管理對象為標準,作為政府主管部門的民政部門將社會組織劃分為社會團體、基金會、社會服務機構三種類型。社會組織與社會治理存在邏輯關聯和價值親和,社會組織不僅是政府主管部門的管理對象,更多時候還是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中的結構性力量,是社會治理體系完善以及社會治理結構優化的重要環節,而社會治理為社會組織提供了目標任務、場域載體、工作崗位和服務空間。目前我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邁向新征程和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社會治理轉型,即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治理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治理轉型、從數字治理向智慧治理轉型、從數量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面對新形勢、新機遇、新要求,需要明晰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重點方向,把握發展大勢,拓展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廣度和深度,以更好地順應社會治理轉型發展要求,服從和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大局。
2.1 服務低收入人群,增進民生福祉,助力共同富裕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推動更多低收入群體跨入中等收入行列是必經的關鍵環節。社會組織以低收入人群為服務對象,參與農村低收入人口動態監測和常態化幫扶,通過產業扶持、技術培訓以及就業介紹,促進有條件的低收入群體增加經營性和工資性收入。公益慈善型社會組織參與公益救助和慈善事業,動員、組織、籌集、分配公益慈善資源,實現資源和財富持續、健康流轉,發揮公益慈善組織和慈善事業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推動共同富裕。
2.2 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完善協商民主體系,促進自治共治和社會和諧發展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個環節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的全鏈條民主,貫通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層面各維度,涵蓋國家各項事業各項工作。基層民主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體現;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是協商民主體系的組成部分。社會組織是推進我國基層民主和協商民主的重要力量,因此,需要吸納社會組織參與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各個環節,尤其是參與決策環節,如在城鄉社區規劃與建設、議定重大項目、公共服務供給、公共政策制定等決策事務中進行協商互動;在基層自治中參與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管理,促進基層社區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面臨人口規模巨大背后所隱含的多樣化利益訴求、服務需求以及重大社會風險、復雜多樣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依靠單方面的力量無法解決諸多矛盾、問題與需求,需要政府、市場、社會等多種力量采取共治模式加以應對。在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焦點場域,需要作為重要社會力量的社會組織參與和服務:表達群眾利益訴求,發揮建言資政作用,不斷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一老一小”等重點對象提供暖心服務,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防范化解重大社會風險(如社會治安防控、安全生產、應急管理、衛生防疫、食品藥品安全、網絡安全等);解決社會問題(如兒童青少年游戲成癮問題、大齡青年和離異人士婚戀問題、勞動就業問題、養老問題、網絡亂象、鄉風文明建設問題等);化解矛盾糾紛(如婚姻家庭矛盾、鄰里矛盾、物業物權糾紛、醫患糾紛、勞動爭議、消費者權益糾紛等),協調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2.3 介入精神貧乏治理,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
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質貧困、精神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物質上的富足并不能完全滿足人們內心的需求。社會組織介入精神貧乏治理,在黨建引領下配合開展理想信念教育、主題宣傳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弘揚紅色革命文化,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色城鄉地域文化、傳統民俗文化,組織開展各類文娛體育活動和志愿服務活動,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追求高尚而充盈的精神境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2.4 參與環境治理,建設美麗中國,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社會組織特別是環境類社會組織參與廢棄物循環利用以及垃圾分類治理、環境綜合整治、生態保護和修復、環境調查與監督、環境公益訴訟與環境污染糾紛調解工作,促進綠色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美麗社區、美麗家園。
3 國內外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經驗及啟示
3.1 國外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經驗——以美國、歐盟、新加坡、日本為例
美國采取稅法監管+政策支持的方式對NGO實施管理。《美國稅法典》對免稅資格認定、稅收優惠、稅賦信息公開等方面加以規制,這種以稅法為主的制度設計保障了NGO 的透明度、公信力和規范運行。同時,美國政府還對NGO組織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如直接向NGO 組織撥款、政府購買服務、吸收NGO組織參與政府政策制定、委托研究、為NGO 組織提供咨詢項目、促進NGO 組織開展慈善募捐、公益活動等[6]。
歐盟基于“參與民主”原則將社會組織納入歐盟事務決策機制,強調讓各類社會組織介入歐盟政治決策過程中的各類參與、對話和咨詢活動。通過頒行《歐盟治理白皮書》《歐盟憲法條約》《里斯本條約》和《歐盟條約》等政治文本,為公民社會組織參與歐盟治理提供了制度性的渠道、機會和結構,促使公民社會組織與歐盟機構形成制度化的合作關系[7]。
新加坡的社會組織被稱為社會團體,有官方社團和民間社團之分。官方社團是由政府出面組織的團體,其任務、資金、所負責任都由政府來規定和監督;民間社團是由公眾自愿組織、由政府強制注冊、嚴密監管的團體。新加坡政府對民間社團參與社會治理給予多方面支持,如對慈善組織撥付行政費用、實施“社區發展議會企業伙伴合作按額資助計劃”、安排促進社會組織發展的項目等[8]38-39。新加坡官方社團與民間社團在社會治理中有明確的界分,前者基于國家合作主義治理模式以發揮政治功能為主,后者以志愿服務為主。
日本社會組織包括非營利組織(NPO)、非政府組織(NGO)和地緣性社會組織三種類型,它們各自有特定的服務面向、服務內容和服務功能。日本社會組織可根據自身業務范圍和宗旨選擇以不同的法人形式成立。日本社會組織在依法監管方面總分結合,既有總的《非營利組織法》,又由相關部門(如教育、衛生、農業等)通過配套法律法規對社會組織進行分類管理,從而強化了管理的針對性和有效性[8]39-40。為了支持社會組織的發展,日本政府建有區域社會組織支持中心,為社會組織提供硬件設施、支持開展活動,協助建立與政府和企業的合作關系。
3.2 國內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經驗做法——以臺灣、香港、浙江楓橋、上海為例
我國臺灣對社會組織的管理體現出規范、自治與扶持相結合的特點。臺灣的社會組織被稱為“人民團體”等。臺灣出臺的《人民團體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社會工作師法》等是調整和指導人民團體的法律規范。臺灣對人民團體開放準入門檻,按照“高度自治”的原則,為人民團體的發展創造了相對寬松的環境。政府對承擔社會公共事務的人民團體實行多樣化扶持,比如資金支持、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制訂社區發展計劃、打造基層社會治理平臺、促進志愿服務活動常態化等[9]。在立法、管理和政策的加持下,臺灣社會組織在承擔社會公共事務、減輕政府公共服務壓力、創新基層社區自治治理、促進社區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香港社會組織強調其公益服務本位,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服務范圍涵蓋慈善救助、家庭服務、照顧嬰兒、老年服務、康復治療等方面,以社會組織專業化、多元化發展來促進公益服務的供給和社會問題的解決。同時,香港社會組織參與政治的積極性高,參與渠道暢通,參與的方式也多種多樣。
浙江諸暨“楓橋經驗”誕生于20 世紀60 年代的浙江諸暨市,其核心內容是: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實現在農村基層“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鎮、矛盾不上交”的穩定局面。此后,“楓橋經驗”不斷發展、與時俱進。新時代“楓橋經驗”已經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更加突出黨政主導、依靠群眾、社會共治的基層社會協同治理經驗。楓橋“義工”聯合會、“紅楓”義警協會、“楓橋大媽”志愿隊等社會組織在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海市社會組織先行先試,曾在慈善超市、垃圾分類治理、青年家園、公益美學、弄管協會、青翼社工、杏林義工、物業管理、孝心服務隊等方面進行探索與實踐,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即規范化建設是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的基礎、信用度評價是社會組織有序發展的保障、專業化服務是社會組織穩定發展的關鍵[10]。2023 年,上海市民政局發布了20 個社會組織特色服務展示點;上海楊浦區評選出了首屆楊浦區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十大創新案例”,涉及濱江治理、助殘就業、社區矛盾調處、社工站建設等多個領域[11]。
綜上,美國、歐盟、新加坡、日本的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方面積累了相當成熟的經驗,如美國以稅法保障NGO 公信力和規范運行;歐盟將社會組織納入歐盟事務決策機制并提供制度保障;新加坡安排促進社會組織發展的項目;日本建有區域社會組織支持中心。在我國,臺灣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實行規范、自治與扶持相結合;香港的公益服務供給和社會問題解決得益于社會組織多元化、專業化發展;浙江楓橋經驗提供了基層治理范本,影響深遠;上海不斷推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創新案例。所有這些對當前我國地方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提供了啟示、參考與借鑒。
4 長沙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現狀及制約因素
2023 年,長沙市共有登記備案社會組織1.17 萬家[12]。近幾年來,長沙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舉措頻出。例如,2018 年,長沙市實施鄉鎮(街道)社工站“禾計劃”項目,至2021 年,全市建有鄉鎮(街道)社工站171 個、社工總站10 個,累計服務群眾90余萬人次[13]。2019年,全市共有210家社會組織參加長沙市第四屆“三社聯動”社區服務供需對接會,簽約項目845 個。2020 年,長沙市打造“黨建+社會組織”,在民政、衛生健康、教育、交通等部門成立了14 個社會組織行業黨委,將黨建工作融入社會組織運行發展全過程。2021年,長沙市150余家行業協會商會開展行業自律行動;有30 余家社會組織圍繞長沙市22 條新興及優勢產業鏈開展“互聯網+”服務;岳麓區梅溪湖街道金茂社區以“興趣社團”為抓手破解了“陌生人社區”治理困境。2022 年,長沙市推進“五社聯動”打造基層社會治理新品牌;探索推進“五社聯動幸福鄰里”工作,搭建了“愛星社”公益慈善信息平臺。2023 年,長沙市開展社會組織助力鄉村振興“黨建聚合力 百社幫百村”供需對接活動,攜手打造鄉村發展新天地。通過多年的治理實踐,在基層黨建引領方式創新、脫貧攻堅、社會救助、為老服務、關愛兒童、扶弱助殘、公益慈善、行業社區治理、矛盾糾紛調處、鄉村振興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然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治理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治理轉型發展進程中,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也存在一些問題:①社會組織社會認知程度不高;②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領域邊界不清晰;③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政策制度支持不完備;④大數據時代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活力不夠,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與公共服務能力不強;⑤社會組織之間聯動合作不夠,多元治理主體合作機制不健全。
5 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長沙市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推進策略
5.1 提升社會組織的知曉度和認同度
加強宣傳與輿論引導,進一步轉變觀念認識,樹立現代化的思維方式,進行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社會價值重塑,積極培育社會組織實施協同治理的社會基礎。以社會組織多元化、專業化、精細化發展促進社會問題解決與服務高質量發展,及時更新和發布社會組織的資源和服務情況,展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實踐的豐碩成果,提升社會組織的知曉度和認同度,營造“社會組織在身邊,社會組織在行動”的良好氛圍。
5.2 界定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作用領域
持續開展養老、育幼、助殘服務,滿足人們美好生活需求;幫扶低收入人群,助力共同富裕;在公共事務中開展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開展精神貧乏治理,促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參與解決復雜社會問題、調處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發展;參與環境協同治理,建設美麗中國;利用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開展智慧治理,打造智慧生活。制訂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領域細則,推進社會治理內容現代化。
5.3 在重點方向和領域加大制度供給,健全適應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政策制度體系
第一,做好共同富裕頂層設計,將鄉村產業振興、低收入人口幫扶、弱勢群體關愛服務、保障和改善民生、公益慈善事業和第三次分配等納入共同富裕范疇進行統籌安排。扶持發展科技類、電商類、公益慈善類、社會服務類等社會組織,對接共同富裕任務,與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功能互補、互促共進。建議制定社會組織助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措施,激活社會組織活力,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修訂慈善法,規范網絡捐贈行為,對慈善組織實行年度報表與稅賦信息公開制度,提升慈善組織公信力;完善地方配套政策,發展慈善組織實體,對公益慈善組織和對向公益慈善組織捐款的企業或個人予以稅收優惠,促進公益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助力共同富裕。
第二,將社會組織納入人才政策、表彰獎勵、民主政治建設進行統籌安排。為社會組織搭建基層協商和社會組織協商的平臺、拓寬民主渠道,建立健全社會組織有序參與的制度、程序、機制和方法,確保社會組織實質性在場,促使社會組織與政府部門、行業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形成制度化的合作關系。
第三,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精神貧乏治理,開發服務項目,組織開展各種教育、科技和文化服務活動,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對傳承和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特色城鄉地域文化、傳統民俗文化的社會組織,政府應予以重點扶持,資助其開展活動,發揮文化維系和社會整合功能。
第四,為環保社會組織參與環境協同治理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地方政府向環保社會組織購買環境治理服務。在多元共治中,使環保社會組織成為推動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針對大齡青年、離異人士婚戀難的問題,建議扶持和發展公益性社交型社會組織,線上與線下服務相結合,為大齡青年、離異人士交友婚戀提供平臺、牽線搭橋。
第五,加快社會組織專業化、信息化建設進程。加強社會組織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大數據平臺和智慧社區建設,加大政府對大數據平臺的制度供給,制定和完善智慧治理行政法規,為社會組織通過大數據分析發現和解決社會問題、革新利益訴求機制、重塑利益訴求渠道、進行精準治理、供給優質服務提供制度保障,通過技術賦能助推基層治理智慧化轉型發展。
5.4 為社會組織成長發展和能力建設提供項目和資金支持
在轉型治理、全域治理中,完善政府購買服務制度,拓寬資金、資源來源渠道,采取社會組織在項目運作中的多邊依賴策略,跨組織、跨專業設置項目,支持各種社會組織聯合承擔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優化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項目,建議設置促進社會組織發展的項目,如設立社情民意調查、決策咨詢、云移大物智技術培訓項目等,了解民眾的意見和建議,提供公共政策領域的咨詢意見,提高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特別是智慧治理的能力。
5.5 加強社會組織聯動協作,健全項目制框架下多元治理主體合作機制
為有效解決巨大的人口規模中出現的多樣化的社會需求、復雜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一方面,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參與治理和提供服務;另一方面,加大社會組織實施協同治理的政策、資源支持力度。鑒于大規模的社會組織孵化培育已告一段落且功能單一化,建議在社會組織孵化基地的基礎上,建立區(縣)社會組織支持中心,增加其職能,擴大其權限,為所在區域社會組織提供孵化培育、硬件設施、支持開展活動,協助社會組織建立與政府、企業的合作關系;加強組織聯合,建立街道(鄉鎮)或城鄉社區社會組織發展聯合會;項目制框架下合作機制的構建要建基于多個不同類型社會組織聯合購買和提供服務上,共同制訂服務、治理和發展方案,實施伙伴行動計劃。通過政策協同、資源協同、聯合治理、綜合治理,既發揮各自專業優勢,又發揮整體規模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