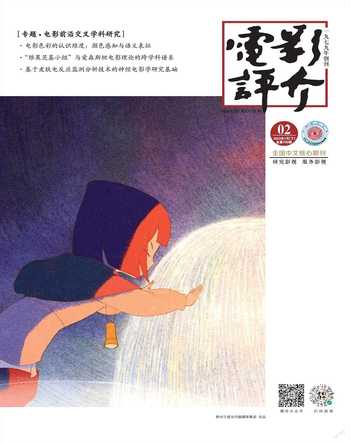東亞家庭喜劇中的敘事母題、多元模態與共態能及性
郄建業 單芷萱
在受儒家影響較大而產生根深蒂固的宗族立法觀念的東亞社會,家庭與家庭成員關系始終是電影表達的重要內容。其中,以家庭為基本敘事單元,在輕松的氛圍與歡快的基調中解決問題,迎來美滿結局的家庭喜劇經久不衰,在東亞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頗受觀眾歡迎。這些家庭喜劇盡管以小家庭為單位展開“小格局”的敘事,但影片中卻蘊藏了關于不同敘事模態相互影響的過程和結果。
一、儒家文化與等級結構的顯隱母題之間
家庭喜劇由于拍攝成本較低且飽經市場檢驗,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電影市場中都是廣受制片商歡迎的產品。但與西方國家拍攝的家庭喜劇相比,以中國、韓國與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家庭喜劇由于融合了儒家文化這一社會文化結構中的基礎性文化,不時顯出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等級結構而尤其具有癥候性。在儒家文化中,家庭單位內的“孝悌”原則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基礎。在此基礎上,一個人才能成為“愛人”的“仁人”與侍奉君主的忠臣,以及國家需要的人才。在孔子看來,做到侍奉供養父母、愛護兄弟姐妹,以及父母反饋的“慈”即是社會道德結構對人的外在要求,也是人性內在高貴的自然呈現;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父母養育孩子就和飼養犬馬沒有區別。他還提到,真正的孝對父母要既尊敬又愛護,即“敬愛”,其重要的外在表現之一是在待奉父母時感到發自心底的愉快,從而自然流露出愉悅的容色;另一方面,如果說“敬愛”與“仁愛”的“愛人”思想體現了孔子思想中重人倫的維度的話,那么體現“禮”的要求的重人倫思想則是孔子思想中另一個重要的維度,也是實現仁愛目的的主要手段,是重建整個國家政治、倫理秩序的基礎。“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1]“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2]孔子強調以崩壞中的周禮作為宗法等級關系的制度和規范,其著眼于處理宗法人倫關系問題的部分是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周禮之“禮”并非重在外在的禮節、禮儀方面,而是扎根在“禮”所反映的仁愛精神和秩序觀念中。儒家文化在親子關系間的“愛”與秩序互為表里,情感間包含著封建社會親子等級之間在人格上的隸屬關系,而對自我的克制與對長者的尊敬又自然流露出家庭成員的情感。對于東亞家庭喜劇來說,這種一體兩面的儒家倫理文化深刻地印刻在影片的文化基因中,成為所有家庭喜劇共有的敘事母題。
盡管強調人倫親情的“愛”與等級結構的“禮”同時存在于影片之中,但二者總是在動態關系中不斷地消長顯影。其中,“愛”構成了緩和角色關系的重要元素,是讓矛盾最終得到和解的關鍵一步;“禮”則對應著觀眾的深層心理結構,支撐著整體故事的框架穩定。二者時不時的沖突與矛盾則構成了敘事向前推進的動力與影片的核心看點——在傳統儒家文化中也是如此。在現代國學大師匡亞明的闡釋中,封建社會的家庭關系必然帶有封建社會宗法家長制的色彩,就是片面強調家庭成員之間人格上的隸屬關系。[3]換言之,強調自上而下等級性的“禮”是第一性的,傳統社會中要求子女對父母保持“孝”的道德標準仍然是故事整體思想情感穩定的基礎;無傷大雅的“以下犯上”反而成為影片喜劇性的重要來源與故事矛盾出現的源頭。
以日本影片《明日家族》(土井裕泰,2020)為例,這部影片在公司職員小野寺理紗與小野寺俊作的家庭中展開。故事的主要矛盾點在于理紗新交往的男友兵頭幸太郎正是其父親小野寺俊作同一公司部門的“頂頭上司”。在公司中下級聽從上級指令形式的規則要在下班回家后逆轉過來。對此,岳父與女婿二人都感到十分尷尬,難以接受。這部整體氛圍輕松愉快的家庭喜劇并沒有為主人公刻意設置婚變、財產危機、刻意刁難主人公的反派等一般電影中的矛盾要素,怎樣解決這一“愛”與“禮”的沖突成為全片最大的懸念。在女婿與岳父的關系陷入僵化之時,小野寺理紗與母親真知子為家庭付出的“愛”與結構的反轉成為矛盾解決的重要契機。在傳統的日本家庭劇中,受“丈夫作為社員拼命工作而妻子做家務”的戰后經濟模式影響,已經婚育的女性角色往往承擔著調節角色矛盾的功能,但其本身的個性較弱;而在《明日家族》中卻并非如此。丈夫小野寺俊作得知不用被調到分公司可以繼續留在總部工作時,高興地買了一盒金槍魚魚腩回家。真知子雖然已經是中老年人,但是在看到這盒魚腩的時候仍然做出了非常夸張的表演:先是雙手捧著魚腩來回舉動,頭頸順著魚腩被舉動的方向夸張的搖擺;女兒小野寺理紗回到家以后,她又高興地踮起了腳原地墊步,小野寺理紗公布自己有男朋友以后,她張大的嘴許久沒有閉上;女兒提到未來男朋友同意住在家里時,她又雙手張開放在張大的嘴前拍打;同時,這段表演的聲音也是刻意“少女化”了,帶有許多撒嬌意味的語氣詞。這樣的表演方式完全是日本影視劇中少女演員的“表演程式”,但真知子的表演者利用這樣的動作與神情顯示出“母親”與“岳母”少女化、年輕化的一面,從而在真正的年輕一輩——理紗與兵頭,以及固執傳統的老一輩——俊作之間充當了中層的溝通橋梁,并以討喜的話語和表現深切地“動搖”了看似牢不可破的等級結構。《明日家族》展示的便是這種屬于“明日”或“未來”的家庭關系。影片結尾,一家人終于跨越了思想觀念上的障礙,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這部作品本身便蘊含著通過這部新的電影作品構建一種建立在溫暖的家庭關系之上的、面向“明日”的對話。電影中的母題作為集體性與歷時性的觀念集成,必然在社會觀念的更新下產生相應的變動與發展。
二、共同體模式與多元模態的建立
在討論這些紛繁復雜的內容時,可以適當地引入在哲學社會學領域提出的“共同體”理論。這一理論目前在東亞電影的研究中大量使用,其影響的環節也包括了電影制片與創作實踐、觀眾的接受美學與社會文化反思等。“共同體”一詞的含義與詮釋頗為廣泛,在德國學者滕尼斯所著的《共同體與社會》中,共同體概念囊括了從古希臘城邦、羅馬父權制國家直到中世紀日耳曼封建制帝國與自由市鎮并軌的歷史,它與近代以來受市民社會與民主制國家進程影響的“社會”相對應。滕尼斯以霍布斯的生平和學說作為研究核心,秉承了自由主義思想,滕尼斯設想了源于每一個體自身意志的革命性政治體成為在現代政治的失敗之后對抗理性社會、重新回歸浪漫的思想資源[4];英國學者齊格蒙·鮑曼則將共同體勾畫為前現代資本主義歷史的“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5]。如同這部作品并非單純的電影或電視劇而是以“電視制片電影”的形態出現一樣,在現代社會建立在家庭基礎上的同時又脫離家庭本身所結成的共同體模式社區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最基本形式。韓國家庭喜劇電影《開心家族》(金英卓,2010)則選用了“陌生人最終成為家人”的主題,四個陌生人不約而同地請平平無奇的尚萬幫助自己圓夢,但所謂的“圓夢”其實主要是讓尚萬找回生活的希望,幫助他和護士妍秀走到一起。片尾處,尚萬終于認出四個他一直沒認出來的陌生人其實就是自己的家人,這樣的脫域共同體形態是血緣、婚姻和朋友關系的融合。
在制作與播出企劃中,許多東亞家庭喜劇也在多方面呈現出共同體美學的特征。盡管在故事的起承轉合上與一般家庭生活題材的電影相似,但它仍然不留余力地保留了電視情節劇的特征。在前文論述過的除了拍攝與演出的實踐外,《明日家族》每播放約20分鐘,待劇情到達一個分階段的節點之后便會出現贊助商廣告。而中國的綜藝IP電影《爸爸去哪兒》(謝滌葵、林妍,2014)同樣進行了將電視綜藝與電影形式結合在一起的嘗試。許多以前只能在電視綜藝中看到的動畫特效、解說字幕乃至貼片廣告堂而皇之地出現在電影劇情中。比起普通電影,《爸爸去哪兒》的“真人秀”性質意味著鏡頭中的“演員”都是即興發揮,鏡頭畫面中特寫少而中景多,粗糙的外景感比較強。盡管并不是所有觀眾都認可這種形式融合的制片方式,但這部“綜藝大電影”仍然在形式上流露出一種與其“闔家歡”“全家桶”內容相呼應的美學主張。從家庭喜劇類型角度出發加以考慮,將東亞文化求同存異的理念與西方政治中的共同體理念相結合,并轉化為電影創作與研究中可運用的美學原則,仍然有相應的可行性。多重可行性在電影制作上最終仍將轉化為多重可能性。
在敘事學領域的可能性探究中,無限多的可能性重疊會導致一種必然性的“可能世界”。這種“必然的可能”理論建立在近代哲學邏輯與量子物理學等學科的知識經驗上,并開拓出一套全新的敘事理論框架。“可能世界理論作為一個參考框架,也用來描述故事世界的動態生成過程、一種迥然不同的故事語法,為敘事性問題提出了一個替代性的理論模型。此外,可能世界理論還容許對敘事的認知過程和情感體驗進行分析和闡述。”[6]以2022年一經上映便引起熱議的“科幻家庭喜劇”《瞬息全宇宙》(關家永、丹尼爾·施納特,2022)為例,影片的主要矛盾在美籍華裔一家人中展開,在極富東亞家庭文化色彩的語境中展現出極其深刻的存在主義內核。人到中年、生活困窘的美國華裔移民伊芙琳終日為維持家庭奔忙,終于在經營的洗衣店保稅出現問題之后被強行拉入另一個宇宙,了解了多重宇宙的存在并掌握了穿梭在多重宇宙間的能力。在諸多令人眼花繚亂的多重宇宙中,伊芙琳的最終目的仍然是傳統東亞的“救贖”——將女兒從無盡的虛無主義中解脫出來,同時也需要找尋自己作為母親與妻子的“存在意義”。其中,親情、愛情與家庭秩序,即“情”與“法”的交錯顯影仍然明顯,但可視化且頗具想象力的多元模態卻讓影片突破了教條式的、“愛拯救一切”的陳詞濫調。
在傳統母題的基礎上,本片不僅是保守主義的家本位敘事回歸,而且更是對家庭喜劇故事嶄新的開掘。在哲學領域,全新世界模態的開掘是解決現實邏輯問題的有效路徑;而在藝術中,多重世界模態的并行則可以開辟全新的敘事空間與審美期待。多重世界模態、“瞬息全宇宙”與“平行時空”不僅是傳統的多線索敘事,而且也是在單一“宇宙”的基礎之上建構一個復雜的模態系統,每個宇宙都以實際存在的方式同時在時間上延伸,并在效果上相互發生不可觀測的累加、影響,從而重建整個文本的構成邏輯。“這些建構不僅是文本現實世界的衛星,而且是完整的宇宙,人物需通過再中心化而到達。”[7]可能世界的運動方式是類似衛星的位移方式,而其與核心世界之間的互動、關聯使“再中心化”成就了文本的多種可能,促使“敘事進程”變得復雜多變。[8]在故事中,原本無法放開女兒與丈夫的伊芙琳最終選擇了和解。這種和解不再是東亞傳統文化強調的、家庭成員為了家庭集體而主動犧牲的精神,而是一種在了解對方選擇理由之后予以對方的信任與寬容。就像伊芙琳目睹女兒成為“魔王”之后并不是加強對她的教育和控制,而是反省自己與她的溝通問題,進而充分尊重女兒的選擇。伊芙琳母女由于工作忙碌而忽視了彼此的感受,而“瞬息全宇宙”正是以豐富的視聽呈現彌補了這一缺憾,將心靈特征視覺化,讓母女看到了不同模態中不一樣的家人,也讓觀眾在多重選擇中重新開辟了審視自我與生活的契機。
三、開放家庭結構中的共態能及性
將以上的多元模態理論運用到東亞喜劇電影文本的闡釋之中,可以在敘事母題本身的復雜性上突破單一人類線性時間與因果邏輯的內在經驗,進而重新在一個靈活多元的共同體中構造出敘事文本內的關聯邏輯。富有意味的是,在所有關于共同體理論的論述中,關于共同體這一概念的種種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在“和而不同”的理念下,從不容改變的社會結構到已經喪失的過去,以及社會群體內部強勢者之于弱勢者對共同體的抗拒等,種種“不同”都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在趨于多元化、多極化的世界中,個體的獨特性及其與群體的離散性成為共同體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所謂的“共同體理念”[9],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承認和保留個性的前提下尋找利于溝通及合作的共性關系。
美國學者道勒齊爾將事物的能及性理解為集合論中的交集,“讓不同的可能世界能夠接觸”[10],多元模態中的家庭正在成為一種開放的敘事單元。在當下的家庭喜劇中,許多帶有家庭倫理關系并非完全在真正的血緣家庭中展開,但敘事上的共性與能及性卻賦予了它們全新的意義內核。例如,繼《我和我的祖國》(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路、徐崢、寧浩、文牧野,2019)和《我和我的家鄉》(寧浩、徐崢、陳思誠、閆非、彭大魔、鄧超、俞白眉,2020)之后,“國慶三部曲”之一的《我和我的父輩》(吳京、章子怡、徐崢、沈騰,2021)徹底將主人公的生活軌跡放置在家庭單位中,在擬態家庭這一共同體中將個人情感與社會秩序結合起來,在以國為家的邏輯起點上展開敘事,并進一步把關于民族的遠大理想與個體性的主體抱負與擔當精神相結合:《乘風》篇取材于抗日戰爭時期冀中騎兵團為保護群眾撤離不顧犧牲、奮勇作戰的故事,并在騎兵團與冀中人民共同抗擊日寇侵略的軍民群像中刻畫出一種源于家庭又超越血緣家庭的大愛。八路軍父子馬仁興與馬乘風為相同的革命信念殊死作戰,馬乘風為保護懷孕的鄉民大春子戰死,馬仁興懷抱這個親兒子用生命換來的小生命悲喜交集,也給他起名為“乘風”。死亡與新生的畫面交叉剪輯在一起,嬰兒的襁褓中浮現出馬乘風的笑臉,電影以畫面講述民族血脈在英雄犧牲中的代代相傳;《少年行》中來自未來的機器人承擔起“父輩”的責任,觀眾會發現這臺由未來兒子開發出的機器人更像是“我”未來的“兒子”。父子之間的身份調換承載了一種面向未來的開放精神與奉獻理念,也意旨一種面向新時代、新事物的態度。《我和我的父輩》給觀眾展現的家庭關系與影像結構是一個“復雜交織”的文本,幾名導演將主旋律的價值追求與審美意識放置在“段落式”敘事方式中,并以靈活的表現手法與開放性的敘事拓展出新的表達空間,既是主旋律電影的新收獲,又為當下中國電影創作積累了新的經驗。
結語
東亞的家庭故事中包含著時代進步造成的代際差異、代際溝通時遭遇的問題等內容。在敘事方面,這些微妙的差異在文本當中帶來了多元模態同時并存的奇妙構思,并利用多元模態帶來的多種可能性在觀眾的認知理解過程中營造出錯位與差異,從而賦予影片更多詼諧的喜劇色彩。這將能引起觀眾對傳統倫理關系的反思,從而增強整體影片的風格和敘事張力,成就東亞家庭喜劇獨具魅力的風格與特色。在人情與禮法的微妙罅隙中,簡單的家庭結構可能衍生出無限微妙的可能性,甚至會突破經驗性線性時間的內在體驗,并以多元模態的共同體邏輯組織起一個具有多重時空關聯的復調文本。
【作者簡介】? 郄建業,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戲劇電影與電視藝術研究;
單芷萱,女,河北邯鄲人,河北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生。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戲劇影視文學)專項建設項目(編號:HBDX-20091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2]孔子.論語[M].劉勝利,譯.上海:中華書局,2006:51,129.
[3]匡亞明.孔子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193.
[4][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張巍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15.
[5][英]齊格蒙·鮑曼.共同體[M].歐陽景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71.
[6][7]張新軍.可能世界敘事學[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1:10.
[8]張立娜.論“東亞喜劇電影”故事世界的多元模態與能及性[ J ].當代電影,2022(11):37-42.
[9][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M].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
[10]Lubomír Dole?el.Heterocosmica: 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