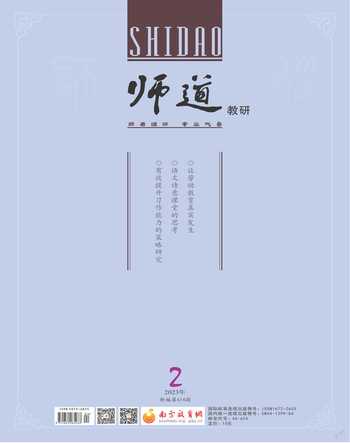語(yǔ)文詩(shī)意課堂的思考
卜階輝
課堂是師生教與學(xué)的園地,語(yǔ)文課堂,更應(yīng)該是洋溢著文化的氣息,閃耀思想的光芒。詩(shī)意課堂的重點(diǎn)應(yīng)在于“意”,但首先著眼于“詩(shī)”,更多地從內(nèi)容和實(shí)質(zhì)上予以突破。
一、突破“詩(shī)體”的局限性,以“詩(shī)意”擴(kuò)展課堂
中學(xué)語(yǔ)文課本匯集了五千年中華文化的精髓。以古代詩(shī)歌而言,唐詩(shī)宋詞元曲明清小說(shuō),山水田園羈旅邊塞詩(shī),各有兼顧,這樣的編排,有利于整體把握,但難免縱深不夠。
譬如《唐詩(shī)宋詞元散曲選編》“唐詩(shī)之旅(上)”,刊選杜甫詩(shī)5首,《月夜》《哀江頭》《蜀相》《又呈吳郎》《登岳陽(yáng)樓》等,寫(xiě)作時(shí)間集中在安史之亂后,詩(shī)歌內(nèi)容都是杜甫顛沛流離的凄惶生活和憂國(guó)思親的家國(guó)情懷。展示給學(xué)生的都是杜甫那副眉頭緊蹙、形容枯槁的悲苦滄桑狀。這是杜甫作為詩(shī)圣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詩(shī)歌經(jīng)典所在,但人的思想總是立體的,思想形成也是漸進(jìn)的,如果此時(shí)教師引入其早期作品,如《房兵曹胡馬》的“所向無(wú)空闊,萬(wàn)里可橫行”,《畫(huà)鷹》的“何當(dāng)擊凡鳥(niǎo),毛血灑平蕪”。這些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富于展望、雄心勃勃的詩(shī)歌,定能幫助學(xué)生放眼詩(shī)人多彩人生,從而突破詩(shī)體的局限性。這樣的課堂,一定是思想縱橫、詩(shī)意橫生的。
二、突破“詩(shī)境”的局限性,以“詩(shī)意”統(tǒng)領(lǐng)課堂
語(yǔ)文旨在提高學(xué)生語(yǔ)文素養(yǎng),培養(yǎng)學(xué)生的邏輯思維能力。語(yǔ)文學(xué)習(xí)不是庖丁解牛,“工多便能手熟”。每篇作品背后都是一段段波瀾起伏的人生經(jīng)歷,都是一縷縷錯(cuò)綜復(fù)雜的思想脈絡(luò)。語(yǔ)文教師要構(gòu)建詩(shī)意課堂,要有站在云端的姿態(tài)和素養(yǎng)。所謂姿態(tài),就是大膽放手把課內(nèi)文章交給學(xué)生;所謂素養(yǎng),就是教師要有透過(guò)表象抓本質(zhì)的能力。
筆者曾在北京實(shí)驗(yàn)學(xué)校聆聽(tīng)到講授蘇軾《寒食詩(shī)》的公開(kāi)課。老師基本上不講詩(shī)歌內(nèi)容,只是提煉問(wèn)題引發(fā)學(xué)生思考。一個(gè)問(wèn)題是“黃庭堅(jiān)認(rèn)為,東坡此詩(shī)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請(qǐng)問(wèn)如何理解?”于是乎,學(xué)生冥思苦想,搜腸刮肚,進(jìn)行對(duì)比閱讀。接著,老師又提煉了一個(gè)問(wèn)題,“有人說(shuō),失意東坡,黃州突圍。如何理解?”教師提示學(xué)生結(jié)合《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定風(fēng)波》等詩(shī)篇,從釋道儒思想去闡述。這節(jié)語(yǔ)文課,教師提煉問(wèn)題激發(fā)學(xué)生思考,學(xué)生思想如天馬行空,語(yǔ)文課堂有如百花齊放。
三、突破“詩(shī)情”的局限性,以“詩(shī)意”發(fā)散課堂
“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yuǎn)看高低各不同。”2000年全國(guó)高考作文話題“答案是豐富多彩的”,引發(fā)了人們對(duì)千變?nèi)f化的世界有了更為辯證的思考。語(yǔ)文課堂,以文化精粹為載體,以思想為觸角,穿越遼遠(yuǎn)的時(shí)空,與作者握手,對(duì)其行文的動(dòng)機(jī)、文章的思想,進(jìn)行個(gè)性揣摩,雖說(shuō)有跡可循,但難免有霧里看花,甚至盲人摸象之感。古希臘普魯塔戈指出,“頭腦不是一個(gè)要被填滿的容器,而是一只需要被點(diǎn)燃的火把。”倘若語(yǔ)文教師在諸如文章主題、人物形象等分析方面,手擎參考書(shū),強(qiáng)求標(biāo)準(zhǔn)答案,將會(huì)使課堂充滿了野蠻粗暴,將毫無(wú)詩(shī)意可言。
譬如,《中國(guó)現(xiàn)代散文選讀》中《道士塔》,在分析王道士“這個(gè)這出悲劇中錯(cuò)步上前的小丑”形象時(shí),參考答案是抓住“刷壁畫(huà),砸雕塑”等動(dòng)作描寫(xiě),以及“目光呆滯,畏畏縮縮”的神態(tài)描寫(xiě),認(rèn)為其是不學(xué)無(wú)術(shù),貪婪無(wú)知的文化罪人。但也有學(xué)生指出,有圖片為證,王道長(zhǎng)的神態(tài)應(yīng)該是“笑容滿面,憨厚質(zhì)樸,是未被消費(fèi)時(shí)代侵蝕的、感人的臉,”也指出“刷壁畫(huà),砸雕塑,筑靈官菩薩”是囿于認(rèn)知的局限性,好心辦壞事,不是萬(wàn)惡不赦,而是情有可原的底層道士形象。
潘新和先生在《語(yǔ)文表現(xiàn)與存在》中深情地向往:“未來(lái)的語(yǔ)文教師要是都能充滿情懷,都能用自己的詩(shī)意感悟去喚起孩子心靈中的詩(shī)人;未來(lái)的孩子如果都能擁抱、譜寫(xiě)自己的詩(shī)意人生,那是多么好。”詩(shī)意的課堂必定是思想自由的天地,語(yǔ)文教師只能喚起情懷,而不能壓制思想。如果強(qiáng)調(diào)王道士只是參考書(shū)中的形象,那么學(xué)生的思想將無(wú)處安放,并且將“吊死在參考書(shū)這棵樹(shù)上”。
構(gòu)建詩(shī)意語(yǔ)文課堂,就是培植思想自由、視野開(kāi)闊、情感升華的文化土壤,讓學(xué)生的文化素養(yǎng)在陽(yáng)光照耀和雨水滋潤(rùn)下茁壯成長(zhǎng)。
責(zé)任編輯 龍建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