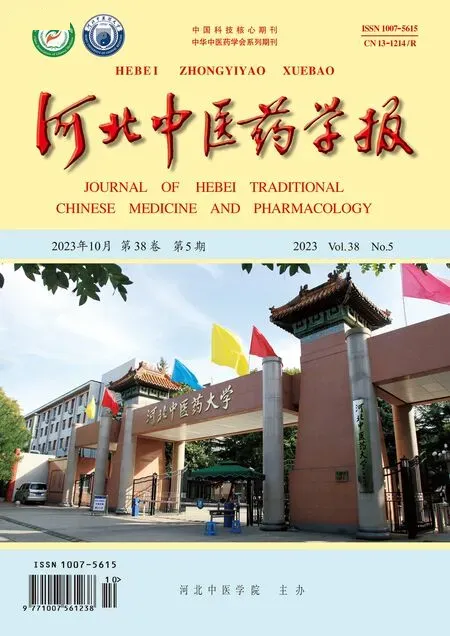基于形神同調探討從心肝論治慢性蕁麻疹*
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
高 暉 藺 依 吳治民 刁若涵 齊若舟 段行武(北京 100700)
提要 基于形神同調理論探討慢性蕁麻疹(CU)從心肝論治的方法。CU屬于中醫“癮疹”范疇,病因復雜、遷延難愈,同時存在氣血功能的失調和精神情志的異常,二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即“形神同病”。而心肝同調氣血、共調情志,與CU形神病變關系密切,臨證治療應注重形神同調從心肝論治,治神重在調肝養心,治形重在調和氣血,使形與神俱、氣血沖和,以達防治慢性蕁麻疹的目的。
慢性蕁麻疹(CU)是一種常見的變態反應性皮膚病,表現為大小不等的風團或血管性水腫伴瘙癢,反復發作超過6 w,人群患病率1%~1.5%[1],屬于中醫“癮疹”范疇。本病反復發作的風團、瘙癢,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和身心健康[2]。有研究表明,約46%的CU患者伴有如焦慮、抑郁、情緒化、人際敏感、失眠、壓力大等不良社會心理因素[3],而本病的發生、緩解與患者的精神狀態和心理變化密切相關,互為因果,這種關系與中醫學中形病及神,神病及形的“形神同病”狀態不謀而合。因此臨床治療CU,在考慮局部皮膚異常的同時,也應考慮精神因素的影響,注重“形神同調”。CU病因復雜,氣血不和為其發病之本,而心肝同調氣血、共調情志,與CU形神病變關系密切。本文基于“形神同調”理論,探討從心肝論治CU,以期為本病的中醫藥治療提供一定思路。
1 形神一體觀的理論內涵
“形神一體觀”理論始見于《黃帝內經》,是中醫整體觀念的內涵之一。“形”是指人體的一切有形之體,包括人體的臟腑、皮肉、筋骨、脈絡及充盈其間的氣血津液等有形物質;“神”則包含廣義的“神”和狹義的“神”,廣義的“神”指人體生命活動的外在表現,狹義的“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4]。如《靈樞》云:“五臟已成……魂魄畢俱,乃成為人。”張景岳言:“形神俱備,乃為全體。”中醫理論認為人體的生命活動與自身形體和精神密不可分,形神相互為用、高度統一,即“形神一體觀”。
生理上形神互根互用。形為神之基礎,“形具而神生”。《靈樞·平人絕谷》云:“五臟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人的精神活動由五臟精氣化生和充養,臟腑氣血調和,軀體功能正常,精神才可居于其中而發揮機能;同時神為形之主宰,人的精神活動亦對人體的生理功能起到調控作用,即“神能御其形”。如《素問·湯液醪醴論》云:“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又謂:“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神去之而病不愈也。”均提示“神”有“生命主宰、造化之機”的涵義[5]。
病理上形神相互影響,“形病則神不安,神病則形受損”。如《靈樞·天年》云:“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景岳全書》亦指出“傷形則神為之消”,可見二者任損其一皆可導致形神共病;《黃帝內經》載“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喜怒不節則傷臟”“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等,也都強調了不當的情志變化可導致氣血功能異常或臟腑功能失調,最終導致疾病發生或加重。
可見,“形神一體觀”是對人體結構與功能、人體生理屬性與精神意識屬性的和諧統一的體現。而隨著現代醫學逐步向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轉變,心身醫學也應運而生,認為精神心理因素在健康的保持及疾病的發生、發展、康復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6],病理變化往往與心理因素交叉形成復雜的病因,治療軀體病癥的同時也要關注其心理因素。這種生理和心理相互作用的心身關系與“形神一體觀”具有高度一致性[7]。心身醫學中所研究的心理層面即屬于中醫“神”的范疇,生理層面屬于中醫“形”的范疇。正如《素問·上古天真論》云:“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只有心理和身體的雙重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形神一體觀”理論能夠有效地指導中醫臨床實踐,辨證論治實質即為“調神守形”的過程[8],臨診之時應關注軀體病癥與心理狀態之間的密切聯系,做到形神兼顧,將養神與治形相結合,達到“形神合一,陰平陽秘”。
2 慢性蕁麻疹形神共病的病機認識
CU屬于中醫“癮疹”“游風”等范疇,其發病與稟賦不足、外邪侵襲、飲食或情志內傷、臟腑虛損等因素相關[9]。而其發無定處、驟起驟消的發病規律,符合“風邪善行而數變”的特點。如《金匱要略·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云:“風氣相搏,風強則為癮疹。”“風邪”被認為是癮疹發病的中心環節。風邪有外來有內生,CU反復發作、遷延難愈,主要責之于體內陰陽氣血失調之內生風邪[10]。對于CU,氣血不和為其發病之本,血瘀、血熱、血虛均可化燥生風:或為情志內傷,氣機不暢,營血郁滯;或氣郁日久化火,煎熬營血;或久病耗傷氣血,氣血虧虛,化燥生風,外發于肌膚,引起皮膚反復起風團、瘙癢[9]。CU表現在外的風疹團塊,即為有形可見的“形病”;而其遷延不愈、瘙癢難耐的癥狀,常導致患者出現煩躁、焦慮、失眠等情志異常改變,即為CU之“神病”,二者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即“形神共病”。
現代醫學研究也表明,精神情志因素與CU的發病存在一定關聯性,部分CU患者的發病及遷延不愈可能與焦慮及抑郁癥狀有關[11];并有臨床研究發現,綜合性心理治療可以提高CU的療效和患者的生活質量[12]。可見CU不是單純的皮膚疾病,而是在整體背景下發生的復雜的身心性皮膚病,因此臨床治療本病,在考慮局部皮膚異常的同時,還應考慮精神因素的影響,即“形神同調”。
3 慢性蕁麻疹形神病變與心肝的關系密切
3.1 氣血失和為發病之本——心肝同調氣血 《素問·調經論》曰:“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CU雖屬于皮膚疾患,但究其發病之本在于氣血失和,而心、肝在調節氣血方面起著相互配合的重要作用。《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諸血者,皆屬于心。”心主血,又主脈,且“心部于表”,心氣布散于全身皮表,統領皮膚肌腠,維持其正常生理功能與御邪能力。只有心氣充沛、血液充盈、脈道通利,血液才能周行全身、外布皮表,濡潤四肢百骸、肌膚腠理。而肝主疏泄、藏血,以血為體、以氣為用,既貯有形之血,又疏無形之氣,可協調臟腑功能、調節全身氣血。同時,肝與心發揮著協同作用,肝主疏泄、藏血為心主血脈提供了條件,而肝藏血的功能也離不開肝的疏泄和心氣的推動。如《薛氏醫案》言:“肝氣通則心氣和,肝氣滯則心氣乏。”《血證論》載:“肝主藏血焉。至其所以能藏之故,則以肝屬木,木氣沖和條達,不致遏郁,則血脈得暢。”王冰云:“肝藏血,心行之,人動則血運于諸經,人靜則血歸于肝藏。”都說明心肝相互配合、同調氣血,令五臟六腑藏泄得當、營血運行通暢、腠理開合有度。若心血或肝血不足,氣血虧虛,生風化燥,則易走竄皮表而發為癮疹;若心氣不利或肝郁失疏,致氣機不暢,血運難行,凝滯于內,或郁久化熱,腠理失密,毛失潤澤,而生內風,引起風團、瘙癢等癥狀反復發作。
同時,如《素問·四時刺逆從論》曰:“少陰有余病皮痹隱軫。”《外科證治全書》云:“癮疹……屬心火傷血,血不散,傳于皮膚。”《醫學入門》載:“赤白游風屬肝火。”心肝調節氣血的功能失常也會導致心肝之火亢害而發為本病。心屬火,心氣布于表,又主血脈,心火熾盛,燔灼津血,化燥生風發為癮疹;而肝以氣為用,氣有余便是火,又肝藏相火,故肝郁易從火化,且風氣歸于肝,肝郁化火,火發則風生,風火相煽,煎熬血液,氣血運化失常,或日久耗血傷陰,而生風燥,發為本病。
由上可知,CU發病之本為氣血失和,而心肝相互配合、同調氣血是本病“調形”的理論基礎。氣血失和,日久可形成血瘀、血虛、血熱、血燥等交錯復雜的證候,風邪內生,導致本病反復發作、遷延不愈。因此維持心、肝的生理功能正常,保證體內氣血調和,是防治CU的關鍵。
3.2 情志失調為神病之根——心肝共調情志 CU作為一種形神共病皮膚病,其精神情志即“神”的異常對本病的發生、發展和轉歸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神志雖與五臟均有聯系,但與心、肝的關系最為密切。心主神明,肝主情志,心、肝是主導調節精神情志的主要臟腑。
《荀子·解蔽》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靈樞·邪客》云:“心者,五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主神明,心神得藏則神明有主,而心主神又與心主血脈相互作用,心神調暢,則血脈充盈,肌膚榮潤無疾;若情志失調,心火亢盛,心神被擾,或氣血不暢,心神失養,則會出現煩躁不安、夜不成眠、焦慮抑郁等精神情志障礙,并可影響心之氣血陰陽的正常運行,血脈運行失調,肌膚失養,致本病纏綿難愈。同時,瘙癢作為CU的主要癥狀,亦與心神密切相關。如《素問·至真要大論篇》云:“諸痛癢瘡,皆屬于心。”王冰注曰:“心寂則痛微,心躁則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痛癢瘡瘍生于心也。”都說明心神不安會導致瘙癢愈甚。現代研究也證實,焦慮和緊張狀態時人們對瘙癢的感覺更為敏感,且情志因素本身即會引起心因性瘙癢,而瘙癢又不同程度地影響患者的生理功能,對患者的精神狀態造成負面影響,從而影響疾病的恢復,形成惡性循環[13]。
除心神外,人的精神情志活動還與肝密切相關。蓋肝主疏泄,喜條達而惡抑郁,凡精神情志之調節皆與肝密切相關。肝氣條達,則氣機調暢,情志平和,氣血調和;若情志抑郁,肝郁氣滯,或郁久化火,則氣血陰陽失調,腠理失和而發病。現代醫學研究也表明,不良的神經精神因素是大多皮膚病發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而蕁麻疹亦常于精神緊張、焦慮抑郁等情況下反復發作[14]。且本病病程遷延,亦常導致患者出現情志焦慮、抑郁等癥狀,最終形成“因病致郁”“因郁致病”的惡性循環。
可見本病出現的精神神志異常等“神”之變,與心肝同調情志的功能失常密不可分。因此對于CU患者,在治其“形病”同時,也要注重調肝治心、安神暢志,以治其“神”。
4 治療重在治肝養心,調形安神
CU作為典型的形神同病疾病,臨床治療重在治肝養心,以達調氣和血、調形安神之功。心肝調暢,氣血沖和,神明調暢,則五臟得安,肌膚乃濡,癮疹乃瘥。另外,對于CU患者,在治療時除使用藥物外,還應配合心理疏導等非藥物治療,即張景岳所言“以情病者,非情不解也”。
4.1 心肝氣郁證,疏肝理血以治其形,解郁寧心以治其神 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言:“情志之郁由于隱情曲意不伸,故氣之升降開闔樞機不利。”情志因素是本證患者發作的重要誘因。情志不暢,心肝氣郁,氣機不暢,氣血運行受阻,無以輸布,內不得宣泄,外不得透達而發病。癥見風團、瘙癢反復發作,多與情志波動有關,喜嘆息,可伴脅肋不適,失眠多夢,舌紅、苔薄,脈弦。治以疏肝理血、解郁寧心,方用小柴胡湯合升降散或丹梔逍遙散加減,使氣機條達,經絡通,陰陽調,氣疏血暢而風團自消。若氣郁日久,瘀阻經隧,經絡皮部氣血不通,營衛之氣不宣,癥見風疹塊黯紅,或常發于受壓部位,兼有口唇舌質較黯或見瘀斑,脈細澀者,治可偏重活血化瘀,方用桃紅四物湯加減。發于上肢者加桑枝、姜黃,發于下肢者加牛膝,癢甚加僵蠶、地龍。
本證患者多憂思善慮,常因情志波動加重病情,或反復發作日久出現情志抑郁焦慮等癥狀,故治神重在解郁寧心。偏于肝氣郁結者酌加柴胡、白蒺藜、香附、薄荷、玫瑰花、佛手、香櫞等疏肝解郁,偏于心神不寧者酌加夜交藤、丹參、合歡花、遠志、百合等寧心安神。除藥物治療外,還應重視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可配合如情志相勝法、移情易性法等心理治療,使療效互為補充、相互促進。
4.2 心肝火旺證,清心平肝以治其形,除煩潛鎮以治其神 對于心肝火旺證患者,癥見疹塊色紅,皮膚灼熱刺癢,搔后即起風團或條痕隆起,常伴心煩易怒、焦慮不安、夜寐不安,便秘溲黃,舌邊尖紅、苔薄黃,脈弦滑帶數。治以清心平肝、除煩安神,肝火偏重者方用龍膽瀉肝湯加減以降瀉肝火,使氣血通暢,則風團自散;心火偏亢者方用消風散加減以清熱涼血、祛風止癢。
本證患者常訴因皮疹反復發作,瘙癢難耐,致心煩急躁;或常發于夜間而致睡眠難安,進一步影響情緒,加重或誘發皮疹、瘙癢,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對于本證患者,治神重在除煩安神、鎮心潛陽。因皮疹持續或反復瘙癢導致的情緒煩躁、睡眠不安者方用梔子豉湯,梔子豉湯主“虛煩不得眠……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臨證可配伍郁金清心開郁,或伍以生地黃、牡丹皮清熱涼血,淡竹葉、黃連清心除煩。對于瘙癢劇烈或頑固,搔抓不止、坐臥不寧者,可酌加珍珠母、生石膏、生龍骨、生牡蠣、靈磁石、代赭石等潛鎮安神之品,以平肝潛陽、鎮心安神,抑制患者精神情志之亢奮,降低其對外界刺激的敏感性,從而緩解瘙癢癥狀。現代藥理學也證明,重鎮安神藥物如龍骨、牡蠣等不僅可以鎮靜安神、抗焦慮抑郁,還可以調節免疫系統,促進恢復免疫平衡狀態[15]。此外,因重鎮安神藥多為金石礦物之品,為防其礙胃,臨床應用時可酌加雞內金、焦山楂、麥芽、山藥等健脾助運藥物。
4.3 心肝血虛證,養血祛風以治其形,補養心肝以治其神 患者年高或久病陰血內耗,心肝血虛,脈道凝滯,內生風燥,癥見風團瘙癢色淡,日輕夜重,遷延不愈,勞累后加重,神疲乏力,心悸健忘,舌淡脈弦細。柯韻伯云:“治風者,不患無以祛之,而患無以御之,不畏風之不去,而畏風之復來。”對于本證,心肝血虛是病情遷延難愈的根本原因,治以補養心肝、養血祛風,使血旺則風自滅,方用當歸飲子加減,方中當歸、川芎、生地黃、白芍補血養血;何首烏補益精血;防風、荊芥穗、白蒺藜疏風止癢,黃芪、甘草益氣固表和中。熱盛加金銀花、連翹、知母;風盛者加僵蠶、地龍、全蝎;瘙癢甚加白鮮皮、地膚子、烏梅。
本證常因日久遷延不愈而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帶來社會及心理壓力,常見憂思抑郁,神疲寐差等癥狀,治神注重補養心肝、養血安神,常用藥物如酸棗仁、夜交藤、茯苓、茯神、大棗、丹參等。酸棗仁功擅補血調肝、寧心安神,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酸棗仁可鎮靜安眠、抗焦慮、抗抑郁等[16];夜交藤功擅養血安神、祛風止癢;茯苓、茯神功可健脾寧心,兩者伍用可達安魂養神,療五勞神傷之功;大棗功能補中益氣,養血安神;丹參功擅活血養血、養心安神,既能行血又不傷正,《滇南本草》謂其能“補心定志,安神寧心,治健忘怔忡,驚悸不寐”,現代藥理研究亦證明,丹參具有安神助眠、抗氧化、免疫調節等功用[17],氣虛者可伍生黃芪、太子參益氣養血。
5 結語
CU是一種復雜的身心性皮膚病,具有復發性、遷延性和難治性的特點,其發病與情緒因素密切相關。基于中醫學形神一體觀理論,本病屬于形神共病,其表現在外的丘疹風團,即為有形可見的“形病”;其瘙癢難耐導致的煩躁、焦慮等情志異常改變即為CU之“神病”。二者相兼出現,互為因果,因此辨治CU時應注重“形神同調”。CU病因復雜,但發病關鍵在于氣血失和,而心主血脈,肝主疏泄、藏血,心肝同調氣血,是為“調形”的理論基礎;此外,心主神明,肝主情志,心肝共調情志,是為“調神”的理論基礎。因此防治CU的關鍵在于維持心、肝的生理功能正常,保證體內氣血調和、神和志安,治以治肝養心,調形安神。對于心肝氣郁者,治形重在疏肝理血,治神重在解郁寧心;對于心肝火旺者,治形重在清心平肝,治神重在除煩潛鎮;對于心肝血虛者,治形重在養血祛風,治神重在補養心肝。除藥物治療外,臨床中還應注重對患者的心理干預,身心同治以充分發揮中醫的優勢,提高臨床療效,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和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