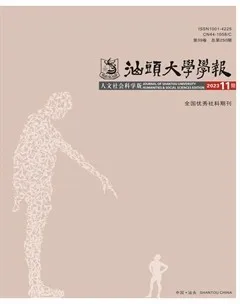“由法而象”客觀解釋原則的演變
——一種對漢易象數(shù)之學發(fā)展邏輯的解釋
王 棋
(中國礦業(yè)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周易》的形而上理論與言象意關(guān)系問題密切相關(guān)。漢易無論占筮派還是注經(jīng)派都未把后者作為基本問題,直到王弼玄學易把意與言、象作形上形下本末關(guān)系的對待,言象意關(guān)系問題才成為易學基本問題。三國時期,五世家傳孟氏易的虞翻對家學法則既有堅持,又做了部分改動,和兩漢諸家易學尤其是和東漢末年鄭玄、荀爽費氏易注經(jīng)一派相綜合,完成兩漢象數(shù)易學的全面總結(jié),將注經(jīng)派推向鼎盛。西漢宣帝時期孟喜創(chuàng)立的孟氏易,是占筮派初始形態(tài)。該派研究象(包括《周易》之象和《周易》之外災異之象)的變化規(guī)律,與神學解釋、政治解釋相結(jié)合,以技術(shù)操作和占驗應用為主要內(nèi)容。發(fā)展至虞翻,有了很大變化,關(guān)注點由象轉(zhuǎn)向象辭關(guān)系,象數(shù)解釋轉(zhuǎn)而與語言解釋相結(jié)合。在這一轉(zhuǎn)變中,鄭玄、荀爽是推動象數(shù)易學神學化、政治化向象數(shù)易學理論化、學術(shù)化轉(zhuǎn)型的重要人物。虞翻做了重要發(fā)展,成為象數(shù)易學理論化、學術(shù)化轉(zhuǎn)型與成熟的集大成者。虞翻著意聲稱所傳易學有孟氏家學淵源,表明他的注經(jīng)派與占筮派有著密切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那么,虞翻所傳家法以及所做的的改動,對漢易重心由占筮派轉(zhuǎn)移至注經(jīng)派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虞翻是如何完備注經(jīng)派象數(shù)易學方法論的解釋理論,卻又受著怎樣的限制而膠著于言象層面,不能升入義理易學形上層面的呢?回答這些問題,從“由法而象”客觀解釋原則的演變,我們不難看到漢易象數(shù)之學的發(fā)展邏輯和內(nèi)在實質(zhì)。
一、占筮派象數(shù)易學解釋的客觀原則
占筮派象數(shù)易學確立解釋的客觀原則,并不是從解釋學的基本問題文本和理解的關(guān)系來說的。即不是從解釋者和解釋對象的關(guān)系來說的,而是從解釋者和解釋目的、解釋要求來說的。不同于先秦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為核心的解釋觀念,將合乎作者和文本原意、樹立客觀原則作為對文本理解的首要的基本要求,西漢董仲舒發(fā)起了一場與神學解釋、政治解釋相結(jié)合的解釋觀念的革新運動,提出了詩無達詁的新見解,倡導多元化解釋與主觀原則。儒學由此進入經(jīng)學時代,迎來經(jīng)學的繁榮。董氏的解釋主張反映了西漢初期五經(jīng)諸領(lǐng)域派別林立的實際狀況和發(fā)展需要。從解釋方法看,僅易學就有多個派別分門立戶,陳述紛紛。易學派別中“曰訓詁舉大義,周、服、王、丁、蔡、韓七家易傳是也;曰陰陽候災變,孟喜、京房、五鹿充宗、段嘉四家易傳是也;曰章句守師說,楊何、施、孟、梁丘、京五家所立博士以教授是也;曰彖象釋經(jīng),費直、高相兩家,民間所用以傳授者是也。”[1]113
學術(shù)界和官方堅信王道政治是出于正統(tǒng)學術(shù)思想的影響而非異端學說的蠱惑,故而競相爭鳴的易學各家,只有歸入師法門戶才能得到官方與學界的共同認可。當時引領(lǐng)易學主流的是官方孟京一系的占筮派章句易學。而以彖象釋經(jīng)的費直易學,作為惟一一家使用古文字的古文易,盡管文本內(nèi)容完整,也完全合乎《易傳》的解釋理路,在堅守儒門易學正統(tǒng)上,有超越官方易學的優(yōu)勢,但是費氏易學致命的不足是有本無師,不具備立于學官的師法條件,只能一直在民間流傳。兩漢各派易學想要躋身官方的學術(shù)格局,師法、家法是立足的基礎(chǔ)。東漢承襲西漢易學的師法,重點在不同家法的盛行上。占筮派象數(shù)易學孟京一系從宣帝時期至東漢末年政權(quán)結(jié)束三百年左右的歷史中,一直是在師法的框架下衍生眾多家法,基本不出法的藩籬。東漢象數(shù)易學沒有值得稱道的理論建樹,法的限制是根本原因之一。
師法、家法是決定易學派系正統(tǒng)性的至為關(guān)鍵的因素和條件。在西漢沒有師法,在東漢沒有師法下形成的家法的話,是很難立足學界的。占筮派象數(shù)易學打破了已有的師法,樹立了《周易》與占筮數(shù)術(shù)結(jié)合的新師法。孟喜是占筮派變革師法的始作俑者。孟喜做出易學創(chuàng)新時,正值“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孟)喜改師法,遂不用喜。”[2]1033原因是“沒有本師,而多反異,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3]404故而托于孟氏易,又得隱士之說的“《京氏》雖立,轍復見廢。”[3]404孟京易學立于學官,都因改師法而有曲折。當他們進入官方承認的師法譜牒體系,孟京占筮派形成新的師法,并將師法、家法客觀原則作為學派立身發(fā)展的基石。
象數(shù)易學上占筮派的貢獻是提出了從象出發(fā)、于象言理的象數(shù)解易的思維與模式。占筮派在著述形式上采用了不同于傳、記、說的章句形式,為他們構(gòu)筑象數(shù)易學理論形態(tài)提供了極大便利。自“宣帝時興起的章句之作,即是‘離章辨句’,將一篇分為若干章,再將一章分為許多的句子,逐章逐句進行解釋。如果說傳記往往是通論經(jīng)書的大義,幾乎像是獨立的著作,那么章句便是拘泥于經(jīng)書的各個局部,完全像是經(jīng)書的微不足道的附屬品。”[4]69章句形式雖有“破碎大道”之嫌,但較之用傳、記、說的形式“為學疏略,難以應敵”的不足,章句形式的優(yōu)勢在于為學更為細密,能與傳、記、說形式的經(jīng)學學術(shù)相抗衡。今文《尚書》學小夏侯之學的開創(chuàng)人夏侯健解經(jīng)“牽引以次章句”[2]928,到他的再傳弟子秦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既然利用章句形式,可以擴充內(nèi)容,那么利用這種形式引入新說,改變師法也未為不可。今文易孟京一系正是從積極的方面利用章句形式,炮制“《易經(jīng)》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2]591,孟京之作占三分之一。目的是以神學解釋來為政治解釋服務,把陰陽與災異、與數(shù)術(shù)結(jié)合,將《易傳》義理為主的解易路子改為象數(shù)為主解易路子。我們稱這是占筮派師法、家法的內(nèi)容與特征應該沒有問題。從文本和理解的關(guān)系角度看,占筮派象數(shù)易學有著偏重解釋的主觀性的顯著特點。這不是說它沒有解釋的客觀原則。占筮派解釋的客觀原則不是來自于文本的易辭部分,我們應從漢易師法、家法及其創(chuàng)立的象數(shù)易學思維模式來認識。
漢代新興起天人感應思潮就其宣揚天命、神學信仰的性質(zhì)而言,它與《周易》保留的神學思想成分沒有實質(zhì)區(qū)別。倒是占筮派利用科學與神學、陰陽災異與占驗數(shù)術(shù)的結(jié)合,使得易學呈現(xiàn)出象數(shù)新特征,開啟了易學的象數(shù)新形態(tài)。孟喜作為占筮派的開創(chuàng)者,“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將陰陽家建立災異與陰陽關(guān)聯(lián)的思維引入易學解釋。孟氏易著早已亡軼。從《周易集解》輯錄孟氏一則使用了災異論的注文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孟氏易的神學解釋傾向。孟氏的這則注文是針對《豐·上六象》“豐其屋,天際祥也”而寫的。孟氏的注文是:“天降下惡祥也。”[5]698考察經(jīng)史文獻,“《昭十八年·左傳》‘鄭之未災也,里析曰將有大祥’。《漢書·五行志》‘妖孽自外來謂之祥’。是‘祥’亦惡征也。天‘際’猶降也。故曰‘天降下惡也’。”[5]698足見孟喜直接運用災異論注《易》的基本路數(shù)。這在當時易學界田何傳易譜系看來,的確是特立獨行,開風氣之先了。孟喜的新法不乏一批追隨者。“蜀人趙賓……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者,萬物方茲也。’……‘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學。”[2]1033一般人們認為《周易》中的箕子一詞指的是歷史人物,而不是把它拆成兩個字,指稱陰陽變化的某種情態(tài)。孟喜將陰陽和災異結(jié)合,改造易辭的內(nèi)涵,朝著災異數(shù)術(shù)的方向做解釋,顯然是出于迎合天人感應神學思潮的理論需要。
與《易傳》淡化天命神學的人文路向不同,為配合經(jīng)學用災異論干預政治,孟氏開創(chuàng)的占筮派吸收天文歷法大量科學知識,用來勾勒宇宙圖式,闡釋掌握天人感應神學原理的陰陽數(shù)術(shù)技術(shù)操作路徑,有著建立象數(shù)易學師法、家法客觀原則的考慮和目的。京氏創(chuàng)造了八宮象數(shù)體系,給宮內(nèi)每一卦附上五行五星、納支納甲、建候積算等象數(shù)形式,建立了發(fā)達完備的技術(shù)操作系統(tǒng)。京氏易的重點鮮明地集中在預決吉兇的筮法體系上,“絕不詮釋經(jīng)文,亦絕不附合《易》義”(《四庫全書總目·京氏易傳》提要),在解釋的主觀性這一方面,京氏較孟氏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京氏從《周易》本文易辭抽繹出“乾坤,陰陽之根本”重要命題,但又不是合著《序卦》乾坤首、既濟未濟終的卦序,而是按照宮卦卦序、卦氣卦序闡發(fā)新義。京氏易甚至把《周易》經(jīng)文編入新的占文,如“‘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無子。”“‘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震,遂泥’,厥咎國多麋。”[6]186-191等等。思路上京氏透過卦象推測天時人事,以“究災異之深旨,導政教于正路”(徐芹庭語),滿足政治對于象數(shù)占驗手段的技術(shù)需要,形成和《周易》本文不同的易學理論體系。京氏易學派在東漢傳承人數(shù)最多、規(guī)模最盛。其著力回答的是天人感應的象數(shù)途徑問題。圍繞這一問題孟京一系形成象數(shù)解易的思維模式與基本特征。作為孟京之學的發(fā)展,《易緯》雖然傍依經(jīng)文,通論大義,表現(xiàn)出對文本一定程度的重視,對孟京偏重主觀解釋的做法予以了一定的修正,但從整體來看,《易緯》在神學解釋的路子上走得更遠。
此處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占筮派將象數(shù)易學與神學、科學相結(jié)合的同時,減少了哲學內(nèi)容。西漢末年“劉向以中古文易經(jīng)校施、孟、梁丘《經(jīng)》,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jīng)與古文同。”[2]591儒家經(jīng)典中唯有《周易》作為卜筮之書幸免于秦火的浩劫,施、孟、梁三家脫漏的“無咎”、“悔亡”似應是《周易》傳文里的文辭。《周易》傳文從德義層面來講吉兇轉(zhuǎn)化的哲理,即使《象》篇給出象數(shù)上的依據(jù),目的也是闡釋“無咎之道,存乎能悔,悔則無咎之所由無,而過之所由補者也。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善補過。’”[5]796《周易》的“無咎”“悔亡”之道既內(nèi)在又超越,神道設(shè)教只是一種手段與形式。西漢師法森嚴,今文易各家脫漏“無咎”“悔亡”重要文辭,應是各家?guī)煼▌?chuàng)立時有意而為,便于將《周易》哲學引向天人感應的神學信仰,也便于占筮派擺脫田何一系易理哲學的制約,發(fā)展出所謂的“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3]360的神秘象數(shù)系統(tǒng)。
據(jù)此我們推測,占筮派在創(chuàng)立學派的時候改動師法,摻入主觀解釋成分,但新的師法、家法一經(jīng)形成之后便被確立為客觀原則。占筮派對六十四卦卦象的研究,并未采用《周易》卦序,而是編制了卦氣卦序、八宮卦序新卦序。從近處說,占筮派的師法、家法并不合乎漢初田何祖師易理易學切近人事的路子。但是從古代易學的歷史演進看,占筮派的卦序以乾卦為六十四卦之首,它應屬于《周易》解釋系統(tǒng)而非《連山》《歸藏》以艮卦、坤卦為首的易學解釋系統(tǒng)。古代易學相繼演變《連山》《歸藏》和《周易》三種不同形態(tài)。三易呈連續(xù)性的發(fā)展,彼此并非斷裂的關(guān)系,研究的都是六十四卦,卦數(shù)與卦形完全相同。用宋代朱元升的話來說,三易“其作用雖異,其為道則一太極也。”[7]807占筮派把三易的象數(shù)共性作為新理論的生發(fā)點,暗含占筮派試圖追溯《周易》之前古易演化的源頭,為其改變《周易》筮法、創(chuàng)立新筮法尋找歷史依據(jù)。占筮派試圖打破不同時代易學視域歷史界限,將新筮法的研究視域與形成六十四卦卦象的上古視域融合成效果歷史。《易緯》既構(gòu)設(shè)了宇宙起源于太易,由無入有的演化生成圖景,又用神學思維設(shè)想了上古之《易》向夏商周三代的發(fā)展譜系①鄭玄認為三易的源頭是上古之《易》。《易緯·乾坤鑿度卷上》設(shè)想了其傳承譜系:“太古百皇,辟基文籀。遽理微萌,始有熊氏(鄭玄注:庖犧氏,亦名蒼牙也)。……息孫,而后傳授天老氏,而后傳授于混沌氏,而后授天英氏,而后傳無懷氏。而后授中孫炎帝神農(nóng)氏,……而后傳烈山氏,而后授三孫帝釐氏,次授老孫氏(鄭玄注公孫氏,軒轅氏)。”繼后“公孫氏。《周易》。”(《易緯·乾坤鑿度卷下》)鄭玄注“公孫氏”曰:“老孫氏,名軒轅,文法改籀篆,理文作契,典墳、八冊、九簡、十牘,咸易變大道之理,法一依上。”鄭玄注“《周易》”曰:“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圣教多難,至孫公之后,……又失其化教源,……至高辛代,……后少求于高崗,得河圖,內(nèi)有易法,而重修,再降大圣,易大行。又距大禹代湯,……而于泰穴得洛書,內(nèi)有《太易》。易之源流,大易既行者,今之《連山》《歸藏》之名”。見林忠軍《〈易緯〉導讀》,齊魯書社2002年版,第113 頁,第136-137 頁。,正體現(xiàn)了占筮派易學力圖通過獲得官方認可的師法、家法與古代傳系的對接,使得災異數(shù)術(shù)象數(shù)易學形態(tài)進入中華易學的創(chuàng)造歷史與智慧文明。占筮派象數(shù)易學確立解釋的客觀原則,有著重要的易學史、學術(shù)史意義。那么,注經(jīng)派象數(shù)易學確立象數(shù)解釋的客觀性原則又是出于何種考慮,有著什么意義呢?
二、注經(jīng)派象數(shù)易學確立象數(shù)解釋的客觀性作為重要的解釋學依據(jù)
前文已述,在漢易眾多派別中,占筮派象數(shù)易學之所以與訓詁舉大義、彖象釋經(jīng)其他治易路數(shù)區(qū)別開來,師法、家法具有根本意義,法是不同派系門戶彼此筑起壁壘的主要工具。東漢末期以鄭玄、荀爽、虞翻為代表的注經(jīng)派突破法的限制,作不同門派師法、家法的綜合與超越。盡管鄭荀虞學派傳承有所不同,鄭玄、荀爽是古文費氏易的重要傳人,虞翻家傳今文孟氏易學,但是他們都走向了今古文兼治的象數(shù)易學,并以費氏易以傳解經(jīng)的原則作為共同遵循的解易原則,形成在治易理念、原則與方法上基本相同的注經(jīng)派象數(shù)易學。在以傳解經(jīng)原則下,鄭、荀并沒有沿襲《周易》大傳義理解易為主的解易方向,否則形成不了象數(shù)易學理路與特色。虞翻也沒有抱守孟氏易災異論師法、家法原則。占筮派象數(shù)解釋所遵循的師法、家法的客觀原則尤其是經(jīng)過荀、虞注經(jīng)派的改造,陰陽災異的思想原則被大大弱化,而以象數(shù)為根本的思想原則則得到凸顯。注經(jīng)派以注經(jīng)為目的,由關(guān)注易象轉(zhuǎn)向關(guān)注象辭關(guān)聯(lián),象辭關(guān)聯(lián)的邏輯預設(shè)必然會提出這一要求。
除了鄭玄易學的神學成分比較明顯外,荀爽、虞翻的易學重心都已經(jīng)不是神學的象數(shù)易學,都轉(zhuǎn)向了哲學的象數(shù)易學。明顯的一點是,三家解易的文體形式變化,不再用章句文體。荀爽匯通儒家經(jīng)典,尤精于易學經(jīng)義的新闡發(fā)。荀爽采用傳作為解經(jīng)文體,字面上傳有符信的意思,荀爽“為經(jīng)做傳,既出于向后學解釋經(jīng)意的需要,也由于對經(jīng)文的理解出現(xiàn)歧義,要從紛紜眾說中尋出正確的解釋。”[8]5今古文易的合流中,對比不同易學家的解釋,解釋的客觀性更多的是來自文本的客觀性,而不是來自師法、家法的限制。為了合乎文本原意,“鄭玄發(fā)明出一種箋注的體裁,‘注’的意思是灌注,注文好比是水,經(jīng)文有疑問的地方好比是縫隙,將注文夾在經(jīng)文之間就像往有縫隙的物件中間灌水一樣。這種箋注體是前所未有的。其拘束、古板、抱守的性格較之章句尤甚。”[4]70-71虞翻也采用注這種文體,沿著易學解釋箋注方向的發(fā)展,意味著對思想自由闡發(fā)的束縛。注經(jīng)派由占筮派關(guān)注易象轉(zhuǎn)向關(guān)注象辭關(guān)聯(lián)構(gòu)成的文本整體,將易學解釋的基本問題落在了文本與理解的關(guān)系問題上,注經(jīng)派以文本作為客觀解釋的重要尺度。挖掘文本內(nèi)涵的象數(shù)元素,構(gòu)建象辭之間的媒介,是注經(jīng)派尤其是荀虞做到客觀性解釋的重要依據(jù)。相較于占筮派,注經(jīng)派對文本的客觀性以象數(shù)的根本性、客觀性和象數(shù)解釋的根本性、客觀性表現(xiàn)出來。
鄭、荀、虞三家將《易傳》并不占第一位的象數(shù)解易方法大大做了提升,超越原本第一序的義理解易方法,使之成為解釋《周易》文本首要的、基本的方法,是以象數(shù)的根本性、客觀性為理論前提的。鄭玄論證象數(shù)的根本性,著名的是在宇宙論上,他論易數(shù)早在天地未形成之前就已經(jīng)同理、氣一起作為宇宙演化的根源。鄭玄還從易學源流演變的歷史角度探尋象數(shù)解易方法的根本性。鄭玄論述道:“《系》曰:‘爻效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其質(zhì)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9]83鄭玄解易有以象解易、以禮解易、以史解易、以訓詁解易諸多方法。鄭玄推崇夏商兩代易學占筮不變的易學原則,并把此原則與周代禮制一并納入他的象數(shù)易學,與思想史關(guān)于易象與禮關(guān)聯(lián)的文化思維基本一致。不同于鄭玄的論證角度,虞翻從自然界象數(shù)的先在性來論證易學象數(shù)的根本性、客觀性,進而賦予象數(shù)解釋方法根本性、客觀性。
《系辭上》“于是始作八卦”,虞翻注釋此“謂庖犧觀鳥獸之文,則天八卦效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乃四象所生,非庖犧之所造也。故曰‘象者,像此者也。’則大人造爻象以象天卦可知也。而讀易者,咸以為庖犧之時,天未有八卦,恐失之矣。‘天垂象,示吉兇,圣人象之,’則天已有八卦之象。”[5]898
這是虞翻關(guān)于八卦卦象來源的一段經(jīng)典論述。文中虞翻從《易傳》“庖犧觀鳥獸之文”的說法引出“八卦效法天卦”的思想。此為宋易畫前之易、自然之易思想的先聲。既然《周易》六十四卦卦象是由效法天象的八卦卦象按照相重組合的規(guī)則排列出來的,那么將六十四卦歸約為八卦卦象,追溯到自然之象也是合乎邏輯的。自然之象是客觀的事實,八卦之象是人們認識的結(jié)果。虞翻從自然之象的客觀性推出八卦之象也具有客觀性,解決八卦卦象的來源問題,繼而將象數(shù)本原論轉(zhuǎn)向象數(shù)認識論,運用八卦取象建構(gòu)六十四卦卦象系統(tǒng)邏輯規(guī)則。虞翻由此將以意逆志的解經(jīng)原則具體落實為從象數(shù)出發(fā)推明文本之意,把象數(shù)解易的方法確立為根本方法。進而言之,八卦卦象在六十四卦卦象變動中占有中心地位。從六十四卦卦象找出震兌坎離四卦象,象征春夏秋冬;找出乾坤坎離四卦象,象征天地日月。虞翻根據(jù)前者樹立了消息體例,根據(jù)后者樹立了月體納甲體例。虞翻象數(shù)易學的兩個重要的理論支柱消息說和月體納甲說就這樣立起來了[10]84。
在自然界,天地日月之道是由天地日月運動變化之象生發(fā)出來的宇宙根本原理。虞翻用八卦思維來治易,基本思路就是認為八卦卦象對天地日月之象的模仿,六十四卦卦象做了擴展,卦爻辭所蘊含的天地日月之道從六十四卦卦象中均能找到相應的八卦卦象作為象數(shù)依據(jù)。虞翻批評前人不得此象數(shù)易學精髓,“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jīng)!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11]1322虞翻自云五世家傳孟氏易,但與孟氏易災異數(shù)術(shù)的象數(shù)易學有著顯著區(qū)別。虞翻否定了孟氏易的災異數(shù)術(shù)思想,突出了象數(shù)原則,并做了發(fā)展。
恰巧虞翻注豐卦的文辭流傳下來,與前文所引孟氏注文可作對比。虞翻注豐卦上六爻爻辭“豐其屋,蔀其家”剔除了災異論,改為象數(shù)分析。虞翻曰:“豐,大。蔀,小也。三至上,體大壯,屋象,故‘豐其屋’。謂四五已變,上動成家人。大屋見則家人壞,故‘蔀其家’。與泰二同義。故《象》曰:‘天際祥’,明以大壯為屋象故也。”[5]696虞翻認為豐卦的三四爻互體成大壯卦卦象。大壯卦象征屋宇(《系辭下》提出觀象制器說,例舉古人仿照大壯卦建造宮室)。爻辭“豐其屋”的“屋”字即是根據(jù)大壯卦卦象得來的。虞翻此處由象解辭,對文辭的解釋對不對,是不是合乎文本的意思,判斷標準在文本自身。費氏易以傳解經(jīng)。虞翻認為《豐·上六小象》之所以曰“天際祥”,就是根據(jù)大壯卦卦象上震下乾,“乾為天,震動為祥”,合起來得出的。這樣,虞翻在解釋實踐中對孟氏師法、家法原則做了部分改動,拋棄了以陰陽災異解易的原則,代之以由象解辭,由辭證象,作象數(shù)推演,將占筮派象數(shù)解易的師法、家法原則做了發(fā)展。虞翻回到文本自身來說解釋的客觀原則,恢復了易學解釋的基本問題是文本和理解的關(guān)系問題。虞翻肯定了用象數(shù)解易方法的合理性、必要性在于它合乎《周易》文本的理性思維,符合象數(shù)易學解釋的客觀原則。虞翻以此糾偏神學易學非理性的神秘主義傾向,與漢末反讖緯、反神學的社會批判思潮相呼應,在易學史、思想史上的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根據(jù)前述分析,本文推斷虞翻自云五世家傳孟氏易,主要指他傳的是孟氏象數(shù)解易的原則,而不是神學解釋原則。虞翻批判兩漢諸家易學,用的即是他闡發(fā)的象數(shù)解易原則。虞翻精于訓詁,但是在易學解釋中他明確地把象數(shù)解釋作為突出《周易》特點的根本途徑,作為實現(xiàn)解釋的客觀性的基本路徑。以八卦思維為特征的象數(shù)解易在虞翻易學中占據(jù)綱領(lǐng)性的關(guān)鍵地位。虞翻樹立的象辭觀以易象為重點,象辭的關(guān)系展開為辭由象出,于象言理,由易辭回溯易象。虞翻甚至認為凡辭皆有象的依據(jù),找出與辭對應的易象,即能建立大而全的象辭解釋系統(tǒng)。虞翻的象數(shù)方法論雖然樹立起象數(shù)解釋的客觀性原則,但是也衍生出來另一面解釋的主觀性與之相對立。這對矛盾構(gòu)成了象數(shù)易學解釋理論自我難以克服的內(nèi)在張力。
三、注經(jīng)派象數(shù)易學解釋理論的自我否定
解釋循環(huán)是關(guān)于解釋文本整體與解釋文本部分二者關(guān)系的一條重要解釋原則。既然“個別只有通過整體才能被理解,反之,整體只有通過個別才能被理解”[12]9“一切理解和認識的基本原則就是在個別中發(fā)現(xiàn)整體精神,和通過整體領(lǐng)悟個別。”[12]7解釋循環(huán)指涉解釋是從整體入手還是從局部入手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如果說占筮派從文本的易象部分入手,回不到文本象辭整體,存在解釋循環(huán)的障礙,那么注經(jīng)派改為從文本整體入手,但建立象數(shù)體例時,一種體例并不能貫通文本的各個部分,往往需要多種體例配合使用,也同樣存在著解釋循環(huán)障礙。這是鄭、荀、虞三家注經(jīng)的一大弊端。在虞翻那里更是膨脹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正如王弼所批判的,象數(shù)易學解易,“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從復或值,而義無所取。”[13]609
《周易》大傳建立哲學原理,以義理為主,兼顧象數(shù),把占筮與哲學做了結(jié)合,引發(fā)了象數(shù)與義理的矛盾。對此,《周易》大傳的處理是,令象數(shù)服從表現(xiàn)義理的需要,沒有限制多重義理的展開。而鄭、荀、虞三家注經(jīng)派使用象數(shù),以象數(shù)作為出發(fā)點,把象數(shù)意義作為易辭根本意義的同時也限定了易辭的意義內(nèi)涵只能局限于象數(shù)層面。象和辭的關(guān)系是辭從象出,象由辭回溯逆推。注經(jīng)派關(guān)于象和辭的這種封閉性解釋,實質(zhì)是另一種解釋循環(huán)。它是造成注經(jīng)派的解釋象辭背后象外之意缺位的重要原因。虞翻易學的這種傾向尤其嚴重。形式上虞翻解釋的是易象和易辭兩個部分,實質(zhì)是建立易象解釋系統(tǒng),解釋易辭的任務又歸結(jié)為解釋易象。因為他把辭的內(nèi)涵限定為象數(shù)內(nèi)涵,排除了易辭的其他多種意義。早在荀爽、鄭玄開創(chuàng)注經(jīng)派的時候就有這種缺陷。以荀爽為例。他注釋《夬·彖》“其危乃光”曰“危去上六,陽乃光明。”[5]554他注釋“道未光也”(《晉·上九象》)曰“陽雖在上,動入冥豫,故道未光也。”[5]476觀魏晉易學家干寶注釋“其危乃光”曰“德大即以心小,功高而意下,故曰其危乃光也。”[14]54注釋《坤·象》“知光大”曰“位彌高,德彌廣也。”[14]77
比較漢代和魏晉的易學解釋,漢代易學家們所講的象數(shù)理法、名物訓詁并不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義理。李鼎祚一語道破鄭玄與王弼易學的不同,“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詮人事。”[5]21李氏概括漢易象數(shù)之學和魏晉義理易學區(qū)別即見于此,可謂切中肯綮,發(fā)人深思。漢易偏重象數(shù),確實不如魏晉易家闡發(fā)人事義理高明。一是注經(jīng)派主觀上謀求樹立揭示象辭內(nèi)在一致性的解易體例,而客觀上與經(jīng)相悖者卻比比皆是。孔穎達注《乾·九二》曾嚴肅批評爻辰體例不合經(jīng)文:“九五為建申之月,為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為建戌之月,群陰既盛,上九不得言“‘與時偕極’。于此時陽氣僅存,何極之有?諸儒此說,于理稍乖。”[15]11-12二是注經(jīng)派樹立象數(shù)體例力圖揭示卦象變化的某種系統(tǒng)性、規(guī)律性,但又時有違例,破壞象數(shù)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一致性。荀爽易學的升降體例人們認識起來較為困難,主要因為升降變動規(guī)則不一致。如坤卦的五爻降至乾卦的二爻爻位,這是坤五降乾二的法則。其余六十二卦,二爻以上的三四五上諸個爻是否都應降至二爻爻位,答案卻不一定。清人張慧言為此辯護說,這正體現(xiàn)了《坤·文言》地道無方之意。事實上,鄭玄、荀爽解釋活動中的牽強附會反過來恰恰說明,易辭與易象并沒有內(nèi)在本質(zhì)的、必然的關(guān)聯(lián)。
注經(jīng)派象數(shù)易學經(jīng)鄭玄、荀爽至虞翻登頂,取象體例愈多,選擇運用何種體例的空間就愈大,取象的主觀隨意性就愈強。比如《屯·六二》“女子貞不字。”虞翻注曰:“字,妊娠也。三失位,變復體離。離為女子,為大腹,故稱‘字’。”清人王引之批駁:“二至四互坤,坤為母,為腹,故有妊娠之象。……何必三變成離而后稱字乎。”[14]9-10王氏批評注經(jīng)派取象穿鑿附會、繁瑣冗雜背離了易簡的基本精神,何談合乎經(jīng)義。虞翻使用象數(shù)體例繁多,尚秉和先生認為主要用了旁通體例和之正體例。比如虞翻注《夬》“揚于王庭。”曰“夬與剝旁通。乾為揚,為王,剝艮為庭,故‘揚于王庭’矣。”[5]551虞翻注《系辭》“是故履,德之基也,”曰“乾為德。履與謙旁通。坤柔履剛,故‘德之基’。坤為基。”[5]950等等。卦爻辭重復是解易的一個難題。對此,虞翻從一處推出與易辭對應的易象,他便以此類推,認為其他重復之辭也對應此易象,可用他發(fā)明的旁通體例、之正體例取得這一易象。他用之正體例,比如他注《同人·彖》“利涉大川,乾行也”曰:“乾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5]229《蠱》“利涉大川。”虞翻注曰:此“謂二失位,動而之坎也,故‘利涉大川’也。”[5]287等等。《周易》經(jīng)傳反復出現(xiàn)的文辭“利涉大川”,在虞翻易學中就變成了尋找與之對應的坎卦之象。方法是令不當位之爻變當位,甚或令當位之爻變不當位,再變當位,特稱為權(quán)變。總之,虞翻的解易重點沒有放在辭義的哲學建構(gòu)上,而是通過豐富取象方法,建立龐大的象數(shù)解釋系統(tǒng)。
西方當代解釋學取得重大突破的大師利科對解釋方法的多樣性做了積極的肯定。但是他在申明這一立場時限定了條件,以解釋對象具有兩重或三層以上意義,而非單一意義為前提。利科主張解釋方法的多樣性并不針對科學研究,因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和答案是確定而客觀的,不能作為解釋對象。利科的意思很明確,在能從事解釋活動的領(lǐng)域,避免不了主觀性。這是西方自迦達默爾主導主觀原則、施萊爾馬赫主導客觀原則以來,利科在解釋活動的主客觀原則關(guān)系問題上的重要總結(jié)。依此來看虞翻所推崇的象數(shù)解易的客觀性,其又衍生出對立面象數(shù)解易的主觀性避免不了。二者構(gòu)成新的矛盾,加劇了象數(shù)易學內(nèi)在張力,埋下了象數(shù)易學自身難以克服的危機。受經(jīng)驗論思維的限制,注經(jīng)派象數(shù)易學是把象和辭的關(guān)系而不是言象意的關(guān)系作為注經(jīng)派的中心問題之一。哲學上看,象數(shù)解釋的方法論不向哲學本體論轉(zhuǎn)換提升,言象意的關(guān)系問題不可能得到認識和解決。王弼以形下形上區(qū)分言象意層次上的不同,樹立了以無為本的新原則,以儒道匯通的方式恢復了儒家象數(shù)服從義理的解易傳統(tǒng),進而建立了執(zhí)一統(tǒng)眾、崇本舉末的玄學義理解釋理路,徹底改變了象數(shù)易學形下層面棄本崇末的解易風氣,王弼正是抓住言象意關(guān)系基本問題實現(xiàn)玄學易本體論對漢易象數(shù)方法論的突破。宋代的理本論、象本論易學哲學都是在漢易象數(shù)方法論的基礎(chǔ)上把理象、道象關(guān)系問題置于形上形下的論域取得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綜上所述,考察漢代象數(shù)易學演變,我們至少了解了以下幾點。第一,占筮派是在打破師法的情況下形成的,在解經(jīng)內(nèi)容上沒有遵循與體現(xiàn)《周易》文本的客觀性,而是做了主觀性的發(fā)揮,有利于占筮派占驗災異,為天人感應論提供數(shù)術(shù)系統(tǒng),干預政治,以達到促使統(tǒng)治者施行德政的目的。但是占筮派又把師法、家法作為解釋的客觀原則,意在進入易學傳承的歷史體系,成為中華易學文明發(fā)展創(chuàng)造的一部分。第二,鄭、荀、虞注經(jīng)派突破師法、家法,作綜合和超越,使得占筮派師法、家法客觀原則的部分內(nèi)涵發(fā)生改變,回到易學解釋理論的基本問題文本和理解的關(guān)系問題,回到文本的客觀性上來。凸顯了象數(shù)在文本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文本的客觀性具體化為象數(shù)及象數(shù)解易方法的根本性、客觀性。虞翻建立了以八卦思維為突出特征的象數(shù)方法論的解釋體系。象數(shù)易學重心由占筮派轉(zhuǎn)向注經(jīng)派,繼鄭玄、荀爽開啟用象數(shù)體例注經(jīng)的模式,虞翻批判了孟氏易的災異數(shù)術(shù)思維,代之以象數(shù)思維、八卦思維,虞翻完備了象數(shù)易學方法論解釋體系。第三,象數(shù)易學神學解釋、政治解釋向哲學解釋轉(zhuǎn)向,虞翻做了總結(jié),但是在象數(shù)易學哲學建構(gòu)上虞翻并沒有達到理論學術(shù)的自洽。虞翻的象數(shù)方法論解釋學只是在言和象之間兜圈子,沒有真正進入形上論域論述言、象、意的關(guān)系問題。虞翻的象數(shù)方法論解釋理論盡管確立了象數(shù)解釋的客觀性,但是他們所理解的象數(shù)解釋的客觀性不等于取象方法的一元性。造成象數(shù)解易的客觀性與取象方法主觀性這對新的矛盾,構(gòu)成注經(jīng)派象數(shù)解釋的根本張力,加劇了象數(shù)易學內(nèi)部矛盾的激化,成為推動象數(shù)易學自我否定的直接力量。漢易象數(shù)方法論最終被魏晉義理易學取代,向易學本體論過渡有其理論發(fā)展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