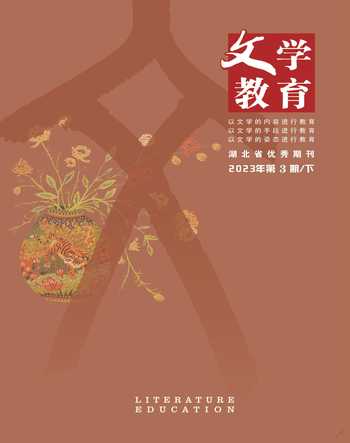自我認知下《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解讀
王雪菲
內容摘要:《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是擅長心理寫實主義的短篇小說大師茨威格的著作,通過信件的方式將一個女性癡迷愛戀的內心獨白袒露出來。陌生女人在她內心情感最激蕩的時刻回憶她的一生,通過對文本分析可以發掘出她自我認知形成、不斷修正最終在殉道精神中走向個體毀滅的全過程。因此,在自我認知視角下將其視為社會性動物,可以分析出核心的社會動機即歸屬、理解他人、控制、被重視和信任的需要如何形成人的自我認知,以及當認知失衡時,自我辯解如何進行調節使之達到再度平衡的。
關鍵詞:茨威格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自我認知 認知失衡 文本細讀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講述的是知名小說家R在生日當天收到一個陌生女人來信的故事。來信的女人自幼認識他愛慕他并多次設法與之相遇,卻最終在不被作家記住的絕望中,在與作家所生的孩子死亡的悲痛中離開了人世。作為傳頌世界的經典作品,《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研究,其中不乏從敘事學角度分析探討文本結構,在人物分析方面大部分研究主要從弗洛伊德的父愛缺失、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或者女性主義的角度入手。而主人公作為社會中的成員所采取的行動、選擇的人生道路,總是出于一定的社會動機,這也是造成人物悲劇的根源所在,因此從社會心理學視角對主人公自我認知的形成進行剖析能都更深層次理解人物的掙扎、體會作品的魅力,具有一定的人文價值。
自我認知理論隸屬于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范疇,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皮亞杰、哈特曼等心理學家都有著不同的理論成果。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埃利奧特·阿倫森在此前的研究基礎上發表的《社會性動物》,綜合介紹了人類行為的社會動機,以及社會動機對自我認知的塑造。“人類有很多普遍的生理生存需要,但我們也有某些基本的社會動機,塑造著我們的思維、情感和關系”[1]社會心理學視角下的認知理論對人類行為具有更強的解釋力,經過文本細讀,主人公的行為充分印證出社會動機對自我認知的塑造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一.自我認知的形成:懵懂的憧憬
在女主人公關于童年的敘述中存在著兩組對比:R先生出現前與出現之后生活的對比以及女人生存條件與R先生生活環境的對比。通過這兩組對比,女主人公將自己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與R先生掛鉤,R先生成為美好世界的象征。在《社會性動物》中埃利奧特·阿倫森介紹了核心社會動機,即“歸屬、理解他人、控制、被重視和信任”[1],它們塑造著人類的思維、情感和關系。在R先生身上,主角的這些社會性需要被滿足,因此個體圍繞著R先生構建起一整套自我認知體系。
根據主角的描述,遇到R先生之前,她的生活是拮據窮酸、寂寞無聊甚至惡劣緊張的。她的家庭并不富裕,父親的職位只是一個“寒酸的會計員”卻已英年早逝,留下母親與她相依為命,而母親也活得敬小慎微、深居簡出,她的成長伴隨的是孤獨和貧窮。除此之外,鄰居的不斷爭吵,男孩的不時欺負,讓她的生活充滿了不安全感。R先生的出現不僅取代了那戶制造混亂的禍首,還讓她見識到了一個內心向往卻沒有具像化過的美好世界。“你自己還沒進入我的生活,你的身邊就出現了一個光環,一個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圍”[2],禮數周到的高等男仆帶給她被尊重的體驗、異國的珍寶編織起關于遠方神秘的想象、大量精裝的外文書籍得到她的崇拜,由此被尊重的社會需求得到了滿足。同時她在第一次見到R先生時就洞察到他的矛盾感,淵博的學者與愛玩的冒險家兩種相反氣質在他身上完美交織,強大的張力對于她貧瘠的人生來說充滿著致命吸引力。這一發現讓她理解他人的需求得到了滿足,同時她也獲得了洞察的快感。隨后,一次偶然的相遇,“溫暖、柔和、深情,似乎是對我的愛撫”般的目光,讓主角體驗到被重視被愛的感覺,乏味的生活環境和充足的社會動機讓女人決定“我就完全屬于你了”,甘愿投入愛河。
主角用獻祭般的說法把自己放在了虔誠信徒的角色上,通過對R先生虔誠的愛使自己的行為也獲得一種神圣感,從而塑造自我的神圣形象。“那些多少有點變壞的女同學叫我反感,她們輕佻的把愛情看成兒戲,而在我的心里,愛情卻是至高無上的激情……你使我的生活整個變了樣”[2]通過將愛情提升至崇高的地位,女人的自我尊嚴得到滿足,于是追求愛情的行為也變得崇高。需要注意的是,這段話是女主人公臨死前對自己曾經行為的評價,并不是13歲的她當時的想法。她反觀自己一生的愛戀,別的女同學沒有這樣至死不渝,同時也沒有人對她這種癡迷的行為施加外力,因此她對自己的行為不斷進行著自我辯護,她告訴自己愛情本應該是這樣獻祭般的全心全意。她將自己的人生價值全部投射進來,通過奉獻自己更加佐證了自己對愛情的認識,在精神上獲得了一種神圣感。三年的偷偷單戀更是讓主角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R先生作為她對于美好世界憧憬的符號,通過觀察R先生,女孩仿佛也體驗了這樣的生活。
童年在主角對于美好的向往和追求無望的困境中結束,并對她造成雙重打擊:一方面主角想與R先生建立聯系,卻在現實中頻頻錯過;另一方面幼小的她不想離開維也納這個有R先生在的地方卻無力主宰自己命運。知道自己必須搬走之后,女主人公孤注一擲想見R先生,這是全書唯一一次女人主動想向R先生介紹自己的行動,離開R先生對當時的她來說無疑是信仰毀滅。同時這也是一次機會,一次得到R先生拯救的機會,于是被重視的動機驅使著年幼的她鼓起勇氣,一晚上的等待卻被R先生伴著女友回家的姿態狠狠擊垮了。在她的預期里,與R先生共處的場景應該是“跪倒在你的腳下…做你的奴隸”、是 “……緊緊地依偎在你身上”、是“撲在你腳下”,她準備好了一場誠摯的告白,而R先生放浪不羈的行徑打破了她認知中預先設定,情況的失控和尋求歸屬感的失敗對她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創傷。在認知失衡理論看來,當人的行為使人受到傷害,而沒有外部原因解釋時,人們傾向于尋求內部原因,改變自己的觀念修正自己的認知以期重新達到平衡,主角的自卑感在行動失敗的打擊后更加強烈,于是在長大的相遇中再也沒有主動介紹過自己,只是期待自己被認出來。
二.自我價值的賦予:神圣感的建立
主角在因斯布魯克度過了孤獨的兩年青春時光,她強迫自己處于孤寂的狀態之中,生活在家人之中卻“感覺像個囚犯”。修道士般的苦行生活對她來說是一種自我價值的賦予,在忍受痛苦的修煉中感受到自我強大的意志力和不屈精神,從而獲得崇高感。“因為要我在腦子里想著和別人戀愛…稍稍動心在我看來就是犯罪”,主角的描述實際上說明和別人戀愛的念頭出現過她的腦海,只是不被她所容。她清醒的為自己安排著孤獨、封閉的生活,19世紀的女性還沒有足夠從事社會事務的權利,她們與社會聯系的方式便是婚姻,她們的自我價值大多來源于成為妻子或成為母親,愛情成為她們定義自我的途徑,這一觀念也符合社會奉行的女性美德,為她的執著提供強大的文化基礎。因此雖然她是為了心中神圣的愛情而踐行自己的信念,但實際上愛情在這里只是個符號,它是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象征著女主人公與世界的聯系。
她通過生活在孤寂中,用現實生活的單調乏味凸顯出與男人共處的時光美好。童年時期自己被強行帶走卻無可奈何,選擇孤寂也是對這種無能為力的反抗,是對自己生活重新控制的自我選擇。同時讓自己沉浸在相思的痛苦狀態,更是為了貼近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愛情理想,讓自己獲得了神圣感,從而實現自我價值。她正是通過折磨自己將自己構建成癡心女的形象,并不斷地加固這種自我認知。
這樣的自我認知構建在女主人公長大之后讓其陷入了更危險的深淵。她為了心中的愛情回到維也納與R先生相見,但卻不敢吐露心中的愛戀,甚至連自己曾經是他的鄰居都不敢聲張,表面上女人是認為R先生是個“喜歡輕松愉快、游戲人生、了無牽掛”的人,自己的愛情會把他嚇跑。但實際上女人連循序漸進的和R先生熟悉的舉動都沒有,她害怕R先生感到有負擔的心情是在害怕自己被R先生討厭,是在怕自己的整個世界也會隨之崩塌。由于童年時期想要袒露心扉的舉動換來的卻是她痛苦的記憶,敞開心扉的行為是她主動為之,但她的主動帶來了難忘的痛苦,所以此后她再也沒有向他透露過自己的信息,這也加重了她的悲劇。
擁有了和R先生血脈相連的孩子對于她來說是幸福的,然而惡劣的生育環境帶給她的只有痛苦。R先生是她為自己構建的世界中心,R先生的天性帶給她的是動蕩不安,而與R先生血脈相連的小生命卻給她的世界帶來了穩定,因此這個孩子的出生是一種救贖。更進一步分析,這也是她完善自己認知的新途徑,這個孩子的誕生構成了她世界的另一半,讓她不在沉浸于不被R先生認識的絕望中。肉體的痛苦更讓她產生了一種自己為愛獻身的崇高感。產科醫院的惡劣環境,不被尊重的痛苦經歷,讓她加深了腦海中的認知:她為了自己偉大的愛情甘愿受的苦,證實了愛情的神圣,她也因此顯得神圣。實際上這些苦痛的經歷是她的自尊心作祟讓她不愿回去求助父母導致的,但出于自我辯護的社會動機,這段經歷被她合理化為了佐證自己愛情觀的實例。
三.矛盾的話語:自我欺騙
信中有很多前后矛盾的話語,這些矛盾有些體現出女主人公思想的矛盾,也有些表現出她在不同人生階段發生的變化。從女主人公對R先生的心愿可以窺見,社會動機在主角自我認知形成的過程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在童年時期,女主人公有兩次真實的表露自己的心愿,第一次是在女主人公愛上R先生的瞬間“我以為,你的柔情蜜意只針對我,是給我一個人的”[2],實際上這是女主人公童年時期懵懂的心愿,是被重視被愛的渴望,是最真實的初心。第二次是女主人公被迫離開維也納的那晚,“想和你說說話”“我想跪倒在你腳下…做你的奴隸”這時R先生是女主人公期待的拯救者,她希望自己能留在她幻想的幸福生活的地方:R先生的身邊。
此后,女主人公的心愿和她的多次強調的“我不責備你”開始產生矛盾。“我一心只想遇到你……我希望你認出我是誰,希望為你所愛”這是她回維也納時真實的心情,而在兩人春風一度后,她等待R先生的聯系足足兩個月時,卻插入“我不責備你,我愛你就是你這個樣子……一往情深卻愛不專一”。前面的話是對R先生真正的心愿,這樣的心愿被辜負只能換來后面的自我欺騙“我愛的就是你的不專一”,這是不被重視、被辜負后的自我辯護。因為她腦海中的愛情已經從兩個人相互回應的想象變成了一個人的自我表演,這是將被遺忘被辜負的現實在腦海中合理化,對自己深愛多年行為進行的自我辯護。再回頭看她愛上R先生時的初心“……柔情蜜意只針對我,是給我一個人的”,“我不責備你”便更像是她壓抑自己的真實想法,只是為了通過守護心中愛情的光環,來證明自己追求愛情的生命不是個笑話,自己在忍受痛苦中也獲得了崇高,“我不責備”正是一場中毒太深的自我欺騙。這樣的自我辯護在文中還有很多,比如主角無意間將自己在環境惡劣的生育醫院所受的非人折磨與有丈夫被在身邊生孩子的婦女相對比,而后又補充“我并不抱怨你”。作為社會性動物,每個人都有與他人聯系的人性需要,愛情正是那個時代她與世界產生聯系的唯一方式。
主角將自己的生命價值與R先生相聯系,在心中構建起神圣美好的愛情信念,在此過程中不斷受苦更加佐證了她心中愛情信念的崇高,也讓自己的生命更有價值。但實際上面對不被愛甚至不斷被忘記的現實,她早已痛苦不已。她的自尊心根本接受不了她所自我欺騙的痛苦。雖然她說“……我這個小故娘都成了你的奴隸”“我在你面前…奴性十足”但當她在拋下一切與R先生歡愉一場,卻被他當做妓女時,她完全承受不了。“被你遺忘還不夠,我還要受得這樣的侮辱”,因此做奴隸這種想法其實只是為了標榜自己為愛情犧牲的程度罷了,她希望被尊重被愛的愿望其實沒有改變,她始終是一位自尊驕傲的女性。
最后她在臨死前還是決定將一切告訴R先生,但卻是以一種說故事的方式,并且仍然沒有告訴R先生自己的名字。她只要求R先生每年在生日的那天代替自己送一些白玫瑰,想象自己死后每年的那一天都像白玫瑰一樣陪著他,這實際上是希望R先生不要忘了她。同樣這份遺書也將她堅貞不渝的愛情袒露在了R先生面前,熾熱但不會灼傷他的愛會讓他對自己產生美好的印象,她想得到的尊重、被重視的需求將會得到滿足。她已經將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獻給她心中的信念——愛情,“可我已經不信天主……只相信你”像耶穌受難一樣,在這獻祭般的愛情中她也獲得自己人格的完善,實現了自己賦予愛情的崇高價值,在殉道精神中得到了自我滿足。
自我認知理論包括自我觀察和自我評價,埃利奧特·阿倫森從社學心理學的角度下手剖析個體對自我的認識,其中核心的社會動機是塑造自我認知的關鍵。陌生女人的愛情悲劇也是源于她從小就渴望得到的被重視、信任、控制、理解他人的社會需求,而R先生給她一種需求被滿足的錯覺。她通過這種錯覺中定義自己的人生,隨后即使看穿了這是錯覺也不愿脫身,這種對于痛苦的堅持給她帶來了獻祭般的神圣感,滿足了她自我認知的建設。通過至死不渝的追求無望的愛情她獲得了一種崇高感,在這種類似殉道的精神中走向了個體毀滅。
參考文獻
[1]埃利奧特·阿倫森,喬舒亞·阿倫森.社會性動物[M].邢占軍,黃立清,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2]斯蒂芬·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M].張玉書,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3]黃素麗.《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愛情悲劇探究[J].今古文創,2021(48):4-6.
[4]譚莉.畸形愛欲觀的特征——從變態心理學角度分析《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J].開封文化藝術職業學院學報,2021,41(10):45-46+54.
[5]魏倩茹.小說《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陌生女人的愛情觀解讀[J].散文百家(理論),2021(06):1-2.
[6]李志宇.從敘述視角探析《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J].大觀(論壇),2020(12):169-170.
[7]代穎.“知識付費”中的知識生產與消費現象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2020.
[8]李莉莉.論E·阿倫森的認知失調理論[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2):27-28+68.
[9]叢曉波.心理學的社會性回歸[J].東北師大學報,2003(06):12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