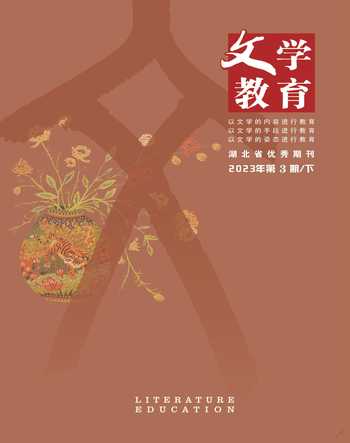梶井基次郎《檸檬》中的消費空間
袁依凡
內容摘要:《檸檬》一文講述的是,一個被不可名狀的憂郁侵襲著的青年終日游蕩在街頭,無所事事。隨后在水果店偶遇一顆顏色鮮艷的檸檬并為其感動,帶著給予自己力量的檸檬進入令人壓抑的書店后,利用檸檬建造了一個“城堡”并幻想檸檬變成炸彈炸毀了丸善書店的故事。《檸檬》的故事發生在京都的寺町大道。而大正時期的寺町大道、新京極大道與那時的東京銀座、淺草等具有相同的城市機能,也就是消費和娛樂的空間。因此本論文將從消費空間的角度分析《檸檬》中的空間,并進一步考察空間在本文中所具有的象征意義。
關鍵詞:梶井基次郎 《檸檬》 色彩空間 消費空間
一直以來對于作品《檸檬》的研究大多由文章開頭段落的“不可名狀的憂郁”所引發,圍繞肺炎、精神衰弱、不安、焦躁等精神和肉體上同時被侵蝕的狀況展開,并從中讀取“我”對一切超越性的價值,也就是“美”的追求。而大正時期的京都寺町大道、新京極大道擁有和如今的東京銀座、淺草同樣的城市機能——消費和娛樂的空間。這些空間在歷史的文脈里被再度構成,近代的形成也映射其中。《檸檬》一書則正是將其吸收進了“紡錘形的身體里”。小林秀雄在<文藝時評>中指出《檸檬》描寫了“近代知識分子的頹廢”,而作者梶井基次郎則是在文中直面并重新審視了“近代”。因此本論文將主要圍繞《檸檬》中空間的構成及其意義,以及探尋主人公“我”的意識變化。
一.梶井基次郎與肺結核
梶井基次郎于1901年生于大阪,1932年3月24日因病去世,短短三十年間梶井留下了二十多篇優秀作品,戰后曾與中島敦、太宰治被并稱“三神器”。其作品充分融合了感覺與知覺,通過簡潔且充滿詩意的描寫創造出了獨特的梶井文學,也讓梶井在日本文壇占了一席之地。1925年,梶井和友人共同創辦《青空》雜志,他便從之前記錄自己在京都憂郁心情的日記《瀬山の話》中抽出一篇《檸檬》作為獨立作品在青空首刊上發表。
在梶井的人生以及作品創作中,肺結核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自社會工業化以后,由于惡劣的工作環境,肺結核患者不斷增多,1918年肺結核已經成為日本死亡人數最多的一種疾病。日本有很多著名作家都曾患過肺結核,如夏目漱石、正岡子規、森鷗外、石川啄木等。而梶井接近一半的人生都在肺結核作斗爭。幼年幾乎都生活在在大阪這個工業都市的梶井目睹了多位親人因肺結核去世,而他自己也在17歲的時候出現了最初的征兆,并且在后來的日子里不斷反復并加重。
由于當時沒有專為肺結核病人設置的療養院,多數人只能在貧困和痛苦中死去,這樣的情況下,肺結核病人是被社會孤立的,也形成了梶井對社會的對抗意識。初期作品中,伴隨著病情惡化,可以看到主人公在與病魔對抗中痛苦憂郁的心情,檸檬就是其一。中期作品中,對病情的描寫逐漸變少,只有冬日這部作品中描寫了一些咳血的場景,這時梶井已經有些自暴自棄,只追求精神上的安寧,逃避現實。后期作品中,他開始接受現實,直面病魔,在資本論的影響下,他開始思考自身疾病以外的事物,如與他人的交流和社會的聯系等等,并描寫當時肺結核患者悲慘的生存現狀,如《悠閑的患者》。
二.《檸檬》中的消費空間
1.梶井基次郎的美學意識
在分析《檸檬》中的色彩空間之前,有必要介紹梶井基次郎的美學意識。關于《檸檬》的先行研究中,大多都是從色彩空間角度分析。主要涉及到色彩對比和明暗對比兩個方面,明暗對比來源于梶井的人生,色彩對比來源于美的意識,二者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幻想與現實共存的色彩空間。而在色彩空間研究中體現出的梶井的美學意識也為我們從消費空間分析《檸檬》提供了啟發。
梶井這一批學生接受過西洋藝術的教育,對西洋近代藝術、尤其是繪畫尤為關注。中谷孝雄曾說梶井生前非常喜歡看西洋近代的畫冊,他會一本一本地抽出來仔細翻看,但是又不會購買,在京都和大阪舉辦的相關展覽會,梶井幾乎都看了個遍。雖然梶井對繪畫和藝術有著濃厚興趣,但他認為重新開始已經來不及了,于是就放棄了這方面的念頭。而這樣一種對繪畫的興趣也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藝術作品具有外在性和內在性,作者創作時傾注的感情也會體現在作品中。而美要通過實際感受獲得而來,要用追求與內心一致。
梶井最喜歡的畫家是保羅·塞尚,曾經用這位畫家名字的日語音譯作為自己的筆名:瀬山極。這位畫家是法國后印象主義畫派畫家,主張不要用線條、明暗來表現物體,而是用色彩對比。在創作中一直主張要用圓柱體、圓錐體和球體來表現自然。采用色的團塊表現物象的立體和深度,利用色彩的冷暖變化造型,用幾何元素構造形象。其最大成就是對色彩與明暗具有前所未有的精辟分析,顛覆了以往的視覺透視點,空間的構造被從混色彩的印象里抽掉了,使繪畫領域正式出現純粹的藝術,這是以往任何繪畫流派都無法做到的,充滿了對近代的對抗意識。這些對藝術和繪畫的認識構成了梶井對于美的個人意識。
在檸檬一文中,梶井十分注重對色彩對比和立體空間的運用。而且相對于周圍的客觀事物,梶井更注重對個人精神和心理上微妙變化的描寫,對美的價值判斷注重視覺、聽覺、嗅覺等感官共同作用。他在日記里也曾提到塞尚的風景和被遺棄的房子兩幅作品,對此贊不絕口。檸檬文中提到這樣一段描寫:
“不知道為什么,我記得那時的我容易被外表美麗的東西深深吸引。比如說美麗卻破舊的街道,比起顯得生分的外街,我更喜歡能看到那些令人感到親切的晾著臟臟的衣物的房子的里街。還有那些仿佛訴說著被風雨侵蝕后快要回到土里的有旨趣的街道上,根基崩壞東倒西歪的房屋——只有植物生氣蓬勃,有時能看到讓人吃驚的向日葵,或者美人蕉。”(柴俊龍,連子心譯.2019)
2.《檸檬》中的消費空間
2.1無法逃離的“丸善”空間
檸檬寫于大正年間,而大正時期京都的寺町大道,新京極大道有著與東京銀座、淺草同樣的城市機能。是消費和娛樂的空間。而在《檸檬》里主要有丸善書店以及寺町大道兩個空間。首先關于丸善。京都的丸善書店如今依舊存在,但那已經是歷經兩次閉店搬遷后的三代丸善。小說檸檬則是以初代丸善為舞臺。
初代丸善于明治40年7月開店,地點為三條麩屋街西側入口處。主要販賣一些進口書以及文具、英國制造的t恤外套等舶來品。丸善與一般的書店不同,從開店起,丸善就以日本全國之繁榮為理想,在經營的同時還會支援福澤諭吉的活動。可以說在那時,所有有關文明開化思想的活動周圍必然會有丸善的身影存在。因此丸善在那時可以說是西歐文化、資本主義、文明開化等的象征。
在分析丸善這一空間時,主人公“我”對丸善態度上的轉變,成為我們分析的重要線索。曾經丸善是“我”最喜歡的地方,而如今“我”對丸善卻只覺得沉重壓抑。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對于丸善的態度發生了如此大的轉變。
文中的主人公“我”是京都第三高等學校的學生,對于“我”來說,丸善可以說是彰顯“我”的驕傲與特權的地方。價格高昂的藝術書籍,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原版書等舶來品,將一些能夠欣賞美的藝術的少數人聯結在一起。但對于現在的,被生活侵蝕的“我”來說,丸善卻只令“我”感到壓抑、如坐針氈。這是因為即便身患肺病、負債累累,“我”依舊有著對于美的追求,但卻不是從丸善,而是在破爛的街道中所感受到的頹廢的美。接下來本文將從消費空間的角度來看“我”對于丸善的態度發生以上轉變的原因。
消費空間是指在這一空間中,商品作為一種符號,擁有與本身的實用性不同的性質。人同樣在這一空間中扮演角色。文中寫到,“為了安慰看到錢時心動的自己,我還是需要一點奢侈的東西。”因此“我”曾花會上將近一個小時,只是看著丸善里陳列的小玩意,最后決定只買一只上等鉛筆。也就是,曾經的“我”通過這樣一種“奢侈“的消費來壓抑“我”在凝視這些閃閃發光的物品時所被勾起的欲望。
而如今,“我”意識到,“我”曾經在丸善享受到的并非是我真正所追求的唯美而高尚的美,而是昂貴商品的美,是集經濟價值于一體的美。“我”所凝望著的,也并不是真正的藝術,而是瓶身復印著藝術畫的香水瓶。也就是說,“我”于丸善所享受到的美只不過是被商業系統所制造出來的一般化的美。這種美以復制與金錢為媒介,任何人都能無數次地獲得。消費空間中的商品以及消費主體,在符號的意義上是共犯關系。而比起實際購買商品,“看”這一行為更能夠增添商品的光芒。
因此在商業系統中,美和藝術只是商人為了達成商品買賣的目的而復制在商品上的。被商品吸引視線的人也被卷入了這樣一種空間,在主體性上來說,他們并不是自律地存在于世界,而只不過是以一種人與物之間的互補性,作為構成消費空間的一個要素。可一旦這樣一種魔術般表演的幕后被曝光后,便仿佛能看到有亡靈漂浮。丸善令“我”不得不作為消費主體存在。琳瑯滿目的商品,排列著的購買者,交換的舞臺,這些仿佛都變成了要求“我”消費的亡靈。
書的開頭說到,“令我陷入這般糟糕境地的,不是因為肺結核或神經衰弱,也不是因為火燒眉毛的借款,而是那種不吉的感覺。”而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推斷:一直縈繞著“我”的不吉的感覺,不單單是因“我”所背負的借款,而是在“我”與那具有超越性的美的享受之間橫跨著如欠款之類的世俗的問題。“我”因疾病、欠款所崩壞的生活成為了一個契機,使得“我”意識到如今這種通過商業系統來進行美的享受的行為,已然將美的價值與經濟價值融為了一體。“我”雖然想要與這種一般性的、經濟性的東西保持距離,但它們反而會以美的形式呈現。讓“我”陷入不安狀態的,正是由于這樣一種想躲卻躲不開的現實。
2.2無處不在的消費空間
除了丸善外,《檸檬》中還有其他的消費空間。
當“我”在街頭徘徊時,喜歡走在里街。與其他的生分的外街不同,里街充滿著人類在這個世界留下的痕跡。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外街,也就是“我”購買檸檬的那家水果店所在的寺町大道。
寺町大道其歷史可追溯到平安朝時代,歷經多次重建改造,從明治時期起,有許多時髦的商店開始作為文明開化的象征出現,如西洋點心屋和照相館最早也是出現在寺町。前面也說到,消費空間里無法確保主體的主動性與同一性,因為在消費空間里的身體已然成為了消費構造的器官之一。因此“我”的身體對于支配外街的價值體系有著本能的排斥。而相反,走在小巷里“我”才能感受到自己真的存在于這個世界。
但是,“我”在水果店購買的檸檬很明顯是在外街售賣的商品,并且在當時的日本,檸檬、香蕉等水果都只有進口貨,屬于超高級水果。對于“我”這樣貧窮的學生來說買一個都是奢侈。“我”也并不是為了吃或是什么實際的,生活性的用途,而是“我”在這顆檸檬上感受到了我所追求的超越性的美。在這一點上,檸檬和丸善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性質。也就意味著“我”并沒有從所謂的商業系統總逃離。那么“我”為何依舊決定買下這顆檸檬?從消費空間角度來分析,“我”購買檸檬這一行為是舍棄了檸檬的使用價值而僅得到了交換價值,這也意味著“我”再一次進入了消費空間,并失去了自己身體的自律性。但在這里我認為檸檬象征著主人公“我”的一次嘗試。嘗試通過剝奪檸檬作為食物的使用價值,并且賦予它新的美的價值,從而與這個美化商品交換價值的世界產生新的關聯。
之前提到,將美通過商業系統進行商品交換的這一現實,將具有超越性的美與金錢等經濟的,世俗性的價值相結合,從而令追求純粹之美的“我”感到坐立難安。但是,這并沒有破壞美的超越性,而是將美的超越性原原本本的納入了商業系統中。構成這樣一種商業系統的,不是別的,正是這樣一種美的超越性,而即便我們再怎么強調這樣一種超越性價值,也無法從提供美的商業系統中逃離,更無法破壞,最后反倒只能支撐著它。因此,“我”在《檸檬》這部作品中所一直追求的幻象,正表明了“我”對于美的價值的強調無法與提供美的商業體系所匹敵,從而產生出的不滿。也正是在這樣一種無法逃離的、無盡的循環中,最終令“我”產生了以丸善的的美術書架為中心發生大爆炸的幻想。這一幻想也表明了“我”對于打破這場循環的愿望。
《檸檬》作為梶井最初的作品,基本指明了梶井文學的性格。并且在檸檬之后梶井的作品愈加黑暗。在加速發展的日本近代化下,經濟飛速發展的另一面,有無數的人為貧窮和病痛的困擾,這也成為梶井后來被《資本論》所吸引的原因,也成為了梶井最后創作《悠閑的患者》一書的契機。可以說梶井作為作家的軌跡,就是從直面美的商業化、大眾化的社會問題開始的文學創作。而《檸檬》不僅是對這一商業體系的反抗,也是對當時的明治近代社會的反抗。
參考文獻
[1]王心悅.以色彩心理看《檸檬》中的顏色運用[J].散文百家(理論),2021(11):49-51.
[2]胡麗花.梶井基次郎文學里的“明”與“暗”探研[J].今古文創,2021(35):37-38.
[3]沈俊霖.論梶井基次郎作品中的色彩描寫和死亡意識[D].上海師范大學,2021.
[4]寧愷.小議梶井基次郎《檸檬》的色彩運用[J].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2013(03):62-66.
[5]宋倩.梶井文學的“暗”與“明”[D].四川外語學院,2012.
[6]張曉朦.梶井基次郎《檸檬》中的對立空間與發現[J].文學教育(上),2022(04):69-71.
[7]近藤のり.梶井基次郎「檸檬」にみる近代と前近代[J].日本女子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2017(23):17-28.
[8]日比嘉高.身體·空間·心·言葉:梶井基次郎「檸檬」をめぐる(京都における日本近代文學の生成と展開)[J].佛教大學総合研究所紀要,2008(1):105-122.
[9]遠藤伸治.「檸檬」論[J].國文學攷,1985(105):23-34.
[10]村田裕和.梶井基次郎『檸檬』論 消費空間における身體[J].論究日本文學,1999(70):30-43.
[11]勝又浩.檸檬と丸善[J].日本文學誌要,1987(36):134-138.
[12]安藤幸輔.「檸檬」における「レモン」の位相[J].駒沢短大國文,1981(11):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