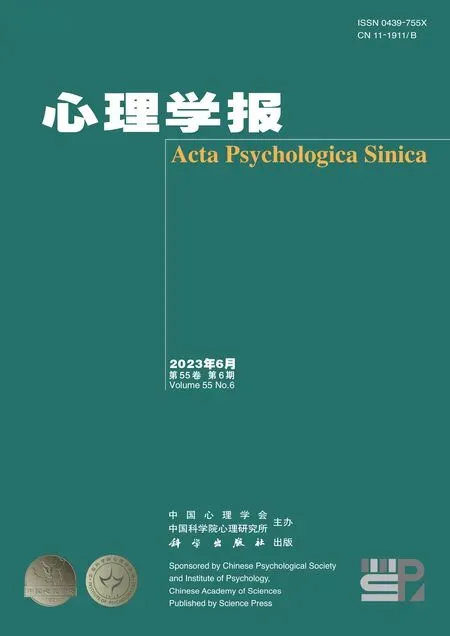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過程的特異性: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的影響
蘭澤波 郭梅華 姜 琨 吳俊杰 閆國利
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過程的特異性: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的影響
蘭澤波1,2郭梅華1,3姜 琨4吳俊杰1閆國利1
(1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 天津 300387) (2福建醫科大學健康學院, 福州 350122) (3閩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漳州 363000) (4天津理工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 天津 300384)
聽障者詞匯識別過程是否表現出特異性一直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問題, 然而當前觀點并不一致。本研究采用語義相關性判斷任務, 通過兩個實驗探討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對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中字形、語音和手語表征激活的影響。實驗1比較不同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的聽障大學生在形似干擾字、同音干擾字和無關干擾字條件下的表現, 實驗2比較他們在手語相關和無關條件下的表現。實驗1結果顯示, 在正確率和反應時指標上, 不同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的聽障大學生表現出相似的字形干擾效應(與無關干擾字相比, 形似干擾字條件下正確率更低、反應時更長), 均未出現語音干擾效應。實驗2結果顯示, 在正確率指標上, 當控制聽障大學生閱讀能力時, 閱讀能力高的手語組表現出顯著的手語干擾效應(與無關條件相比, 手語相關條件下正確率更低), 閱讀能力高的口語組未出現手語干擾效應。當控制聽障大學生語言經驗, 閱讀能力高的手語組和閱讀能力低的手語組表現出相似的手語干擾效應。綜合兩個實驗的結果可以發現, 語言經驗影響聽障大學生的詞匯表征, 閱讀能力不影響聽障大學生的詞匯表征。在此基礎上, 本研究嘗試提出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的認知加工模型。
聽障大學生, 書面詞匯識別, 字形表征, 語音表征, 手語表征
1 引言
閱讀是一項復雜的認知活動, 指讀者從文本中獲取語義的過程。熟練閱讀依賴高效地識別書面詞匯, 從而將更多資源分配給高水平的句子理解, 高效的詞匯識別包括快速和自動檢索高質量的詞匯表征(Perfetti, 2007)。在一般的讀者中, 詞匯識別包括通達穩定的字形表征、語音表征和語義表征, 這些表征得到了大腦神經網絡研究的支持(Dehaene, 2009)。然而, 閱讀對于聽覺經驗缺失的聽障者而言, 則是一項具有較大挑戰的任務。研究表明, 聽障者整體閱讀水平較低, 通常只能達到健聽者四年級的閱讀水平(Traxler, 2000), 他們要達到與同齡健聽者的閱讀水平具有一定困難。研究者發現, 由于缺乏聽覺信息輸入而發生的視覺加工變化, 如聽障者在邊緣視野的視覺注意增強(Pavani & Bottari, 2012), 以及由于缺乏口語經驗而導致的語音表征能力減弱(Sterne & Goswami, 2000), 都可能改變聽障者的閱讀過程。相關研究表明, 與正常發展的健聽讀者不同, 字形表征和語音表征可能在聽障者詞匯識別過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Emmorey & Lee, 2021)。此外, 手語作為聽障者的一種交流方式, 也影響聽障者的詞匯識別過程(Ormel, 2008)。因此, 研究聽障者詞匯識別的認知加工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詞匯識別即獲取詞匯的意義, 是閱讀的必要環節, 指讀者根據字形或語音信息在心理詞典中查找和提取相應詞條的過程(白學軍, 閆國利, 2017)。以健聽讀者閱讀為例, 詞匯通達存在兩條可能的通路: 一條是形?義的直接通達路徑, 即視覺信息激活字形表征, 字形表征激活語義表征; 另一條是以語音為中介的通路, 即視覺信息激活的字形表征激活了語音表征, 語音表征進一步激活語義表征(Coltheart et al., 2001)。聽障者無法有效通達語音信息, 他們的詞匯通達路徑是否與健聽讀者相似?研究者對該問題進行了探討。Bélanger等人(2012, 2013)發現, 雖然聽障成人在法語詞匯識別過程中激活了正字法表征, 但他們在任務中沒有像健聽者那樣激活語音表征。Fari?a等人(2017)針對西班牙語的研究同樣發現, 閱讀能力較高的聽障成人激活正字法表征, 未激活語音表征。上述研究表明聽障者的詞匯識別過程與健聽者不同, 他們存在形?義的直接通達路徑, 不存在形?音?義的語音中介路徑。需要注意的是, 有研究發現聽障者在詞匯識別過程中也能夠激活語音表征。Friesen和Joanisse (2012)發現, 聽障成人在英語詞匯判斷任務中表現出與健聽者相似的同音假詞效應, 判斷同音假詞的反應時顯著慢于拼寫控制假詞, 但效應弱于健聽讀者。蘭澤波等人(2022)發現, 聽障大學生在中文閱讀中表現出繞口令效應, 但效應弱于健聽讀者。這表明聽障者在詞匯識別過程中能夠激活語音表征, 但激活程度可能比健聽讀者弱。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針對主要使用手語的聽障成人的研究發現, 他們在詞匯識別過程中激活了詞匯對應的手語表征(Kubus et al., 2014; Morford et al., 2011, 2014, 2017; Thierfelder et al., 2020a), 而且即使是處在閱讀發展階段的聽障中學生(Villwock et al., 2021)和小學生(Ormel et al., 2012)也激活了手語表征。因此研究者認為, 手語聽障者的詞匯通路包括兩條:一條是與健聽者相似的形?義直接通達路徑, 另一條是手語中介通達路徑, 即視覺信息激活的字形表征激活了手語表征, 手語表征進一步激活語義表征(Ormel et al., 2012)。
從以上綜述可以看出, 以往研究發現聽障者在詞匯識別中能夠激活穩定的字形表征, 但是在語音表征激活方面, 現有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結果(Mayberry et al., 2011), 針對手語聽障者的研究發現, 他們能夠激活穩定的手語表征。Lederberg等人(2012)認為, 聽障兒童的語言學習環境影響其語言發展。大約5%聽障兒童出生在聽障家庭, 他們通常接觸的都是使用手語的人群, 因此這類聽障兒童能夠自然習得手語, 繼而通過手語掌握書面詞匯。相比之下, 大約95%聽障兒童的父母聽力正常, 他們需要各種各樣的支持和幫助來習得手語或口語。因此這類聽障兒童在語言能力上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特點, 這主要取決于父母采用何種語言撫養孩子、聽障兒童自己的語言使用情況、以及聽障兒童對口語的獲取程度(Ormel & Giezen, 2014)。由于聽障者的語言學習環境復雜, 他們在語言經驗(通過手語、口語康復訓練、唇讀等習得語言)和閱讀能力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 這些均可能影響聽障者閱讀的認知過程(Hirshorn et al., 2014),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 不同語言經驗的聽障讀者由于習得語言的過程不同, 勢必影響其書面詞匯的識別。當前研究主要關注了口語經驗對聽障者語音表征的影響。Blythe等人(2018)發現具備口語能力的聽障中學生在閱讀中能夠激活語音表征, 并利用語音表征進行詞匯識別。蘭澤波等人(2020)進一步發現口語熟練的聽障大學生在中文詞匯識別過程中激活了語音表征, 口語不熟練者則未激活語音表征。僅有少數研究直接比較了口語經驗聽障者和手語經驗聽障者在語音意識任務上的表現, Koo等人(2008)發現在聽障讀者中, 口語或唇讀使用者的表現與健聽讀者相似, 均優于手語使用者, 表明口語聽障者具備與健聽者相似的語音意識, 而手語聽障者未發展出語音意識。以上研究提出了值得進一步驗證的理論假設, 即語言經驗塑造聽障者詞匯識別中的詞匯表征。具體表現為:部分聽障者經過口語康復訓練、唇讀等途徑具備一定的口語經驗, 發展出與健聽者相似的語音意識, 按照與健聽者相似的語言習得過程來學習書面詞匯, 能夠利用語音表征進行詞匯識別。而手語聽障者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手語, 無法有效通達語音, 未發展出穩定的語音意識, 與健聽者的語言習得過程不同, 他們主要通過手語來習得書面詞匯, 因此他們無法有效利用語音表征完成詞匯識別, 而是利用手語表征進行詞匯識別(Ormel et al., 2012)。
其次, 根據聽障者閱讀詞匯習得模型(Model of Reading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or Deaf Children, Hermans et al., 2008), 使用手語的聽障者在開始學習書面詞匯時需要借助實時的手語翻譯獲得書面詞匯的語義, 隨著閱讀經驗增加、閱讀能力提高, 他們將表現出與健聽者相似的詞匯表征, 書面詞匯的字形表征與概念語義系統緊密相連, 并逐步發展出口語語音系統, 逐漸減弱對手語的依賴。近年來有研究采用相關分析方法發現, 隨著閱讀能力的提高, 高閱讀能力聽障者表現出更強的字形表征和語音表征(Thierfelder et al., 2020b), 手語表征則更弱(Morford et al., 2014), 支持了聽障者閱讀詞匯習得模型的觀點。當前僅有兩項研究比較了閱讀能力高、低的聽障成人的詞匯表征, 發現高閱讀能力和低閱讀能力的聽障成人均激活了穩定的正字法表征(Bélanger et al., 2012)和手語表征(Morford et al., 2017), 未激活語音表征(Bélanger et al., 2012), 不支持聽障者閱讀詞匯習得模型的觀點。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兩項研究中選取的被試年齡范圍跨度較大(從18歲到55歲), 且Morford等人研究中未對聽障成人的閱讀能力進行嚴格的統計學檢驗, 未報告兩組聽障者在閱讀能力上是否有差異。因此, 進一步通過實驗研究探討閱讀能力對聽障者詞匯表征的影響有助于驗證相應的理論模型。
綜上所述, 聽障者詞匯識別中的詞匯表征一直是聽障者閱讀研究的熱點問題。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實驗材料和范式進行了考察, 但研究結果存在一定爭議(Mayberry et al., 2011)。一方面, 有研究者認為聽障者與健聽者的詞匯識別過程是相同的, 聽障者能夠利用字形表征和語音表征進行詞匯識別, 只是在語音表征的質量上與健聽者存在差異(Elliott et al., 2012); 另一方面, 有研究者認為聽障者表現出與健聽者不同的詞匯識別過程, 聽障者無法利用語音表征完成詞匯識別, 而是利用字形表征和手語表征進行詞匯識別(Ormel et al., 2012)。此外, 近年來研究者還關注到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對聽障者詞匯表征的影響。然而, 當前尚缺乏實驗研究來直接驗證該問題。鑒于此, 有必要在探究聽障者詞匯識別認知機制的基礎上, 進一步明確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在其中的影響, 即口語聽障者表現出與健聽者相似的詞匯表征, 手語聽障者則表現出不同的詞匯表征, 以及隨著閱讀能力的提高, 高閱讀能力聽障者的詞匯表征更接近健聽者。考察上述問題具有一定的新意和價值:第一, 對聽障者詞匯識別中詞匯表征的研究, 可加深對聽障者閱讀認知機制的理解。第二, 當前探討聽障者個體差異對其閱讀認知機制影響的研究尚不深入, 進一步探討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等個體差異對閱讀認知機制的影響有助于回答個體差異在塑造聽障者詞匯表征中的作用, 為聽障者的閱讀教學指導提供依據。
本研究設計了兩個實驗, 實驗1采用語義相關性判斷任務, 要求被試判斷先后出現的兩個詞匯之間是否有語義聯系, 操縱詞匯的字形和語音相似性考察字形表征和語音表征。實驗2采用相同的任務, 操縱詞匯的手語相似性考察手語表征。另外, 為了考察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的影響, 本研究選取了3組聽障讀者作為研究對象:閱讀能力高的口語組聽障大學生(Skilled Oral Deaf, SOD)、閱讀能力高的手語組聽障大學生(Skilled Sign Deaf, SSD)和閱讀能力低的手語組聽障大學生(Less-Skilled Sign Deaf, LSSD)。通過比較SOD和SSD組的表現考察語言經驗的影響, 比較SSD和LSSD組的表現考察閱讀能力的影響。由于字形表征是其它類型表征激活的前提, 本研究預期聽障大學生與健聽大學生均表現出穩定的字形干擾效應。基于前文所述的理論觀點, 預測語言經驗影響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過程, 口語組聽障大學生表現出與健聽者相似的語音干擾效應, 手語組聽障大學生則表現出手語干擾效應, 語音干擾效應即使出現也較弱。閱讀能力影響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過程, 表現為高閱讀能力聽障大學生的字形干擾效應大于低閱讀能力聽障大學生, 手語干擾效應則弱于低閱讀能力聽障大學生, 高閱讀能力聽障大學生可能表現出較弱的語音干擾效應, 符合聽障者閱讀詞匯習得模型的理論觀點。
2 實驗1: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對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中字形和語音表征激活的影響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試
64名天津理工大學在讀聽障大學生參與實驗, 男生30名, 女生34名, 平均年齡22.50歲(= 1.53歲), 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所有被試在3歲前(學語前)失聰(= 1.04歲,= 0.94歲), 聽力損失程度大于70 dB (= 99.90 dB,= 13.80 dB), 屬于重度聽力障礙, 未植入人工耳蝸。46名學生有佩戴助聽設備習慣(佩戴年齡:= 3.66歲,= 3.07歲)。24名被試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口語, 40名被試主要使用手語。所有被試完成語言經歷和語言水平問卷、非言語智力測驗和閱讀流暢性測驗。
(1)語言經歷和語言水平問卷。選取Marian等人(2007)編制的語言經歷和語言水平問卷(LEAP-Q)中部分題項。語言經歷問卷要求被試對自己接觸每種語言時間的百分比進行評定: “請列出目前你所接觸每種語言(口語和手語)時間的百分比(各項百分比之和應為100%)”。語言水平問卷要求被試對自己語言表達和語言理解方面的語言水平進行評定: “標出你在1~10的數值范圍之內, 口語/手語表達能力、理解能力方面的語言水平”, 采用Li等人(2020)推薦的方法計算被試整體語言水平。
(2)非言語智力測驗。采用李丹等人(1988)修訂的瑞文測驗聯合型(CRT), 由A、AB、B、C、D、E六個單元構成, 每單元12題, 共72個測題。
(3)閱讀流暢性測驗。采用三分鐘快速閱讀測驗(程亞華, 伍新春, 2018)。該測驗包含100個簡單句子, 要求學生在3分鐘內快速默讀句子, 并對句子意思進行正誤判斷。例如, 燕子會飛(√); 太陽從西邊升起(×)。將學生回答正確題項的總字數減去回答錯誤題項的總字數作為閱讀流暢性成績。
依據聽障大學生的語言使用比例和閱讀流暢性將其分為SOD、SSD和LSSD, 3組聽障大學生的具體信息見表1。
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計算3組聽障大學生的語言使用比例、語言水平、智力、閱讀能力、聽力損失程度和聽障時間的差異。結果顯示, 在年齡[(2, 62) = 0.66,= 0.52]、智力[(2, 61) = 0.32,= 0.73]和聽障時間[(2, 61) = 0.52,= 0.60]上主效應不顯著, 在口語使用比例[(2, 61) = 182.90,< 0.001]、口語水平[(2, 61) = 58.90,< 0.001]、手語水平[(2, 61) = 9.90,< 0.001]、閱讀流暢性[(2, 61) = 26.53,< 0.001]和聽力損失程度上主效應顯著[(2, 61) = 4.48,< 0.05]。
事后比較分析表明:首先, SOD組的口語使用比例和口語水平顯著高于SSD組(s < 0.001), 在手語使用比例和手語水平上則是SSD組顯著高于SOD組(s < 0.05), 在閱讀流暢性[(61) = 0.51,= 0.87]和聽力損失程度[(61) = ?1.94,= 0.14]上兩組差異不顯著。這表明SOD組和SSD組在閱讀能力上匹配, 兩組在語言經驗上存在差異。其次, SSD組的閱讀流暢性[(61) = 6.27,< 0.001]和口語水平[(61) = 3.19,< 0.01]顯著高于LSSD組, 但是在口語使用比例[(61) = 1.78,= 0.18]、手語水平[(61) = 1.29,= 0.41]和聽力損失程度[(61) = ?1.17,= 0.47]上兩組差異不顯著。這表明SSD組和LSSD組在語言經驗上匹配, 兩組在閱讀能力上存在差異。
另外選取28名健聽大學生作為對照組(Hearing),平均年齡19.90歲(= 1.03歲), 平均智商IQ為118.50 (= 14.03), 母語為漢語, 均未接觸過手語。
2.1.2 材料
實驗材料為100組詞對, 每組詞對由1個線索詞和4個測試字組成。線索詞為雙字詞(如“舒展”), 測試字包含4種類型漢字: 1個目標字和3個干擾字。目標字與線索詞語義高度相關(如“伸”), 被試的正確按鍵反應為“是”。邀請20名健聽大學生評定線索詞和目標字的語義相關性(1=非常不相近, 5=非常相近), 平均語義相關性4.00(= 0.39)。干擾字與線索詞語義無關, 被試的正確按鍵反應為“否”, 包含3種類型:與目標字字形相似但語音不同(形似干擾字, 如“坤”)、與目標字語音相同但字形不相似(同音干擾字, 如“深”)、與目標字字形和語音均不同(無關干擾字, 如“嫻”)。邀請20名未參與語義相關性評定的健聽大學生評定干擾字與目標字的字形相似性。實驗材料具體信息見表2。
采用單因素三水平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計算干擾字的字頻、筆畫數和字形相似性的差異。字頻和筆畫數上, 干擾字類型主效應不顯著[字頻:(2, 198) = 1.17,= 0.31; 筆畫數:(2, 198) = 1.53,= 0.22]。字形相似性上, 干擾字類型主效應顯著[(2, 198) = 3516,< 0.001, ηp2= 0.97], 形似干擾字顯著高于同音干擾字[(198) = 72.30,< 0.001]和無關干擾字[(198) = 72.93,< 0.001], 同音干擾字與無關干擾字的差異不顯著[(198) = 0.63,= 0.81]。
正式實驗采用拉丁方平衡設計實驗字對, 形成4組, 每組包含8個練習試次、100個實驗試次和50個填充試次。實驗試次中每個測試字條件出現25次, 正確按鍵反應為25個“是”和75個“否”。為平衡按鍵反應, 添加了50個填充試次, 正確按鍵反應為“是”。被試隨機接受其中1組進行實驗。

表1 聽障大學生人口學信息比較[M (SE)]
注:SOD閱讀能力高的口語組, SSD閱讀能力高的手語組, LSSD閱讀能力低的手語組; ***< 0.001; **< 0.01; *< 0.05, 下同

表2 實驗1的實驗材料基本屬性M (SE)
注:a 詞頻/字頻來自基于電影對白編制的漢語字/詞語料庫(Cai & Brysbaert, 2010)
2.1.3 設計
4 (組別:Hearing組、SOD組、SSD組、LSSD組) × 4 (測試字:目標字、形似干擾字、同音干擾字、無關干擾字)的兩因素混合實驗設計。組別為被試間因素, 測試字為被試內因素。
2.1.4 儀器
通過13英寸Dell筆記本電腦呈現實驗材料并記錄實驗結果, 屏幕顯示器分辨率1920×1080像素, 刷新率60 Hz。被試眼睛距離屏幕約50 cm, 每個漢字在屏幕上的大小為55×55像素, 占據視角1°。使用E-prime 3.0編寫實驗程序。
2.1.5 程序
被試單獨施測, 熟悉實驗環境后坐在電腦屏幕前閱讀指導語。要求被試又好又快地判斷屏幕上先出現的一個雙字詞和后出現的一個字之間是否有語義聯系。參考Xu等人(1999)研究中的實驗程序(見圖1), 每個試次呈現如下刺激:首先在屏幕中心呈現500 ms注視點“+”; 然后在屏幕中心呈現一個線索詞500 ms, 緊接著出現一個測試字, 被試通過鍵盤按鍵“F”或“J”作是/否判斷, 若3000 ms內被試未做出判斷即開始下一個試次, 試次間隔1000 ms。從開始呈現測試字到被試做出“是”或“否”按鍵時間記為反應時。

圖1 實驗1流程圖
2.1.6 數據分析
僅分析實驗試次中干擾字條件下的數據。研究選取正確率和正確判斷的反應時作為因變量。在分析數據之前, 刪除了反應時小于300 ms和未按鍵的數據(健聽大學生0.1%, 聽障大學生0.3%)。采用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 GLM)分析正確率, 采用線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 LMM)分析反應時, 反應時數據分析之前刪除超出每個被試在每個條件下平均值3個標準差以外的數據(健聽大學生2.0%, 聽障大學生7.8%), 為使數據正態化, 反應時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
首先單獨分析健聽大學生的數據, 其次分析聽障大學生的數據時, 組別(SOD vs. SSD, SSD vs. LSSD)、干擾字類型(形似干擾字vs.無關干擾字, 同音干擾字vs.無關干擾字)及其交互作用作為固定效應, 被試和項目作為隨機效應。全模型的隨機效應包括被試層面的隨機斜率和截距、項目層面的隨機斜率和截距, 通過主成分分析(Bates et al., 2015)選擇最優模型, 最后報告指標的回歸系數(), 標準誤(),/值,值和95%置信區間。使用‘BayesFactor’包的lmBF函數(Morey et al., 2018)進行貝葉斯因子分析, 來確定3組聽障大學生字形干擾效應和語音干擾效應的證據強度。參考Yao等人(2021)的研究, 字形干擾效應的貝葉斯因子由“包括字形干擾效應、被試和項目截距的模型”與“只包括被試和項目截距的零模型”比值所得, 語音干擾效應的貝葉斯因子由“包括語音干擾效應、被試和項目截距的模型”與“只包括被試和項目截距的零模型”比值所得, 比值大于1時認為傾向于存在字形干擾效應和語音干擾效應。
2.2 結果
聽障大學生中SOD組1人, SSD組3人未能完成實驗, 3組中各有1名被試因正確率較低(目標字條件下正確率低于60%)未被納入數據分析中。最終數據分析中Hearing組28名, SOD組22名, SSD組20名, LSSD組15名。健聽大學生和3組聽障大學生在不同干擾字條件下的正確率和反應時見表3。
2.2.1 健聽大學生
正確率指標上, 形似干擾字顯著低于無關干擾字(= 1.40,= 0.20,= 6.96,< 0.001, 95% CI = [1.01, 1.80]), 同音干擾字顯著低于無關干擾字(= 0.56,= 0.20,= 2.81,< 0.01, 95% CI = [0.17, 0.96])。貝葉斯因子分析發現, 字形干擾效應的貝葉斯因子為4.95e11, 語音干擾效應的貝葉斯因子為3.66, 支持健聽大學生表現出字形干擾效應和語音干擾效應。
反應時指標上, 形似干擾字顯著長于無關干擾字(= ?0.03,= 0.01,= ?3.01,< 0.01, 95% CI = [?0.06, ?0.01]), 同音干擾字與無關干擾字的差異不顯著(= ?0.00,= 0.01,= ?0.21,= 0.84, 95% CI = [?0.02, 0.02])。貝葉斯因子分析發現, 字形干擾效應的貝葉斯因子為6.66, 語音干擾效應的貝葉斯因子為0.06, 支持健聽大學生表現出字形干擾效應, 未表現出語音干擾效應。
2.2.2 聽障大學生
3組聽障大學生的線性混合效應模型統計結果見表4。正確率指標上, 形似干擾字顯著低于無關干擾字, 同音干擾字顯著低于無關干擾字。交互作用均不顯著。貝葉斯因子分析顯示, 字形干擾效應上, SO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9.79e14, 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3.64e11, L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8.60e5, 為3組聽障大學生存在字形干擾效應提供了支持的證據。語音干擾效應上, SO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0.50, 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0.10, L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0.12, 不支持3組聽障大學生存在語音干擾效應。
反應時指標上, 形似干擾字顯著長于無關干擾字, 同音干擾字長于無關干擾字, 差異邊緣顯著。交互作用均不顯著。貝葉斯因子分析顯示, 字形干擾效應上, SO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25.07, 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19.80, L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38.84, 為3組聽障大學生存在字形干擾效應提供了支持的證據。語音干擾效應上, SO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0.39, 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0.10, L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0.19, 不支持3組聽障大學生存在語音干擾效應。
通過以上分析發現, 正確率指標更能夠反映出讀者在語義相關性判斷中是否產生字形或語音干擾效應。將無關干擾字下的正確率分別減去形似干擾字下的正確率、同音干擾字下的正確率來直觀顯示4組大學生的字形干擾效應和語音干擾效應(見圖2)。4組大學生的字形干擾效應均高于12%, 語音干擾效應均低于4%。首先, 采用檢驗分析發現, 4組大學生的字形干擾效應均顯著大于語音干擾效應[Hearing:(27) = 5.13,< 0.001; SOD:(21) =6.03,< 0.001; SSD:(19) = 5.83,< 0.001; LSSD:(14) = 4.11,< 0.01]。其次, 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 4組大學生的字形干擾效應無顯著差異[(3, 81) = 0.91,= 0.44]。

表3 實驗1結果的平均值(標準誤)
注:反應時指標的單位為 ms

表4 實驗1中線性混合模型分析結果

圖2 四組大學生在語義相關性判斷任務中的字形和語音干擾效應
2.3 討論
實驗1的結果表明, 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均不影響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中字形表征和語音表征的激活。被試在語義相關性判斷任務中出現字形干擾效應, 是因為形似干擾字的字形信息被激活后, 與其字形相似的目標字語義也由字形表征激活了, 干擾被試做出正確的判斷, 從而降低被試的正確率, 延長被試的反應時。同理, 同音干擾字的語音信息被激活, 與其語音相同的目標字語義也由語音表征激活, 干擾被試做出正確的判斷, 從而降低被試的正確率, 延長被試的反應時。本研究結果表明, 健聽大學生與3組聽障大學生在任務中均表現出穩定的字形干擾效應, 但是, 即使是健聽大學生, 語音干擾效應在任務中表現也不穩定, 只在正確率指標上存在中等程度的證據支持。研究結果可能受到中文文字系統的影響。中文詞匯識別的表征與加工模型(周曉林, 1997)認為, 在中文詞匯識別中, 從語音表征到語義的通達是有限的, 語義激活主要受字形制約。因此, 不論是聽障大學生還是健聽大學生, 在中文詞匯識別過程中語義的激活都主要受字形制約, 對語音表征的激活較弱。
3 實驗2: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對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中手語表征激活的影響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試
同實驗1。
3.1.2 材料
實驗材料包括啟動詞和目標詞, 操縱啟動詞與目標詞的手語相關性:(1)語義無關、手語相關詞對(S?S+), 如花?電燈; (2)語義無關、手語無關詞對(S?S?), 如蝸牛?插頭, 每種類型條件下有50組詞對(見表5)。手語相關性的操作參考Morford等人(2011)的研究, 當兩個詞匯的手語在手語語音參數上存在兩個及兩個以上參數相同時, 它們即為手語相關詞, 例如, 花的手語和電燈的手語在手形、位置、動作參數上相同。

表5 實驗2材料示例
邀請20名健聽大學生評定啟動詞和目標詞的語義相關性。最終選取出符合實驗要求的詞對56組, 其中S?S+條件24組, S?S?條件32組。獨立樣本檢驗分析發現, 兩組詞對的語義相關性不存在顯著差異,(54) = 0.55,= 0.59。所有詞語對應的手語均為1個手勢。為控制啟動詞和目標詞對應手語的復雜性, 匹配了它們手語中手的個數(單手或雙手), 如果啟動詞的手語是使用雙手, 那么目標詞的手語也是使用雙手。為平衡被試的按鍵反應, 另外選取了56組語義相關的詞對。
3.1.3 設計
4 (組別:Hearing組、SOD組、SSD組、LSSD組) × 2 (手語相關性:相關、無關)的兩因素混合實驗設計。組別為被試間因素, 手語相關性為被試內因素。
3.1.4 儀器
同實驗1。
3.1.5 程序
參考Morford等(2011)研究中的實驗程序(見圖3), 每個試次呈現如下刺激:首先在屏幕中心呈現500 ms注視點“+”; 然后在屏幕中心出現一個啟動詞500 ms, 在500 ms空屏間隔后出現一個目標詞, 被試通過鍵盤按鍵“F”或“J”作是/否判斷, 若3000 ms內被試未做出判斷即開始下一個試次, 試次間隔1000 ms。從開始呈現目標詞到被試按鍵做出“是”或“否”判斷時間記為反應時。

圖3 實驗2流程圖
3.1.6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與實驗1相同。在分析數據前, 刪除反應時小于300 ms和未按鍵的數據(健聽大學生0.15%, 聽障大學生0.47%), 反應時數據分析前刪除超出每個被試在每個條件下平均值3個標準差以外的數據(健聽大學生1.66%, 聽障大學生1.91%)。采用貝葉斯因子分析計算被試存在手語干擾效應的支持強度, 貝葉斯因子由“包括手語干擾效應、被試和項目截距的模型”與“只包括被試和項目截距的零模型”比值所得, 比值大于1時被認為傾向于存在手語干擾效應。
3.2 結果
健聽大學生4人, LSSD組1人未能完成實驗, SSD組和LSSD組中各有1名被試因正確率較低(正確率低于70%)未被納入分析中, 最終數據分析中Hearing組24名, SOD組24名, SSD組23名, LSSD組14名。健聽大學生和3組聽障大學生在手語相關條件和手語無關條件下的正確率和反應時見表6。
3.2.1 健聽大學生
正確率指標上, 手語相關條件與手語無關條件無顯著差異(= 0.36,= 0.38,= 0.97,= 0.34, 95% CI = [?0.37, 1.10])。手語干擾效應的貝葉斯因子為0.49, 不支持健聽大學生存在手語干擾效應。
反應時指標上, 手語相關條件與手語無關條件無顯著差異(= ?0.03,= 0.02,= ?1.44,= 0.16, 95% CI = [?0.07, 0.01])。手語干擾效應的貝葉斯因子為0.27, 不支持健聽大學生存在手語干擾效應。
3.2.2 聽障大學生
3組聽障大學生的線性混合效應模型統計結果見表7。正確率指標上, 手語相關條件顯著低于手語無關條件。SSD組和SOD組在手語相關和手語無關條件下的交互作用顯著, 簡單效應分析表明, SOD組在手語相關條件與手語無關條件差異不顯著(= ?0.54,= 0.37,= ?1.44,= 0.15), SSD組在手語相關條件下的正確率顯著低于手語無關條件(= ?1.58,= 0.42,= ?3.76,< 0.001), LSSD組在手語相關條件下的正確率顯著低于手語無關條件(= ?1.08,= 0.41,= ?2.63,< 0.01)。貝葉斯因子顯示, SO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0.33, 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11.23, L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4.02, 支持SSD組和LSSD組聽障大學生存在手語干擾效應, 不支持SOD組存在手語干擾效應。

表6 實驗2中結果的平均值(標準誤)
注:反應時指標的單位為 ms

表7 實驗2中線性混合模型分析結果
反應時指標上, 手語相關條件顯著長于手語無關條件, 交互作用均不顯著。貝葉斯因子分析顯示, SO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1.51, 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1.27, LSSD組的貝葉斯因子為1.56, 存在較弱的證據支持3組聽障大學生存在手語干擾效應。
將手語無關條件下的正確率減去手語相關條件下的正確率來直觀顯示4組大學生的手語干擾效應(見圖4)。健聽大學生和SOD組聽障大學生的手語干擾效應低于4.5%, SSD和LSSD組聽障大學生的手語干擾效應高于8%。單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組間差異邊緣顯著[(3, 81) = 2.80,= 0.05], 4組大學生的手語干擾效應差異不顯著(s ≥ 0.13), 但數據趨勢可以看出SSD和LSSD組聽障大學生的手語干擾效應大于健聽大學生和SOD組聽障大學生的手語干擾效應。

圖4 四組大學生在語義相關性判斷任務中的手語干擾效應
3.3 討論
實驗2的結果表明, 語言經驗影響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中手語表征的激活, 閱讀能力不影響其手語表征的激活。由于在語義相關性判斷任務中給被試呈現的是中文詞匯, 如果被試判斷手語相關詞對為語義無關時表現出更多錯誤, 反應時更長, 則表明他們在中文書面詞匯識別時自動激活了手語表征。本研究發現健聽大學生未表現出手語干擾效應, SOD組聽障大學生手語干擾效應較弱, SSD組聽障大學生和LSSD組聽障大學生均表現出穩定的手語干擾效應, 這表明語言經驗影響手語表征的激活。SSD組聽障大學生和LSSD組聽障大學生的手語干擾效應不存在顯著差異, 表明閱讀能力不影響手語表征激活。這與拼音文字研究結果一致, Morford等人(2017)采用相同的任務發現高、低閱讀能力聽障成人表現類似, 激活了穩定的手語表征, 兩組聽障成人的手語表征激活量不存在顯著差異。值得注意的是, 當前研究選取的研究對象均為聽障大學生或聽障成人, 他們已經是成熟讀者, 即使通過閱讀測驗將他們分為高、低閱讀能力者, 并不能夠代表詞匯習得發展階段。事實上, 前人研究發現即使是正處在閱讀發展階段的聽障兒童和聽障中學生, 他們在詞匯識別中也激活了手語表征(馮敏等, 2017; Ormel et al., 2012; Villwock et al., 2021)。
4 總討論
本研究采用語義相關性判斷任務, 考察了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對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中字形、語音和手語表征激活的影響。綜合分析兩個實驗發現, 語言經驗影響聽障大學生詞匯表征的激活, 閱讀能力不影響其詞匯表征的激活。值得注意的是, 受中文系統的影響, 即使是健聽大學生, 語音表征的激活也較弱, 因此語言經驗主要影響手語表征的激活。下面分別討論語言經驗和閱讀能力對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的影響及對構建模型的啟示。
4.1 語言經驗對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口語組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的認知機制與健聽者相似, 手語組聽障大學生發展出與健聽者不同的詞匯識別認知機制。一方面, 口語組聽障大學生在中文詞匯識別中能夠激活穩定的字形表征, 對語音表征和手語表征的激活較弱, 這與中文詞匯識別的表征與加工模型(周曉林, 1997)的觀點比較一致。該模型認為在中文詞匯識別中, 語義激活主要受字形制約, 從語音表征到語義通達是有限的。另一方面, 手語組聽障大學生在詞匯識別中激活了穩定的字形表征和手語表征, 未激活語音表征, 這與聽障者詞匯識別的交互激活模型(Ormel et al., 2012)觀點比較一致。該模型認為, 詞匯的字形表征能夠直接激活語義表征, 也可通過手語表征間接激活語義表征。
研究結果驗證了語言經驗塑造聽障者詞匯識別中的詞匯表征這一理論假設。聽障兒童成長的語言環境多樣化, 與手語聽障者相比, 受過口語康復訓練的聽障者表現出對語音表征的依賴, 突出了語言經驗在塑造聽障者詞匯表征中的重要性。Hirshorn等(2014)通過腦成像研究發現與手語聽障者相比, 口語聽障者從左側顳上回到背側閱讀網絡中基于語音區域(如左側中央后回)的連接更緊密。Cardin等人(2013)發現在加工手語時, 只有手語聽障者表現出左側顳上回區域的激活增強, 口語聽障者未表現出增強。以上研究通過腦成像技術發現, 在拼音文字系統中, 口語聽障者閱讀時依賴語音表征, 手語聽障者可能依賴手語表征。需要關注的是, 在中文閱讀中, 即使是健聽者, 語音表征的激活也較弱, 因此本研究未觀察到口語聽障大學生語音表征的激活。但是本研究同樣發現手語聽障者在詞匯識別中更依賴手語表征, 口語聽障者對手語表征的激活較弱。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中SOD組聽障大學生和SSD組具有相同水平的閱讀能力, 這表明不同語言經驗的聽障者, 雖然語言習得過程不同, 詞匯表征存在差異, 但通過努力學習均可以獲得較高水平的閱讀能力。
4.2 閱讀能力對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 當控制語言經驗, 相比低閱讀能力聽障者, 高閱讀能力者在詞匯識別中對字形表征的依賴沒有更強, 未發展出穩定的語音表征, 手語表征的激活沒有減弱。事實上, 在拼音文字研究中, Bélanger等(2012)發現高、低閱讀能力聽障成人在法語詞匯識別中的表現相似, 主要激活正字法表征, 未激活語音表征。Morford等(2017)發現高、低閱讀能力聽障成人在英語詞匯識別中的表現相似, 均激活了穩定的手語表征。以上研究結果與本研究一致, 不支持聽障者詞匯習得模型的觀點。由于當前研究選取聽障大學生或聽障成人作為研究對象, 而聽障者詞匯習得模型描述的是聽障學生詞匯學習的整個過程, 包含從初學讀者到成熟讀者這一發展過程, 閱讀發展階段的中小學聽障者在詞匯識別中的詞匯表征與聽障大學生是否存在差異有待進一步驗證。
閱讀能力不影響聽障大學生的詞匯表征, 表明他們的詞匯識別能力并無較大差異, 那么是什么因素導致他們閱讀能力上的差異?閱讀是一項復雜的認知活動, 除了詞匯識別, 還包括句子理解、篇章理解等過程。句子理解是在詞匯識別的基礎上利用各種句法、語義和語境線索獲得句子意義的過程。陳朝陽等(2018)發現, 高閱讀能力聽障中學生在句子閱讀中存在語境預測性效應, 低閱讀能力聽障中學生不存在語境預測性效應。語境預測性效應反映讀者利用自上而下的概念信息來促進詞匯加工, 進而幫助讀者進行高效地閱讀(任桂琴等, 2012)。在閱讀過程中, 高閱讀能力聽障者在利用各種線索信息等方面比低閱讀能力者是否更加高效?對該問題的持續探討有助于揭示造成聽障者閱讀能力較低的影響因素, 為制定有效地干預措施提供依據。
4.3 對建構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認知模型的啟示
在拼音文字系統中, 有兩種理論模型用于解釋聽障者的詞匯識別過程。雙通道模型(Dual-Route Cascaded Model of Reading by Deaf Adults, Elliott et al., 2012)認為聽障者與健聽者的詞匯識別過程相同, 他們能夠激活正字法表征和語音表征。交互激活模型(Deaf 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Ormel et al., 2012)認為聽障者的詞匯識別過程與健聽者不同, 聽障者激活的是正字法表征和手語表征。以上兩種理論模型能夠解釋不同語言經驗下聽障者的詞匯識別過程。雙通道模型更適用于有口語經驗的聽障者, 交互激活模型更適用于手語經驗的聽障者。
本研究表明漢語聽障大學生表現出與拼音文字系統不同的詞匯識別過程。一方面, 拼音文字是表音文字系統, 書面詞匯主要在音素層面編碼語音, 讀者即使不知道它的意思, 也能讀出該單詞。故雙通道模型理論認為語音表征在聽障者詞匯識別中同樣起著重要作用。中文是表義文字系統, 每個漢字通常對應一個語義單位或語素, 每個漢字對應一個音節, 讀者必須記住每個漢字的發音(Li et al., 2022), 故語音表征在中文詞匯識別中的作用有限, 表現為在詞匯識別中語音表征的激活較弱。因此, 雙通道模型無法適用于漢語聽障者。另一方面, 交互激活模型強調手語表征在聽障者詞匯識別中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發現手語組聽障大學生在詞匯識別中激活了穩定的手語表征, 符合該模型的觀點。口語組聽障大學生對手語表征的激活較弱, 無法用交互激活模型的觀點解釋, 他們的詞匯識別過程更符合中文詞匯識別的表征和加工模型的觀點。
基于本研究發現, 參考拼音文字系統中提出的聽障者詞匯識別模型, 結合中文詞匯識別的表征和加工模型(周曉林, 1997), 本研究嘗試提出漢語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的認知加工模型。如圖5所示, 與中文詞匯識別的表征和加工模型(周曉林, 1997)不同的是, 聽障者的心理詞典包含字形、語音、手語和語義四種類型表征。與現有的聽障者詞匯識別模型一致, 在詞匯加工初期, 字形表征首先被激活, 字形表征的激活是其它類型表征激活的前提, 當心理詞典中字形信息被充分激活后, 與之相聯的語音和手語表征也將自動被激活。在雙通道模型(Elliott et al., 2012)和交互激活模型(Ormel et al., 2012)的基礎上, 本研究增加了語言經驗的影響, 具體表現為不同語言經驗的聽障者對語音表征和手語表征的激活不同。手語聽障者無法有效激活語音表征, 更多激活的是手語表征, 手語表征進一步激活語義表征。口語聽障者對手語表征的激活較弱, 無法利用手語表征激活語義表征, 他們雖然能夠激活語音表征, 但在中文詞匯識別中, 通過語音表征激活語義的作用有限。總體而言, 在中文詞匯識別中, 語義激活主要通過字形表征通達, 手語聽障大學生還可以通過手語表征通達語義。

圖5 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的認知加工模型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 本研究只考察了聽障大學生在書面詞匯識別中字形、語音和手語表征的激活情況, 其它年齡階段的聽障學生情況如何, 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另外, 本研究基于當前研究結果提出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的認知模型, 后續研究可采用更多的實驗范式和任務來進一步驗證該模型的適用性, 如可以采用錯誤中斷范式, 借助眼動追蹤技術, 在生態效度較高的句子閱讀情境下進一步考察該問題。
5 結論
首先, 在控制閱讀能力后, 語言經驗影響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中的詞匯表征。口語組聽障大學生詞匯識別的認知過程更接近健聽大學生, 主要激活字形表征, 對手語表征和語音表征的激活較弱; 手語組聽障大學生則發展出與健聽大學生不同的詞匯識別過程, 激活穩定的字形表征和手語表征。其次, 在控制語言經驗后, 閱讀能力不影響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中的詞匯表征。最后, 參考拼音文字系統中提出的聽障者詞匯識別模型, 結合中文詞匯識別的表征和加工模型, 本研究嘗試提出了聽障大學生中文詞匯識別的認知加工模型。
Bai, X. J., & Yan, G. L. (2017)..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白學軍, 閆國利. (2017)..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Bates, D., Kliegl, R., Vasishth, S., & Baayen, H. (2015). Parsimonious mixed models.arXiv: 1506. 04967.
Bélanger, N. N., Baum, S. R., & Mayberry, R. I. (2012). Reading difficulties in adult deaf readers of French: Phonological codes, not guilty!(3), 263?285.
Bélanger, N. N., Mayberry, R. I., & Rayner, K. (2013). 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preview benefits: Parafovealprocessing in skilled and less-skilled deaf readers.(11), 2237?2252.
Blythe, H. I., Dickins, J. H., Kennedy, C. R., & Liversedge, S. P. (2018).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during silent reading in teenagers who are deaf/hard of hearing: An eye movement investigation.(5), e12643.
Cai, Q., & Brysbaert, M. (2010). SUBTLEX-CH: Chinese word and character frequencies based on film subtitles.(6), Article e10729.
Cardin, V., Orfanidou, E., R?nnberg, J., Capek, C. M., Rudner, M., & Woll, B. (2013). Dissociating cognitive and sensory neural plasticity in human superior temporal cortex.(1), 1473.
Chen, C. Y., Liu, Z. F., Su, Y. Q., & Cheng, Y. H. (2018). The prediction effects for skill and less-skill deaf readers in Chinese reading: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6), 692?699.
[陳朝陽, 劉志方, 蘇永強, 程亞華. (2018). 高低閱讀技能聾生詞匯加工的語境預測性效應特點: 眼動證據.(6), 692?699.]
Cheng, Y. H., & Wu, X. C. (2018). Reading fluency of first-graders predict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second- and third-graders.,(3), 314?321.
[程亞華, 伍新春. (2018). 小學一年級閱讀流暢性對二、三年級閱讀理解的預測.(3), 314?321.]
Coltheart, M., Rastle, K., Perry, C., Langdon, R., & Ziegler, J. (2001). DRC: A dual route cascaded model of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aloud.(1), 204?256.
Dehaene, S. (2009).. New York: Penguin.
Elliott, E. A., Braun, M., Kuhlmann, M., & Jacobs, A. M. (2012). A dual-route cascaded model of reading by deaf adults: Evidence for grapheme to viseme conversion.(2), 227?243.
Emmorey, K., & Lee, B. (2021). The neurocognitive basis of skilled reading in prelingually and profoundly deaf adults.(2), e12407.
Fari?a, N., Du?abeitia, J. A., & Carreiras, M. (2017). Phonological and orthographic coding in deaf skilled readers., 27?33.
Feng, M., Han, Y., & Guo, Q. (2017).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activation of sign language in hearing-impaired persons' Chinese characters recognition., (11), 25?31.
[馮敏, 韓媛, 郭強. (2017). 聾生漢語詞匯識別過程中手語激活的實驗研究., (11), 25?31.]
Friesen, D. C., & Joanisse, M. F. (2012). Homophone effects in deaf readers: Evidence from lexical decision.(2), 375?388.
Hermans, D., Knoors, H., Ormel, E., & Verhoeven, L. (2008). Modeling reading vocabulary learning in deaf children in 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s.(2), 155?174.
Hirshorn, E. A., Dye, M. W. G., Hauser, P. C., Supalla, T. R., & Bavelier, D. (2014). Neural networks mediating sentence reading in the deaf., 394.
Koo, D., Crain, K., LaSasso, C., & Eden, G. F. (2008). Phonological awareness and short-term memory in hearing and deaf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backgrounds.(1), 83?99.
Kubus, O., Villwock, A., Morford, J. P., & Rathmann, C. (2014). Word recognition in deaf readers: Cross-language activation of German Sign Language and German.(4), 831?854.
Lan, Z. B., Liang, X. W., Wang, Z. G., Jiang, K., Meng, Z., & Yan, G. L. (2020).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during sentence reading in deaf college students: An eye-tracking study.(4), 997?1003.
[蘭澤波, 梁曉偉, 王正光, 姜琨, 孟珠, 閆國利. (2020). 聽障大學生句子閱讀中語音加工的眼動研究.(4), 997?1003.]
Lan, Z. B., Lin, M., Song, Z. M., Meng, Z., Jiang, K., & Yan, G. L. (2022). Phonological activation during reading in deaf college students: Evidence from the tongue-twister effect.(2), 491?497.
[蘭澤波, 林梅, 宋子明, 孟珠, 姜琨, 閆國利. (2022). 聽障大學生閱讀中的語音激活:來自繞口令效應的證據.(2), 491?497.]
Lederberg, A. R., Schick, B., & Spencer, P. E. (2012).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of deaf and hard-of-hearing children: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1), 15?30.
Li, D., Hu, K. D., Chen, G. P., Jin, Y., & Li, M. (1988). Test report of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 (CRT) of Shanghai city., (4), 29?33.
[李丹, 胡克定, 陳國鵬, 金瑜, 李眉. (1988). 瑞文測驗聯合型(CRT)上海市區試測報告., (4), 29?33.]
Li, P., Zhang, F., Yu, A., & Zhao, X. (2020). Language History Questionnaire (LHQ3): An enhanced tool for assessing multilingual experience.(5), 938?944.
Li, X., Huang, L., Yao, P., & Hy?n?, J. (2022). Universal and specific reading mechanisms across different writing systems., 133?144.
Marian, V., Blumenfeld, H. K., & Kaushanskaya, M. (2007). The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Proficiency Questionnaire (LEAP-Q): Assessing language profiles in bilinguals and multilinguals.(4), 940?967.
Mayberry, R. I., del Giudice, A. A., & Lieberman, A. M. (2011). Reading achievement in relation to phonological coding and awareness in deaf readers: A meta-analysis.(2), 164?188.
Morey, R. D., Rouder, J. N., Jamil, T., Urbanek, S., Forner, K., & Ly, A. (2018).. Version 0.9.12. from https:// CRAN.R-project.org/package=BayesFactor
Morford, J. P., Kroll, J. F., Pi?ar, P., & Wilkinson, E. (2014). Bilingual word recognition in deaf and hearing signers: Effects of proficiency and language dominance on cross- language activation.(2), 251?271.
Morford, J. P., Occhino-Kehoe, C., Pi?ar, P., Wilkinson, E., & Kroll, J. F. (2017). The time course of cross-language activation in deaf ASL-English bilinguals.(2), 337?350.
Morford, J. P., Wilkinson, E., Villwock, A., Pi?ar, P., & Kroll, J. F. (2011). When deaf signers read English: Do written words activate their sign translations?(2), 286?292.
Ormel, E. (2008).(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Ormel, E., & Giezen, M. (2014). Bimodal bilingual cross- language interaction: Pieces of the puzzle. In M. Marschark, G. Tang, & H. Knoors (Eds.),(pp. 74?10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mel, E., Hermans, D., Knoors, H., & Verhoeven, L. (2012). Cross-language effects in written word recognition: The case of bilingual deaf children.(2), 288?303.
Pavani, F., & Bottari, D. (2012). Visual abilities in individuals with profound deafness: A critical review. In Murray, M. M., & Wallace, M. T. (Ed.),(pp. 421?445). CRC Press/Taylor & Francis.
Perfetti, C. (2007). Reading ability: Lexical quality to comprehension.(4), 357?383.
Ren, G. Q., Han, Y. C., & Yu, Z. (2012). The activation of orthography and phonology during Chinese sentence reading: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4), 427?434.
[任桂琴, 韓玉昌, 于澤. (2012). 句子語境中漢語詞匯形、音作用的眼動研究.(4), 427?434.]
Sterne, A., & Goswami, U. (2000). Phonological awareness of syllables, rhymes, and phonemes in deaf children.(5), 609?625.
Thierfelder, P., Wigglesworth, G., & Tang, G. (2020a). Sign phonological parameters modulate parafoveal preview effects in deaf readers., 104286.
Thierfelder, P., Wigglesworth, G., & Tang, G. (2020b). 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activation in Hong Kong deaf readers: An eye-tracking study.(12), 2217?2235.
Traxler, C. B. (2000). The Stanford Achievement Test: National norming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deaf and hard-of-hearing students.(4), 337?348.
Villwock, A., Wilkinson, E., Pi?ar, P., & Morford, J. P. (2021).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deaf bilinguals: Dea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activate written English and American sign language during lexical processing., 104642.
Xu, Y., Pollatsek, A., & Potter, M. C. (1999). The activation of phonology during silent Chinese word reading.(4), 838?857.
Yao, P., Staub, A., & Li, X. (2022). Predictability eliminates neighborhood effects during Chinese sentence reading.(1), 243?252.
Zhou, X. L. (1997). The limitation of the phonology in semantic activation. In Peng, D. L., Shu, H., & Chen, H. -C. (Eds.),. Jinan, China: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周曉林. (1997). 語義激活中語音的有限作用. 見:彭聃齡, 舒華, 陳烜之(編)..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The distinctness of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in hearing-impaired college readers: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reading ability
LAN Zebo1,2, GUO Meihua1,3, JIANG Kun4, WU Junjie1, YAN Guoli1
(1Faculty of Psycholog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2School of Health,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22, China) (3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4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nsultation Center,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Compared with hearing readers, orth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phonological information may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word recognition process for hearing-impaired readers. As a communication mode for hearing-impaired readers, sign language may also affect their word recognition proces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activation of orthographic representation,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during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in hearing-impaired readers.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hearing-impaired readers could activate stable orth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but there were inconsistent results in the activation of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whereas studies on hearing-impaired readers who primarily use sign language have found that they can activate stable sign language representations. Hearing-impaired readers grow up in a complex language environment, which leads to grea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reading ability. However, previous works have not clearly identified the effect of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reading ability 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reading in hearing-impaired readers. Continuous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will help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o guide reading instruction for hearing-impaired readers.
This study conducted two semantically related decision tasks to investigate the activation of orthographic, phonological, and sign language representations during Chinese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in hearing-impaired college students. 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word recognition for hearing readers, but sign language representations are a phenomenon unique to deaf reader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activation of orthographic and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in Experiment 1 and the activation of sign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in Experiment2.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their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reading fluency, hearing-impaired colleg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deaf college students with oral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higher reading ability (Skilled Oral Deaf, SOD), deaf college students with sign language experience but higher reading ability (Skilled Sign Deaf, SSD), and deaf college students with sign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lower reading ability (Less-Skilled Sign Deaf, LSSD).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showed that (a) hearing students showed a stable orthographic interference effect, whereas the phonological interference effect was weak. (b) The SOD group and the SSD group showed similar performance. Both showed a stable orthographic interference effect but did not show a significant phonological interference effect. (c) The SSD group and the LSSD group showed similar performance. Both groups showed a stable orthographic interference effect but did not show a phonological interference effect. Experiment 2 found that (a) hearing students did not show a sign language interference effect. (b) The SOD group and the SSD group differed in performance. The SSD group exhibited a sign language interference effect, whereas this effect was absent in the SOD group. (c) The SSD group performed similarly to the LSSD group. Both groups showed a stable sign language interference effect.
Taken together,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from the two studies: (a) after controlling for reading ability, language experience affected Chinese lexical recognition in deaf college students;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oral deaf college student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hearing readers., orth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were mainly activated; and the activation of phonological and sign language representations was weak. Deaf college students who used sign language developed a uniqu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they activated stable orthographic and sign language representations during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b) After controlling for language experience, reading ability did not affect lexical representation during Chinese word recognition in hearing-impaired college students. (c)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models of Chinese word recognition, we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cognitive model of Chinese word recognition for hearing-impaired college readers.
hearing-impaired college students,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orthographic representation,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sign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2022-07-28
*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2JJD190012)。
閆國利, E-mail: psyygl@163.com
B842; B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