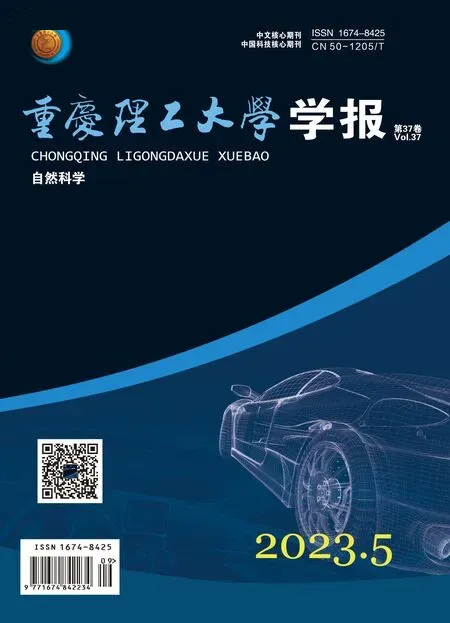某純電動汽車空調采暖系統的仿真優化
劉 西,余 磊,胡遠志
(重慶理工大學 汽車零部件先進制造技術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重慶 400054)
0 引言
近幾年,由于現代工業體系使用大量化石燃料,碳排放問題成為了國際社會日益關注的重點[1]。中國為了適應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提出了向新能源汽車轉型的相關政策,例如雙積分法等[2]。在此環境下,國內各大車企對純電動車型的研究投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純電動汽車的發展與應用成為了當今環境下不可阻擋的趨勢。眾所周知,純電動汽車在低溫環境下沒有發動機提供熱源,大多車型應用PTC進行制暖。國鐵楓[3]設計了一款電動汽車,該車型使用了PTC水暖加熱系統。由于PTC為大功率耗電部件,制暖時對整車的動力性以及續航里程產生了一定的威脅,通過對策略的優化改進可以提高PTC制熱時汽車的經濟性。朱成等[4]對低溫環境下影響純電動汽車的續航里程的相關因素進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張子琦[5]對熱泵空調系統的傳熱結構進行了研究,通過優化換熱結構能改善系統的能耗。曹曉玉[6]通過AMEsim軟件建立空調系統模型,研究發現環境溫度對系統能耗有較大的影響。朱波等[7]利用電機余熱作為輔助熱源,通過優化加熱器的控制策略得到了較低的系統能耗。楊君[8]提出水暖PTC加熱器功率的自動化線性調節,通過精確化控制精度降低能耗。本文基于某公司某純電車型的開發項目,對控制策略進行了優化,增加了對電驅余熱的利用,通過AMEsim軟件與Matlab聯合仿真驗證了該優化模型的控制效果。
1 低溫熱管理制熱系統
本文中低溫熱管理加熱系統包括對乘員艙、動力電池的加熱。其加熱結構原理如圖1所示。

圖1 低溫熱管理加熱原理框圖
乘員艙及電池采暖原理:PTC的發熱量將在乘員艙或電池需要加熱時為其提供熱源,熱量在水暖回路中經過三通閥調節分配支路熱量。隨后通過暖風芯體,利用鼓風機與乘員艙室內空氣換熱;或者水暖回路熱量經過三通閥調節后,通過電池板與電池冷卻水回路換熱,電池循環水路中熱量通過水泵驅動與電池包換熱。
電池加熱系統中,溫度傳感器位置集成至電池包進水口,以反饋出電池水循環的最高水溫。該回路電池水循環滿足水泵出口高溫水優先流經加熱需求高的部件,優先流經工作時發熱功率高的電池包。根據電池電芯的溫度、電池包進水溫度、PTC出水溫度等輸入信號,經過控制系統輸出電池水泵轉速、水暖水泵轉速、PTC加熱功率等信號。
2 AMEsim仿真模型及驗證
2.1 仿真模型
該低溫制熱仿真模型由乘員艙模型、水暖回路模型、電池回路模型以及相關控制模型組成。乘員艙回路根據工況的不同來模擬在不同車速和環境溫度下大氣環境與乘員艙內前排以及后排室內氣體的熱交換仿真。水暖回路由暖風芯體、PTC、三通閥、水暖水泵等組成,可根據乘用車的需求調節三通閥開度和水泵轉速以控制回路熱焓流率。其中PTC水路流阻特性參數、三通閥各支路流阻特性、水泵揚程流量特性、暖風芯體水套流阻特性均由相關單體測試試驗采集獲得。電池回路由發熱元件模型、膨脹水壺、電子水泵等組成循環回路。其中板換流阻特性、水泵揚程流量特性、電池包流阻特性均由相關單體測試試驗采集獲得。電池包流阻特性如圖2所示。

圖2 電池包流阻特性
在低溫制熱系統的原模型中,前排腿部溫度過高將會通過PID控制器限制PTC功率的輸出。三通閥的開度由電池升溫信號經過處理后,通過PID控制器輸出其開度控制信號。
在低溫加熱過程中,熱風經過暖風芯體從乘員艙前后排風口吹出,到乘員艙前排腿部位置,有一定的熱量耗散,因此,乘員艙模型需要利用對標測試數據進行標定,通過標定改變乘員艙模型自身屬性參數,減小與實際模型之間的誤差。圖3為相關模型標定結果。
為了保證暖風芯體仿真模型、板換仿真模型能夠模擬真實的換熱性能,需要對其進行標定,并把標定好的參數應用到模型中。此外PTC在水暖回路中的制熱功率、電池包在電池回路中的吸熱功率均需要相關對標測試數據對仿真模型進行標定。系統模型建立后,測試驗證系統制熱性能達到要求,完成仿真。主要仿真參數如表1所示。
2.2 試驗
為了驗證模型的準確性,在環境倉內進行采暖性能模擬臺架試驗。仿真模型中的PTC、三通閥、水泵的控制邏輯與試驗保持一致,仿真與試驗保持在同一工況下。
2.2.1試驗準備
試驗開始前根據實驗規范選擇測量點并布置相關儀器設備。安裝座足部溫度探頭時,安裝于座椅位置中間,距離地板表面20~50 mm,前后方向距駕駛員頭部測溫500 mm處。試驗前按照電動汽車有關技術規定,對車輛進行技術檢查和保養。試驗開始前保證電池SOC不低于90%。
2.2.2試驗方法
1) 浸車降溫階段。將車輛固定在底盤測功機上,確保試驗人員和駕駛員的安全。在環境溫度為-20±1 ℃條件下浸置6 h以上,使電池充分冷卻,電芯溫度達到20±3 ℃,電芯最大溫差≤10 ℃,即完成車輛冷車。
2) 溫升階段。司機進入車內,關閉門窗及通風孔,采暖裝置及風量開啟并處于最大位置,整車施加測試質量滑行阻力曲線,啟用吹腳外循環模式,按表2工況要求進行試驗,全程記錄各測量點數據。

表2 試驗工況
根據相應試驗規范條件,對乘員艙進行采暖性能試驗時,首先對其浸置,然后按照工況進行試驗。在仿真時,可以直接設置乘員艙內的初始狀態,前后排初始溫度設為-20 ℃。電池初始溫度設為-20 ℃。相關試驗與仿真結果如圖4—5所示。

圖4 乘員艙前排腿部溫度仿真與試驗曲線

圖5 電池電芯溫度仿真與試驗曲線
在環境溫度為-20 ℃環境下的采暖試驗中,仿真結果與試驗數據大體吻合。由于實際中的乘員艙為三維立體結構,艙內溫度受到內部氣流流動的影響。在一維模型中無法對流體進行精確化計算,將其看作是一個穩態的內部氣體容腔,仿真得到的溫度信號響應落后于實際出風口采集到的腿部溫度。
在車輛低溫起動時,乘員艙溫度在前400 s時間迅速上升,實際出風溫度出口處的腿部溫度值響應快于仿真值,但當艙內溫度趨于穩定時,在1 300 s左右溫升曲線速率逐漸平緩,仿真值能夠很好地反應實際艙內溫度,而當在2 400 s車輛怠速時,實際測試的出風口腿部溫度值的升高響應也稍快于仿真得到的溫度信號值,在2 600 s后前排腿部溫度與后排腿部溫度仿真值與測試值的差值逐漸降低。電池溫度的仿真值與測試值溫升基本一致。
3 模型優化
在采暖時保證乘員艙和電池包制熱性能的前提下提高采暖系統的經濟性,通過AMEsim軟件在原模型三通閥控制以及PID控制PTC發熱功率的基礎之上,加入電池回路水泵與水暖回路水泵實時動態控制;為了優化系統的經濟性,采用MPC控制PTC制熱功率[7],引入電驅回路余熱到水暖回路中,降低PTC制熱負荷。優化后的低溫制熱仿真模型如圖6所示。

圖6 優化后的低溫制熱仿真模型示意圖
3.1 控制策略優化
控制系統由Matlab/Simulink模塊搭建,其部分控制結構如圖7所示。

圖7 部分控制結構示意圖
在AMEsim仿真模型中,車輛熱管理模型的前排腿部溫度、水暖回路循環水溫度、電池回路循環水溫度以及電池電芯溫度作為控制部分的輸入,通過Matlab搭建的控制器輸出PTC發熱量、三通閥開度、回路中水泵電機轉速的控制信號。PTC的控制部分以前排腿部溫度、乘員艙內目標溫度作為MPC控制器輸入,輸出PTC發熱量控制系數。本系統在保證達到制熱性能的前提下對原模型控制器的部分結構做出了進一步優化,設計了3種不同的控制策略。表3—5中:Tf為乘員艙前排腿部溫度;Tr1為乘員艙目標溫度;Tb為電池包電芯溫度;Tr2為電池包電芯目標溫度;Tw為電池循環水溫度;Tmin、Tmax分別為電池循環水目標溫度范圍的最小值和最高值;Ti(i≥1)為電池包電芯在溫度逐漸升高情況下下傳感器測得的溫度。
3.1.1三通閥的控制邏輯
三通閥由乘員艙前排腿部溫度Tf、電池電芯溫度Tb以及電池冷卻水進水溫度Tw作為參考信號,基于選擇的3種不同策略,依據輸入信號得到的乘員艙和電池的狀態,輸出相應情況下系統的最優控制信號。通過控制三通閥開度,來確保電池與乘員艙熱量的合理分配,以改善制熱過程的制熱性能與系統能耗。表3中三通閥開度輸出有4種模式,電池側低開度(Bl)、電池側高開度(Bh)、PID控制三通閥開度(PID)、并行開度。三通閥的控制邏輯見表3。
3.1.2電池水泵控制邏輯
乘員艙電池水泵以前排腿部溫度Tf與電池電芯溫度Tb作為參考信號輸入,電池溫度處于由低到高的不同區域對應著水泵占空比由高到低的等差分配。在選擇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的情況下,由于車輛底盤結構中電池回路的管路部件與室外大氣有著很大接觸面積。為了避免電池回路在僅需乘員艙加熱時與外界有過高強度的換熱,通過參考前排腿部溫度控制水泵轉速,確保在乘員艙溫度未達到目標溫度之前,降低甚至切斷電池循環回路的換熱。在其他策略情況下,則以電池電芯的狀態作為參考。電池水泵控制邏輯見表4。

表4 電池水泵控制邏輯
3.1.3水暖回路水泵電機控制邏輯
水暖回路水泵電機以前排腿部溫度Tf與電池電芯溫度Tb作為參考信號輸入,當乘員艙與電池都未達到目標要求,則提高水暖水泵電機占空比,增大乘員艙、電池循環回路與水暖回路冷卻介質的溫差,提高各回路間的熱交換強度。當乘員艙與電池所需的制熱負荷較低,則降低水泵電機占空比,以改善回路電子水泵的經濟性。 水暖回路水泵電機控制邏輯見表5。

表5 水暖回路水泵電機控制邏輯
3.2 余熱利用
通過回收電機余熱為乘員艙制熱來減少制熱功耗的空調系統,能夠有效增加空調系統在較低環境溫度工況下的制熱能力[9]。車輛啟動運行后,電機工作產生的余熱量是可觀的,在電機長時間高功率運行的狀態下,電驅回路熱量快速累積,正常情況下則是利用低溫散熱器帶走電驅回路熱量。板式換熱器結構的引入使得電驅回路在有余熱可利用的情況下將熱量代入水暖回路中,以減輕車輛在低溫環境下運行時PTC制熱負擔。由于電驅回路中循環水在流入散熱器前熱量累積最高,本系統在電驅回路散熱器前集成板式換熱器,以高效地利用電驅余熱量。此系統在車輛需要制熱時能夠提高系統制熱量的同時,降低了低溫散熱器不必要的能量消耗。
電驅回路產生的熱量通過板式換熱器將熱量代入水暖回路中,板式換熱器相鄰板片之間用特制的密封墊片隔開,熱流體間隔的在板間沿著由墊片和波紋所設定的流道流動,不同循環水路的熱流體在各自的通道中通過間隔的板片進行熱交換。
集成板式換熱器內部能量平衡[10]可由式(1)描述:
(1)
式中:u為板換內部的能量;m為板內的總質量;∑Pext為熱流體經過板換這一部件后因體積改變引起的能量變化;∑dmhi為熱流體進出板換,由于熱對流效應引起的能量變化,體現為進入或流出的熱流體對板換內部腔室能量的貢獻,即進出端口焓流率之和,可由式(2)表示:
∑dmhi=dmh1+dmh2
(2)
在板換內部熱流體流動過程中,考慮壓力這一因素會引起流體做功,則∑Pext可改寫為式(3):
(3)

板式換熱器集成至低溫制熱系統中,水暖回路通過板式換熱器利用電驅回路的熱量。為了準確地模擬板式換熱器的換熱特性,需要對其換熱能力進行標定。輸入相關測試試驗值,通過AMEsim標定模塊調整板式換熱器換熱性能的參數,如表6所示。

表6 板式換熱器單體測試試驗值
得到的仿真模型與測試標定結果如圖8所示,誤差控制在3%以內。

圖8 板式換熱器測試標定結果直方圖
4 結果分析
4.1 優化效果
原模型與優化后的仿真模型在2個NEDC工況下的電池SOC變化如圖9所示。由圖可知,車輛在低溫環境下啟動后行駛22 km過程中,對原模型的控制策略以及余熱利用的優化可有效提高系統經濟性,在模型優化后電池電量提高了6%,原模型制熱消耗了22.9%的電池電量,經濟性提高了26.2%。

圖9 NEDC工況原模型與優化模型制熱時電池SOC變化曲線
優化后模型的制熱效果在各策略各環境溫度下乘員艙溫升效果良好,在7 min之內均可達到28 ℃,如圖10所示。高速工況下動力電池最低加熱速率為乘員艙優先策略下的1 625 s內從-7 ℃加熱到15 ℃,大于電池包加熱性能要求25 ℃/h,高速工況下各策略均滿足電池加熱目標要求。低速工況下除了在環境溫度為-7 ℃時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的電池加熱性能在20 ℃/h,其余低速工況均滿足,如圖11所示。對于該車型,隨著環境溫度低于-7 ℃后,電池溫升速率會越來越差強人意,產生續航和動力問題。解決此問題,則需要在短時間內提高電池活性,應該進一步優化熱管理部件或提高PTC功率以在短時間內提供更多的熱源利用量。

圖10 不同環境溫度各策略制熱乘員艙前排腿部溫度變化曲線

圖11 低速工況電池加熱溫度變化曲線
4.2 仿真結果分析
4.2.1制熱性能
1) 環境溫度的影響。
隨著車外環境溫度的改變,不同策略以及駕駛工況的不同,乘員艙與電池溫升有著明顯的區別。同一環境溫度下高速工況電池的溫升速率高于低速工況,到達目標溫度總體時間也大幅縮短。由圖12可知,從車外環境溫度變化上來看,溫度越低同一策略下帶來的溫升效果有以下趨勢:無論是乘員艙還是電池,溫升速率基本不變,但達到目標溫度所需時間隨著溫度的降低而顯著增加。

圖12 各環境溫度下不同工況制熱時電池溫度變化曲線
2) 控制策略的影響。
如圖10所示,同一工況下,不同策略對電池或乘員艙的溫升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動力電池的溫升上,例如在高速工況下環境溫度為5 ℃時電池優先加熱策略比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快23 s,在環境溫度為-1 ℃時快176 s,在環境溫度為-7 ℃時快292 s;在乘員艙室內的溫升上,有著類似的趨勢,環境溫度越低,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比電池優先加熱策略的加熱時間更快。
并行加熱策略在乘員艙與電池的加熱上的趨勢與其他策略類似,所需加熱時間的長短處于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與電池優先加熱策略之間。對于乘員艙和電池的總體加熱時間上來看,同一溫度下,電池優先加熱策略時間最短,并行加熱策略次之,乘員艙加熱策略時間最長。值得一提的是,并行加熱策略在達到目標溫度后有大幅波動,出現波動時車輛處在環境溫度較低的情況下。
3) 運行工況的影響。
由圖12分析,從車輛運行工況上來看,高速工況下的電池溫升效果明顯優于低速工況,各溫度下120 km/h工況比40 km/h工況平均快15 min。乘員艙溫度升到目標溫度所需時間基本一致,但達到穩定后有段時間會有小幅度波動,如圖10所示。這是由于電池達到目標溫度后電池側三通閥關閉導致的暖水回路溫度的短時間升高的原因,而且溫度越高,電池溫升所需時間更短,波動出現的時間越提前。
4.2.2系統經濟性
1) 環境溫度的影響。
如圖13所示,從結果分析上來看,環境溫度越低,系統的整體能耗越高。在環境溫度為-7、-1、5 ℃時,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制熱完成后的電池電量分別為59.81%、68.38%、70.27%。電池優先加熱策略在制熱完成后在對應的環境溫度下的電池電量分別為57.87%、64.19%、70.28%。因為環境溫度過低,乘員艙與外界環境溫差更大,室內同一目標溫度下由于外界溫度降低,溫差增大使得乘員艙內新風換熱的熱交換強度增加,導致熱負荷需求增大。

圖13 不同環境溫度各策略制熱電池SOC變化曲線
另一方面,環境溫度的下降,由于純電動汽車上動力電池的質量較大,根據熱量計算公式Q=cmΔt,使得電池的制熱負荷需求顯著增加,這是制熱啟動過程中能量損耗的主要原因。引起注意的是,隨著環境溫度的升高,電池優先加熱策略和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在能耗上的差距逐漸變小,在環境溫度為5 ℃時兩策略能耗無顯著差別。
2) 控制策略的影響。
從控制策略上來看,無論是在何種環境溫度和工況下,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的能耗都更小,其次是并行加熱策略,耗能最高的是電池優先加熱策略,如圖14所示。而且環境溫度越低,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節能效果越明顯,如圖13所示。進一步分析原因,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相比其他加熱策略溫升更快,而該模型中高壓電池主要耗能部件為PTC,乘員艙前排腿部溫度信號直接決定了PTC瞬態功率變化的大小。此外,在寒冷條件下乘員艙內的制熱負荷相比電池要更小,所以用于單一電池加熱所需加熱時間明顯高于乘員艙加熱時間。另外,一旦乘員艙達到目標溫度,勢必也會改善水暖回路中水泵電機的負荷,使得低壓電池能耗降低,加上該系統啟用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時,電池水泵電機在一開始處于停轉狀態,低壓電池能耗會進一步下降。綜上,該模型中有較短乘員艙溫升時間的策略耗能更低,這也是乘員艙優先加熱策略相比其他策略經濟性最優的原因之一。

圖14 不同工況各策略制熱電池SOC變化曲線
3) 運行工況的影響。
如圖15所示,從車輛運行工況上看,同一策略下高速工況的整體能耗低于低速工況的能耗。高速工況相比低速工況而言,乘員艙與外界熱交換強度增加,乘員艙熱負荷需求增加。但由于高速工況下,驅動電機以及控制器等部件在高功率下工作,電池放電功率也增大,其自身發熱量顯著提高。高功率下單位時間內可利用的電驅余熱的累積量相比低功率更多,這一優勢幾乎彌補了高速工況下乘員艙帶來的劣勢,從而進一步減輕了PTC高耗能部件的制熱負擔。由于高速工況低溫制熱系統的電池發熱量多以及電機余熱利用量多的特點,使得系統能耗在高低速工況下有著一定差距。如圖15所示,在電池優先加熱策略下,環境溫度為-7、-1、5 ℃時,高速工況比低速工況的經濟性分別提升了8.2%、7.19%、5.23%。

圖15 不同溫度環境各工況制熱電池SOC變化曲線
5 結論
本文針對某公司某純電車型在低溫制熱過程中的乘員艙與電池的熱平衡進行了仿真,并基于試驗數據對仿真模型進行了驗證。在此基礎上對原仿真模型的控制策略和能耗經濟性進行了優化,通過仿真分析得到如下結果:
1) 優化前的低溫熱管理仿真模型能夠較好地預測搭載PTC制熱系統的乘員艙及電池溫升的動態性能,可以為相關科研工作者提供一種仿真思路。
2) 該模型優化后達到了降低能耗的目的。針對于制熱系統相關部件的能耗分析,在控制策略以及余熱利用結構上的優化,能夠使PTC制熱系統的經濟性大幅提升。
3) 該低溫制熱仿真模型有以下特點:環境溫度的升高降低了系統制熱負荷;合理地選擇控制策略可顯著降低系統制熱過程的能耗;車輛工況會影響低溫制熱,從制熱系統來講車輛運行速度越高,溫升越快,能耗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