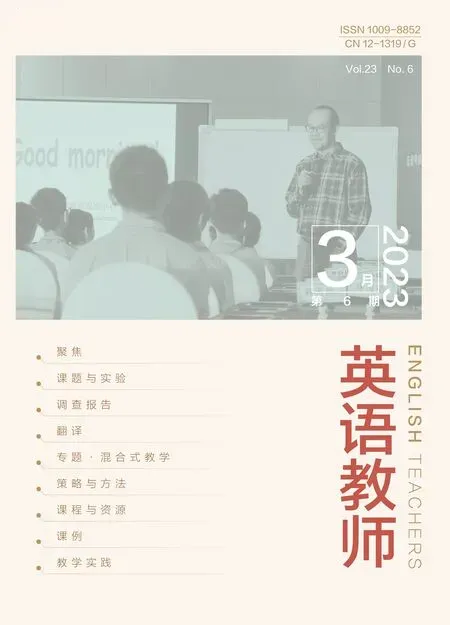節氣術語的英譯與譯名統一
——以《紅樓夢》為例
何佳怡 祁小雯
引言
二十四節氣是我國重要的文化瑰寶,是古代中國農耕文明的產物。它是先人們對時令、氣候、物候變化的觀察和總結,是古代中國重要的知識體系,指導著勞動人民的農耕與生活。2006 年,國務院批準二十四節氣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它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2022 年,第24 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舉行,開幕式倒計時別出心裁,以“二十四節氣”的形式再一次向世界顯示中國的文化底蘊。
在日常生活中不難發現,二十四節氣的英譯版本多種多樣,中國天文學會·全國科技名詞委、香港天文臺、外研社、中國氣象局等機構發布了各自的參考譯本,除了少數節氣具有較一致的譯名外,大多數節氣有多個譯本。這種譯名不統一問題對文化傳播和文化走出去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節氣術語的規范化勢在必行。
《紅樓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生動反映出中國封建社會的人生百態。作為中華文化的瑰寶,其藝術成就和思想文化底蘊吸引了各領域學者的注意。《紅樓夢》中多次出現了與節氣有關的情節,并展現了不同節氣的人文風俗。通過對比楊憲益夫婦和霍克斯的《紅樓夢》英譯本,分析譯者對小說中節氣術語的英譯,并由此探討節氣術語的統一問題。
一、二十四節氣文化內涵研究
根據古書記載,二十四節氣在先秦時期就初具雛形,因研究條件和生活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其名稱并未得到統一,整個知識體系也沒有完全建立(查有梁2018)。有研究顯示,第一次完整提出二十四節氣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淮南子·天文訓》,其中詳細記載了二十四節氣的運行體系。
對二十四節氣的研究從未停止,自2016 年被列入非遺名錄后,它又在學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潮流,涉及文化、中醫藥和氣象等領域。隋斌和張建軍(2020)梳理了二十四節氣的發展脈絡,總結了其內涵特質,贊揚了其價值和作用,并提出了對二十四節氣保護傳承的有效措施。王研霞(2021)依據圖像敘事模式,分析了二十四節氣的文化內涵,認為文化的傳播要迎合時代,二十四節氣的視覺化正好符合這一要求。李靜和張光霽(2019),馬楚龍和李風森(2019),蔡怡航、劉佳敏、唐麗娟等人(2019)從節氣與中醫的角度,分別探討了節氣與中藥方劑選擇的關系;節氣對疾病防治、預防養生的重要性;節氣理論對中醫臨床診療的指導作用。許多學者在氣象方面對節氣的探究著眼于特定地域,因此不再贅述。
譯者對節氣譯名的研究也從未止步。有學者研究發現,早在20 世紀初期,《華英詞典》就對“二十四節氣”作出了翻譯,但廣大譯者似乎對該版節氣翻譯持保留態度,各種節氣翻譯仍然層出不窮。余恒(2014)對比了三大不同體系對“二十四節氣”的翻譯,發現部分節氣的譯法雖然已達成共識,但是差異仍然存在,主要體現在“大/ 小”等詞的表達上,他追根溯源,為二十四節氣譯名的統一工作提供了參考意見。張君遲和田傳茂(2019)對比分析了5 個已出版的“二十四節氣”譯本,并歸納總結了7條節氣術語譯名統一原則,依據專名化、科學化、規范化、規律化、概括化、簡潔化、審美化的原則,提供了自己對節氣的不同譯版。張志艷(2021)意識到文化翻譯過程中文化空缺的現象,分析了文化空缺造成的節氣術語的困難,并針對這些難點總結了幾點翻譯策略,促進二十四節氣的文化傳播。
二、《紅樓夢》中的節氣術語翻譯
國內對《紅樓夢》的研究數不勝數,內容涉及方方面面。就術語翻譯而言,學者們對《紅樓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術語及中醫藥術語的翻譯,對于著作中節氣術語的翻譯研究則較少。
基于紹興文理學院語料庫,對《紅樓夢》中出現的節氣作了統計。在小說中,部分詞語除了表示節氣外,還有其他含義,如“大雪”,在文中出現時常伴隨“大雪地”“豐年大雪”“這么大雪”等,根據語境,可知“大雪”指的是一種自然現象,而不是節氣,因此對此類語料進行了刪選,最后《紅樓夢》中節氣的統計結果如下表所示:

《紅樓夢》中的節氣及出現頻次
如上表所示,《紅樓夢》中共出現了10 個節氣,包括立春、雨水、春分、清明、芒種、白露、秋分、霜降、小雪、冬至。下面依據例子,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分析楊憲益夫婦(以下簡稱“楊”)和霍克斯(以下簡稱“霍”)對《紅樓夢》中節氣的翻譯。
例1: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曬干,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
楊:These four kinds of stamens must be dried in the sun on the followingvernal equinox,then mixed well with the powder.
霍:and dry them all in the sun on the day of thespring equinoxof the year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year you picked them in.Then you have to mix them with the powder I told you about and pound them all up together in a mortar.
例2: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
楊:and if she gets through thespring equinoxwe may expect a cure.
霍:I should say that if she can get past thespring equinox,you could look forward to a complete recovery.
例3: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際,必犯嗽疾。
楊:Daiyu,who suffered from a bad cough aroundevery spring and autumn solstice.
霍:As for Dai-yu,twice every year,following thespring and autumn equinoxes,she suffered from a recurrence of her old sickness.
以上三個例子是楊憲益夫婦和霍克斯對“春分”的翻譯。“春分”在古代又稱“日夜分”,顧名思義,就是春分之日,日夜平分。霍克斯對“春分”的翻譯前后一致,都是Spring Equinox。在英語國家,equinox 表示二分時刻,即太陽通過天赤道與黃道相切的兩點中的任意一點時,晝夜長短幾乎相等。雖然英美國家沒有春分這一節氣,但是有相同的天文概念,因此譯者采用了直譯的方法,用spring 修飾,很好地區分了春分、秋分的概念。反觀楊憲益夫婦對“春分”的翻譯,在三個例句中,對春分的處理各不相同。根據《美國傳統詞典》,vernal 指“屬于、關于或發生于春天的”,與spring 是近義詞,兩者可進行互換;solstice 在英語中表示一年中太陽離赤道距離最遠的時刻,對應的應該是中文中“至”這一概念,因此楊憲益夫婦在例3 中對“春分”的翻譯存在偏差,會造成讀者的誤解,也不利于這一傳統概念的傳播。
例4: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
楊:You also have to collect twelve drains of dew on the dayWhite Dew,twelve drains of frost on the dayFrost Falls,and twelve drains of snow on the daySlight Snow.
霍:Then you have to collect twelve drams of dew on the dayWhite Dew in the ninth month,twelve drams of frost atFrost Fall in the tenth,and twelve drams of snow atLesser Snow in the last month of the year.
例5: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才過小雪時。
楊:Slowly drooping below congealed dew and heavy frost.Just after a feast in its honour onthe Day of Light Snow.
霍:The feasting over and thefirst snow fallen,The flowers frost-stricken lie or sideways lean.
例4 是小說中出現節氣術語最密集的段落,該情節是薛寶釵在講述“冷香丸”的制作,這些材料的珍貴展現了她病癥的特殊。根據上述兩個譯本及已收集到的四個官方機構(中國天文學會·全國科技名詞委、香港天文臺、外研社、中國氣象局)公布的節氣術語翻譯來看,譯界對“白露”的翻譯似乎已達成共識。“霜降”預示著天氣轉涼,大地開始出現初霜現象,因此兩個譯本對“霜降”都采用了直譯的方法。Frost fall 基本表達出了“霜降”的內涵,“初”這一概念卻被省略。根據原文可知,“冷香丸”材料難得,十分珍貴,因此“霜降”中“初次落霜”的概念尤為重要,此處省略確有不妥。因此認為First Frost更恰當。“小雪”意味著有些地區開始降雪,夜凍晝化,雪量加大。例4 中,兩個譯本分別將“小雪”譯為Slight Snow 和Lesser Snow,slight 和lesser 都有程度輕、數量少的意思,能很好地與“大雪”形成對應。在例4 和例5 中,楊憲益夫婦譯本簡潔明了,對“小雪”進行了直譯。例4 中,霍克斯譯本增譯了部分限定語,更加清晰明了地展現了“小雪”的時間,但在月份上似乎不太準確,“小雪”通常在11 月,而“大雪”在12 月,即一年的最后一個月。增譯部分本是為了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文化的內涵,結果適得其反,造成目標讀者對傳統文化的誤解。例5 中,霍克斯對“小雪”進行了意譯,他的譯文簡單明了地展現了“小雪”作為中國節氣的文化內涵,即初雪降落的時候,是不錯的譯文。
例6: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
楊:Nowthe Clear and Bright Festivalcame round again.Jia Lian,having prepared the traditional offerings,took Jia Huan,Jia Cong and Jia Lan to Iron Threshold Temple to sacrifice to the dead.
霍:It was the day ofthe Spring Cleaning festivaland Jia Lian,having prepared the usual offerings,had gone with Jia Huan,Jia Cong and Jia Lan to the Temple of the Iron Threshold outside the city to clean the family graves.
例7: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
楊:Through tears she watches the stream,Onthe Clear and Bright Day;A thousand lithe east wind blows,But her home in her dreams is far away.
霍:In springthrough tears at river’s bank you gaze,Borne by the wind a thousand miles away.
清明節與節氣中的“清明”在同一天,在當天,大家提到“清明”多是將它看作節日,卻忽視了“清明”也是一個重要節氣。事實上,兩者密不可分,共同構成“清明”的傳統文化內涵。每逢清明,氣候轉暖,草木生長,天清氣朗。清明時節民間有許多活動,如掃墓、放風箏、吃寒食、踢蹴鞠等。例6 中,霍克斯將“清明”翻譯為Spring Cleaning festival,既指出了清明的時間,又指出了相關的活動習俗,而且較好地照應后文clean the family graves。其中的插入語進一步補充了清明大家不僅要掃除灰塵、清除雜草,而且要攜帶酒食果品進行供祭,并在祖先墓前焚化紙錢等文化習俗。因此,霍克斯的譯文更完整地展現了中華傳統文化。例7 中,楊憲益夫婦將“清明”譯成Clear and Bright Day,從氣象方面展現出清明天清氣朗的特點,對于缺乏節氣知識背景的目的語讀者,這個譯文就顯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霍克斯將“清明”譯為in spring,對其進行了模糊處理,即將“清明”泛化,只是簡單表達出時間概念,也沒有很好地展現其深層內涵。
綜上所述,霍克斯對節氣的翻譯更貼近讀者,通過直譯、增譯等手段,清晰展現了節氣的時間、習俗等特點,這更有利于節氣中文化內涵的傳播。楊憲益夫婦對著作中的節氣術語更多采用的是直譯,雖然表達出部分內涵,但是仍有信息的缺失。值得一提的是,兩個譯本在大多數多次出現的節氣術語上做到了譯文一致,偶有不一致現象發生。
三、節氣術語譯名的統一問題
術語名詞規范化工作開展已久,吳鴻適(1988)就外來術語的漢譯問題提出了幾條原則,指出科學技術名詞的定名應遵循科學性、習慣性、系統性和符合漢語特點等原則。除了術語的譯入,術語的譯出也不可忽視。郭尚興(1992)就中國文化術語的英譯問題進行探討,認為英譯文化術語時,若出現語義空白情況,可通過音譯解決;指出翻譯文化術語時應保持文化的對應或近似對等,若是世界性文化術語(如宗教術語),應考慮術語的同一性。郭尚興(2001)進一步就中國傳統文化的跨文化翻譯進行了思考,認為譯者在進行文化的跨文化翻譯時,應注意民族文化的特征,從文化和形神結構方面分析民族文化的核心內容,充分遵循跨文化翻譯的原則,減少文化虧損。章思英(2016)認為文化術語的翻譯應充分借鑒漢學家及前人的翻譯成果,這樣能更好地促進文化術語的傳播與接受;同時他指出,在具體語境中,文化術語翻譯可以具有不唯一性。
節氣術語是文化術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文化術語的英譯原則對節氣術語的翻譯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文化術語的英譯是為了實現文化走出去,因此在宣揚文化內涵的同時,目標語讀者的接受度應得到考慮。也就是說,在翻譯節氣術語時,首先,要考慮對方文化中是否有對應的概念,如“分”和equinox,兩者共享一個天文概念,具有很好的對應效果,能讓讀者輕松領悟其中含義。其次,要實現譯文的神形兼備,既要實現內容的對等,又要滿足形式的對等。當然,節氣術語的翻譯也應遵循術語的簡潔性原則,即用簡短的語言表達其中豐富的文化內涵。
結語
針對節氣術語的翻譯,楊憲益夫婦和霍克斯主要采用直譯和意譯的翻譯策略,盡量實現讀者接受度與文化傳播的平衡。同時,關注源語和目的語國家術語的對等或近似對等現象。例如,“分”的翻譯,雖然英美國家沒有“春分”“秋分”的節氣文化,但是大家共享著“分”的天文概念,因此譯者在直譯這類節氣時選用了目的語中的對等詞。除了直譯與意譯,譯者還輔以增譯的翻譯策略,通過解釋節氣的時間、習俗等信息,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術語中的文化內涵,從而實現文化的傳播。
《紅樓夢》的研究方興未艾,學者們從多角度對這部文學著作進行了剖析研究,其中蘊含的豐厚中華文化內涵是其翻譯與傳播的一大難點。二十四節氣在華夏文明的發展變遷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節氣術語專名化、規范化問題始終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