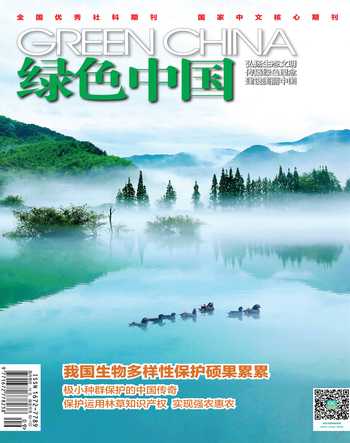五福潭
卜谷

登臨一些普通風景,有時也需要極大的決心和勇氣。往往是那些過程頻頻賦普通以不凡,予風景以神秘、神奇、神采。五福潭,就屬于此類。
五福潭是深山老林里一座深潭的名字,又是按“五福”取名五座水潭的代名,也是一個自然村名。
詩與遠方無覓處
五福潭,曾經是有路的,山徑、古驛道、機耕道。荒蕪十年,有的路段被山洪沖毀、掏空,裸露出嶙峋山骨;更多路段被冬茅、野草、樹枝完全遮沒。只有老曾開四輪驅動的“皮卡”能走一段,因為路是他修的,然后就只能徒步。不光用腳走,還得用手爬、拽。茂密的冬茅鋪天蓋地包裹了石板路,像搭了個密實的雨棚。人就得彎曲腰身一段八九米,一段十幾米地爬行通過,偶爾與驚詫的山雞、野兔對峙。
風景仍是風景。站立在大山隘口仰望,五福潭周圍五座山峰如五只老虎,真是氣吞山河如虎,十分雄偉險峻。
五福潭又叫五虎潭、五瀑潭,這些名字關乎信念、歷史、地形地貌諸多蘊含。所有的風景秀麗都有季節性,在季節中轉換,不同季節就是不同的風景。
五瀑潭屬于春天。春雨絲絲,春潮涌動時節,春暖花開,瀑布在隆隆春雷中覺醒,在盛開的映山紅中飛騰。唯有這個季節,五條瀑布才能同時展翅,水花迸濺,成為五條騰飛的玉龍,五福潭才是真正的五瀑潭。
我有理由說五福潭最美的是冬季。2023年元月再次踏入五福潭,我看見大片臘梅在原野綻放。山道伴隨山溪蜿蜒,梅林伴隨山道蜿蜒。一道彎曲的山谷,便有幾株十幾株臘梅意外地展現,讓人一陣陣驚喜。我沒想到這原始的山谷會有十米多高的野生臘梅,沒想到臘梅能夠長得那么龐然高俊,沒想到濃濃臘梅香氣陣陣,把整個山谷包裹。
人顯得渺小,自然顯得偉大。讓人感覺這是迷幻的現實,是詩境,充滿濃郁詩意。或許這正是寫詩的地域,這里也是遠方。是許多人日夜念叨、向往,卻無處可尋無處可覓的詩與遠方。
竹筍 大山的精靈
半個世紀前,我隨媽媽下放來過寧都縣青塘鎮坎田村五福潭。五眼水潭如五個處子,靜靜地張著五個深情眸子與13歲的我對視。此后,我常常奔走于水潭間,隨著清澈的泉水第一次融入大山與鄉村生活。每天在五福潭18號院墻旁邊的那眼水潭飲用、洗滌、澆灌,嘗試著許多個人生第一次,礱谷、磨豆腐、打糍粑、砍柴、挖竹筍……
竹筍不愧是大山的精靈。有個謎語說竹筍:“小時層層包 ,大時節節高 ,初生當菜吃 ,長大成材料。”那年春節,我穿行于出門即是上山、下山的板石路,往來于村民、鄰居家,籌備年貨。媽媽忙忙碌碌每日籠蒸、油炸、沙炒,我在灶下燒火。有一天,胯下的竹椅突然懸起來了,坐下去,又被頂起來。是誰在調皮搗蛋呢?用火光一照,竟然是一根粗壯的竹筍,不知鉆了多遠鉆了多久,從地底下竄入屋里與我游戲。
如今,18號大院內的房屋早已坍塌,成為毛竹的家園。去往院門十余米道路,被密密實實的冬茅扎根為高大、堅韌的屏障。帶路的老陳是名退伍軍人,有一股虎虎生威的斗志。用腳踏、手掰、身體滾,硬生生地擠兌開一條縫隙。我們便沿著這條“路”前進,四腳著地,連滾帶爬回到曾經的家,兩手被冬茅劃開一道道血痕。
處處小心翼翼,處處不小心。我在原來的住房一腳踩著松軟空地,卻是個螞蟻窩。一群群大黑螞蟻傾巢出動,分幾路襲來,我只得像個侵略者頻頻后退。
延續百年的綠色童話
一把燒荒的火,紅火了五福潭最初的家園,延續了500年煙火。五福潭村是客家村,全部姓陳。明朝宣德8年,陳氏遷入五福潭時才3戶,最多時近百戶。又因林木、鎢礦業務擴大陸續遷出。
五福潭地廣人稀,長長的溪流似一根長長的扁擔,一頭一尾擔著4個鎢礦采礦坑口。五福潭村沿潭、溪而建,隨礦山而興、盛,又隨礦山關閉而衰、亡。漸漸地,五福潭回到了它的前世今生。從500多年前“人進林退”的紅色童話相仿,正在演繹“人退林進”退耕還林的綠色童話。偌大的村莊不斷縮小,10年前還有兩戶,如今成為空村。僅存的幾幢土屋有如孤島,行將被綠濤林海吞沒。
老陳告訴筆者:61平方公里的坎田村,21個村小組中的五福潭、陳玉地、高斜、石古塘、靜石5個小組,已經在扶貧工程中整村搬遷。有趣的是,這些易地搬遷農戶并非全部遷入坎田村,而是根據其意愿有13戶54人遷入青塘鎮保障房,11戶54人遷入寧都縣城保障房,還有數十戶隨打工的兒女遷往贛州、廣州、深圳……與其祖先大遷徙的路線、性質恰恰相反。礦山、村莊消退,治理仍在進行。原王前壩坑口的尾砂廢渣區,正進行8萬平方米的綠地修復,在大自然中演繹著綠色浪漫、綠色童話、生態詩歌的新篇。
返程,又來到大山隘口。山谷的風徐徐吹拂,能嗅覺到臘梅暗香陣陣,似在送行,送別那半個世紀的似水流年。
回望五福潭,已不復存在。水潭仍在,5座虎頭山峰仍在。對于螞蟻、山雞、野兔,五福潭是安全舒適的新家;對于大自然,是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碳中和、碳達峰;對于筆者,是記憶深深;對于所有人則是一頁全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