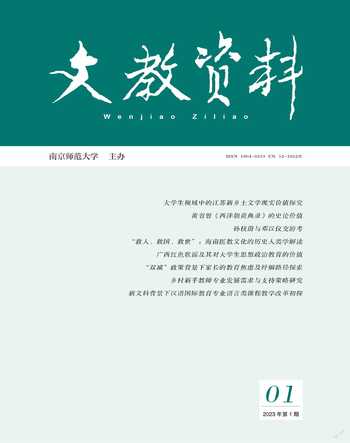孟子美學思想中的“三重生態”探微
楊金松
摘 要:孟子是中國古代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中蘊含濃厚的生態美學思想以及生態審美意蘊。在自然生態方面,孟子提出了“不違農時”的自然生態全美觀;在社會生態方面,孟子提出了“養生喪死無憾”的社會生態和諧觀;在精神生態方面,孟子提出了“充實為美”的精神生態教育觀。三者逐級生發,互相循環,共同構成更廣闊意義上的生態和諧之美,最終使人與自然和諧依生、人同社會生態共生、人的精神深入整生,逐步實現“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萬物美生之境。
關鍵詞:自然生態 社會生態 精神生態 孟子美學
20世紀伊始,生態問題就已進入人們的視野。自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生產力飛速提高,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忽視生態的問題孟子思想中蘊含的豐富的生態理念,正可以對當下的生態現狀予以啟發。
儒家學說是一門關乎“人”的學說。孔子的核心思想便是“仁”,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對“仁”的釋義為:“親也。從人,從二。”[1]儒家學者從血緣之愛引申到人與人之間的愛,然后再從人與他人之間的愛發展到人對社會的愛,進而升華為人對世間萬物的愛,最終使“仁”超越了基本的自然血緣內涵,逐漸變為有普適性的范疇,而孟子則將其生態內涵發揚光大。
魯樞元先生在著作《生態文藝學》中將生態系統分為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而這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某些思想不謀而合。中國哲學的一大特點就是對人自身、人和他人、人和環境、人和社會以及人和宇宙的探討,而自然生態的構建勢必需要人參與其中,因為人自身就是生態的一部分,社會生態則更需要人的參與。
人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而存在,“社會性”是人類的本質屬性之一。人與人之間的生態關系必定會影響到社會生態的發展,而后的精神生態則是人對自身思想境界的構建,進而從個人精神的圓滿輻射到整個社會。這三者形成了一個循環:自然生態的完好促成社會生態的和諧,社會生態和諧為精神生態搭筑了溫床,而精神生態的充盈又使人們的審美和道德愈發完善,反過來愈發重視并反哺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建構過程。
一、“不違農時”——孟子的自然生態全美觀
自然生態是自然界各部門組成的生態系統相互平衡的一種狀態,體現了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在中國哲學中,對于“人與環境”這一問題的審視古已有之,而孟子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孟子注重“時”與“物”的關系,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他提到“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2]。
他強調人要遵從自然界的運行規律,以求保護自然環境,實現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可以看出,“不違農時”的自然觀表現了對生態規律的掌握和遵循,是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3]思想的直接體現。
孟子所言鮮明地體現出一種尊重自然、和諧發展的思想,在人自身作為主體去影響自然的時候,如果能夠關注并尊重自然的規律,那么自然也會給人以豐厚的饋贈,從而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相互依存的和諧狀態,顯現出豐富的生態智慧。蒙培元先生說:“所謂‘生的目的性,是指向著完善、完美的方向發展,亦可成為善。善就是目的。”[4]這樣的目的正是孟子自然生態思想的內在呈現。“它強調人們應遵從自然自身的發展演變規律,保護它們的生長。”[5]這即體現為“農耕文明性與自然目的性相和諧”。
孟子對自然生態美的認知也是極為深入的,而且對于生態保護和循環利用問題也有獨到的見解:“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6]孟子細致地描述了“牛山”生態環境的現狀和成因:“牛山”從一座青蔥蒼翠的山巒變為現如今孟子所知道的荒山,其原因在于人們沒有意識到自然物的循環利用也是與人類的生存息息相關的,伐木的時候沒有想著為來年留下儲備,在伐木之后也忽略了草木萌發的新芽,又選擇去進行無限制的放牧,最終造成了牛山“濯濯也”的現狀。孟子認識到人類的生活所需皆源于自然,自然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因而人理應遵從自然物的自身發展演變規律,保護它們的生長。
孟子在這一描述后也下了一個論斷,即“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7],“其”在本質上指向的就是前文孟子所說的“時”。當自然得到充分的養育,就沒有事物不生長,沒有得到應有的養育,則沒有事物不會消亡。在這里孟子旗幟鮮明地指出了應該對自然進行應有的養育,而不是無節制地去消耗自然的資源,只有這樣才不會重演“牛山之木嘗美,而今濯濯也”的悲劇,體現為“人類目的性和自然目的性相適應”。“農耕文明性與自然目的性是和諧的,社會規律性與自然規律性是一致的,人類目的性和自然目的性是適應的……這就形成了人類生態依從自然生態的地球全美。”[8]在人類文明初顯的時期,即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期,其勞作或者說是采集的生態活動形成了食物鏈的最高一級。當人類遵循生態規律與自然依生共存時,此時自然得以循環發展,人類也收獲了足夠的食糧,從人與自然兩個維度來講都是“善”的,而“美善同一”的思想在我國古已有之,故也可以說“人類遵循生態規律,人與自然依生共存”的生態活動是美的。而反之,便是不善的亦是不美的。“這合乎生態系統的規律性和目的性,促進了地球生態美,初成了自發的地球全美走向自律的地球全美的轉機,構成了人類生態依存自然生態的地球全美。”[9]。
這種人類生態與自然生態相互依存的“地球全美”思想,其實就是孟子思想中“因時取物,不違農時”思想的現代化闡釋。這種“全美”是人自身發揚主觀能動性去尊重客觀規律、遵從自然規則而產生的美,是因人類生態的自律匯入自然生態的自律而產生的,表現出 “人與自然相互依生”的古代依生論的美學特征,也顯示出和諧的特質。
二、“養生喪死無憾”——孟子的社會生態和諧觀
社會生態是人與社會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所形成的穩定、平衡的生態系統。人是社會的存在物,社會性也是人的本質屬性之一,因此人與自然的平衡關系是人與社會和諧穩定關系的前提,二者共生,共同促進社會的和諧,為精神生態美的生發給予有力的保障。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是相輔相成、密切關聯的,二者構成了一種涵蓋了自然、人類、社會等多重因素的整體性生態平衡。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集中體現,其中也包含了諸多生態理念。《孟子·梁惠王上》中有這樣一段論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0]這是孟子對社會的美好構想,也是孟子“王道”思想的一部分。其思想內容的本質就是從百姓富裕出發去引導社會的和諧。而因為孟子所生活的時代是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的時代,人的本質力量還很弱小。人們雖然已經脫離了原始人類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開始在自然面前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總的來說,人的力量仍是弱小的。要想使人依生自然,接受自然的饋贈來達到社會富裕,進而使百姓生活和美,以實現政治上的“王道之始”,就要尊重自然的規律。這與上文提及的自然生態之美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充分地尊重自然,在高揚自然生態之美與自然生態之美共生的前提下,這種政治社會生態的和諧美才能夠生發。
換一個角度,拋開“王道”的整體思想,從構成“王道”的家庭來講,單就其描述的生活情狀而言,也是一幅生態和諧而富有詩意的田園風光。五畝之家房前有桑,桑下有雞豚狗彘之畜;百畝之田一片金黃,數口之家足以憑此無饑無寒;天地之中有人有物,有自然賦予大地的一切生機。這正和東晉陶淵明《歸園田居·其一》中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11]相互照應,而這與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的棲居”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周來祥先生對“詩意的棲居”有如下評價:“海德格爾理想著‘詩意的棲居,所謂‘詩意的棲居、審美的生存,實際上不過是和諧的棲居、和諧的生存。”[12]而陳望衡先生在其《環境美學》中也道:“詩意,只是一個比喻,它強調的實際上是審美的生存。”[13]在這樣一個天人相適的環境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必定會對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就像前文所提到的“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樣,必定會作為一個良性的循環注入社會生態之中,而這種社會生態審美的落腳點其實也是在“生態和諧”之中的。
這種“詩意的棲居”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的棲居,它同樣要求在此棲居的人們在進行實踐活動時綜合生態規律和生態目的后產生生態之美。而生態和諧就是生態之美在此時外在于本質的形式,它使生態規律與目的同審美規律和目的相統一,是生態性與審美性趨于同一的形態。孟子希冀著將這種生態和諧之美推廣至全社會,使個體小家的和諧進而達到施“王道”而產生的政通人和的社會生態美。在孟子看來,理想的社會生態便是政通人和的圖景,“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是對其最為精確的描述。
三、“充實為美”——孟子的精神生態教育觀
自然生態之美是通過人與自然的依生基礎而產生的,社會生態之美則是通過人與自然生態共榮共生進而輻射整個社會而產生的,而精神生態之美主要是經由人自身而深入整生的,它看似與前面的自然生態之美和社會生態之美沒有直接聯系,但其實在共同構成萬物美生方面存在內在的關聯。
針對“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的論斷,在社會生態的視野下,我們可能更多地去關注生態和諧能給整個社會帶來怎樣的改變,而在精神生態的視野下,這段論述仍有其獨到的價值。“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這句話中孟子提到了教化的功用和必要意義,把“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概括為“老有所養”。對此孟子也提出了解決方案,那便是“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換句話說即“受教育”。
談到教育這個問題,就必須論及孟子的性善論,即孟子人性論的核心思想。孟子正面論述了人性中善的屬性,并將它上升到人性的主導地位。“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14]依照著這樣的說法,仁、義、禮、智就成為人先天具備的東西,如同人的四肢一樣是先天固有的,這樣從某種意義來說便將“人性本善”的原則先天固定在了人本身。
孟子雖然肯定人先天具有善心,但并不意味著他認為人先天就有良好的道德。善心只是道德的萌芽,如果想使善心之種開花結果,仍需要后天教育的參與。教育就必定會帶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而人得以教化的結果則會對社會與自然產生影響。《孟子·盡心下》中記載:“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15]孟子對于美的解釋是“充實”,即充實人的品德,就是指上文所提到的仁、義、禮、智等美好品質,“美”正是這些品質的直接顯現。
從人自身精神的角度來看,孟子以一種生態的視角對本體的心性加以審視,特別強調了人自身道德修養的重要性。“這里的道德修養是一種藝術化、詩學化的道德哲學”[16],是審美與道德的合二為一。作為審美主體的人,也正是在道德情感的升華與超越中逐漸被美的境界所浸染。只有當人受教育后,在道德上充實、完滿,才能體驗到真正的美,即孟子所謂的“充實之謂美”。
而“充實而有光輝”則是“大”,就是仁、義、禮、智等美好品質像光芒一樣照耀四方。在這里其實人的品格所帶來的影響已經超越了人自身的限制,突破個人狹隘的界限,開始向外界輻射,而“圣”和“神”也是如此。這便是人自身精神境界的逐步完善,在人自身的精神生態充盈之后,便會自然而然地輻射到外部社會,且對社會生態的構建也有極大的作用。
無論是“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還是因為教化使道德的輻射層面逐漸擴大,不可否認的是它們都對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產生了相當大的作用。自然生態的和諧為精神生態的充盈奠定了物質基礎,而社會生態的和諧又是發展精神生態的必然要求,當精神生態充盈之后,人們的生態意識與和諧思想都愈發完善,又進一步使社會生態愈發完滿,故精神生態的完善也是孟子“三重生態”的旨歸。人們要先通過實踐從精神層面生發出依生自然的觀念,從而推及到與社會生態的共生,二者的完備為精神生態的深入整生孕育了基礎,當三者相互循環共同生發后,就產生了以“美生”為主旨的生態和諧。此時,自然生態也隨之得到了更大力度地保護和發展,這樣就將自然生態之美、社會生態之美和精神生態之美構建成一個更為牢固的結構,共同構成“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生態和諧之美。
四、結語
孟子作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有著濃厚的生態審美意蘊,他關于“因時取物,不違農時”的看法、“施仁政而行王道”的理念以及“充實為美”的思想將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及精神生態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展示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我和諧統一的理想生態境界”[17]。三者逐級生發,互相循環,共同構成了更廣闊意義上的生態和諧之美。
對孟子美學中“三重生態”關系的探討可以看出孟子美學以人的內在道德為基石,將人、精神、社會、自然包含到生態關懷之內,在使主體“道德完善和精神完滿的過程中體悟到人與自然萬物的內在一致與和諧統一”[18]。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孟子美學的“三重生態”實質上遵循著“精神—自然—社會—精神”循環往復的內在邏輯,亦可理解為在人的生態意識生發的前提下,主動與自然和諧依生,同社會共榮共生,人的精神深入整生,以期逐步抵達“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萬物美生之境。
參考文獻:
[1]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附檢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161.
[2] [3] [6] [7] [10] [14] [15] (戰國)孟軻.孟子[M].楊伯峻,楊逢彬,注譯.長沙:岳麓書社,2000:5,244,196,196,5,56,255.
[4] 蒙培元.人與自然——中國哲學生態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5] [17] [18]宋寧.孟子生態審美思想研究[D].曲阜:曲阜師范大學,2016.
[8] [9] 袁鼎生.整生論美學[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391.
[11] (東晉)陶淵明.陶淵明集·和陶詩六種[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7.
[12] 周來祥.和諧社會與和諧人生(走向和諧) [N].人民日報,2007-01-06.
[13] 陳望衡.環境美學[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83.
[16] 蒙培元.情感與理性[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