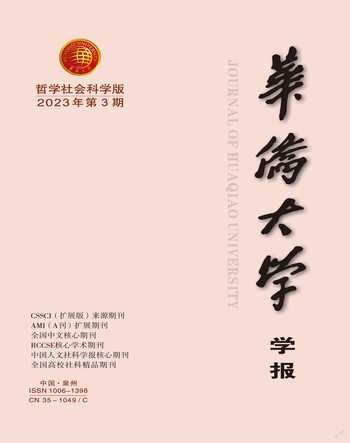共同解釋原則下中國法院解釋稅收協定的路徑構建
摘要:中國作為經濟大國、政治大國、稅收大國,現有105個已生效的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以下簡稱稅收協定),中國法院解釋稅收協定應遵循何種路徑,國內相關法律法規及司法實踐對此并未明確; BEPS公約于2022年9月1日對中國生效,理論上任何一項跨境交易所得都有可能會涉及稅收協定及BEPS公約的適用,中國法院作為稅收協定解釋的重要行為者,必將面臨更加復雜的協定解釋難題。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指引下,中國法院應秉承務實的中間立場,通過共同解釋的國際司法對話渠道,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為基礎,堅持上下文自主解釋優先,構建適合中國的稅收協定解釋路徑,從而處理好國內稅法和BEPS公約及稅收協定的關系,信守國際條約義務,增強協定伙伴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理解和信心,同時維護國家稅收利益以及跨國納稅人的正當稅收權益。
關鍵詞:條約解釋;稅收協定解釋 ;共同解釋原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作者簡介: 鄭林,廈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國際稅法、國際法(E-mail:12920210156029@stu.xmu.edu.cn;廈門36100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稅收治理體系”(202DA104)
中圖分類號:D99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398(2023)03-0114-12
一 構建中國法院稅收協定解釋路徑的必要性
(一)構建解釋路徑是解釋稅收協定的重要手段
法律解釋賦予法律條款以生命力,賦予條款文字以意義,但法律解釋并不是嚴謹的科學,而只是為解釋者提供了各種方法。解釋者按一定的步驟把這些方法組合,對法律進行解釋的過程將建構出不同的解釋路徑,而采用不同路徑將最終影響對事實的裁剪和對法律適用的判斷。構建合理的解釋路徑,是指在解釋過程中,使各種解釋方法得以相互補充而不是排斥或對抗,從而進一步拓展對法律的解釋力。國際條約的解釋因其具有雙重性而更為復雜。所謂雙重性指其既具普遍性,又具在地性。普遍性在于一定意義上條約是國際社會的法律以及共同的法律語言;在地性在于條約需要在不同國家基于不同條件下執行和實施。所有條約解釋者都是在一定歷史、政治和社會框架的背景下解釋條約,這些框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條約解釋。這一解釋在為國際條約注入在地性的同時,也不免使其偏離應有的普遍性。稅收領域的國際條約主要以稅收協定的形式存在,對稅收協定的解釋還因涉及國家的政治立場、稅收利益,在地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只會更加突出,因此構建解釋路徑對解釋稅收協定來說十分必要。
(二)國內法院構建解釋稅收協定路徑時所面臨的難題
晚近以來,由于國際條約規范在規范社會生活不同領域的作用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國際法規則越來越具有 “內向性”,國內法院參與解釋和適用國際條約的機會越來越多,已經成為國際法中顯著的行為者。根據國際法,國家有義務在國內法律秩序中以特定方式行事,而當國家不遵守時,那些受國家非法行為影響的人首先會在國內法院對國家提出挑戰,國內法院是接受這種挑戰的第一站。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國內法院是國際法的 “天然法官”。在跨境稅收中出現爭議時更是如此,因作為國際稅收爭議主要解決渠道的相互協商程序存在效率低、不透明等固有缺陷,納稅人常會選擇國內法院解決爭議。因此國內法院也是稅收協定解釋的重要行為者。但國內法院大多深受本國法域司法體系思維和理論框架的熏陶,也大都是國內稅收及公共設施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在解釋的過程中易從“本國法律文化”中“取材”,易受到其政治立場的干擾;但稅收協定是雙方締結的國際條約,理應探求雙方的內心真意。《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多邊公約》(以下簡稱BEPS公約)是國際稅收領域為數不多的多邊公約,目前已對各締約國先后生效,這為稅收協定解釋注入了更復雜的多邊因素。因此,在后BEPS時代各國法院如何構建解釋稅收協定的路徑,既在最大范圍內維護本國的稅收利益,又維護好跨境納稅人的合法權益,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難題。
(三)中國法院參與稅收協定解釋的現狀及構建解釋路徑的緊迫性
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中國法院處理國際民商事爭議的數量不多,且目前各級人民法院適用民商事條約還存在不同區域的水平差異,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不均衡性,這與中國法律缺乏國際條約適用規則有關,也存在部分法官對國際條約的內容掌握程度不夠等情況。另外,雖然中國司法系統與其他國家司法系統的性質和作用相類似,但其建立在中國本土社會環境基礎上,必然具有中國自己的特色。這種不可回避的特殊性,讓外國爭議當事方往往對中國法院信心不足。稅收協定的司法適用同樣存在上述問題。截至目前中國法院處理的跨境稅收爭議案件相對較少,一方面固然可以歸結于跨國納稅人對中國司法制度缺乏了解,從而對中國法院缺乏信心,較不愿意在中國提起稅務行政訴訟,導致稅務行政訴訟的數量總體較少,稅收協定司法適用的概率也較低;另一方面,即便是現有有限數量的適用稅收協定案例中,中國法院似乎也未明顯意識到稅收協定有別于國內稅法的特點,在適用時未觸及或回避了稅收協定解釋的問題。
但構建中國法院解釋稅收的路徑已是緊迫的現實需求。目前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截至2022年6月底,已有105個已生效的稅收協定,同時加入的BEPS公約于2022年9月1日對中國生效,這意味著BEPS公約以及目前所涵蓋的47個協定將適用于所有相關跨境所得的課稅。如遇到稅收協定問題,不但需要考慮已生效的稅收協定,還需要考慮BEPS公約,因此理論上任何一項跨境交易所得幾乎都會涉及BEPS公約及稅收協定的適用,未來中國必將面臨更加復雜的協定解釋難題。關于稅收協定的解釋工作,國家稅務總局大量借鑒經合組織及聯合國范本注釋的有關內容,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布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但這些文件只能作為中國法院解釋稅收協定的參考,中國也尚未有專門的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對此予以明確規定。同時,構建中國法院解釋稅收協定路徑也是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習近平同志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諸實施,各國有責任維護國際法治權威,依法行使權利,善意履行義務。”如何在運用現有國際經濟規則維護中國合法權益的同時,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與完善,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戰略能否取得進一步成功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國發揮世界影響力、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應有之義;國際法發展的歷史表明,一國司法作用的充分發揮是該國參與國際法治建設的重要方面。內國司法機關是國際規則的實施者,同時,內國司法機關所奉行的法治精神和司法理念,所運用的法律原則和作出的司法裁判,也是國際規則誕生、發展和演變所不可或缺的法律淵源。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應當同時追求建設中國圖景中的法治中國與世界圖景中的法治中國,實現對內事務與對外事務的全面法治,平衡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之間的需求,兼顧中國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利益。這就要求中國法院在審理涉外稅務行政訴訟案件中,要處理好國內稅法和BEPS公約及雙邊稅收協定的關系,既要信守國際條約義務,又要維護中國國家以及跨國納稅人的正當稅收權益,這就對中國法院構建出適合中國的稅收協定解釋路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 中間立場和共同解釋原則:構建中國法院解釋稅收協定路徑的最優選擇
(一)構建中國法院稅收協定解釋路徑應奉行中間立場
1.中間立場之概念闡釋
如前所述,國內法院是稅收協定解釋的重要行為者,因此其對稅收協定解釋既可能促進對稅收協定的解釋更加趨同,也可能增大彼此分歧。而國內法院的解釋究竟會成為分裂的根源還是整合的根源,很大程度取決于國內法院構建解釋路徑時選擇何種立場。國際法下國內法院構建條約解釋路徑的三種立場也同樣適用于國內法院構建稅收協定解釋路徑。這三種立場是:特殊主義、世界主義以及中間立場。特殊主義認為本國利益至上,國內法院在決定如何解釋和適用國際法時,應符合國內解釋規范,而不考慮其他一般解釋方法和具體案件中的解釋是否會影響外國利益相關者和全球福祉。該方法解決了國家自身關切,但不利于全球協調與合作。世界主義認為,不應特別重視本國利益,本國法官應抵制國內壓力,以國際法官的方式解釋國際法。一旦國內法院采用國際法院所使用的解釋規則,國際體系將獲得改善,全球協同法治將得以加強,這一主張看似合理,卻因違背了國內法院的天然本國屬性而成為無源之水。中間立場則是分別就以上兩種立場取精華、去糟粕而形成的折中立場。該立場基于國際法中的人類主權的托管說,認為國內法院在進行條約解釋的時候,應確保那些沒有參加國際條約起草的團體、利益攸關方的聲音得到重視,在維護本國利益和關切的同時,考慮到可能受到裁判影響的他國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該立場并不要求國內法院屈從于這些權益,而只是要求在對本國利益沒有(或沒有重大)負面影響的情況下同步促成他國利益。進一步來說,在當利益激烈沖突時,該立場也贊成最終應優先考慮本國利益,但必須在程序上和實體上對他國利益相關者給予應有的尊重。具體到稅收協定解釋上,該立場即倡導國內法院在解釋稅收協定的時候,應在全球范圍內為本國利益服務;但在強調本國利益的同時,兼顧考慮他國利益及全球福祉。
2.中國法院奉行中間立場的必要性
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已從過去的“站起來的外來者”“富起來的參與者”變成“強起來的引領者”。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他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與之相匹配,中國對待國際法的態度是擴寬位域構建的“合作國際法”,是一種“共贏國際法”。中國將構建國與國之間“合作伙伴”關系視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途徑,而伙伴之間開展的合作必然遵循共贏原則,即秉持“弘義融利”“義利相兼”等理念主義的正確義利觀,做到“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構建稅收協定解釋路徑上選擇中間立場恰是符合有中國特色“共贏國際法”的做法。對國際稅收領域而言,在經濟全球化以及數字經濟的大背景下,早已無法按國別獨善其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國際稅收常態。如果奉行將本國稅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特殊主義,那么構建國際稅收體制將陷入空談。但如果奉行世界主義,采取與國際法院及仲裁庭同樣的路徑,既不符合稅收的本質,也不符合本國的實際,該立場只能是無根之木。因此,中間立場應是中國法院構建解釋稅收協定之路徑的最優選擇。在遵從國際條約的同時,在程序上和實體上對他國利益相關者給予應有的尊重,充分了解他國解釋稅收協定的路徑,在理解他國解釋底層邏輯的基礎上,找到與其合作和共鳴的可能,從而推進各締約國國內法院使用相同或相近的解釋方法、遵循相同或相似的解釋路徑,推動構建共贏的國際稅收治理體系。
(二)構建中國法院解釋稅收協定路徑應遵循共同解釋原則
1.共同解釋原則對解釋路徑構建的重要性
稅收協定解釋中的共同解釋原則,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方締結的稅收協定應只有一種解釋。第一,共同解釋原則是奉行務實中間立場的必然要求。該原則是采用中間立場的自然邏輯延伸,要求各國法院在解釋稅收協定的時候可開展跨國司法對話和比較觀察,借鑒參考締約國另一方(乃至第三國)法院所作出的相關裁判及其優缺點,并使國內法院了解及回應外國納稅人的利益和關切。第二,共同解釋原則是稅收協定目的解釋的必然要求。稅收協定目的在于避免雙重征稅和雙重不征稅,如締約國雙方對協定同一條款解釋有歧義,必然導致協定宗旨落空。因此,締約國一方法院解釋稅收協定時顧及締約國另一方法院對同一條款的解釋,是共同解釋的必然要求。德國學者克勞斯·佛格(Klaus Vogel)作為將共同解釋引入國際稅法領域的權威學者,他認為依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1)條的規定“參照條約目的及宗旨”解釋稅收協定,自然要求各國應尋求最有可能被締約國雙方接受的協定解釋結果,這個過程就是共同解釋。因此,共同解釋要求廣泛和積極地考慮其大多數締結稅收協定國家的立場,目的是對稅收協定達成自主共識。第三,共同解釋原則是遵循國內法解釋原則的必然要求。在國內法語境中,國內法院法官對共同解釋原則并不陌生,其指的是法官裁判案件時應參考國內其他法官類似判決及其推理,并傾向選擇最有可能被普遍接受的解釋,即類案同判。它符合國內法解釋原則,是法律確定性及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對于本國法院固然如此,對于外國法院也應遵循類似道理。
2.中國法院遵循共同解釋原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就中國來說,共同解釋原則雖未在學理界明確被提出,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中國法院有共同解釋的國內法傳統,也有參與國際法共同解釋的意愿和能力。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視法律適用的統一,包括起草制定司法解釋或其他規范性文件、落實類案檢索制度,發布指導案例等等,實際上遵循了國內法語境中的共同解釋原則。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統一法律適用加強類案檢索的指導意見(試行)》系統規定法官檢索類案并制作報告的義務。202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統一法律適用工作實施辦法》中對法官強化類案檢索提出進一步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賦予類案檢索以顯著的功能期待,并將之作為類案運用制度化的主要進路。也就是說,在中國成文法體制中,類案同判是正確司法裁判的“附帶現象”,在效用維度上,類案能夠展現的價值或效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參照”“參考”“示范”“借鑒”乃至“啟發”等多種方式。另一方面,中國法院在國際商事領域已經表現出期待其所作判決能夠讓外國同行援引的意愿,并向國際司法界表達出了愿意尊重國際司法準則的善意、推動共建公平正義的國際司法制度的決心。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明確鼓勵“多語言公布中國法院裁判的典型案例,為各國法院和仲裁機構正確理解和適用中國法提供基礎,增強國際商事主體對中國法律的了解和信任”。并向國際司法界表達出了愿意尊重國際司法準則的善意、推動共建公平正義的國際司法制度的決心。比如,2017年6月8日,在第二屆中國—東盟法官論壇上,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將“在本國國內法允許的范圍內”“努力消除各國商法間的沖突矛盾,最大程度地實現各國商法的協調與互補”“善意解釋國內法,減少不必要的平行訴訟”。一個突出的成就是中國司法案例已經成為豐富國際法實踐的重要來源,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法規判例法數據庫已收錄中國司法案例36件。因此,在稅收協定解釋這一國際法的細分領域,中國有可能也有必要遵循共同解釋原則,通過司法對話,增加締約國對方對中國稅制及司法體制的了解和肯定,從而緩解、調和不同稅制之間的矛盾,動態地補充符合締約國雙方稅收協定目的的解釋素材,填補稅收協定文本的漏洞,為納稅人提供更多穩定的稅收預期,有效提升跨境納稅人對中國稅收制度的信任。
三構建適合中國的解釋稅收協定之路徑:中國法院的對策
(一)中國法院應明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重要地位及適用方式
1.明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
對于國際法院或國際仲裁庭而言,《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至第33條的解釋規則作為條約解釋規則適用于國際條約的解釋似乎是應有之義,但國內法院是否可以適用這些解釋規則及該如何適用?司法實踐中,國內法院在多大程度實際運用這些規則對條約進行準確的解釋?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模糊的。從各國司法實踐來看,不少國內法院解釋條約時并不參考《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和第32條,寧可就地取材適用國內法上的解釋規則乃至合同解釋規則。如果再把問題限縮于國內法院對稅收協定進行解釋,問題則更為突出。中國有學者認為不能因稅收協定是條約,就認為法院的解釋當然應受《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調整。“稅收專約之所以規定不同于《條約法公約》的解釋方法,是因為稅收專約的締約國不允許專約的解釋受到《條約法公約》的約束,以免稅收主權受到限制”。該觀點還認為,即使法院優先采用國內法解釋稅收協定會影響到雙重征稅爭議解決的結果,也不能否認國內法解釋方法的正當性,原因是法院必須維護國家的稅收利益和稅收主權。事實上,由于稅收協定解釋者的異質性以及國際法中文化和法律的顯著多樣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作為共同解釋的橋梁有特別的價值。《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從序言到條約履行,再到條約解釋都規定強調了善意原則,善意原則是支配國際法律義務創立和履行的基本原則,要求“誠實”“公正”“合理”,共同解釋則是對善意原則的延伸和落實。具體來說,《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6條規定了條約的善意履行,而條約的善意解釋是善意履行的前提。“善意履行條約以善意解釋條約為必要前提條件,因為不善意即歪曲解釋條約,必然導致不善意履行條約的結果。……因此,條約必須信守原則,需要加上條約必須善意解釋原則,在適用上才能毫無遺憾。”第31條明確地要求根據善意原則解釋條約;善意原則的適用,不僅在運用條約約文的通常含義、上下文、目的和宗旨、當事國的隨后實踐等解釋方法時應當同時適用善意原則。而且,解釋活動的結果也須善意地加以理解。因此,在條約解釋時適當考慮其他國家的條約解釋,遵循共同解釋的解釋原則是促成善意解釋、善意履行條約的應有之義。在各國差異性顯著的國際稅收領域,《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對解釋原則最低限度地協調,可以促進不同國家的法院在稅收協定方面解釋的趨同,這一協調可能有助于“彌合語言、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的鴻溝”,提供一套“描述、爭論、判斷和說服的慣例”,以促進跨國司法對話;換句話說,稅收協定解釋者越多樣化,《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解釋原則的粘合作用就越重要。《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在中國也有其適用的實踐基礎。該公約于1997年10月3日對中國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釋及個案裁判中均強調了《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在國際條約解釋中的作用。在稅收協定領域,國家稅務總局在解釋稅收協定時也援引了《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例如,國家稅務總局所制定的中國與新加坡協定及議定書條文解釋就是以中新協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為法律依據。所以中國法院在適用BEPS公約及稅收協定時,可以也應當明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重要性及適用性。
2.中國法院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進行稅收協定解釋的具體場景
(1)兩種以上文字作準協定的解釋。在締約稅收協定的時候,使用不同文字的締約國雙方通常有可能將兩種文字均列為作準文字,有時還可能選中第三種文字作為作準文字。無論起草協定時用詞如何精心謹慎,不同文字版本所產生的分歧終究不可避免。中國批準的BEPS公約以及稅收協定也存在此類問題。《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3 條對用兩種以上文字作準認證的國際條約如何解釋作出了規定。這一多文字版本解釋規則也適用于包括BEPS公約在內的稅收協定。
(2)協調稅收協定與BEPS公約及其他領域國際條約的關系。第一,關于稅收協定與BEPS公約的關系。BEPS公約是國際公法下的多邊條約,具有直接效力,其獨特之處在于修改了各締約方之間雙邊稅收協定的適用。雖然BEPS公約條款中規定了具體的兼容性條款,以及明確如何修改具體涵蓋協定的條款,但其與所涵蓋的稅收協定之間的關系協調仍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相關規定。特別是公約第30條規定的關于同一事項先后所訂條約之適用的情況,第39條和40條規定的后續條約對條約的修正以及第59條規定的條約因締結后訂條約而默示終止或停止施行的情況等。第二,關于稅收協定與國際投資協定的關系。國際投資協定是指關于外國投資保護的雙邊或多邊投資協定。其目的在于為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的投資制定保護標準,如公平和公正的待遇、充分的保護和安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資本自由轉移等。稅收措施原則上也包括在投資協定所管轄的投資措施中,但也有一些投資協定規定了稅收例外條款,將稅收事項部分或全部排除在投資協定范圍之外。作為宗旨和功能不同的兩種國際條約,稅收協定與投資協定在適用上可能發生重疊。BEPS公約在性質上屬于多邊稅收協定,其適用也可能與投資協定重疊。例如BEPS公約下的反避稅措施(例如主要目的測試、利益限制或其他具體的反避稅措施)及其追溯適用可能被認為違反投資協定下的公平和公正待遇、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措施,乃至構成征收,此時就需要依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善意之原則以及條約必須遵守規則進行和諧解釋。第三,關于稅收協定與貿易協定的關系。BEPS公約也可能與國際貿易協定發生沖突,例如BEPS公約反濫用條款的歧視性效果可能被視為違反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或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的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要求。此外,BEPS公約下所引入的措施也可能被認為是關貿總協定下的“補貼”和反補貼措施協議下的 “補貼”。這同樣要求盡可能遵循《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善意之原則以及條約必須遵守規則實現BEPS公約與國際貿易協定的和諧解釋。
(3)重要的解釋材料可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下獲得法律依據。第一,BEPS公約解釋性聲明。雖然BEPS公約解釋性聲明在稅收協定解釋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在國際法下,締約國只受本國批準國際條約的約束。解釋性聲明不是公約的一部分,故締約國不受其約束,因此,解釋性聲明在締約國國內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約束力。但是解釋性聲明可以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下的解釋依據。一方面,解釋性聲明可以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4)條規定的用語的特殊含義,并優先于該用語的任何其他定義。另一方面,解釋性聲明可作為BEPS公約的準備工作,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2條下的解釋之補充資料,并在依照第31條的解釋而意義仍屬不明或難解;或所獲結果顯屬荒謬或不合理時予以適用。無論是何種適用途徑,盡管解釋性聲明不具有直接法律約束力,但在進行解釋時都具有重要意義。第二,經合組織范本注釋(以及聯合國范本注釋)。由于非經合組織成員國并沒有參與經合組織范本注釋的起草,所以經合組織注釋不能當然用于非經合組織成員國之間或經合組織成員國與非經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稅收協定。相比之下,經合組織范本注釋對經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簽署的稅收協定的解釋具有重大作用,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只有在簽訂的協定實際遵循經合組織范本的情況下才是如此。但即使對經合組織成員國來說,注釋仍然是軟法,不具有法律強制力。而從《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路徑,經合組織范本注釋則可能構成各種解釋的依據,因其內容極為龐大,其可能構成以下幾種情況:
a 注釋中的含義體現了《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第 1款規定的通常意義。
b 注釋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第 2 款 a 項下的一項協定。
c 注釋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第 2 款 b 項下的一項文書。
d 注釋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第 3 款 a 項下的嗣后協定。
e 注釋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第 3 款 b 項下的嗣后慣例。
f 注釋中的含義體現了《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第 4 款規定的特殊含義。
g 注釋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2 條下解釋之補充資料。
(4)BEPS公約及協定的專門解釋規則應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加以解釋。稅收協定有其自身的解釋規則,即類似經合組織范本第 3 條第 2 款的規定。BEPS 公約也有其自身的解釋規則,即第2條第2款的規定。上述專門解釋規則也需要解釋,也需要遵守相應的解釋規則。從法理上講,專門解釋規則并不能根據其自身構建的解釋路徑以及設定的解釋邏輯加以解釋,應回歸更根本性的解釋規則。換言之,上述解釋規則作為國際條約的一部分,其解釋應適用國際條約的解釋元規則,即《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關于條約解釋的規定。
(二)中國法院適用協定第3條第2款時上下文自主解釋應優先于國內法解釋
1.背景:國際稅法界關于第3條第2款的論戰。稅收協定有其自身的解釋規則,即類似經合組織范本第3條第2款的規定。該協定第3條第2款規定如下:“締約國一方在實施本協定的任何時候,對于未經本協定明確定義的用語,除上下文另有要求的以外,應當具有協定實施時該國適用于本協定的稅種的法律所規定的含義,此用語在該國有效適用的稅法上的含義優先于在該國其他法律上的含義。”“除上下文另有要求以外”(“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這一用語的理解在國際稅法界一直都是爭議的熱點。主要存在兩派觀點:上下文自主解釋優先說與國內法解釋優先說。以邁克爾·朗(Michael? Lang)為代表的一派學者主張上下文解釋優先說。該派學者認為,協定中已被定義的術語應以協定中定義來解釋,否則將與協定的目的和宗旨相矛盾;就算有協定未定義術語要援引國內法來解釋,首先也需確認“該術語是什么”,而確認的過程就是按照協定上下文、宗旨目的去進行解釋的過程。該過程往往涉及不同文本、語系或者法系對該術語的不同表述,要將這些表述進行比對、等同,就需要對該術語先行根據上下文進行解釋。因此將上下文的自主解釋前置,是將上下文作為重要的篩選閥門,將協定未定義的術語范圍縮小,從而對該術語進行更加客觀、精準的解釋。 而以約翰·艾福瑞·瓊斯(John Avery Jones)為代表的另一派學者則持相反觀點,即國內法解釋優先說。其認為因為最早的稅收協定是普通法系國家之間簽訂的,因此普通法系關于“除上下文另有要求以外”的解釋對理解稅收協定第3條第2款有重要參考價值;在普通法系的代表國家英國,與“除非上下文另有要求”類似的措辭是國內法或合同中的慣用措辭,并無實際意義且基本不被適用,僅在出現了極不合適結果才會適用該條款進行修正,因此協定第3條第2款中的該措辭也應發揮類似的作用;“除非”(“unless”)意味著僅除去非常有限的例外情況(上下文另有要求),其余一般情況明確賦予“援引國內法”解釋以優先權。此外,普通法系大多是二元制的國家,在二元制的國家里,協定若未轉化為國內法,那么協定在該國是不存在的,是國內法賦予了協定高于國內法的地位。因此,英國等普通法系的國家法院大多習慣采用這種解釋路徑,在解釋協定的時候不優先參考《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相關條款,而寧可優先從國內法中取材完成解釋。如引發國際稅法學術界和實務界熱議的英國最高法院福勒訴稅務機關案就采用了國內法含義優于上下文的解釋路徑。
2.中國法院的選擇:應將上下文解釋優先于國內法解釋。通過上下文解釋優先,明確未定義術語的內涵、范疇,從而更準確地援引國內法進行解釋,這是中間立場和共同解釋原則的應有之義。協定是締約國雙方經過充分談判而審慎簽訂的,協定的目的和宗旨恰恰是兩個締約國之間最初的本意,應一以貫之的內核。充分尊重協定上下文,在解釋的時候將其置于優先地位,是尊重協定目的及宗旨的做法,符合國際條約解釋的邏輯,如果動輒援引國內法含義解釋稅收協定用語,則很容易偏離雙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中國實行的一元制以及稅收協定締約實踐現狀也更適合協定上下文優先的解釋路徑。
具體而言:第一,從協定實踐來看,中國現行絕大多數稅收協定中所包括的對應于經合組織范本第3條第2款規定的具體中文表述為:“締約國一方在實施本協定時,對于未經本協定明確定義的用語,除上下文另有解釋的以外,應當具有該締約國適用于本協定的稅種的法律所規定的含義。”2008年之前,該款中的英文“require”在協定中文版本中都被翻譯為“解釋”;2008年之后中國簽訂的協定中,“require”在第3條第2款的中文翻譯發生了變化,“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這句關鍵表述,除了中國與捷克稅收協定中的該款還沿用“除上下文另有解釋的以外”的說法外,其他協定中的中文翻譯都變更為“除上下文另有要求的以外”,將“require”的翻譯由“解釋”改為了“要求”;但“require”在第3條第1款中,仍然翻譯為“解釋”,出現了同一個英文單詞“require”中文同時翻譯為“解釋”和“要求”的情況。從文義上看,似乎認為在協定的中文版本中,“解釋”和“要求”等效,并在2008年之后將“解釋”改為了“要求”,可以認為協定上下文具有解釋術語的功能;將“解釋”改為“要求”(require)進一步強調了上下文的解釋在法律上是強制性的,而非授權性。“除……以外”,則表達了中國稅收協定要求先按上下文的要求進行解釋是具有優先性的。第二,中國官方語言是中文,而中國對外簽訂協定的官方版本大多是中英文并行。在官方語言與協定文字不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上下文優先的解釋路徑也有利于先根據協定上下文對將要援引國內法進行解釋的術語進行準確解讀,確認符合協定宗旨的內涵和外延,從而提高援引國內法的準確性。第三,中國是一元制國家,即協定不需要轉化為國內法即可生效,因此在國內稅收協定與國內法有著同等地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協定還將優先于國內法適用,尊重協定上下文自身的解釋,根據協定的宗旨和目的首先進行自主解釋,是符合中國尊重及捍衛國際法的大國司法立場。
(三)中國法院可對外國法院稅務案例進行合理參考及借鑒
如前所述,共同解釋原則要求國內法官進行某種程度的“司法對話”,即考慮其他國家國內法院的裁判,因為這些關于國際法的外國司法裁判可能構成與條約有關的嗣后慣例,從而對條約的正確解釋產生影響,有時甚至是習慣國際法存在及其內容的證據。這種國內法院之間就國際法的解釋和適用進行的橫向對話被具體表現為一國的國內法院引用、討論、接受或拒絕另一國法院在判決書中的立場,從其它國家法院的裁判中獲得靈感,或者將其作為有說服力的權威依據。而稅收協定因其所涉主題,尤其是展開跨國司法對話的絕佳領域。
近年來,越來越多國家的國內法院也開始重視外國案例,英國上議院在福瑟吉爾訴君主航空公司(Fothergill v. Monarch Airlines)一案的判決正是范例之一。該案中,英國法院深入討論并評估了外國判例法。在國際稅法學界,也有越來越多學者呼吁締約國一方在解釋稅收協定時可以使用外國法院案例。中國學界也有此類呼聲,但迄今為止,中國法官很少援引國際裁決或外國法院判決。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對國際法(包括國際司法裁決)仍然存有一定疑慮。實際上,在共同解釋的原則下中國法院在解釋稅收協定過程中似可合理借鑒和參考外國法院稅務案例。從《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7條及第31條、第32條的規定來看,協定應依其用語按其上下文并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義,善意加以解釋,并考慮締約國之間就協定的解釋或其條款適用所達成的任何嗣后協議,確定締約國對其解釋達成協議的任何嗣后慣例、解釋之補充資料,上述規定也為共同解釋原則下參考締約國另一方法院稅務案例提供了法律依據。實踐中,在解釋稅收協定時對締約國另一方乃至第三方法院稅收案例的參考借鑒并非照單全收,則需要根據不同情況加以甄別及審查認定。
第一,基于司法主權,原則上任何域外法院裁判在中國境內并無當然之法律效力。域外法院裁判需經中國法院依法審查裁定承認后方在中國境內具有中國法下的效力。第二,外國法院稅收案例可能作為外國法的證明。例如《經合組織范本》第6條規定“不動產”一語應具有該財產所在締約國法律規定的含義,又如第 4(1)條規定“締約國居民”一詞是指根據該國法律負有納稅義務的任何個人。上述規定均指向不動產所在國法律或居住國法律。此時為了證明該國稅法的內容,當事人(納稅人及稅務機關)均可能提供該國稅務案例作為相關法律證明,中國法院遵循法官知法的原則,也可以主動檢索外國法院稅收案例,以查明確定相關外國稅法規定內容。從技術上講,作為外國法證明的外國稅收案例,應注意其是否生效、法院層級以及裁判理由,以及是否被撤銷。第三,在解釋協定時如何使用、借鑒并給予外國法院判決適當的權重。根據共同解釋原則的要求,中國法院可以廣泛參考稅收協定締約國對方關于同一條款解釋的案例,乃至締約國對方與第三國協定關于同一條款解釋的案例。需要強調的是,締約國對方案例的裁判規則如與中國稅務機關實踐及中國司法機關司法實踐一致,則可能構成《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第3款b項下的嗣后實踐或是第32條的解釋之補充資料而具有國際法上的意義,乃至產生一定的拘束力。
綜上,國際社會是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主權國家的利益與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并不當然一致,在國際稅收領域更是如此。與有些大國恣意奉行單邊主義,把本國利益凌駕于國際社會利益的做法不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始終主張合作共贏,倡議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作為稅收協定締約大國,中國法院作為稅收協定的重要行動者,應是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稅收治理體系的重要推手。這就要求中國法院在構建本國稅收協定解釋路徑的時候秉承務實的中間立場,遵循共同解釋原則及《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積極參與國際稅收領域的司法對話,合理借鑒和參考締約國對方以及其他國家的稅收協定解釋案例,解構其裁判的底層邏輯;同時堅持上下文自主解釋優先于國內法含義的前提下,結合中國國內法的規定進行合理解釋,讓中國法院的判決做到能信守國際條約義務,又能維護國家稅收利益以及跨國納稅人的正當稅收權益,繼而形成具有國際公信力的裁判,擴大中國稅收司法的影響力,發出中國的聲音,與他國一起共同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稅收秩序。
Approach for Chinese Courts to Interpret Tax Treatie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Joint Interpretation
ZHENG Lin
Abstract: As a major economic, political and tax state, China currently has 105 effective treaties to avoid double tax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ax treaties). The approach that Chinese courts should follow when interpreting tax treaties is not clear in relevant domestic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practice; Furthermore, the multilateral conven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related to tax treaties to prevent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BEPS Convention) has entered into force for China from September 1, 2022. Theoretically any income from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may involve the application of tax treaties and the BEPS Convention. As an important actor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ax treaties, Chinese courts will certainly face more complex challenges in treaty interpretation. The Chinese courts should adhere to a pragmatic and intermediate stance and construct an approach suitable for China to interpret the tax treatie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dialogue of joint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nd adhering to the priority of context independent interpretation. And such an approach is essential for Chinese courts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tax laws and BEPS convention and tax treaties, to abide by international treaty commitments,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nfidence of treaty partners in China's judicial system, and simultaneously protect national tax interests and the legitimate tax rights of interests of multinational taxpayers.
Keywords: treaty interpretation; tax treaty interpretation; the principle of joint interpretation;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責任編輯:陳西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