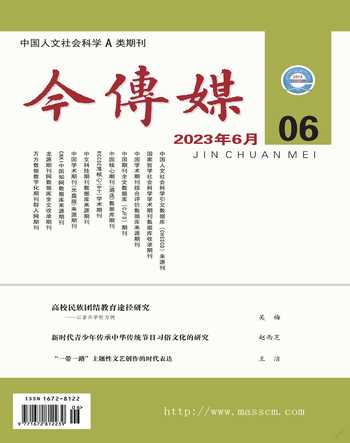傳達(dá)·介入·建構(gòu)
費(fèi)揚(yáng)
摘 要:我國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借助異域影像空間,以少數(shù)民族生活為表現(xiàn)對象,真實(shí)地展現(xiàn)了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影像記憶。電影《青春祭》改變了以往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的內(nèi)容創(chuàng)作模式,開始注重探究個體情感轉(zhuǎn)變與民族地緣化的表達(dá),其影像符號具有獨(dú)特的美學(xué)價(jià)值和文化含義。本文基于麥茨的電影符號學(xué)理論解讀了《青春祭》中所蘊(yùn)含的傣族文化,探討了電影中人物情感的特殊表達(dá),借助符號學(xué)進(jìn)一步開啟了對美、對人性的挖掘和探索,旨在為相關(guān)研究提供參考。
關(guān)鍵詞:電影符號學(xué);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符號;隱喻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3)06-0092-03
20世紀(jì)80年代,我國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的內(nèi)容創(chuàng)作改變了以往對少數(shù)民族生活熱情禮贊的模式,開始注重探究個體情感轉(zhuǎn)變與民族地緣化的表達(dá)。其中,導(dǎo)演張暖忻的作品《青春祭》以獨(dú)特的視角和符號化的鏡頭表達(dá),講述了漢族青年李純在傣寨受到傣族人民的幫助、關(guān)懷和自我意識覺醒的故事。影片以詩化的風(fēng)格為觀眾呈現(xiàn)了少數(shù)民族的地域特色,其中的影像符號具有獨(dú)特的美學(xué)價(jià)值和文化含義,對解讀電影中人物情感的特殊表達(dá)具有重要意義。
一、麥茨電影符號學(xué)概要
現(xiàn)代符號學(xué)的研究起源于索緒爾的語言學(xué)理論,他從語言學(xué)角度來研究符號學(xué)。皮爾斯在此基礎(chǔ)上,使用哲學(xué)和邏輯學(xué)來研究符號學(xué)。1964年,麥茨指出電影就是一種符號系統(tǒng),其能指和所指表現(xiàn)為由畫面、聲音構(gòu)成的不同體系,電影的含義主要通過二者的組合來表達(dá)。麥茨的電影符號學(xué)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第一符號學(xué)(1964-1973年)、第二符號學(xué)(1975-1985年)[1]。在第一符號學(xué)中,麥茨把電影看作一種特殊形態(tài)的影像語言,即把電影作為具有某種特殊含義的符號來處理。這一階段的工作主要是:論證電影的語言特性;進(jìn)行電影的代碼分類;提出鏡頭的八大組合段分類體系[2]。在第二符號學(xué)中,麥茨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出發(fā),借助弗洛伊德理論中的原發(fā)過程和二次過程精神機(jī)制運(yùn)作模式,來解釋電影和夢的關(guān)系,分析了電影文本中有關(guān)凝縮、移置的問題;他引用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分析了電影觀眾的心理,提出了“鏡子和銀幕”的觀點(diǎn),全面解釋了電影放映中觀眾觀看電影過程的心理學(xué)現(xiàn)象。麥茨將電影符號學(xué)從符碼、內(nèi)涵與外延的研究,延伸到了電影機(jī)器、隱喻、換喻等符號心理學(xué)研究,分析電影也從簡單的文本內(nèi)部符號分析轉(zhuǎn)變?yōu)閯討B(tài)的心理符號分析。
二、對《青春祭》的符號解讀
(一)原生態(tài)的民族次符碼建構(gòu)
從符號學(xué)角度出發(fā),麥茨把電影的符碼分為兩類:一是一般的,二是特別的。電影符碼屬于一般的,電影次符碼則是特別的。一般的電影符碼是指影片系統(tǒng)建構(gòu)的元素,對所有影片都適用,比如,電影所運(yùn)用的溶接、淡出、淡入等形式。電影次符碼是指影片系統(tǒng)建構(gòu)元素,只適用于某些影片,并非所有的影片[1]。在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中,次符碼是必不可缺的內(nèi)容,對展現(xiàn)少數(shù)民族特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原生態(tài)民族次符碼構(gòu)建了《青春祭》所蘊(yùn)含的傣族文化的整體格調(diào)。在影片中,傣族獨(dú)特的次符碼———“筒裙”,象征著傣族獨(dú)特的審美文化,凸顯出典型的、自信的、富有魅力的民族審美認(rèn)同以及人們對美的價(jià)值追求,構(gòu)成了一種特定的影像次符碼。漢族女孩李純,第一次以主觀視角注視傣族姑娘“依波”的背影時(shí),認(rèn)為筒裙是有魔力的,它會讓人變得美麗、自信。導(dǎo)演在影片開頭將李純置于畫面的角落,她默不出聲,穿著灰色發(fā)舊的工裝,似乎無法融入傣族姑娘的群體關(guān)系中。當(dāng)追求美的意識開始覺醒時(shí),換上筒裙的李純變得熱情、灑脫,像傣族人民一樣赤腳、游泳、抓飯……真正融入了傣族人民的生活。筒裙作為影片中的次符碼,是對李純身份的一種重新界定。她身穿筒裙時(shí),與傣族姑娘一樣熱情、大膽地追求美麗,而為了逃避傣寨大哥的愛戀,李純被迫離開了她眷戀的傣寨,褪下筒裙換回了藍(lán)色工裝,又回歸于古板、內(nèi)斂的形象,直到疼愛她的“伢”去世,李純再次換上筒裙回到傣寨為“伢”送葬。對李純來說,底蘊(yùn)深厚的傣族文化是她精神慰藉中無法割舍的一部分,仿佛穿上筒裙她才能不受約束地去表達(dá)自己內(nèi)心真實(shí)的情感。
傣族人民歡慶豐收的慶典儀式是影片中次符碼呈現(xiàn)最為直觀的部分。“谷子黃,傣家狂”,慶典儀式刻畫了傣族原始、自然的狂歡奇觀,作為次符碼也凸顯出電影的民俗性與奇觀性。比如,慶典儀式中的傣語歌、原始圖騰形態(tài)的舞姿等,呈現(xiàn)出傣族人民豐收后的喜悅,讓觀眾感受到生命的本質(zhì)。影片中所使用的民族次符碼表面上具有整體性敘事功能,實(shí)際上擁有更深層次的作用,具有多樣化的表意內(nèi)涵。比如,大量使用的原生態(tài)雨林景觀、民俗儀式以及傣族服飾等清晰可辨的傣族文化次符碼,不僅體現(xiàn)出導(dǎo)演獨(dú)特的文化視角,記錄了傣族最原始、浪漫的象征符號,也承載著現(xiàn)代社會人們懷鄉(xiāng)戀舊的情感寄托以及對精神歸屬之處的向往。
(二)特殊意象隱喻的展現(xiàn)
通過分析弗洛伊德理論中原發(fā)過程和二次過程精神機(jī)制的運(yùn)作模式,麥茨探討了電影文本生成原發(fā)機(jī)制的運(yùn)作方式問題,即凝縮和移置如何構(gòu)成電影文本的原發(fā)修辭。凝縮和移置是弗洛伊德在討論夢的工作機(jī)制時(shí)提出的兩個概念,拉康參照雅克布遜的修辭學(xué)理論,提出了隱喻和換喻的概念,他認(rèn)為:“以一種平常的方式,弗洛伊德所稱的凝縮,就是我們在修辭里所稱的移置,即是換喻”[2]。麥茨沿著拉康的思路把隱喻、換喻帶入了電影研究,總結(jié)出對應(yīng)電影文本符號學(xué)分析的四個主類型,可簡要概括為“隱喻—組合”“隱喻—聚合”“換喻—聚合”“換喻—組合”。在電影《青春祭》中,大量的特殊符號隱喻著主體意識的覺醒和特殊情緒的表達(dá),將它們放置于文化語境中,還有更深層的審美、文化等含蓄意指。
在符號的場域中,影像符號總是與情節(jié)的發(fā)生有著重要關(guān)聯(lián)。電影中一般會存在多種元素符號,并具有不同的隱喻意義。在《青春祭》中,荷花也是影片中的一個與美有關(guān)的重要隱喻符號。當(dāng)李純受到排斥,在水塘邊沉思時(shí),導(dǎo)演多次穿插了主觀視角下白荷花的特寫鏡頭,一方面,隱喻著李純正處于如花朵般美麗的年紀(jì),應(yīng)該像荷花一樣向陽生長,充滿生命力;另一方面,也隱喻著李純內(nèi)心對荷花傲然開放的向往之情———在周圍環(huán)境的影響下,李純開始反思自己,對著水面收緊了灰色的工裝,她的審美意識開始覺醒。
此外,從傣族人民視角出發(fā),荷花還有一個重要的隱喻功能。水塘邊的“老啞巴”將白荷花送給陌生的李純,體現(xiàn)出傣族人心中對美的追求,質(zhì)樸的內(nèi)心如同白荷花一樣,不加雕飾。影片所呈現(xiàn)的這一細(xì)節(jié)顯現(xiàn)了存在于兩種不同話語系統(tǒng)之中的傣文明與漢文明對話、融合的可能[3],荷花這一符號,便是麥茨所建立的對應(yīng)電影文本中的“隱喻—聚合”類型,具有不同的引申含義,但是在呈現(xiàn)上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電影中,一個文化符號每出現(xiàn)一次,其第二層次的隱喻意義便能夠在接收者心中強(qiáng)化一次[4]。孤立地看待這些文化符號,它們有明晰的能指和所指,我們很難將它們與影片中的個人身份和民族情感相聯(lián)結(jié),但是在《青春祭》中,導(dǎo)演借助傣族文化的內(nèi)驅(qū)力將這些符號重新組合,傳達(dá)出少數(shù)民族文化情感獨(dú)有的隱喻功能。
(三)個人情感變化的“內(nèi)涵”與“外延”
麥茨認(rèn)為,電影與文學(xué)一樣皆有“內(nèi)涵”和“外延”。“外延”由一個能指和一個所指組成,為第一系統(tǒng);“內(nèi)涵”則是“外延”之派生,為第二系統(tǒng),在此,能指和所指聯(lián)結(jié),產(chǎn)生意指。后來,麥茨在《電影符號學(xué)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指出,在電影中,外延是由影像或聲音所重現(xiàn)的景觀,而內(nèi)涵則是美學(xué)語言,其所指是影像風(fēng)格、類型、象征、氛圍等;其能指為外延的整體材料,通過研究內(nèi)涵,我們能更接近藝術(shù)電影[1]。因此,可以立足“內(nèi)涵”和“外延”層面,解讀導(dǎo)演在電影有限的場域內(nèi)所蘊(yùn)含的更多含義。
李純作為影片的敘事主體,她的情感“外延”有著非常明顯、豐富的表現(xiàn),通過對不同時(shí)期的“內(nèi)涵”與“外延”進(jìn)行分析,可以直觀地感受到李純在傣族文化熏陶下情感的變化過程。影片開始,李純和傣族姑娘一起勞作后,導(dǎo)演穿插了李純獨(dú)自在遠(yuǎn)處眺望傣家男女對歌傳情的鏡頭,并采用不同的構(gòu)圖方式進(jìn)行對比,呈現(xiàn)出他們之間似乎無法融合的關(guān)系。在此情節(jié)中,“外延”由一個能指(李純、傣族年輕人)和一個所指(傣族年輕人在對唱歌曲、李純在眺望)構(gòu)成;“內(nèi)涵”則是導(dǎo)演借助視聽語言來呈現(xiàn)。在拍攝傣家男女對歌的片段時(shí),導(dǎo)演將李純置于全景畫面的右下方,以近景拍攝傣族年輕人,并將他們置于畫面中心,以此揭示李純與傣族年輕人截然不同的性格;直到李純第一次換上筒裙與傣族姑娘們?nèi)ゼ校@時(shí)的她不再處于畫面的邊緣,而是被傣族姑娘們簇?fù)碓谥虚g,展現(xiàn)了李純受傣族文化感染后性格得到改變,開始融入傣族人生活中的內(nèi)涵。
影片結(jié)尾,返城多年后的李純再次來到傣寨,面對一場泥石流帶走了傣寨所有人、所有物的現(xiàn)實(shí),她放聲痛哭。此時(shí),導(dǎo)演運(yùn)用俯拍鏡頭并不斷拉遠(yuǎn),呈現(xiàn)出被泥石流沖刷過后的灰色地面,給觀眾帶來一種壓抑感。在此情節(jié)中,“外延”是李純站在傣寨遺留的土地上流淚,而“內(nèi)涵”則蘊(yùn)含著具有沖擊力的情感表達(dá)。面對自己難以割舍的情感和精神向往源頭的徹底消逝,李純放聲痛哭,同時(shí),導(dǎo)演穿插了李純記憶中熟悉的趕牛行路背景音,從而凸顯出影片更深層次的話語意義,即在時(shí)光境遷中祭奠自己的青春。
三、結(jié) 語
《青春祭》作為一部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其中蘊(yùn)含的時(shí)代個人命運(yùn)的反思與民族文化價(jià)值達(dá)到了高度融合。張暖忻導(dǎo)演以個人化形式的探索與深刻的人文關(guān)懷,拍攝了一部具有個人、民族情感關(guān)懷的詩性電影,通過符號化的影像表達(dá),體現(xiàn)出電影符號對具體歷史語境的傳達(dá)、介入與建構(gòu)功能。作為聚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青春祭》的影像符號具有重要的美學(xué)價(jià)值和文化含義,本文基于電影符號學(xué)視角,進(jìn)一步開啟了對美、對人性的挖掘和探索。
參考文獻(xiàn):
[1] 齊隆壬.電影符號學(xué)[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3:105+120+108-109.
[2] 克里斯蒂安·麥茨.想象的能指[M].王志敏,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6+149.
[3] 胡牧.從承繼到創(chuàng)新,從啟蒙到娛樂[D].南寧:廣西民族大學(xué),2010.
[4] 菲斯克.傳播符號學(xué)理論[M].臺北:遠(yuǎn)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5:225.
[責(zé)任編輯: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