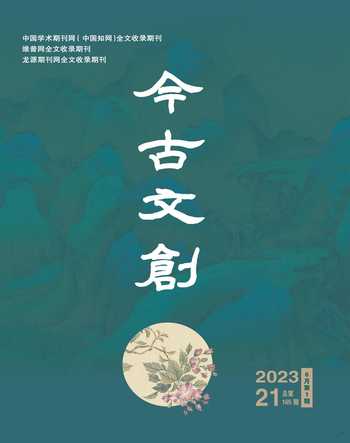《人生大事》:攖寧·善死·朝徹
魏玲
【摘要】本文從中國哲學的角度出發,細讀殯葬題材電影《人生大事》中所包孕的幾重生死之道:首重是以生觀死,洞曉的是通達攖寧心境的生之道;次重是以死觀生,明徹的是“生死齊一”的死之道;三重是“觀化而化己”,通達的是“生死已外”的圣人之道。結語表明生死之道的核心要義就在于鉆探生命的本真、死亡的本質與人生的見獨。
【關鍵詞】《人生大事》;中國哲學;生死之道;殯葬
【中圖分類號】J905?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21-008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1.028
基于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理念,中國人在看待生死的問題上,往往都秉承著生大于死的態度,這種態度也在某種程度上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內化于中國電影的創作中。故而類似于《紅高粱》《黃土地》那般張揚生命意識的影片在國人的審美里能夠經久不衰,縱使是疾病類的影片《滾蛋吧,腫瘤君》《再見吧!少年》等也都在話語表述上刻意地遮蔽患病主體的疼痛體驗,而把頌揚“生如夏花之燦爛”般的生命力抽調到電影文本中最顯影的位置。可見,“死亡意識”的深描在中國電影創作者的思維里,似乎被長久地擱置在了“暫緩考慮”之列。盡管近兩年來電影市場似乎有了轉峰的跡象,“死亡敘事”也開始作為主角漸次登上大銀幕,但轉峰后的落點也都大半分布在了“災難片”“戰爭片”等頭部電影的區間,脫離時下“熱點事件”而站在真正意義上對死亡深描的影片如數家珍。于2022年六月下旬上映的電影《人生大事》在此類問題卻是首開一指,不再囿于把“死”置于某個宏大的敘事框架下,或頌揚,或遮蔽,而是以“死生無變”的淡然視角詮釋了死亡本身“自然屬性”,同時也呈露出老莊哲學對“萬物生生不已之道”的闡發,這既開拓了類型電影的廣度又呈示出中國傳統哲學于影像層面的深度。
一、攖寧:安時處順以達生
“攖寧”取自《莊子·大宗師》中南伯子葵與女偊的對話。“攖”,大意為“擾”,為汩亂塵世中的困橫拂郁。“寧”,大意為“定”,為懸解俗雜人世的湛然之態。前者是生而為人所面臨的種種累患,與海德格爾“煩”頗為相似;后者是人超克諸多累患后所達到的“道”的境界,接近于海德格爾對“本真狀態”的闡述。倘若把這“攖”比作世人數十載遇到的愛、欲、貧、病、死。那“寧”的超然之道便是世人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所取得的真經。而這真經的首本便是電影《人生大事》所訓解的第一層生死之道:安時處順以達生。中國人喜好講故事,即便是闡述閎意妙指的哲思也都慣于以內嵌式的寓言呈現,諸如戰國時期的儒學著作《論語》、文哲經典《莊子》、魏晉玄談《世說新語》以及家喻戶曉的四大名著等。而在故事的講述中,較于對死亡靜的白描,國人更青睞對狂放生命的潑墨。電影中生命的意象越狂、越韌、越強,觀眾就越發著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傳統神話中的悲劇神靈“孫悟空”“哪吒”。
電影《人生大事》中,莫三妹出場便是以“孫悟空”的意象為其性格能指的:叛逆正義的性情/孫悟空色系的衣褲/狂放——罹難——救贖——罹難——懸解的戲劇模式等。不消說在后續的宣發中,也都打著“孫悟空”的旗幟,引導觀眾建構起孫悟空/莫三妹這兩個藝術形象間的同構性。較于其他神話人物,孫悟空最顯要的特征是為妖、化神、升佛、成人皆可。電影《人生大事》中,“孫悟空”的意象就化身為了凡胎濁骨的莫三妹,不過兩種藝術形象在性格上被有意同構的同時,也呈現出明顯的區隔性。首先,作為神的孫悟空,其天性的放達為歡與“且趣當生,奚遑死后”的生死觀雖使他遭受了最高規格的規訓與懲罰,但也噴薄出極致的生命張力。而在電影《人生大事》中,作為一個被剔除了神性的“凡人悟空”,莫三妹既翻不了跟斗云,也耍不出七十二變。神力的缺席倒讓這個“人間獼猴”的放達性情釀成了其牢獄之災的禍端。其次,神話里孫悟空孕化于天地之間,其具象的父母形象是缺席的,他自由的性情與天生的神力多得益于自然的造物。《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 “道”是萬物之始終,它隨自然而運化,無所有而無不有。故而孫悟空在自然的孕化下一出生便是擁有“若夫成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的圣人之才。反觀莫三妹,這個“獼猴”生于人間煙火處,長于市井百態間,加之父親自小對他的規訓與壓制以及周遭“他者”對其家族職業的橫眉冷對,以至其潛意識里的“本真”與“天性”被部分閹割。“盡管閱盡生死別”,卻從未懂得“死亡”真義。“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2]生與死是宇宙萬物之本根的兩種固有作用和傾向,故而欲參透“死”的真經,“生”之意義的通曉是第一層次的“道”。人對“生之意義”的尋求,就是要在本真意義的概念上理解并且獲得自己。
但在電影《人生大事》中,莫三妹不僅沒能在本真意義上尋求到“自我”,而且在相繼遭遇毀譽、被棄事件后,“自我”意識反而落到了如煙墮海的境地。于是,在尋求“自我”無果的境遇下,哪吒小文作為一種“潛意識”走進了他的世界。小文一出場,其性情、裝扮及紅纓槍就意象呈現出一個活脫脫的小哪吒。“我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婦孺皆知,石頭里蹦出來、大鬧“天宮”(火葬場)、偷吃“仙丹”(圓形橡皮珠)的是孫悟空。家中排行老三,與父不和的是哪吒。導演在兩個人物形象上刻意的含混折射出含而不露的意旨:小文是莫三妹自我意識中的一體兩面,是其在父權壓制下于童年起就被閹割的那一部分“自我”。小文的出現是莫三妹挪開“五指山”,從而漸次找到本真自我、通往“達生”之境的引子。與其說莫三妹與小文的相遇——別離——團圓,是導演為了刺激觀眾的淚點而營造的某種溫情脈脈,毋寧說是導演為莫三妹安排的一場“追尋自我”的“取經之旅”。于是,在“孫悟空”—— “哪吒”——莫三妹——小文四個人物形象的纏繞交織下,莫三妹重新建構出一個新的“自我”:撞見生命的“本真自我”— “達生”。“本真”在《存在與時間》中的表述就是對“生命意義”的尋求,就是作為“此在”的存在者能夠找到那些自己“愿意”為之“操勞”的事物,這是一種對自由高度最大化的趨近。正是因為找到了靈魂深處的那個“愿意”(小文),莫三妹才能擺脫物役與累患的攖擾,做到安時處順并通達“自為”生命的本真。
二、“善死”:“生死齊一”“哀樂不入”
中國先哲在對待死亡問題上有著不同的分野。孔子主張“悅生惡死”,喪祭以“厚葬重哀”為禮;莊子主張“生死齊一”,喪祭以“輕裝薄葬”為道。厚葬風俗在中國殯葬史中源遠流長,自夏商周三代始厚葬習氣就已蔚然成風。春秋更有“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3]的禮制,后至戰國陵墓興起,更是為厚葬奢靡之風把薪助火。傳至明清隆喪習氣已躍入頂峰,加之風水學郁勃,民間的厚葬風尚也盛極一時。新中國成立后,為厘正厚葬風氣,政府大力推行火葬,以節約資源及財富,并幾度下達關于殯葬事業改革的文件,這也意味著喪葬習俗從厚葬逐步轉為薄葬是大勢所趨。殯葬文化上的革鼎故新也鏡像折射出當代人在看待生死理念上的嬗變,這在電影《人生大事》中亦可窺一斑而知全豹。在影片的段落布局上,導演設置了五場對喪祭場面的描述,且每一場的“淡入淡出”都在高潮跌宕的情境中呈示出主人公在求取生死之道途中的蛻變與成長。個中最濃墨重彩的當屬“劉爺爺”的“活人葬禮”與莫三妹父親的“煙花葬”。
在以儒家為顯學的哲學場域中,“死亡”的議題往往不喜被提及,在這個“確定的未知性事件”降臨之前,它都是以懸擱的狀態被遮蔽在私密領域中的。即便是未知成已知的情形下,親屬們也諱莫若深。譬如片中在醫院亡故的女孩父母最初對喪葬的抵抗與避諱。往生者尚且如此,活人對此更是三緘其口。故而,當影片中桑榆暮景的“劉爺爺”欲為參與自己未來有可能的缺席而提前辦一場“葬禮”時,莫三妹的反映是無可置信。這也宣露出劉爺爺對死亡懸臨時的態度:無畏亦無懼,以一種敞開的姿態去坦然接受死亡于終極意義上的確知性及于時間意義上的未知性。“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4]說的就是劉爺爺此般對生死必然性的放懷。正是因為日薄虞淵的劉爺爺參悟到生命與死亡就如造物與造化一般是自然的一體兩面,他才會如此通達無畏的坦然“赴死”。
與之相對,現代人的喪祭觀也在這荒誕不經的戲劇中被呈露。“皇帝的葬禮”代表著傳統厚葬的最高規格,“嬪妃”“宮人”的放肆號哭更是儒家“重哀”的極致呈現。傳統喪葬觀上,這對往生者是最體面的告別。導演的巧思在于,這場戲恰是以省略號的方式收尾的。伴隨著“大鬧天宮”的配樂,這場戲謔的“皇帝葬禮”在劉爺爺家屬棍棒的討伐下不了了之。“大鬧天宮”原本在國人的意識里就有反叛傳統的意味,“后現代”式的收尾更是對厚葬重哀喪祭觀的消解與解構。此外,劉爺爺對“葬禮”緣由的吐露,也映射出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部分兒女不顧親情而淪為“倒置之民”的現狀。劉爺爺可以看透“生死齊一”的自然之道,卻放不下“喪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子孫帶給他的生之累患,這倒頗有一絲“以生為喪,以死為反”的意味。
“買骨灰盒的錢還不如全家人一起搓一頓”。莫父臨終的這段遺囑是對薄葬觀最徑直的表達,莫三妹對其父煙花葬的處理亦是對“質本潔來還潔去”生死觀最露骨的讀解。“煙花葬”既有死后歸于天地自然的意味,又是對亡故者燦爛一生最高規格的禮贊。國人的思維邏輯里,似乎與“煙花”發生勾連的皆是與生命相關的事宜:婚嫁、生辰、節慶等。然則死亡亦是“此在”綿延生命里最不可或缺的存在。身體縱然會消亡朽去,但經由生命釀造的那些故人情思卻能似那經年的老窖任東流逝水都無礙于它的醇美與熱烈。如此,生命的落敗不過是在蒼茫宇宙中以另一種形式化作了那漫天的星辰。“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5]寒來暑往,生死輪替哪般不是宇宙運動綿延又周而復始的自然之道?生生不已,是因生之道本身就涵括了個體的滅盡無余。
三、“朝徹”:“觀化而化己”
“朝徹”取自《莊子·大宗師》“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6]。在武延緒的《莊子札記》中,“朝徹”訓解為普遍的通達,即大通之境。回到電影中,從事殯葬職業的莫三妹以超然之態觀他人生死是較易的,而劉爺爺與莫老爺子以達觀之姿超脫本己性的死亡亦能做到哀樂不入又難上一層,但都還未到達生死之道的第三重境界—“至人”之境。那在電影中,誰才是那個承托“至人”之境的至德者?一者,作為主角的莫三妹自然身處最為顯要的位置,“孫悟空”意象的設定,也給觀影者留足了想象的“空白”。這樣的召喚結構,顯然是要讓莫三妹成為電影中“至人”的首選,畢竟孫悟空在成為新一任的燃燈古佛前,也是個無法無天、大鬧天宮的潑猴。二者,作為一個缺席的在場者,“二哥”這個角色自始至終都是個僅出現在莫父記憶與對話中的人物,他既是莫三妹父子關系不睦的“緊箍咒”,又是點亮莫三妹那顆圣人心的燈芯火燭。
《人生大事》中,攖擾莫三妹的諸多累患多源于他對女友的情之所起:入獄毀譽為情,欲棄家業為情,父子離心亦是為情。然則卻落得被拋棄、羞辱的境地。盡人皆知,這世間最難解的仇怨中,奪妻之恨應屬其一。即便現實社會不能同文藝作品中那般手刃仇敵,其中的恨意也是難以消解的。可當老六意外身故,“前女友”央求他為丈夫斂容拼骨時,那顆萌芽的圣人心卻渡化了他心中的恨意。常言道,“生別異,死和同”,當他目睹老六那殘存的碎肉散骨時,讓故者以最體面的方式離去便是他最為誠摯的希冀。“一順筋,二拼骨,從腳到頭往回數……”伴隨著莫父擲地有聲的傳教,莫三妹一針一線的縫合著老六的殘肢,也縫合著他多年來對父輩從事殯葬行業的曲解與誤讀。
再看二哥,這是個“留白”的角色。觀眾對他的知解皆源于莫父對其往事的提及:1988年莫父與二哥去長江撈尸,二哥撈回了孩子失了自己。如此,綜合片中的若干細節及莫父的回憶,“二哥”這個人物形象便有了具體的能指:他可以是排雷英雄杜富國、基層書記黃文秀,也可以是每一個堅守崗位、舍生忘死的平民英雄。“道”之意義就在于所有事物都經由它才成為自己,它是每一條你可以走但未曾走的路,而“至德者”也有可能是每一個你所敬仰卻不愿成為的人,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莫父“齊一生死”,三妹以德化仇,皆是“圣人”中“圣己”的一面。而二哥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對死人遺體的尊重絲毫不吝于對自己生命的尊重。對生、死及自然萬物都懷有同等的敬畏,這就是“至德者”的第三重境界:“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朝徹,而后能見獨;見獨,而后能無古今。”[7]
四、結語
生死之道的核心要義就在于鉆探生命的本真、死亡的本質與人生的見獨。而死亡本身又同臨終關懷、殯葬事宜等同氣連枝。但上述兩類題材在國內電影領域內又鮮有建樹,尚屬孵化階段。此時《人生大事》的上映無疑為國內影視藝術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類型視角。海德格爾曾言:“死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種須從生存論上加以領會的現象。”[8]可見,中西哲學在生死同質的問題上,并無過厚的壁壘,皆認同生死對于人生與藝術的意義是不可厚此薄彼、單剖某一面來談的。在當代,受消費社會的侵襲,藝術的商品化趨向早已將現代人意識中能夠深度思考“死亡”的腦細胞洗劫而空,從而使其置身于“娛樂至死”的消遣氛圍中,以便淪為資本易控的“單向度的人”。而疫情又“暴力”叩開了“鐵屋子”的大門,迫使這些沉湎在“物役”中的“飽食窮民”們覺察到死亡的焦慮與恐懼。于是,在“大夢”—“大覺”的兩極中,現代人的精神與心靈已經被撕扯的千瘡百孔,到了亟待療愈的階段。此時,也唯有藝術與哲學的慰藉,才能作為一種最佳的療愈工具幫助現代人重新建構起對“本真生命”的理解,從而做到“物物而不物與物”,這便是對“人生大事”四字真經的最佳詮釋。
參考文獻:
[1]老子.道德經[M].張景,張松輝譯.北京:中華書局,2022:99.
[2]莊子著,陳鼓應譯.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646.
[3]墨子,墨子·節葬下[M].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595.
[4]莊子著,陳鼓應譯.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209.
[5]莊子著,陳鼓應譯.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526.
[6][7]莊子著,陳鼓應譯.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217.
[8](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