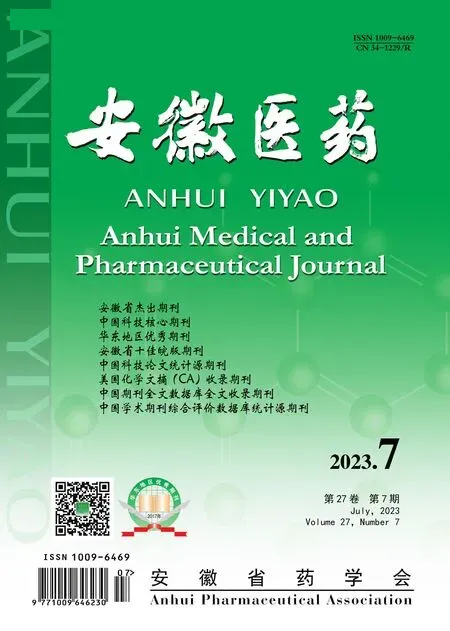結直腸癌432例微衛星狀態及病理特征對預后的影響分析
聶其學,吳文周
據世界癌癥研究基金會稱,結直腸癌(CRC)(指結腸、直腸或肛門的惡性腫瘤)目前排在全球常見惡性腫瘤的第三位。僅僅2018 年,就診斷出超過180 萬例新發CRC 病例[1]。據統計,在我國,近年來,結腸癌病人較前比率增加了大約20%[2]。約20%~25%的CRC 病例是由遺傳易感性引起的,包括與DNA 修復、細胞周期和細胞凋亡相關的錯配修復基因的單基因突變[3]。DNA 錯配修復(MMR)對確保基因組的完整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MMR 通路的主要功能是識別和糾正DNA 在復制和重組過程中產生的堿基錯配或插入[4]MMR 缺陷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基因組微衛星區域的不穩定性(MSI),而MSI 表型被廣泛用作腫瘤細胞MMR 缺陷的診斷標志物,其中MSI 對結腸癌病人的評估尤為重要,MMR 蛋白包括MLH1、PMS2、MSH2 及MSH6,其中任何一個表達缺失,都會導致MSI[5]。MSI在結直腸癌病人中起著至關重要的結果,研究表明,與微衛星穩定的結直腸腫瘤病人相比,MSI 結直腸癌病人對免疫治療的敏感性更高[6]。為了進一步了解微衛星的不同狀態對結直腸癌病人的影響,本研究采用回顧性病例分析,從臨床及病理資料作相應對比分析,探討MSI與臨床病理特征的相關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采用回顧性病例分析,選取2015年1月至2021年5月安徽省第二人民醫院收治的符合條件的432 例結直腸癌病人,男性248 例,女性184 例,年齡范圍19~87 歲,其中MSI-H 組病人27例,MSI-L/MSS 組405 例,分別比較兩組病人的臨床及病理資料。納入標準:(1)臨床各數據資料完整,術前病理診斷為結直腸癌;(2)接受結直腸癌根治術(腹腔鏡手術或是開腹手術)。排除標準:(1)合并其他惡性腫瘤;(2)術前接受新輔助化療或是術前放化療;(3)由于腫瘤導致的機械性腸梗阻病人。病人或其近親屬知情同意,本研究符合《世界醫學協會赫爾辛基宣言》相關要求。
1.2 觀察指標分別收集兩組數據的臨床及病理資料,臨床資料有性別、年齡、家族史、病程時間、癌胚抗原(CEA)、糖類抗原199(CA199),病理資料有腫瘤部位、腫瘤長徑、腫瘤組織學分型、病理學形態、腫瘤TNM 分期、分化程度、神經脈管是否侵犯、癌結節有無。從以上各個方面比較兩組差異。TNM分期采用AJCC(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第8版標準。
1.3 微衛星狀態分析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腫瘤組織中錯配修復基因MLH1、MSH2、MSH6及PMS2 的表達。其中有任何一項錯配修復基因表達缺失,被定義為MSI,否則定為微衛星穩定(MSS)。其中一個表達缺失則稱為低度微衛星不穩定(MSIL),2種或2種以上蛋白表達缺失為高度微衛星不穩定(MSI-H)。此蠟塊閱片由兩位病理醫師獨立閱片,并獨立分析。
1.4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25.0軟件包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檢驗水準α=0.05。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第25、75百分位數)、即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U檢驗(Z值表示)。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臨床特征分析兩組病人在家族史中對比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MSI-H 組家族遺傳性可能性更大,在性別、年齡、病程時間、CEA、CA19-9 方面統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結直腸癌432例微衛星區域不同狀態下一般資料比較/例(%)
2.2 兩組病理學特征對比分析MSI-H 組在腫瘤發生部位上以右半結腸較多,而MSI-L/MSS 組以直腸發生較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病理學形態上,MSI-H 組浸潤性較MSI-L/MSS 組明顯增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TNM 分期、原發腫瘤浸潤深度(T)和淋巴結轉移情況(N)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腫瘤長徑方面,MSI-H 組腫瘤明顯較大于MSI-L/MSS 組,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腫瘤是否侵犯神經方面,MSIL/MSS 組較MSI-H 明顯增多,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癌結節方面,MSI-H 組病人癌結節明顯較多,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腫瘤分化程度、遠處轉移情況(M)、組織學類型、脈管有無侵犯及增殖細胞核抗原(Ki-67)方面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結直腸癌432例微衛星區域不同狀態下結直腸癌病人病理資料分析/例(%)
3 討論
微衛星是由依次重復的短核苷酸片段(1~10個核苷酸,也稱為短串聯重復序列組成的DNA 序列),由于它們的重復性,這些DNA 片段在DNA 復制過程中容易出現DNA 聚合酶暫停和滑動,從而導致突變[7]。錯配修復(MMR),即DNA 修復系統,人類細胞DNA 在復制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錯誤的核苷酸序列,在修復過程中,把錯誤的核苷酸序列從子鏈中清除,防止子代細胞發生基因突變,這種修復機制是為了校對新復制的DNA 和修復DNA 突變而存在的。MMR的產物是錯配修復蛋白,錯配修復蛋白包括Muts和Mutl兩大家族,其中前者包括MSH2、MSH3 和MSH6 等,后者包括MLH1、MLH3、PMS1 和PMS2。錯配修復系統功能缺陷的原因之一是胚系突變(家族遺傳性),突變可累及MLH1、MSH2、MSH6、PMS2,這種胚系突變具有顯性遺傳性,會引起所謂林奇綜合征[8]。林奇綜合征是一種常染色體顯性疾病,由于存在已知影響DNA 錯配修復能力的基因突變,導致其終生患結直腸癌的風險達到70%~80%。與其他散發性結腸癌相比,林奇綜合征發病年齡較早(中位年齡為40歲),病灶更靠近脾曲。林奇綜合征還會表現為子宮內膜癌、卵巢癌、尿路上皮癌等多種腸外腫瘤。當這些突變發生在微衛星區域內,導致重復DNA 序列的缺失或擴增時,這被稱為MSI,MSI 與導致人類細胞錯配修復缺陷(dMMR)的MMR 基因突變有關[9]。根據MSI突變位點的數目,可分為高突變型(MSI-H)、低突變性(MSI-L)和無突變型(MSS)。
癌癥免疫治療是一個新的快速發展的癌癥治療領域,現已成為繼外科手術、細胞毒性化療、放射和靶向治療以外新興的、有前景的腫瘤治療選擇。免疫療法背后的概念是利用對腫瘤細胞的免疫反應,以便對惡性腫瘤更好的靶向治療。對惡性腫瘤的正常免疫反應的一個組成部分是針對腫瘤細胞的T細胞活化。這種機制有幾個由免疫系統設置的檢查點,試圖保持這種反應的平衡,防止過度激活和自我誘導的傷害。一個這樣的靶點是程序性免疫細胞死亡。T 細胞表面有一種受體,即程序性細胞死亡-1(PD-1)受體,由腫瘤細胞表面的PD-1 配體或鄰近的免疫細胞激活。這種配體與PD-1 受體的結合發出細胞凋亡的信號。抗PD-1 免疫療法是一種藥理學抗體,已開發出針對該靶點并促進持續的T 細胞活性以防止這些細胞凋亡。抗PD-1 免疫療法已被證明對多種癌癥有效。生物標志物已被確定用于更好地預測哪些癌癥可能對抗程序性細胞死亡-1(抗PD-1)免疫療法有反應[10]。這些生物標志物包括PD-1受體及其配體的表達分析、高腫瘤突變負荷和MSI 的存在[11-12]。在結直腸癌中MSI-H 腫瘤的占比約為15%,而中晚期MSI-H 腫瘤僅占所有轉移性結直腸癌的2%~4%[13]。結直腸癌病人也可能受益于免疫治療,尤其是患有MSI-H 腫瘤的結直腸癌病人,他們對免疫治療的敏感性明顯高于患有MSS 及MSI-L 腫瘤的結直腸癌病人[14]。研究表明,MSI-H 結直腸癌病人比MSS/MSI-L 結直腸癌病人從免疫治療中獲益更多[15]。
本研究中,MSI-H 組在腫瘤發生部位上以右半結腸為主,且與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與Birgisson[16]的研究一致,充分表明了MSI 與結直腸癌的發生部位密切相關。在病理學形態上,MSIH 組浸潤性占9 例(33.3%)明顯高于MSI-L/MSS 組19(4.7%)(P<0.05),在分化程度上,MSI-H 組低分化腫瘤占16(59.3%),這說明在結直腸癌中,MSI-H 腫瘤的分化程度更低,在組織學類型中,MSI-H 組其病理分型多為低分化腺癌或低分化黏液腺癌,且少發生淋巴結浸潤及遠處轉移。充分說明了MSI-H病人的腫瘤更多見于右半結腸及低分化黏液腺癌,但相關文獻報道MSI-H 淋巴結轉移更常見[17]。在本研究中的TNM分期中,MSI-H組的Ⅰ期及Ⅱ期腫瘤明顯高于MSI-L/MSS組,且在原發腫瘤浸潤深度上,MSI-H組T2 期腫瘤明顯高于對照組,在淋巴結轉移情況中,MSI-H 組的N1 腫瘤亦明顯高于MSI-L/MSS 組(P<0.05),這與相關學者研究對比相似[18]。在腫瘤長徑方面,MSI-H 組明顯較大,且腫瘤神經侵犯較多,亦伴有癌結節(P<0.05)。在臨床基本特征中,表現為MSI-L的結直腸癌家族史明顯較多(P<0.05)。
從相關研究表明,與微衛星穩定病人相比,微衛星不穩定病人的平均生存期更長,預后更佳[19]。在臨床及病理基本特征對比分析上,高度微衛星不穩定與低度微衛星不穩定和微衛星穩定兩者比較有明顯差異,且微衛星不穩定分期更早,預后更好。但在腫瘤治療方面,手術切除腫瘤是基本,后續需要聯合化療或是免疫治療,這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