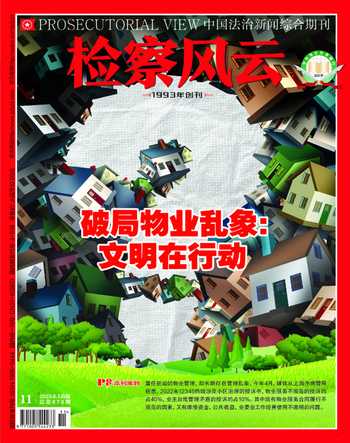短視頻新聞不能“只圖一樂”
張苗
如果你刷一會兒短視頻,大概率會看到這樣的視頻新聞:一張頗具沖擊力的圖片或一段視頻,頂部用黑底黃字或鏤空紅字的格式,一句簡單的事實描述加一句網友評論,整個畫面稍顯粗糙。如果有采訪,當事人的回應一般是這樣的:“當時覺得很有意思,就順手拍下來,沒想到居然火了。”
近年來,短視頻新聞越來越成為人們獲取資訊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一種“新黃色新聞”正在悄然無息的蔓延。
前世今生
“黃色新聞”是一種以煽情刺激性內容和夸張獵奇手法吸引受眾的新聞作品和理念,這一概念源自19世紀末兩位美國報業大亨約瑟夫·普利策與威廉·赫斯特的商業競爭。他們通過在新聞報道中使用煽動性的大號標題,描寫刺激性和娛樂性的內容來迎合讀者,甚至對不重要的新聞選用“渲染”“夸張”的手法,以達到提高報紙銷量的目的。
在赫斯特與普利策的商業競爭中“黃孩子”之爭最為典型。當時《世界報》曾雇傭漫畫家創造了一個身穿黃色衣服小男孩的漫畫形象,以“黃孩子”之口講述當時紐約的熱門新聞,后來赫斯特找到了漫畫作者,以高薪“挖角”。普利策不甘示弱,另找畫家繼續畫這個“黃孩子”。于是,兩家報紙各自有一個穿著黃衣服的孩子,缺著大門牙講述著當時煽情的“新聞故事”,并且都稱自己才是正版。這也是“黃色新聞”一詞的由來,后美國新聞史上將其稱為“黃色新聞浪潮”。
過了100年后的今天,人們驚訝地發現,沉寂已久的“黃色新聞”似乎借著短視頻的東風正在被“復活”。它們以“短平快”為突出特征,活躍于各大短視頻平臺之上,具備很高的同質性且擁有非常“亮眼”的傳播數據。
我們在短視頻平臺上看見的“新黃色新聞”,標題一般采用黑底黃字,內容由“一句事實描述+網友評價”所構成,其中核心事件的視頻時長不超過20秒,有時還附帶一兩句真假不明的采訪。這種“黃色字幕+簡單采訪”的新聞短視頻往往制作簡陋、時長較短、新聞六要素也并不齊全。比如,“年輕人的游湖方式——網友:不得不說,老舒服了”“司機將酒駕入刑標志貼在遮陽板上——網友:達摩克利斯之劍”“女子自帶酒水進入KTV被攔截后當場給小哥普法——網友:用最溫柔的語氣說最狠的話”……
不到20秒的視頻、沒頭沒尾、不知所云,輕松獲得十幾萬點贊。雖然不能給觀眾提供任何有價值的信息,但因標注了時間地點,因此被認為具有一定的新聞性。但隨著此類視頻“野蠻生長”,有的短視頻新聞甚至不具備新聞性,除了舊聞當新聞發,還有的出現了擺拍新聞、虛假新聞等。
“泛濫”之思
簡而言之,“新黃色新聞”是以醒目的標題加上情緒化的配樂,模板化報道社會事件的短視頻新聞。重慶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賴黎捷表示,目前短視頻平臺中盛行的“新黃色新聞”雖與美國“黃色新聞浪潮”沒有歷史淵源,但其產生的社會影響卻與美國黃色新聞相似。
與美國“黃色新聞浪潮”不同,“新黃色新聞”的傳播渠道往往以短視頻為主,借助多類社交平臺實現快速“繁殖”。記者簡單歸納了這類新聞的特點:新聞要素不全,帶有引導性,通常表現為“簡單的事實判斷+情緒鮮明的價值判斷”;趣味性、戲劇性高且充滿懸念,新聞事件描述時含有網絡流行語或網絡熱梗,具備多級傳播特質;傳播主體范圍廣,UGC(用戶生產內容)、PGC(專業生產內容)、OGC(職業生產內容)交織;廣泛活躍于短視頻傳播平臺且情感沖擊力強。此外,“新黃色新聞”的視頻內容日常化、生活化趨勢明顯,“日常瑣事”“搞笑抓拍”等也會成為“新聞”。
那么,“新黃色新聞”為何會如此猖獗呢?
與大眾的一般印象相反,很多時候不是媒介內容決定形式,而是媒介形式決定內容。短視頻的時長決定了用戶很少對觀看內容進行深度思考,而只是“圖一樂”。媒介的娛樂功能在算法的加持下成為了用戶觀看邏輯的唯一主宰,而“新黃色新聞”的特征完美匹配了短視頻平臺的邏輯:醒目吸睛的標題、一目了然的沖突、無須思考的主題。所以毫無營養的短視頻新聞被批量生產,以其娛樂性而非新聞性滿足大眾對于信息的需求。

大數據時代全新的采編流程是“新黃色新聞”繁殖的技術因素。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志安認為,過去的黃色新聞是市場選擇,而今天的“新黃色新聞”是市場和平臺的雙向選擇。張志安表示,新社交時代網絡新聞傳播的最大變化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審核把關機制的讓步,算法推薦的把關對整個內容分發體系產生了根本性的革命;二是對于數據流量的“迷戀”;三是網絡新聞傳播趨向于流行、趣味和煽情的內容偏好。
中央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郭全中認為,“新黃色新聞”的泛濫,并非是媒體門檻變低,而是內容門檻變低。相較于文字創作時代,短視頻時代吸引了更多自媒體創作者參與其中,這也導致其生產內容良莠不齊。究其本質,并非媒體的門檻越來越低,而是技術帶來的平權效應使得內容創作的門檻越來越低。
對于當下“新黃色新聞”的泛濫和嚴肅深度報道的式微,重慶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副院長賴黎捷認為,技術賦予了普通人拍攝、剪輯視頻的能力,人人都是記者的生產模式為“新黃色新聞”提供了語料來源。此外在短視頻時代下,流量即收益,“短平快”的“新黃色新聞”是收割用戶注意力最便捷的方式。相反,以文字報道為主的深度報道受眾面變窄,受眾流失導致媒體生存壓力劇增,倒逼媒體人逐漸放棄據守十數年的深度報道轉戰短視頻新聞。
在記者看來,短視頻平臺掌握著渠道、數據與流量,從而對新聞生產者提出要求,這種要求必然與短視頻的媒介形式相適應。當平臺和算法捕捉到人們對于娛樂的需求后,便專注于用流量的壓力“倒逼”媒體產出毫無營養的“新黃色新聞”。短視頻新聞的現狀,實質上是用戶、平臺與媒體三者合流的結果。
亟須改“色”
社會公器既是權力,也是責任。
在我國,新聞媒體具有輿論引導的重要功能。一味地迎合受眾不利于新聞內容質量的提升。公眾賦予了媒體大的聲量權重,媒體須以普遍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在信息洪流中發掘出真正有價值的新聞內容提供給公眾。
因此,媒體應掙脫平臺流量的算法邏輯。諸多的“新黃色新聞”是對用戶生產新聞的二次編發,生產“新黃色新聞”不僅違背新聞生產規律,也不利于形成健康、優質的新聞生態格局。此外,過度追逐流量只會導致“媒體追著事件跑”,媒體設置話題和輿論引導的作用將降低。
為了改變這種短視頻生態格局,賴黎捷稱新聞從業者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引,嚴格律己、秉持新聞價值規律、拒絕流量誘惑;學習新技術、更新技術觀念,避免造成短視頻新聞內容“格式化”“工廠化”;堅持“新聞是跑出來的”實踐真理,須知短視頻新聞的內容依舊是文字,媒體人應踐行“四力”為群眾挖掘優質的新聞報道。
張志安認為,一個合格的新聞工作者在生產短視頻新聞時須注意兩個方面。第一是將趣味性和其他的新聞價值相結合。因為新聞價值包含真實性、時效性、接近性、重要性、趣味性等,短視頻新聞要在短時間內把所有要素都兼顧較難,故可以確定以一個要素為主導,再加上一兩個更重要的要素。第二是把關,專業新聞媒體和自媒體最大的區別在于核實,專業媒體會對內容的真實性負責,故媒體應向爆料者進行核實,以確定視頻是否真實。
當人們開始集體反思“新黃色新聞”的泛濫時,一種悄無聲息的變革可能才剛剛開始。美國在經歷了19世紀末黃色新聞浪潮后才走上了新聞專業主義的道路,那么眼下的“新黃色新聞”是否也只是新聞業發展中的小小彎路?“新黃色新聞”是新媒體時代面臨的問題,需要新聞從業者、平臺和公眾共同努力、共同抵制才能改“色”,提高新聞質量、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