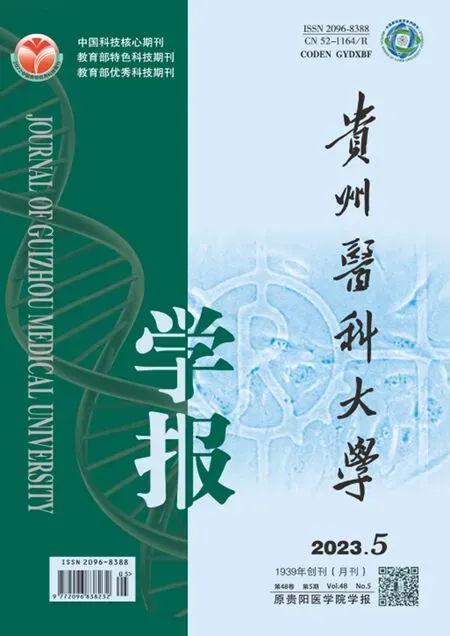外周血NLR及LMR對局部晚期鼻咽癌長期生存預后的評估價值*
趙洪韜, 吳偉莉, 金風, 李媛媛, 龍金華, 羅秀玲, 唐紅, 陳宇, 張芒, 周灣
(1.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頭頸腫瘤科, 貴州 貴陽 550001; 2.貴州醫科大學 臨床醫學院, 貴州 貴陽 550001; 3.貴州省腫瘤醫院 頭頸腫瘤科, 貴州 貴陽 550001)
早期鼻咽癌患者的癥狀一般不明顯,難以發現,一旦確診,約80%患者已處于局部晚期。早期鼻咽癌的5年生存率可達90%以上,而局部晚期鼻咽癌的患者亦達到74.5%~86%的5年生存率,究其原因得益于放射治療技術和化療方案的不斷更新[1]。腫瘤淋巴遠處轉移(tumor node metastasis,TNM)分期系統是預測鼻咽癌預后的金標準,TNM結合血漿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DNA拷貝數對患者預后有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但血漿EBV-DNA拷貝數的檢測只能在級別較高的醫院進行,并且檢測水平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需要尋找更簡便的腫瘤預后指標來指導鼻咽癌的臨床治療。血常規是臨床最基本的血液檢驗項目,外周血中許多細胞及蛋白等指標被發現與腫瘤的預后相關。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s to lymphocytes ratio, NLR)是指外周血中中性粒細胞計數絕對值與淋巴細胞的計數絕對值的比值,淋巴細胞與單核細胞比值(lymphocytes to monocytes ratio, LMR)是指外周血中淋巴細胞計數絕對值與單核細胞的計數絕對值的比值,本研究選取了這兩個已被證實與多個實體瘤預后相關的比值進行研究,同時結合指標的不同風險程度進行分組,綜合分析其對局部晚期鼻咽癌長期生存的影響,旨在探尋一種簡單易行且準確性較高的預后預測方法,為臨床預測腫瘤患者預后提供一定指導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3年3月—2015年9月收治的初治局部晚期鼻咽癌的患者200例。納入標準:(1)完成多西紫杉醇+順鉑+氟尿嘧啶(TPF)方案(2~3周期)誘導化療、調強放療聯合大劑量順鉑(DDP,2~3周期)同期化療局部晚期鼻咽癌的患者;(2)有較完整的隨訪資料。200例患者中,男性139例、女性61例,年齡21~72 歲、平均(47.9±11.1)歲;根據TNM腫瘤分期法,T分期為3~4期115例、1~2期85例,N分期為0~2期有115例、3期85例;臨床分期為Ⅲ期有57例、Ⅳ期143例。患者中位隨訪時間為54個月(8~86個月),45例患者在隨訪期間死亡,19例疾病進展,5年總生存率77.5%、無進展生存率68.0%。
1.2 研究方法
1.2.1治療方法 (1)誘導化療:TPF方案誘導化療2~3周期,第1天,采用多西紫杉醇75 mg/m2、靜脈滴注;第1~5天,采用順鉑75 mg/m2、分5 d用、輸液泵持續泵入(10∶00~22∶00);第1~5天,氟尿嘧啶750 mg/(m2·d),輸液泵持續泵入(22∶00~次日10∶00);21 d為1周期,共完成2~3個周期。(2)同期放化療:誘導化療結束后3周開始同期放化療,采用調強放療(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therapy,IMRT)技術,接受直線加速器6 mV-X線照射,根據ICRU50號及ICRU62號報告原則進行靶區勾畫。鼻咽病灶劑量69.96~73.92 Gy/33次,有頸淋巴結轉移患者的劑量69.96 Gy/33次,亞臨床靶區及高危淋巴引流區劑量60.06 Gy/33次,低危淋巴引流區劑量50.96 Gy/28次;同期化療采用順鉑 100 mg/m2,第1天,持續滴注,21~28 d為1周期,共完成2~3個周期。
1.2.2隨訪 于同期放化療結束后隨訪,2年內每3月、2~5年每6月及5年后每1年復查一次,采用門診或住院方式隨訪,記錄患者5年的總生存期(overallsurvival,OS)及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 free survival,PFS),OS時間定義為治療開始之日~患者死亡時間,PFS時間定義為從治療開始之日起至疾病進展(復發、轉移等原因)、或者發生任何原因死亡的時間。
1.3 觀察指標
收集患者首次化療前72 h內的血常規報告,記錄中性粒細胞、淋巴結細胞及單核細胞絕對值,計算外周血NLR與LMR。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析確定2組指標的最佳臨界值,并計算出相應曲線靈敏度、特異度,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生存曲線,并根據2組指標的最佳臨界值對患者的OS及PFS的進行預后分析;根據NLR、LMR最佳臨界值高低對200例患者進行分組(年齡、性別、T分期、N分期及臨床分期在各組間的所占例數和百分比),并進行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及多因素Cox風險模型對OS及PFS進行獨立危險因素分析,確定影響鼻咽癌患者OS和PFS的預后因素。將NLR及LMR組合分析,其中NLR及LMR高于、等于,或小于、等于其最佳臨界值,兩者同時對鼻咽癌提示不良預后的結果分為高風險組;將NLR及LMR高于、等于,或小于、等于其最佳臨界值,兩者只有一個提示不良預后的結果分為中風險組;將NLR及LMR高于、等于,或小于、等于其最佳臨界值,兩者同時提示較好預后的結果分為低風險組;計算三組的OS率及PFS率,進行組間比較;對不同分組的T3-4及N3所占比例進行組間比較。
1.4 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 NLR、LMR預測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5年生存情況
200例患者治療前外周血NLR為(3.76±0.23,范圍1.06~27.38),LMR為(3.53±0.17,范圍0.63~12.33)。根據NLR、LMR與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5年生存率情況進行ROC曲線分析,NLR對患者5年生存率的診斷價值AUC=0.839(P<0.05)、靈敏度77.8%、特異度84.5%、最佳臨界值為3.81;LMR對患者5年生存率的診斷價值AUC=0.781(P<0.05)、靈敏度97.4%、特異度55.6%、最佳臨界值為2.03。見表1、圖1。

圖1 NLR和LMR的ROC曲線

表1 外周血NLR與LMR對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
2.2 不同臨界值NLR和LMR患者的一般資料差異性比較
根據NLR、LMR最佳臨界值高低對200例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進行分組,比較各組患者年齡、性別、T分期、N分期及臨床分期的分布情況。見表2。

表2 一般臨床資料[n(%)]
2.3 影響OS的獨立危險因素分析
通過單因素及多因素Cox回歸分析提示,N分期(HR=0.425,95%CI為0.185~0.975,P<0.05)、NLR≥3.81(HR=0.117,95%CI為0.048~0.282,P<0.05)、LMR<2.03(HR=0.449,95%CI為0.212~0.952,P<0.05)是OS獨立危險因素,見表3。

表3 影響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總生存率的單因素及多因素Cox回歸分析
2.4 影響PFS的獨立危險因素分析
通過單因素及多因素Cox回歸分析提示,N分期(HR=0.288,95%CI為0.141~0.589,P<0.05)、NLR≥3.81(HR=0.215,95%CI為0.110~0.420,P<0.05)是PFS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4。

表4 影響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無進展生存率的單因素及多因素Cox回歸分析
2.5 NLR和LMR聯合檢測對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預后的影響
危險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根據NLR和LMR聯合檢測結果,將200例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分為3組:高風險組30例(NLR≥3.81且LMR<2.03)、中風險組35例(NLR<3.81且LMR<2.03,或NLR≥3.81且LMR≥2.03)及低風險組135例(NLR<3.81且LMR≥2.003。3組患者的5年OS率分別為13.3%、68.6%、94.1%,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83.973,P<0.05);3組患者的5年PFS率分別為6.7%、57.1%、84.4%,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47.286,P<0.05)。見表5。生存曲線見圖2、圖3。

圖2 不同風險組的總生存曲線

圖3 不同風險組無進展生存曲線

表5 不同風險分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的OS率及PFS率比較
2.6 不同風險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的T、N分期比較
3組T分期為T3-4患者數所占比率分別為低風險組59.3%、中風險組45.7%及高風險組63.3%,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3組N分期為N3的患者數所占比率分別為低風險組35.6%,中風險組37.1%,高風險組80.0%,組間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6 不同風險組N分期比較[n(%)]
3 討論
據統計,慢性炎癥與世界上約25%的癌癥有關[2],已被證實的有如胃癌的發生與幽門螺桿菌感染相關,乙肝病毒與丙肝病毒的感染可以增加肝癌的患病風險。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提示了炎癥反應通過體內各種途徑介導腫瘤的發生發展過程,證實了腫瘤與炎癥的存在密切的聯系。
炎癥反應主要通過調控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來影響癌癥的發生發展過程[3-4]。而在臨床工作中,這些有調節作用的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通常無法被常規測量。但是,可以通過測量外周血中表達它們的細胞成分作為替代。近年來,已經提出基于這些外周血細胞計數的不同指標的組合標志物來研究其與腫瘤預后的相關性。其中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和單核細胞作為臨床常用檢驗指標,其組合標志物的NLR和LMR被認為可能與多種惡性腫瘤的預后相關[5-8]。
近些年來,相關的研究表明NLR升高可能與腫瘤的發生、發展及預后不良相關,是一種預測因子[9-11]。NLR的升高在一定程度上提示腫瘤可能處于高代謝狀態,發生發展更快,而同時患者的免疫功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預后可能較差。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治療前外周血NLR升高是其5年OS率和PFS率降低的獨立危險因素,與An等[12]和Chang等[13]的研究結論一致。同時在Chang等[13]的研究中,也使用ROC曲線進行分析,得出NLR最佳截點值為3.73,但在該文中,納入的3237例病例,納入早期至晚期的患者,且占比例較多的局部晚期的治療方式和化療方案不統一。目前有關NLR與預后相關的研究多屬于回顧性的研究,李曉惠等[14]不僅證明 NLR>3 是鼻咽癌患者的不良預后因素,還發現了NLR>3的患者其總生存率、無局部復發率、無遠處轉移率均遠低于NLR≤3的患者。而在本文中,研究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并應用相同的治療模式和化療方案后通過ROC曲線等方法得出結論,治療前NLR對患者5年生存率的診斷價值AUC=0.839(P<0.05)、靈敏度77.8%、特異度84.5%、最佳臨界值為3.81,且NLR≥3.81是預測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OS率及PFS率降低的獨立危險因素。雖然關于臨界值目前沒有統一的標準,但目前已有的相關報道表明,高NLR不利于患者預后。
LMR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宿主免疫和腫瘤微環境之間的平衡關系,較低的LMR可能提示宿主的免疫功能不全,并參與了腫瘤的發生發展,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淋巴細胞的減少有助于腫瘤細胞避開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s)的免疫監視,另外,外周血單核細胞可經過滲透,抵達腫瘤部位并且分化成腫瘤相關巨噬細胞,產生細胞因子,其可促進血管生成、免疫逃逸以及腫瘤細胞的增殖與轉移[15]。目前,有一些研究稱LMR在霍奇金淋巴瘤、非小細胞肺癌、急性白血病、轉移性胃癌預后中有一定相關性;另一些研究表明在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等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治療前外周血 LMR較低與患者預后不良相關[16]。但關于LMR與鼻咽癌預后的相關研究較少,一些研究報道證明LMR升高意味著單核細胞下降而抗原誘導的淋巴免疫細胞增殖,可能是 NPC患者預后的有利因素[17]。在張晶晶等[18]的研究中,發現LMR值下降提示NPC患者有更晚的分期和更差的預后,但發現LMR下降對總生存的預測作用相對于傳統的AJCC分期和EBV-DNA,還是存在一定局限性。而從本研究得到的結果來看,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外周血的LMR降低是其OS率的獨立危險因素。目前LMR對惡性腫瘤患者的OS預測的最佳臨界值也沒有統一標準,本研究中通過ROC曲線分析得到2.03是預測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預后不良的最佳臨界值,且LMR<2.03是預測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
此外,本研究聯合了NLR及LMR對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進行進一步分析后發現,高風險組(NLR≥3.81且LMR<2.03)5年OS率及PFS率明顯降低,而低風險組(NLR<3.81且LMR≥2.03)患者的OS及PFS明顯改善,提示我們將NLR和LMR聯合起來,對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進行分層分析,能夠有效地預測其生存情況。其中,分組為高風險組的患者預后相對較差,在治療上可以考慮使用如聯合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等更積極的腫瘤治療,以便有機會獲得更好的生存。同時,我們在分組分析時發現,高風險組的N3分期的人數所占比例明顯升高(高風險組80.0%、中風險組37.1%、低風險組35.6%,組間差異有統計學分析意義,P<0.05),而N分期越晚的患者其遠轉可能性越高,提示治療前外周血NLR升高且LMR降低的患者可能有更差的N分期、臨床分期及預后。
目前,找尋評估腫瘤預后預測因素的研究較多,但在臨床工作中,TNM分期仍是預測鼻咽癌預后的首要方法。但因其有一定的局限性,較難針對個體做出精準的預測。本研究發現,高NLR且低LMR分組中,其N分期相對較晚,預后較差。NLR及LMR易檢測,且重復性高,為預測局部晚期鼻咽癌預后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同時,NLR升高與LMR降低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患者免疫抑制狀態及免疫功能不全,對于NLR高及LMR低的患者,本研究結果也為其是否采用靶向、免疫等相關治療可能提供了一定參考價值。
綜上所述,治療前外周血NLR升高及LMR降低能夠有效地預測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放化療后的OS率及PFS率,提示了治療前外周血NLR和LMR有望成為預測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長期生存的重要因素,并且兩者聯合檢測對臨床指導意義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