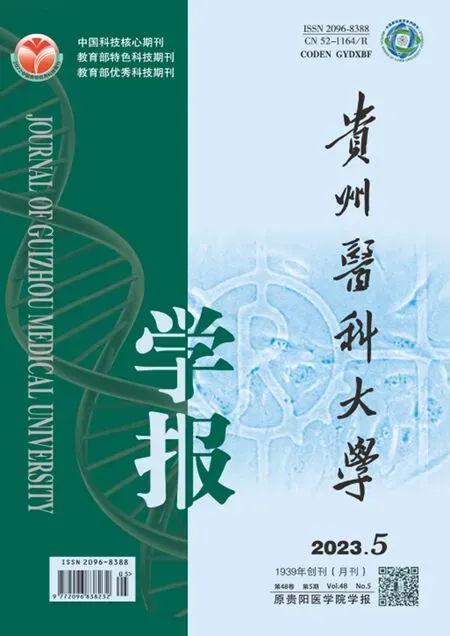膿毒癥患者早期血清學指標對死亡的預測價值及診斷價值*
左和平, 吳佳麗, 梅斌
(1.安徽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EICU, 安徽 合肥 230601; 2.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超聲診斷科, 浙江 杭州 310013; 3.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麻醉與圍術期醫學科, 安徽 合肥 230022)
膿毒癥是由于宿主對感染產生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并可能最終發展為嚴重的器官功能障礙、膿毒性休克或死亡,每年有超過1 900萬人發生膿毒癥,約600萬人死亡, 該病具有極高的病死率以及遺留生理功能缺陷,目前仍是醫院面臨的重大難題、亦是全球性負擔[1-3]。膿毒癥的病理生理過程復雜,其早期識別和干預對其病理生理的逆轉、降低病死率和致殘率至關重要。目前對于感染所致膿毒癥診斷仍以微生物培養作為金標準,但因其耗時長、抗生素的早期使用使血培養的敏感性降低,以血培養作為早期診斷標準存在很大局限性[4]。膿毒癥患者的實驗室指標和評分是臨床上較容易獲得指標,其對患者的診斷和評估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分析不同轉歸膿毒癥患者的早期臨床指標,以評價這些指標的臨床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年1月—2021年9月明確診斷膿毒癥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符合膿毒癥和膿毒性休克的診斷標準[4];(2)18~95周歲。排除標準:(1)入院24 h內死亡或自動出院者;(2)合并終末期惡性腫瘤者或行放化療患者;(3)患有結締組織病、血液系統惡性腫瘤、自身免疫性疾病、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肝炎等疾病;(4)臨床資料不完整者。本研究獲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批號YX2021-132)。
1.2 分組
根據患者患病后28 d生存情況分為存活組(n=69)和死亡組(n=42);根據是否發生休克又分為膿毒癥組(n=58)和膿毒性休克組(n=53),膿毒性休克是指膿毒癥患者出現持續性低血壓,且在充分容量復蘇后仍需血管活性藥來維持平均動脈壓≥65 mmHg、血乳酸水平>2 mmol/L;根據是否發生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分為膿毒癥合并MODS組(n=51)和膿毒癥未合并MODS組(n=60)。
1.3 觀察指標
收集入組患者的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原發感染部位、生存時間及疾病轉歸。入院24 h內對患者進行急性生理學與慢性健康評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scoring system,APACHEⅡ) 、序貫器官衰竭(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評分及入院24 h內取血檢測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血常規、血清乳酸脫氫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總膽紅素(tota bilirubin,TBIL)、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D-二聚體(D-Dimer)、血纖維蛋白原(fibrinogen,FIB)。
1.4 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 臨床資料
本研究最終納入膿毒癥患者111例,其中男59例、女52例,年齡24~93歲、平均(62.96±15.02)歲。根據原發感染部位分成肺部感染15例、腹腔感染29例、泌尿系感染19例、中樞感染3例、軟組織感染10例、合并多部位感染35例。以28 d轉歸結果對生存組和死亡組進行分析,死亡組患者的年齡、APACHEⅡ評分、SOFA評分、血清LDH、BUN、SCR和D-Dimer高于生存組,而FIB低于生存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生存組與死亡組臨床資料單因素分析
2.2 膿毒性休克或合并MODS患者臨床資料單因素分析
結果顯示,膿毒癥無休克與休克組比較、無合并MODS與合并MODS組比較,血清LDH、BUN、SCR、FIB及D-Dimer指標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PCT在是否合并休克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CRP在兩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表3。

表2 膿毒癥休克組與膿毒癥無休克組患者血液學指標比較

表3 膿毒癥合并MODS組與膿毒癥未合并MODS組患者血液學指標比較
2.3 膿毒癥患者28 d預后Cox回歸生存分析
以28 d生存狀態為結局,將單因素分析存在意義指標納入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結果顯示血清LDH的OR值1.001,95%CI(1.001~1.001)、FIB的OR值0.793,95%CI(0.655~0.961),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提示血清LDH、FIB是膿毒癥患者死亡的危險因素。

表4 膿毒癥患者28 d生存預后的Cox回歸分析
2.4 膿毒癥患者各指標ROC曲線分析
以28 d生存狀態為結局繪制ROC曲線,結果顯示APACHEⅡ評分、SOFA評分及血清LDH對膿毒癥患者28 d預后的預測價值較高,AUC分別為0.928、0.904、0.879,高于CRP、PCT、BUN、SCR、FIB及D-Dimer的預測價值。見表5。

表5 影響膿毒癥患者28 d預后相關風險因素
2.5 膿毒癥患者危險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線
將以上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指標納入危險因素分析,以28 d生存狀態為結局、以最佳截斷值分組繪制Kaplan-Meier生存曲線(圖1),高血清LDH、BUN、SCR和D-Dimer患者累計生存時間均顯著縮短(P<0.05);而不同水平FIB患者的累計生存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449,P=0.503)。見表6。

圖1 不同預后膿毒癥患者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

表6 各危險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線分析
3 討論
盡管對膿毒癥的臨床研究已經較多,在治療方面也取得重大進展,但是膿毒癥仍有近一半的高死亡率[5],困擾廣大臨床醫生,早期病情嚴重程度判斷對治療策具有重要作用。最初膿毒癥被認為是過度炎癥反應導致組織和器官損傷,研究者重視炎癥指標在膿毒癥患者中的評估作用,Jekarl等[6]指出PCT是膿毒癥獨立危險因素,劉大東等[7]研究中死亡組白細胞較生存組顯著升高,與病情嚴重程度呈現正相關,但因炎癥指標易受感染病原體類型、年齡、宿主反應能力、疾病狀態等因素影響,年齡較大病情較重者可反應不典型[8],在本研究中雖然死亡組CRP、PCT較生存組高,但在兩組之間卻未見統計學意義,且AUC分別為0.570和0.563,其預測價值較低。近些年來APACHEⅡ和SOFA評分系統越來越多用于膿毒癥患者的評估中,Daga等[9]研究指出APACHEⅡ評分可作為膿毒癥早期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當評分數值超過22.5預測死亡率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均超過80%,且SOFA評分預測早期死亡率的AUC為0.971,在本研究死亡組的APACHEⅡ和SOFA評分顯著高于生存組,但不可忽略APACHEⅡ和SOFA評分均包括多個變量且依賴實驗室結果,是一個耗時且復雜的項目。
近些年膿毒癥在細胞免疫、凝血、微循環、能量代謝和器官功能障礙等方面的病理生理機制研究倍受關注,本研究收集膿毒癥患者入院后24 h內血液指標,發現血清LDH、BUN、SCR、FIB、D-Dimer不僅在死亡與生存組之間存在統計學差異,亦在不同嚴重程度組存在統計學差異。既往研究發現機體為抵抗應激能夠通過葡萄糖代謝重編快速產生能量,即無論機體是否缺氧,免疫細胞等可轉換葡萄糖原有的能量代謝途徑而增加糖酵解過程,血清LDH作為催化酶將丙酮酸轉化為乳酸參與其中,此過程在膿毒癥中起著關鍵作用[10-11],此外研究者發現內毒素、低血壓等創傷下可造成組織受損、細胞通透性增加或細胞凋亡,亦可導致血清LDH增加及活性升高[12],本研究中死亡組血清LDH明顯高于生存組,膿毒性休克或合并MODS者亦明顯升高,經統計分析血清LDH對預后評估具有較高敏感性和特異性,為膿毒癥患者的獨立危險因素,與既往段金旗等[13]和Lu等[14]的研究結果一致。BUN是人體內蛋白質代謝的最終產物并通過腎臟代謝,內毒素及炎癥反應不僅可增加機體對能量需求造成負氮平衡,同時內毒素刺激可致腎臟內尿素轉運蛋白表達降低,腎血流量及腎內滲透壓下降[15-16],嚴重膿毒癥常可出現腎小管壞死至急性腎損傷[17],同時影響BUN代謝,出現BUN、SCR水平的升高,增加患者的病死率,在Zhao等[18]的一項隊列研究中發現,BUN可作為膿毒癥1年總生存率的獨立預測因子,在范泉等[19]研究中BUN對膿毒癥早期預后AUC為0.731(95%CI:0.635~0.827),本研究繪制Kaplan-Meier生存曲線亦發現高BUN、SCR的累計生存時間顯著降低。凝血功能紊亂在膿毒癥疾病的發展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20],早期內毒素及炎癥因子促進組織因子釋放,激活凝血系統并出現纖溶亢進,導致纖維蛋白降解產物增多,與本研究死亡組低FIB和高D-Dimer結果一致,但隨著膿毒癥疾病進展凝血及纖溶均可受抑制,出現血液高凝、纖維蛋白未降解至微血栓形成,最終導致彌漫性血管內凝血的出現[21],該過程還需更大樣本及更深入研究進行闡述。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研究,且納入樣本量尚不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續可行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以明確相關指標的預測價值,其次未增加遠期預后,后續仍需更大樣本多中心長時間的研究,進一步了解在膿毒癥患者中相關指標的臨床價值。
綜上所述,經過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可知血清LDH、BUN、SCR、FIB、D-Dimer均是膿毒癥預后不良的危險因素,涉及炎癥反應、細胞代謝、能量等方面,其中血清LDH對膿毒癥預后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及特異性,結合其他指標對疾病嚴重程度及預后具有較高的預測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