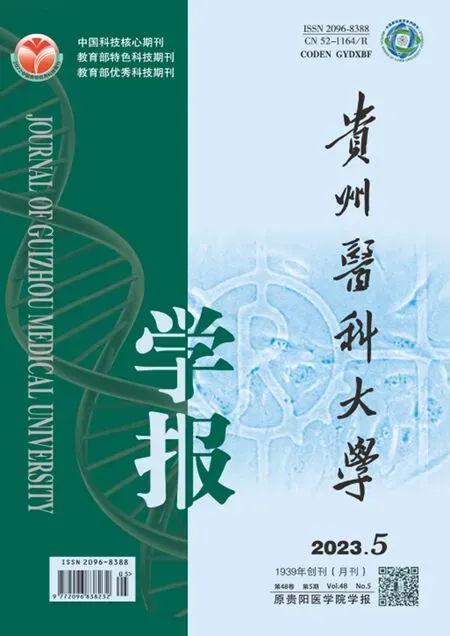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股骨頸與腰椎的骨密度特點*
晏揚, 刁曉艷
(1.貴州醫科大學 臨床醫學院, 貴州 貴陽 550004; 2.貴州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心血管內科, 貴州 貴陽 550004)
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HF)是各種心血管疾病的嚴重表現和終末階段,是心室收縮和(或)舒張功能障礙、進而導致心臟充盈和(或)射血功能受損,臨床表現為循環淤血,器官、組織血液灌注不足為特征的一組綜合征。骨質疏松癥(osteoporosis,OP)是一種骨骼疾病,是以骨量低、易發生骨質疏松性骨折的全身性骨病。心血管疾病和骨質疏松癥多發生于老年患者,隨著社會老齡化,未來會是我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以往多數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和骨質疏松癥常常并存[1],心血管疾病患者發生骨質流失的風險更高,更容易產生骨折風險;另一方面,與具有正常骨量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相比,低骨量個體發生心血管事件死亡率更高[2]。目前國內外針對心力衰竭與骨密度變化二者之間的機制尚未明確,相關研究尚少,本研究通過比較心衰患者股骨頸與腰椎骨密度,探討不同類型心力衰竭與骨密度之間的相關性。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病例組選自2018年11月—2019年12月心血管內科住院病人,根據患者病史、癥狀、體征以及相關檢查,參照《中國心力衰竭診斷和治療指南2018》[3],通過心臟超聲射血分數(ejection fraction,EF),B型鈉尿肽前體(NT-pro BNP)測定結果以及有無心衰癥狀、體征進行分組,將患者分為:EF<40%的患者為射血分數降低的心力衰竭(HFrEF)組(51例)、EF為40%~49%的患者為射血分數中間值的心力衰竭(HFmrEF)組(52例)、EF≥50%的患者為射血分數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組(108例)。病例組的入選標準:(1)符合心力衰竭診斷標準,年齡≥50歲,女性均限定為絕經后婦女;(2)可接受心臟彩超和骨密度檢查。排除標準:(1)排除肥厚型心肌病、結構性心臟病、浸潤性心臟病、心內腫瘤等;(2)各種可導致骨質疏松癥的繼發性疾病患者,如甲亢、原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腎上腺腫瘤等疾病;(3)非心源性呼吸困難水腫、嚴重腎病、貧血、動靜脈瘺;(4)影響骨密度測定值的疾病,如Paget骨病、多發性骨髓瘤、類風濕性關節炎、強直性脊柱炎、癌癥;(5)長期使用抗骨質疏松藥物治療的患者,如降鈣素、激素類、雙膦酸鹽類、甲狀旁腺激素、選擇性雌激素受體調節劑、類固醇激素等。取同期心功能正常(NT-Pro BNP<125 ng/L,EF>50%,沒有心衰竭體征及癥狀)的健康體檢者107例作為對照組。本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2019074K)。
1.2 研究方法
1.2.1一般資料 所有研究對象進行常規體格檢查,記錄體重、身高,計算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記錄患者性別及年齡等資料。
1.2.2血生化指標 患者入院當晚22點開始禁食,次日清晨抽取肘部空腹靜脈血,采用全自動血液生化流水檢測儀檢測NT-pro BNP、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總膽紅素、直接膽紅素、間接膽紅素、肌酐、尿酸、空腹血靜脈血糖、甘油三酯、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促甲狀腺素(TSH)、血清游離三碘甲狀腺原氨酸(FT3)、血清游離甲狀腺素(FT4)、維生素 D等指標。
1.2.3骨密度測定 選擇雙能X線骨密度儀、采用雙能X線吸收法(DXA)測量并記錄腰椎1-4骨密度(lumbar bone mineral density,LBMD)、任一側股骨頸骨密度(femoral neck bone mineral density,FNBMD),每個部位重復3次,取均值,結果以T值表示。按照中國《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診療指南(2017)》骨質疏松癥診斷的金標準:T值≥-1.0為正常,-2.5~-1.0 為低骨量;T值≤-2.5 為骨質疏松[4]。
1.3 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不同類型HF組患者與對照組被檢者的性別、年齡及BMI指標進行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各HF組患者和對照組被檢者一般資料比較
2.2 血生化指標
與對照組比較,3組HF患者維生素D均有明顯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在不同類型HF組患者中,總膽紅素、尿酸及NT-pro BNP隨著射血分數降低,有升高趨勢;其余生化指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各HF組患者和對照組被檢者血生化指標比較
2.3 骨密度T值≤-2.5發生情況
3組HF患者中骨密度T值≤-2.5共計 138 例,發生率為65.40%。其中,HFpEF、HFmrEF 以及 HFrEF 各組骨密度T值≤-2.5發生率分別為 75.00%、59.62%、50.98%,對照組僅為 36.51%,各HF組患者骨密度T值≤-2.5的比例均高于對照組。見表3。

表3 各HF組患者和對照組被檢者骨密度T值≤-2.5發生情況比較
2.4 不同部位骨密度比較
結果表明,3組HF患者的股骨頸的骨密度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3組HF患者與對照組腰椎骨密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類型HF患者組的股骨頸骨密度比較、腰椎骨密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各HF組患者和對照組被檢者不同部位骨密度T值比較
2.5 各指標與骨質疏松的相關性
結果表明,年齡、NT-pro BNP與骨質疏松(骨密度T值≤-2.5)呈正相關(r值分別為0.282、0.205,P<0.05);BMI、維生素 D與骨質疏松(骨密度T值≤-2.5)呈負相關(r值分別為-0.184、-0.231,P<0.05)。見表5。

表5 各指標與是否發生骨質疏松的相關性分析
3 討論
在本研究中,HF患者膽紅素和尿酸均有升高,這可能與心衰時中心靜脈壓升高靜脈淤血導致肝淤血或心輸出量減少導致肝缺氧損傷有關[5],HF患者普遍存在腎臟灌注不足,腎小球濾過率降低,從而尿酸排泄減少,體內蓄積的尿酸增多[6]。此外HF患者有不同程度的低氧血癥,缺氧使得 ATP 減少,間接促使腺嘌呤降解為尿酸、肌苷、黃嘌呤和次黃嘌呤,最終導致尿酸產生增多[7],因此一方面由于尿酸產生增多,另一方面尿酸的排泄減少,最終致使血液中尿酸濃度升高。
HF與骨密度變化有著緊密聯系,HF會加速骨質流失,骨密度下降,最終發生骨質疏松性骨折,嚴重影響患者身心健康及生活質量。這可能歸因于二者具有共同影響因素諸如高齡、絕經后狀態、吸煙、缺乏運動、維生素 D 缺乏、腎臟疾病及糖尿病等危險因素[8]。與HF有關的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甲狀旁腺激素[9-10]、同型半胱氨[11-12]等同樣對骨代謝和鈣吸收有關。HF患者利尿劑的長期應用及活動減少都會影響鈣的吸收,加重骨質疏松。Abou-Raya等[13]對126名65歲以上HF患者的研究中顯示:與對照組相比,HF患者骨密度明顯低于對照組。Xing等[14]共包括六項研究(552名CHF和243名非CHF患者)的薈萃分析中表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與非心力衰竭患者相比,其總骨密度更低。朱彤等[15]在對慢性HF患者的骨密度分析研究中也驗證慢性HF患者的骨密度值低于正常對照組。
本研究結果表明,HF患者普遍存在骨密度下降,與國內外研究結果一致,并且對HF患者的不同部位骨密度進一步分析時,發現股骨頸骨密度下降更顯著,而腰椎骨密度沒有明顯降低趨勢,這與國外研究對已接受心臟移植的患者和等待移植的HF患者的研究以及Majumdar的隊列研究中結果一致,均表明HF組的股骨頸骨密度更低,骨折發生率更高,而腰椎骨密度保持相對正常[16]。但目前HF患者股骨頸骨密度相比較腰椎骨密度更低的實際依據尚不清楚,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一是腰椎椎體由于長期站立、重力因素影響,常發生椎體壓縮,壓縮的骨質疏松椎骨導致假性椎骨高密度;二是主動脈鈣化、腰椎增生也可能進一步造成測量過程中腰椎骨密度升高[17]。因此HF和股骨頸骨密度降低存在著潛在機制,但目前仍需大量研究與試驗去發掘。
此外,與對照組相比,3組HF患者的維生素D水平較低,這表明骨質流失的原因與維生素D缺乏有關,缺乏維生素D不僅會直接加速骨轉換,使得骨吸收過程整體快于骨形成,還會引起血甲狀旁腺激素濃度升高,導致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癥,進一步導致骨量丟失[18]。維生素D的缺乏會促進機體炎癥[19],炎癥介質釋放加重心肌受損程度,同時也會引起RAS的過度激活,增加心衰的風險[20-21]。
最后在進行骨密度降低相關性分析中,年齡、NT-pro BNP與骨密度T≤-2.5(骨質疏松)呈正相關,BMI、維生素 D與骨密度T≤-2.5(骨質疏松)呈負相關。目前,BMI和骨密度的相關性尚未完全統一,既往有研究表明一定范圍內,BMI越低,骨密度T值≤-2.5發生率越高,這與本研究中所得結果一致,身體質量作為一種長期存在的機械負荷,更大的體重會增加骨骼、肌肉的刺激,從而通過骨骼重塑刺激成骨,進而增加骨密度[22]。此外,HF患者由于自身疾病影響,通常伴隨不同程度的營養不良,可能會加重相應微量元素吸收不良,進而加重骨量丟失。NT-pro BNP作為HF診斷和治療中應用最為廣泛的生物標志物,主要由心房或心室舒張壁牽拉增加所產生。在國內外研究中認為,隨著骨密度的下降,NT-ProBNP的濃度會隨之升高[23-24],但 NT-ProBNP 促進骨質疏松的直接機制尚不清楚,而在本研究中對 NT-pro BNP與骨密度相關性分析中,結果顯示 NT-pro BNP與骨密度T≤-2.5呈正相關,這與上述研究一致。
HF患者普遍存在骨密度流失,以股骨頸骨密度降低表現更突出,骨質疏松甚至骨折發生率更高,提示HF患者更應該關注股骨頸骨密度的降低,預防骨質疏松和骨質疏松性骨折。另外,適當保持BMI及補充維生素D、補鈣等來預防骨密度下降,早期進行干預,減少骨質疏松甚至骨折的發生。但本研究由于時間及樣本量較少,仍需大量基礎研究及臨床試驗尋找HF與骨密度之間的病理生理機制,為臨床開拓診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