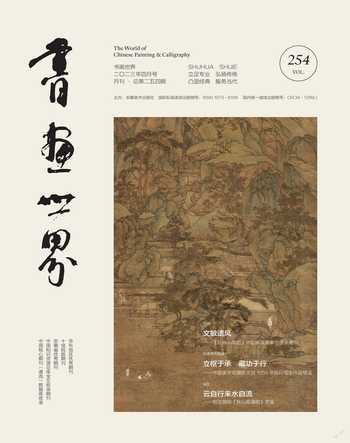安徽博物院藏元代汪克寬小楷書《江嚞傳》辨析
董建


安徽博物院藏元代汪克寬楷書《江嚞傳》(又稱《江先生傳》)手卷(圖1),紙本,縱24.8厘米,橫56.2厘米。《江嚞傳》傳主江嚞,字明遠,為宋代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名醫(yī)。據(jù)《江嚞傳》,江嚞活動于宋理宗趙昀(1225—1264)時期。《江嚞傳》款署:“延祐五年衢州路儒學教授洪炎祖撰,泰定二年乙丑,祁門桃墅里人汪克寬書。”卷后有清人、同里程鴻詔、陳得荃、吳得英跋。
讀到《江嚞傳》,筆者的第一感覺此作為明代王寵所書。安徽博物院編、安徽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金題玉躞——安徽博物院藏古代書畫》一書中有《江嚞傳》的作品簡介:“此作乃汪克寬于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中鄉(xiāng)試前一年(24歲)為婺源名醫(yī)江嚞所書的小傳。其結構精謹,筆致工穩(wěn),氣韻樸厚,風韻蕭散,卓然有大家風范。作者入世后其書放逸,不復見有工謹若此者。”[1]筆者未能找到汪克寬其他手跡,但按照簡介所說,簡介作者應該見過汪克寬其他手跡,但認為與此《江嚞傳》大異其趣。
汪克寬(1304—1372),字德輔、仲裕,號環(huán)谷。祁門縣南鄉(xiāng)桃墅(今屬塔坊鄉(xiāng))人。元末明初理學家。汪克寬6歲能作駢偶,11歲能自斷四書句讀。問業(yè)于吳仲迂,學益篤。元朝泰定三年(1326)中舉,次年會試失利,遂棄科舉業(yè),專意經學。教授宣、歙間,學者稱“環(huán)谷先生”。洪武元年(1368),朝廷下詔求賢,推辭不就。次年朝廷聘其協(xié)修《元史》,欣然應聘。書成,將授官,以老疾辭歸。著有《環(huán)谷集》《經禮補逸》等十余種。
汪克寬生年有1301年、1304年兩種提法,本文從《黃山市志》(黃山書社2010年版)“1304年”一說,故定汪克寬書《江嚞傳》時21歲。盡管汪克寬早慧,但筆者檢閱大量資料,均未見到有提及汪克寬學書、擅書之事。前文筆者就說過此書極似明代王寵所書,那么,是不是先有汪克寬此類書風,而王寵受其影響?或者二者書風暗合?但就其書風來看,比如起筆方法和“稚拙”的間架,都與元代書風不符。
曹淦源在《〈王寵款冊〉與汪克寬小楷書法》[2]100-103一文中,認為劉九庵《王寵書法作品的辨?zhèn)巍芬晃挠小白孔R”,但是不敢茍同其對《王寵款冊》的鑒賞。于是曹淦源對《王寵款冊》的書法特征等進行了分析,結論《王寵款冊》是“王寵偽跡”。《〈王寵款冊〉與汪克寬小楷書法》一文有“《王寵款冊》與汪克寬小楷”一節(jié),曹淦源將《王寵款冊》與汪克寬《江先生傳》卷對照,選出世、遠、輒、號、所等“40多個共有的字,無論結體、筆法完全相同,甚至像‘當字都作自左向右兩點一撇的筆順和筆法,‘挑與‘桃的‘兆字特殊寫法,‘富少一‘點,都一模一樣。非朝夕臨摹,長期研習難于達到如此精妙的程度。汪克寬21歲所作《江先生傳》墨跡,已早露出成熟的書藝,與明初平正圓熟的‘臺閣體相比,顯得格高韻勝,料想其人書俱老,必入佳境,惜其墨跡流傳絕少,鮮為世人所知。由此推斷,《王寵款冊》作偽者在繼承汪氏書藝后,卻又苦于不能創(chuàng)立新意,名聲未揚,只能借托名家鬻書牟利。另一方面,王寵小楷也有汪克寬書風特征,于是就有了《王寵款冊》的出現(xiàn)”[2]103。從曹淦源此文可以看出,他認為《王寵款冊》是偽作,而作偽者曾刻苦學習過汪克寬的小楷《江嚞傳》,且已達逼真的程度。曹淦源感嘆21歲的汪克寬書藝早已成熟,料想汪克寬“其人書俱老,必入佳境”。但筆者認為,汪克寬的小楷《江嚞傳》與《王寵款冊》或者王寵小楷存在關聯(lián),但不是《王寵款冊》書者學習汪克寬小楷,而是“汪克寬”(作偽者)學習王寵書法。因為筆者認為《江嚞傳》并非汪克寬的真跡,而是明末或清代人學習王寵小楷者的偽托之作,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書風與時代不合。
一個時代的書風有一個時代的特點,大致不會差到哪里去。元人小楷,大多寫得規(guī)矩,如趙孟、楊基、俞和等,但倪瓚風格獨特,與其氣質和畫風有關,為獨一無二的例子。明代初期,宋濂、沈度及祝允明、文徵明、文震孟、文彭等也都寫得循規(guī)蹈矩,除明初幾位學“館閣體”,余者皆出入鐘繇、“二王”一路。王寵書法受祝允明影響較大,但小楷主要學鐘繇、王獻之,稍晚追求以拙取巧、拙中見趣,形成筆短意長、神韻超逸的個人風格。汪克寬逝于洪武五年(1372),入明才幾年,可以說他應是地道的元代人,而且他是正統(tǒng)的理學家,未聞其善書,并且在其21歲時寫出如此干練、老到、韻味十足的小楷,實在令人難以想象。另外,《江嚞傳》署款處所鈐“汪克寬字德輔”長方形細朱文印,也和當時印風脫節(jié),與時代風格大異,亦是重要疑點之一。
《江嚞傳》有三跋(圖2—圖4)。其一題跋者吳得英為此卷始得者,后將此卷轉贈陳得荃。其二即為陳得荃跋。而另一位題跋者程鴻詔并未見過此卷,而是“竹溪尊兄錄跋見示”,令程鴻詔“輒為神往,它日當求觀筆跡,更慰望古之思也”。吳得英、陳得荃題跋皆在同治四年(1865),程鴻詔題跋在同治七年(1868)。雖然陳得荃為《江嚞傳》重新裝池,如真為汪克寬真跡,從汪克寬書寫時間到吳得英、陳得荃題跋的540年間,竟無明代和清代早、中期一人題跋,豈非怪事?或者辯解說原有前人題跋,陳得荃重新裝裱時割去,那也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前人的題跋,更能說明此卷的重要性和流傳有緒。
約稿:秦金根 責編: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