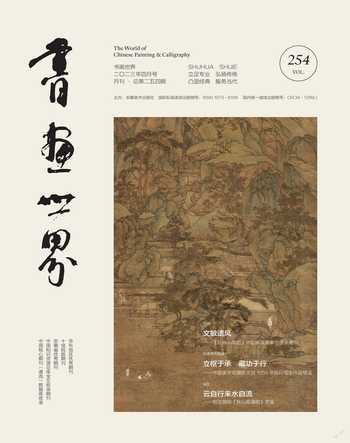漢《馮煥闕》書法藝術探究
田莉莉



關鍵詞:漢闕;馮煥闕;書法風格;波磔
一、《馮煥闕》及其相關問題
巴蜀地區漢代石刻銘文以其形制、書風的多樣令世人矚目,并在漢代石刻當中占據一席之地。巴蜀作為歷史的地域概念,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即指當時的巴國和蜀國。[1]“巴蜀”在漢代指益州刺史部所管轄的“巴郡”和“蜀郡”。[2]《馮煥闕》在今四川渠縣境內,漢代時隸屬巴郡,故應為巴郡的建筑刻石。[3]
“闕,門觀也。”[4]最初的闕是宮室外的一種防御建筑,高高的臺基上有樓屋,守衛者可以站在上面瞭望四方,故稱之為“觀”。因一般分立大門兩旁,中部開闕為道,故又稱為“闕”。后來,這里又成了天子公布法令的地方,稱之為“象魏”。《廣雅》載:“象魏,闕也。”因此,闕也成為國家和天子的象征。后來,這些功能都漸趨淡化,但闕作為裝飾性建筑,長時期廣泛地修建在宮、廟、祠、墓之前,以襯托和美化主體建筑,加強建筑組群的莊重感。早期的闕用磚木建造,東漢時開始出現純石料建造的闕。時至今日,“闕”已經不只是漢代標志性的建筑物,更是兩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馮煥闕》(圖1)又稱《馮使君墓闕銘》《幽州刺史馮煥神道》,東漢建光元年(121)造,上有銘文隸書20字。[5]2041宋代趙明誠《金石錄》記載《漢馮使君闕銘》,云“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6]。《后漢書·馮緄傳》載:“緄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7]而《緄碑》亦云馮緄為“幽州君之元子”。“此字在宕渠緄墓前雙石闕上,知其為煥闕也。”[6]以上這些記載肯定了馮使君就是馮煥,安帝時曾任幽州刺史。關于《馮煥闕》的銘文內容、主人公履歷及石刻的史學價值前人多有解讀,本文將重點關注其書法藝術。
二、《馮煥闕》書法藝術特征
(一)前人對《馮煥闕》書法風格的評述
關于《馮煥闕》的書法藝術,宋洪適《隸釋》、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及葉昌熾《語石》對其均有評述。宋代金石學家洪適在《隸釋》說《沈府君闕》《馮煥闕》《王稚子闕》皆是八分書,即張懷瓘所謂的“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者也”。其評價與康有為有異曲同工之妙。清代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云:“《孔宙》《曹全》是一家眷屬,皆以風神逸宕勝。《孔宙》用筆旁出逶迤,極其勢而去,如不欲還。《馮君神道》《沈君神道》亦此派也,布白疏,磔筆長。”[8]洪適以“八分書”來描述《馮煥闕》的隸書銘文,又借張懷瓘之《六體書論》中的“作威投戟,騰氣揚波”[9]212進一步表述其書法特點。而康氏的描述似乎更勝一籌,借漢隸《曹全碑》用筆之逶迤來形容《馮煥闕》筆畫的勢,并評說《馮煥闕》與《沈君神道》獨特的用筆特點,即“磔筆長”。《永字八法》稱右下為磔。[9]875唐太宗李世民《筆法訣》又稱:“磔須戰筆外發,得意徐乃出之。”[9]119這些對《馮煥闕》的“磔筆”都進行了很好的闡述。同時康氏對《馮煥闕》的章法描述為“布白疏”,即其章法布白疏曠爽朗。清代葉昌熾《語石》卷五云:“漢《沈君左右闕》《李業闕》《楊宗闕》《馮煥闕》,蜀《賈公闕》。凡闕,多東西相對……有題字者為舊拓,《沈》《馮》兩闕最清朗。”[10]葉昌熾評述其“最清朗”,這便容易讓讀者聯想到一代書圣王羲之《蘭亭序》中的“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文句,颯爽之感便會油然而生。而筆者以為三位前賢對《馮煥闕》書法風格的評述唯有葉昌熾的不大妥當,其評《沈君神道》為“清朗”者倒也恰當,但《馮煥闕》的書法風格帶給人的感受必然是超“清朗”之上的,更有“戰筆”之意。關于《馮煥闕》的書法藝術風格古人已做出了評述,而對于《馮煥闕》及相近書風的漢代銘石隸書,它們在風格上的內在聯系近年來卻并未得到學者們的足夠重視。
(二)《馮煥闕》書法風格的承襲淵源
自西漢中期以來,隸書逐漸地脫離了篆體,朝著字形扁方、筆勢長波的方向發展。無論是書寫較為自由的漢簡尺牘,還是各類不同形制的石刻銘文,我們都能從中看到字形的變化、筆畫橫勢的拉長。恰如建始元年(前32)的《武威王杖詔令冊》、天鳳三年(16)的《萊子侯刻石》、永平六年(63)的《開通褒斜道刻石》以及永壽三年(157)的《安國墓祠題記》等。
通過古人對《馮煥闕》書法評述,不難看出《馮煥闕》正是具備著隸書脫去篆體、字形方扁、筆畫長波的特點。與上述簡牘、石刻具有形體上的共通之處。
《武威王杖詔令冊》(圖2)[11]為西漢成帝時期的簡牘墨跡,就其字形來看多有橫畫、波磔逸出的形態,使通篇書法開張縱橫,姿態橫生,風神宕逸。由于是書寫在竹簡之上,故字形顯得飄逸灑脫。其橫勢極盡舒展,有如“極其勢而去如不欲還”。除此之外,《武威漢簡》《甘谷漢簡》等已褪去“古隸”模樣的簡書都具有此特點。故而可以看出,早在西漢時期書家即有掠筆、波磔的習慣,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穩定且社會普遍效仿的筆法。
《萊子侯刻石》(圖3)[12]62又名《天鳳刻石》,刻于天鳳三年即公元16年,早《馮煥闕》105年。清代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載:“以篆為隸,結構簡勁,意味古雅,足與孔廟之《五鳳二年刻石》繼美。”與公元前56年的《五鳳刻石》相比,《萊子侯刻石》更顯蒼勁簡質,字形的趨扁程度十分明顯。與同時期的簡牘隸書相類似,《萊子侯刻石》筆畫尤帶篆意,前三行筆畫橫勢較強,后數行強化了斜向線,顯得跌宕生動,如“使”“毋”二字。全文35字,少數字的筆畫呈現出不大明顯的波磔,而橫畫中出現波磔筆意的字在西漢隸書刻石中為最多。《萊子侯刻石》中的波磔雖在左右的橫勢上較之《馮煥闕》并沒有那么明顯的長波,但已出現“磔筆”之勢。
《開通褒斜道刻石》(圖4)[12]106,東漢永平六年(63)至永平九年(66)造,為東漢早期摩崖石刻,早《馮煥闕》55年。清代楊守敬《學書邇言·評碑記》云:“縱橫排奡。”[13]“奡”即指矯健有力的樣子。我們從兩塊石刻的整體面貌上來看,兩者都具有恣肆曠野、縱逸生奇之勢,然而就掠筆和磔筆來說,《馮煥闕》顯然要比《開通褒斜道刻石》更勝一籌。如“道”字:《開通褒斜道刻石》“道”字(圖5)的捺畫較為僵硬,斜下而出;《馮煥闕》“道”字(圖6)的捺畫則平出傾斜而挑出,增強了縱逸之勢。又如在石刻中出現的 “君”字,兩者的撇畫顯然不同:《開通褒斜道刻石》的“君”字(圖7)掠筆之勢較為含蓄,撇畫較短;而《馮煥闕》的“君”字(圖8)撇畫掠勢則如拔劍出鞘,風神凜然。字形上雖然前者趨方、后者趨扁,但二者在整體視覺感上同樣給人一種“恣肆曠野”之感,這就得益于兩塊石刻筆畫線條的簡練圓勁。
通過對《馮煥闕》與《武威王杖詔令冊》《萊子侯刻石》《開通褒斜道刻石》的對照研究,我們知道西漢時期書家便有了掠筆的動作習慣,進而演變成了一種成熟的波挑與磔筆的用筆規律。而當隸書轉換了載體,載體發生了材質的變化時,隸書結構依舊可以按照簡牘或方或扁的字形來展現,但其載體刻石帶來的刊刻不便進而又演變出平畫寬結或斜畫緊結的字形結構。當刻石材質的書寫發揮面積遠遠大于原先狹窄的簡牘之時,加之漢代書家本身所習慣的掠筆、磔筆動作,二次創作所刊刻出的隸書也就衍生出“磔筆長”的特點。故筆者認為《馮煥闕》書風特色的產生并不是簡單的胡寫亂畫,一時興起。其書風的產生背后定有著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并一脈相承。
(三)《馮煥闕》書法風格的比較分析
正所謂“漢碑每碑一奇”,將《馮煥闕》與書風較為接近的《石門頌》《曹操宗族墓字磚》《曹全碑》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其間的關聯。
《石門頌》全稱《故司隸校尉犍為楊君頌》[5]570,為摩崖石刻,漢建和二年(148)刻,晚《馮煥闕》27年。清代楊守敬在《學書邇言》中評:“《石門頌》之飄逸,各有面貌,各臻妙境。”[13]有“隸中之草書”一說。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云:“‘命字垂筆有長過一二字者……因石理剝裂,不可接書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隸法也。”[14]關于“命”字的垂筆過長問題,翁方綱認為是石質的自然裂痕恰巧使“命”字豎畫拉長,然現代學者認為這并非石質裂痕的結果,我們從出土的大量漢簡中可以得知,漢隸書寫任性恣情時總有“逸筆”出現,即筆畫的縱勢或橫勢的加強。翁方綱會如此認為,應與當時漢簡并未有出土實物有關。《馮煥闕》和《石門頌》同為奇縱恣肆一路的漢隸書風,兩塊石刻卻也各有其特色。
以“故”字為例,《石門頌》中的“故”字與《馮煥闕》的“故”字用筆皆瘦硬圓勁,氣勢大開。在結字上《馮煥闕》“故”字呈現出一種斜向的姿態,且字形中部緊收;而“石門頌”結體均勻分布,更為疏朗。如果說《馮煥闕》與《石門頌》是兩個面對兵臨城下的將士,那么《馮煥闕》表現出來的就是“拔劍出鞘,突出重圍”,《石門頌》表現出來的則是“胸有成竹,請君入甕”。除“故”字外,其他字形與《石門頌》相比皆是結體較為緊收。
《曹操宗族墓字磚》(圖9),漢靈帝建寧三年(170)刻,晚《馮煥闕》49年。《曹操宗族墓字磚》中多數書法用筆隨意自然,值得注意的是隸意較濃的“會稽曹君”四字,強調中鋒用筆的圓勁流暢,向外延伸,具有剽悍之氣、雄放之氣。無論與茂密雄強、渾穆厚重的《衡方碑》相比,還是與清麗典雅、端莊嚴謹的《曹全碑》相比,凡須波挑之處,《曹操宗族墓字磚》中字體的筆畫無不盡興舒張,線條起始幾近平直,并未著意強調其“一波三折”的特性。[15]正因這種橫向筆畫的“少波折”,故而其用筆隨意,中鋒拉出,圓勁挺健,反而簡潔明快,而這種用筆方式也正是與《馮煥闕》用筆的相通相合之處。
除卻其恣肆開張的筆畫,《曹操宗族墓字磚》在字體結構上與《馮煥闕》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關于《馮煥闕》字體結構之緊收的特點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到,與其他縱逸類的石刻隸書相比,《馮煥闕》結體之緊收,是其他早于《馮煥闕》的石刻無可及的。分析《曹操宗族墓字磚》中的“曹”字(圖10)與《馮煥闕》中的“東”字(圖11),二者筆畫分布均勻,皆字形壓扁。由于“曹”字的字形較高,若我們遮去其下半部“曰”,不難發現其風格、結體與《馮煥闕》如出一轍。
試將《馮煥闕》與晚其64年的《曹全碑》比較,可見《曹全碑》之婉暢多姿、秀潤勻整、左掠右磔、橫向舒張的藝術特征。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云:“《孔宙》《曹全》……皆以風神逸宕勝。……《馮君神道》《沈君神道》亦此派也,布白疏,磔筆長。”[8]康有為把《曹全碑》與《馮煥闕》在藝術風格上歸為一類,而我們若再細究二者的字形結體,如表1所示選取《馮煥闕》的“州”“令”“史”“神”等字與《曹全碑》對比,當會發現《馮煥闕》另有奧妙。(表1)
從字形上看,《曹全碑》與《馮煥闕》驚人地相似,且其體式相若呈微微向上拱起的狀態。從結構上看,二者布白較為均勻,中宮收緊,撇捺左右逸宕。兩者唯一的不同就是《馮煥闕》線條圓勁,無“雁尾”;《曹全碑》則更顯飄逸,稍有“雁尾”。
一種書風的產生及其延續、發展絕不是偶然的,它經過了書家、刻工的發現與總結、學習與承襲才得以流傳。從《馮煥闕》到《曹操宗族墓字磚》,再到《曹全碑》,可見當時的書家刻工對此隸書風格已經有了一定的認知和認可。
結語
《馮煥闕》作為巴蜀地區漢代石刻,有著獨特的一面。本文嘗試去解開《馮煥闕》書法藝術風格的源頭密碼和后期的發展,厘清其書風脈絡。除上文所舉例論證的石刻之外,相信還有很多的漢代石刻等待我們去研究發現。而漢代石刻書法藝術的取法、發展問題的探索,對于漢代石刻書風的分類及書法藝術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約稿、責編: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