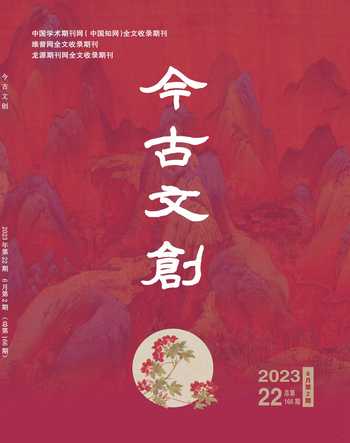“馕”“胡餅”之歷史演變
王順宇

【摘要】維吾爾族原本將“馕”稱之為“埃特買克”,后隨塔吉克語改稱為“馕”;中原地區對“馕”的稱呼也由最初的“胡餅改為“燒餅”抑或其他,直到今天與新疆地區一樣稱之為“馕”。詞匯演變的背后是歷史文化的變遷,其體現在語言文字上的部分值得人們深究。
【關鍵詞】“馕”;“胡餅”;語言;文字;歷史
【中圖分類號】H17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22-012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2.038
“馕”作為新疆人民日常飲食結構中的重要角色,其歷史悠久、來源說法不一。一說原產于新疆、一說原產于中西亞后傳入我國西北。“馕”不僅僅反映了西北少數民族的飲食偏好及其背后的文化內涵,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各民族交流融合的過程。
一、“馕”
(一)從“埃特買克”到“馕”
夏雷鳴先生一直致力“馕”文化研究,在其文章中提到:“‘馕(nan)是波斯語,突厥語稱‘馕為‘埃特買克。” ①“埃特買克”應為“?tm?k”之音譯。之所以將“埃特買克”改稱為“馕”,是因為受到波斯語的影響。“馕”音原為波斯語,取“面包”之意。波斯語和塔吉克語均屬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因此,波斯語“馕”音逐漸為塔吉克民族所接受,而新疆其他民族亦逐漸接受了塔吉克語對“馕”的改稱,最后“馕”取代“埃特買克”,至今仍在沿用。
塔吉克族雖然只有語言沒有文字,但其語言保存良好。塔吉克語屬于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帕米爾語支。古波斯語屬于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伊朗語支的西南方言。塔吉克語和波斯語屬同一語族,塔吉克語吸收了古波斯語中“馕”音,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雖然屬于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但是逐漸接受了塔吉克語中對于薄餅的叫法,逐漸將原本的“埃特買克”棄之不用,也改稱為“馕”。
(二)“馕”字造字理據
《說文解字》中未載“馕”字。“馕”字最早字形為篆書
,從食從囊,囊兼表聲。《說文解字·?部》“囊:橐也。從?省,襄省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小而有底曰?,大而無底曰囊。”《說文解字今釋》:“析言有分,渾言無別。”《說文解字》中篆文字形為? ?。《字源》:“形聲字,初文作? ?,像扎住袋口的囊(小圈兒象征扎系袋口的繩索),象形字。后改為從? (橐之初文)的形聲字。小篆及秦漢古隸從? ?,襄省聲。草書與楷書則是從? ?省(省去“木”),襄省聲。”又《常用漢字源流字典》:“囊,形聲字,小篆從橐省,襄省聲。隸定為“囊”,本義為口袋,引申為像口袋的東西。”《詩經·大雅·公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毛亨傳:“小曰橐,大曰囊。”簡言之,“馕”從“囊”得,“襄”省聲。
從“襄”省聲的字都與“包裹”之意有關。“襄”為形聲字,從衣,? ?聲,其字形演變為? ? ? ? ? ? ? ? ? ?,可見西周時期像口袋包裹東西之形。戰國時期? 訛省得面目全非。不僅從“襄”孳乳來的“囊”有包裹之意,還有其他幾個字與“囊”同源。沈兼士在其文集中以圖示之②,清晰明了:
我們將“囊”“鑲”“釀”“瓤”主要義項羅列,加以分析:
“囊”:袋子、口袋;用囊盛物;③
“鑲”:把東西嵌入另一物體,或圍在另一物體的邊緣;④
“釀”:釀造。⑤即將酒曲與糧食和水密封在容器中等待發酵;
“瓤”:指某些皮或殼里包著的東西。⑥
依據張聯榮先生的觀點,詞的語義成分由兩部分組成:即義類范圍和語義特征。如果從義素分析法的角度來看,義類范圍可以稱為類屬義素,表示語義特征的部分可以稱為特征義素。
因此,“囊”“鑲”“醸”“瓤”可以進一步分析為:
“囊”:[袋子](類屬義素)+[將物包裹](特征義素)→包裹
“鑲”:[東西](類屬義素)+[嵌入其中](特征義素)→被包裹
“釀”:[酒曲、糧食、水](類屬義素)+[被封于容器內](特征義素)→被包裹
“瓤”:[皮/殼](類屬義素)+[包裹](特征義素)→被包裹
由此可見,從“襄”孳乳而來的“囊”“鑲”“醸”“瓤”均有“包裹”這一特征義素。“馕”即從“囊”得,那么也必然將“包裹”這一特征義素遺傳下去。
二、“胡餅”
(一)“胡餅”之“胡”何解
《說文解字·肉部》: “胡:牛顄垂也。從肉古聲。”《說文解字》中篆文字形為? ?,左聲右形。本指牛頷下垂肉,后詞義擴大:《詩經·豳風·狼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孔穎達疏:“毛以為狼之老者,則頷下垂胡。”朱熹注:“胡,頷下垂肉也。”指代“獸類下巴上的垂肉。”然本義現已不用。《漢語大字典》中“胡”字釋為:“古代稱北方和西方的少數民族,如:《漢書·匈奴傳上》:“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又指來自少數民族的,如:《戰國策·趙策二》:“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又泛指國外,如:《搜神記·卷二》:“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胡”字本義“頷下垂肉”與后來的常用義“西方和北方的少數民族”之間差別較大。依據王貴元先生觀點,多義詞形成途徑之一就是“詞義移植”。所謂“詞義移植”,就是根據其共有特征或彼此關聯,用舊詞表示新義。如“西”本義指飛鳥棲息,后因飛鳥歸巢棲息之時也是太陽西落之時。因此“西”由本義“棲息”轉指方位詞。同理,“胡”字在本義“頷下垂肉”的基礎上詞義移植,由于頷下多有毛,進而轉指“下巴上的胡須”。這一說法具有一定合理性。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釋胡》:“今人謂須為胡,字作鬍,亦為垂于頷下受名也。”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十》:“蝶美于須,蛾美于眉,故又名蝴蝶,俗謂須為胡也。”因此,“蝴蝶”本作“胡蝶”,因其頭上觸須與人胡須相似,由此得名。“須”表示下巴上的胡須,“須”“胡”渾言無別。“胡”表“胡須“義,在南北朝已有用例,如:南朝梁元帝《金樓子·箴戒》: “帝紂垂胡,長尺四寸,手格猛獸。”且“胡須”一詞至今沿用,是漢語詞匯雙音節化的結果。后又因少數民族毛發旺盛多胡須而以特征代本體。《漢書·西域傳》:“自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目多須髯。”王國維《觀堂集林 · 西胡續考》:“是胡之容貌,顯與他種不同。而其不同之處,則‘深目多須四字盡之。”因此在“胡須”義基礎上指代“少數民族人民”。需要注意的是,此處的“胡”與匈奴自稱的“胡”并不是同一概念,《西北民族詞典》:“‘胡 的北方民族語音當為ghur,相當于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語言中的gur,意為‘聯合‘團結 。匈奴為許多北方部族聯合而成因而自稱為‘胡。”
(二)“胡餅”的改稱
“胡餅”作為一種風味面食,自傳入后廣受歡迎。高啟安、索黛兩位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盡管古代的胡餅與今天的任何一種餅,其形制和方法都有一定的區別,但許多人認為維吾爾族的“馕”的制作方法和大小相當于唐宋時期的胡餅。” ⑦因此,可以認為“胡餅”就是“馕”的前身,且從現今“馕”與“胡餅”制作方法來看,依然可以佐證這一觀點。
當前史料文獻中最早可以查檢到“胡餅”二字在東漢時期,因靈帝喜食胡餅,所以京城內外食胡餅變為一種流行。如:
(1)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京都貴戚皆競為之。(范曄《后漢書·五行志》)
(2)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司馬彪《續漢書》)
此外,劉熙在《釋名》中還專門講解了“胡餅”的做法:
(3)餅,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冱,亦言以胡麻著上也。(劉熙《釋名·釋飲食》)
畢沅《釋名疏證》:“《說文》無‘漫字。此當作‘?胡。”又鄭玄注《周禮》‘鱉人云 :‘互物謂有甲?胡,龜鱉之屬。則‘?胡乃外甲兩面周圍蒙合之狀。胡餅之形似之,故取名也。” 言即“胡餅”兩面稍硬,形似龜殼。“胡麻”即“芝麻”,做“胡餅”的最后一步就是撒上芝麻。這與現今烤制的“馕”兩面稍硬,上著芝麻相同。
至兩晉時期買賣、食用胡餅變得十分平常,如:
(4)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常於市中販胡餅。(陳壽《三國志》)
(5)王氏諸少年并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胡餅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胥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王欽若《冊府元龜》)
北魏賈思勰在其著作《齊民要術》中又提到了胡餅的制作方法:
(6)髓餅法:以髓脂、蜜,合和面。厚四一分,廣六七寸。便著胡餅中,令熟。勿令反覆。餅肥美,可經久。(賈思勰《齊民要術·餅法第八十二》)
此種做法與《釋名》中相較,原材料除水和面,還加入了髓脂和蜜,即牛羊油和糖,且注明在制作過程中不要翻動,這與今天食用的餅的做法稍異,然“馕”置入馕坑后也不再翻動,直到“馕”熟后才取出。
“胡餅”在唐朝極為流行。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品平民百姓,無一不喜食之,其中《延尉決事》中記載唐朝張桂由于賣胡餅出名后被封為蘭臺令。其他例子諸如:
(7)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元載《肅宗實錄》)
(8)劉宴入朝,見賣蒸胡餅之處,買啗之。(劉禹錫《嘉話》)
(9)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白居易《長慶集·十八·寄胡餅與楊惠州》
兩宋時期“胡餅”一詞雖然不如唐多見,但在文獻典籍中依然不少,如:
(10)縣素荒寂 , 市中唯有賣胡餅一家 。(洪邁《夷堅丁志·雞子夢 》)
(11)進曰意旨如何。曰胡餅有甚汁。(禪林僧寶傳《佛語錄》)
然而,在兩宋以后,“胡餅”一詞見諸文獻的次數大大減少。我們合理推測可能與當時民族政策與民族觀念的轉變有關。南北宋以后,建立的封建王朝有遼、大理、西夏、金、元。這些朝代的統治者包括契丹族、白族、黨項族、女真族和蒙古族。也就是所謂的少數民族。正因為統治者為少數民族,所以其頒布的政策和推行的文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過去的“夷夏觀”。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⑧而語言中的詞匯最容易受到社會變化影響,換言之,社會變化可以最及時地體現在語言中。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改變雖然不如語言迅速,但也一定會因語言改變而隨之改變。“胡餅”一詞在文獻中使用頻率的減少正是由于“胡”字帶有對少數民族的貶義色彩,因此必須更換一個新詞來表示同一事物。這也是后來“燒餅”等多見于書中,而“胡餅”一詞卻難尋其跡的原因。與此類似的還有“胡麻”改稱“芝麻”,“胡瓜”改稱“黃瓜”,“胡桃”改稱“核桃”。新詞的產生與舊詞的消亡一同反映了民族交流融合的過程以及民族共同體觀念的逐步推進。
三、“馕”文化
飲食文化作為一個民族日常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其內核體現了一個民族共同的習俗、認知和信仰。“馕”作為新疆地區人民日常飲食的重要角色,亦是我們了解少數民族食俗和文化的重要中介。廣而言之,不論是現在分食一枚小小的“馕”,還是古代跨越千里、乘絲路之便將“馕”傳入新疆再到中原地區,都是各民族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過程。“絲綢之路”貫通和繁榮的意義絕不僅僅局限于政治和經濟,更是極其深遠地滲透在語言和文字當中。正是這些文字跨越了時空的界限,使得語言,以及語言背后所蘊含的文化書之于表、有跡可循。誠如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所說:“一個字就是一部文化史。”今天,我們強調各民族加強團結友好,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圍繞在一起,得以實現這些希冀的精神紐帶,正是跨越千年的中華文化。這些文化因子不僅體現在日常飲食和食俗中,更是滲透在每個人的血液里。因此,其表征在語言文字上的部分值得我們學習和深究。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新疆地區,原本表示“馕”的“埃特買克”因受波斯語影響,后改稱為“馕”。在中原,則是由“馕”改稱為“胡餅”,后又改稱“燒餅”及其他。至于“馕”字的產生,則是為了記錄“馕”音專門造一新字以記之,其左形右聲的結構特點符合漢字的造字理據。“馕”的傳入及流行是“絲綢之路”貫通的成果。“馕”所體現的不僅是詞匯的借用、漢字的孳乳和新詞的產生,更是民族的融合、觀念的轉變和社會的進步。
注釋:
①夏雷鳴:《西域薄馕的考古遺存及其文化意義——兼談波斯飲食文化對我國食俗的影》,《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第94-100頁。
②沈兼士:《沈兼士學術文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7頁。
③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2卷,第762頁,第10字。
④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8卷,第4603頁,第6字。
⑤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6卷,第3842頁,第17字。
⑥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第5卷,第2844頁,第16字。
⑦高啟安,索黛:《唐五代敦煌飲食中的餅淺探——敦煌飲食文化之二》,《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76-86頁。
⑧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三,轉引自白翠琴:《魏晉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頁。
參考文獻:
[1]沈兼士.沈兼士學術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4:97.
[2]李正元.馕的起源[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22(01):112-117+150.
[3]何家興,張全生.釋“馕”[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39(05):146-148.
[4]夏雷鳴.西域薄馕的考古遺存及其文化意義——兼談波斯飲食文化對我國食俗的影[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01):94-100.
[5]夏雷鳴.《突厥語詞典》與維吾爾族馕文化[J].西域研究,2001,(03):64-70.
[6]岸本通夫,趙晨.印歐語系民族的遷徙[J].民族譯叢,1981,(06):23-26.
[7]王蘋,房玉霞.也談維吾爾族的馕[J].喀什師范學院學報,2013,34(01):37-40+54.
[8]陳紹軍.胡餅來源探釋[J].農業考古,1995,(01):260-263+275.
[9]吳建偉,李小鳳.胡餅考[J].回族研究,2002,(03):79-81.
[10]閆艷.釋“燒餅”兼及“胡餅”與“馕”[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5(05):1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