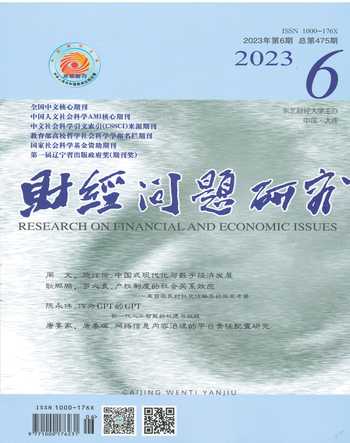產權制度的社會關系效應
耿鵬鵬 羅必良



摘 要: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使得農村土地及其權益的競爭性配置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中國農村地權的模糊性和不穩定性曾一度長期存在,并成為塑造傳統村社形態的重要誘因。本文利用2018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數據,采用有序Probit模型,經驗分析了地權穩定性對農民村社交往頻率、人情往來密度和關系型交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在地權穩定性相對不足的村莊,農民具有更高的村社交往頻率,一方面,通過筑牢親友關系以提升地權競爭優勢;另一方面,通過提升非親友交往頻率以強化地權排他能力。進一步的證據表明,歷史遺留的人地矛盾能夠形塑農民的村社交往格局和關系型村社形態,而人地關系的變動則會動搖地權穩定性以及相關聯的村社交往秩序。此外,由成年男性表達的談判優勢和由體制內就業表達的政治資源,是農戶家庭地權競爭實力的重要力量,并對農民基于地權競爭而開展的村社交往具有替代效應;“鄉政”對“村治”的管制和地權法治化,則將會弱化基于地權排他的關系締結。筆者強調,中國農民村社交往格局和關系型村社形態,隱含著深刻的產權經濟學邏輯。
關鍵詞:產權制度;地權穩定性;人情往來密度;村社交往頻率;關系型交易;社會關系效應
中圖分類號:F301.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23)06?0016?15
一、引 言
產權的重要功能在于規范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利界限,形成化解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的反應規則和經濟組織的行為秩序,從而構筑具有內在協調性與自我執行性的社會交互關系[1]。其中,產權的穩定狀態決定了社會交互關系的基本結構和內在邏輯。穩定的產權內含資源配置的權能和利益,從而成為契約型交易和開放性市場活動的基礎要件,而產權穩定性缺位附著的資源控制權不足和非正式競爭規則往往將生成關系型交易和封閉性活動秩序。由此,產權及其穩定狀態成為社會經濟利益關系處置和社會活動運行的重要“觀察窗”。
中國是以農耕文明著稱的大國,土地稟賦及農耕活動不僅是維系社會經濟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根基,也是關乎農民生計安全、家庭幸福不可替代的核心內容。因此,穩定地權、保障農民土地財產權益成為當前農村地權制度改革的基本線索。然而,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農村人地關系極為嚴酷,農地資源的競爭、調整、博弈和再分配在中國農村一度長期存在。可以說,地權不穩定的制度遺產和生存記憶是與中國農民血脈相連的,也深刻地影響并形塑農民的經濟社會行為邏輯。
農地產權穩定性不足所關聯的地權“公共領域”擴大及其租值耗散將誘發兩方面的農民行為響應:第一,就產權競爭性而言,地權不穩定將激發村社成員對產權租值爭奪的機會主義沖動。村社關系網絡密度所形成的團體實力決定了家庭在利益爭奪中的比較優勢,家族勢力和親緣關系成為攫取地權租值的重要力量[2]。因此,農戶通過壯大家庭原生性的競爭力量,構筑以親友關系為基礎的社會資本網絡,將形成有益于農戶攫利地權競爭享益的格局。第二,就產權排他性而言,地權模糊及其關聯的農民產權弱化往往意味著以家戶為單位的地權分配和處置格局缺乏有效保護而極易遭受侵犯。因此,擴大村域交往半徑,獲得村莊社會認同,構建非正式的人情秩序以保護地權成為農民強化產權強度、維護產權安全的理性選擇[3]。顯然,地權的模糊性和不穩定性將使得維護地權安全、保護地權利益、強化地權競爭性和排他性成為村社農民地權博弈的核心訴求和主要內容。重要的是,這也為社會資本、家族、宗親和“差序格局”關系網絡等非正式制度及其形成的地權保護屏障和行動秩序嵌入農村社會經濟交往秩序提供了必要條件。
事實上,中國農村長期被視為是以“關系”為基本特征的社會形態,基于血緣、地緣所構建的關系網絡在村社經濟交易、社會交往和安全防御等方面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4-5]。在傳統農村社會中,土地對于農民而言兼具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農民以農為生且以農為業,土地及其經營收益承載著一家全年的生計和未來的希望。這也決定了農戶生存的安全性和保障性極易受到地權風險的影響,加之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商業保險市場發展長期不充分且不完善。因此,農戶往往通過構建社會關系網絡,強化與親戚朋友、村社鄰里的人情往來,形成隱性契約關系,締結基于化解地權風險的隱性承諾,形成非正式的地權保護機制和風險分擔機制[6]。
由此,地權穩定性與農民社會交往關系締結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性。然而,被視為“熟人社會”的村莊內部依然存在“差序格局”遠近親疏的群體關系。從傳統思想的角度看,中國人重視家族和宗親,其互助與交易維持于較小范圍的家族親友之間,非同一家族的人難以達成合作[7]。從地權分配的角度看,農地產權的調整與配置是基于村社存量土地與集體成員數量的平均分配,面臨著農地規模約束且地權邊界的不清晰,村社農戶之間實際上保持著地權競爭對手的關系。這意味著,村莊農戶之間不僅是地權享益主體,也是地權排他對象。所不同的是,親友是自己人,是從一個根上長出來的枝條,親密的血緣關系可以限制沖突和競爭[8]。而非親友雖為村社熟人,但卻是地權競爭和排他的潛在主體。不難發現,中國村莊社會內部的交往關系可能具有不同的內涵,尤其是在地權穩定性缺位引致的地權風險普遍存在的時期,村社交往可能具有對內強化競爭性、對外強調排他性的隱性契約性質。本文試圖從地權穩定性視角考察村社交往秩序、人情往來格局及其關聯的村莊社會形態的變化,并利用2018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數據,經驗分析了地權穩定性對農民村社交往頻率、人情往來密度和關系型交易的影響,以期揭示中國農民交往活動與人情往來關系的制度內涵與產權邏輯。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本文從農村地權穩定性、農民地權競爭性和農民地權排他性的視角,以農民親友圈內交往和非親友圈外交往的本質差異性為切入點,識別農村社會內部不同群體交往活動的運行邏輯和基本性質。第二,中國農村正經歷著亙古未有的巨大變革與轉型,村莊社會形態也在發生著根本性的演變,本文基于產權經濟學理論,從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背景下的地權制度出發,解釋中國村莊形態生成、存續與演化的產權邏輯和制度根源。
二、分析線索
(一)村莊非正式秩序的產權機理:競爭性秩序和排他性秩序
村莊是農業社會主要的空間載體和活動單元,是具有親緣、地緣和業緣等關系的農民群體聚居所形成的具有非正式秩序和行動規則的關系社會。面對共同威脅和外部侵犯,村莊成員具有幫扶互助、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的特點,但對于不可避免的內部競爭和權利分配,村莊成員既要重視強化自身力量的競爭性,又要關注防范被侵擾的排他性,使得村莊不同群體之間所締結的社會關系網絡內含不同的產權機理。
1.村莊社會關系網絡的二重性:簡要的辨析
村莊形成之初及村社關系網絡的構建與運行,最重要的考慮之一是基于安全防御和風險化解方面的需要[9]。由此,農村地域群體的形成、存續和拓展取決于村莊成員之間共同的生存信念。費孝通[8]在解讀農村社會時將村莊描述為若干“家”聯合起來的地域群體,并強調地域群體的形成取決于內部成員的共同利益,當遭遇自然災害或外來侵犯威脅時(并非影響單個人而是影響居住地所有的人),他們將協同行動以保護自己。顯然,整個村莊的社會關聯是基于外部威脅或共同利益而展開的,并未涉及村莊內部利益分配和團體性威脅的社會關系網絡。事實上,面對共同威脅和群體利益潛在受損時,村莊形成整體“私”的群體,故有村莊范圍內的整體認同和社會關系網絡。但村莊內部的權利分配將村莊細分為多個以“家”為形式的“私”單位,故形成了家族內部認同與家族外部競爭[10]。基于“私”的范圍界定,農村社會的人際關系網絡實際上可表達為村社成員之間既相互依存、幫扶互助以維護共同利益、化解外部威脅;又相互競爭、強化排他性以維護家庭利益、抵御內部遭遇侵犯。中國歷來的文化傳統和思想觀念也呈現出各異的交往邏輯。一方面,中國傳統思想中重視血緣和家族親友關系,“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1強調家族、宗親之間互助互愛的社會合作理念;另一方面,中國小農思想根深蒂固,也難以與家族外的群體形成高度的信任與合作,“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2雖說是一種理想社會,但也反映出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格局[7]。尤其是當出現村社內部利益分配和競爭時,親友關系和非親友關系呈現出不同的行為邏輯。
2.地權風險的特殊性
在人均農地極少且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鄉土中國,農地產權是鄉村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的核心[11]。人地關系嚴酷的基本國情和現實農情使得農地均分往往成為小農克服生存風險、減少安全威脅的一種集體理性的回應[12],因此,農地均分的制度基因在中國農村長期得以保留和傳承,農村地權的調整與再分配普遍發生,地權不穩定且農民產權脆弱性問題長期存在。村莊內小塊土地上的個體家庭經營作為整個鄉村社會的經濟細胞,具有孱弱性、封閉性和分散性的特征,以家庭為單位的地權分配格局意味著農戶難以抵御潛在的風險,尤其是地權獨立的有限性和地權邊界的模糊性進一步弱化了小農的產權強度和地權排他性[1]。實際上,在以非正式制度安排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農村,地權的調整鑲嵌在血緣、地緣關系之中,村莊內部的社會關系網絡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農地分配和保護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13]。
地權穩定性缺位內含的地權風險與自然災害和外來侵襲等風險具有本質的差別。村莊的土地稟賦數量和質量具有“固化”特征,地權只有存量而少有增量。村莊內部的農地調整和均分是基于村莊全部土地在集體成員間的存量分割[14]。這就意味著,村社成員間不僅是土地分配的權利主體,也是地權博弈的競爭主體。尤其是,地權不穩定所擴大的產權“公共領域”將加劇村社內部農戶間基于攫取租值的機會主義競爭和糾紛。此時,一方面,村社農戶的家族勢力和親緣團體力量對資源分配的角力過程產生影響,且與地權的界定和實施密切相關[15];另一方面,村落內部其他家族勢力強大的家庭將會成為本戶地權遭受外來侵犯的潛在主體,關聯自身地權的安全性和享益性。顯然,地權不穩定誘發的農民地權風險實際上是存在于村社內部的利益分配,而非外部的共同風險,農民內部的社會關系將出現分異,并進一步演化為村社家族、親友關系與村社其他家族、非親友關系之間的博弈、競爭與排他。而村社內部的社會關系也會呈現出內涵差別,即基于強化地權競爭性的親友關系維護和基于強化地權排他性的非親友關系締結。
(二)地權穩定性與農民行為響應:基于農民交往格局的分析
地權穩定性不足所形塑的村社交往秩序和基本格局既可詮釋中國農民團結家族親友力量以維系地權安全、優化權利競爭格局的生存策略,也可表達農村社會締結保護產權的隱性契約以“化干戈為玉帛”,形成尊重產權的社會認同以維護地權排他性的農民智慧。
1.地權不穩定、強化地權競爭性與農民親友交往格局
地權不穩定意味著農民產權的弱化和地權風險的加劇,關聯農民農事經營的信心和生活預期的穩定性。與此同時,地權不穩定也會誘發村莊內部的地權糾紛、爭奪和博弈。村社成員必須通過村莊自發的行動秩序強化家庭的生存韌性,同時提高對所獲地權的有效保護,這種行動秩序更多地表達為參與主體之間原生性討價還價的行為能力。事實上,村莊集體土地產權重新界定與分配達成的平衡往往取決于地權競爭參與主體之間家庭力量的對比。(1)家族、親友關系網絡締結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互助互惠、強化安全、共御風險。通過構筑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生存保障機制和權利享益格局,農戶可以有效強化生存韌性,抵御并化解地權風險。由于血緣、親情關系的內在維系,使得親友之間具有團結合作、抱團取暖、共同進退的生存共識并逐漸形成共同制定并集體遵守的信任格局和交往秩序。村社親友群體之間通過禮金互贈的形式構筑基于幫扶互助、互利共贏的“道德經濟體”以降低家庭風險[12]。基于防范地權風險的視角,親友之間人情交往越多,交往越密切,就意味著保險系數越大,家庭的風險防范能力越強[16]。就約束機制而言,親友關系內部往往具有更多的非正式履約機制和可信承諾,群體壓力將使得親友往往要履行“扶困救弱”的道德義務。(2)當產權模糊或合約不完全時,行為能力較強的農戶獲得“剩余權利”更有效率[17]。并且,產權不穩定意味著所有權的控制權缺乏穩定性,所有者不得不為其本應得到的權利不斷進行斗爭和討價還價[18],最終演變為農戶之間家庭力量的角逐[19]。由村莊社會關系網絡密度所表達的團體力量決定了農戶在利益爭奪、權利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其中,家族勢力和親緣關系成為攫取地權租值的重要砝碼,人情往來及其關系資本則是爭奪地權利益的重要補充手段。顯然,地權不穩定將誘使農戶通過構建與家族、親友之間密切的關系網絡以提升個人在地權博弈、權力競爭中的實力。
2.地權不穩定、強化地權排他性與農民非親友交往格局
產權“公共領域”的擴大和租值耗散將導致村社農民爭奪產權租值的機會主義沖動,農地產權弱化又意味著農戶的土地產權缺乏有效保護而易遭受侵犯。實際上,村莊內親友之間的地權侵犯少有發生。因為,親友間的利益攻訐與侵犯會破壞農戶聲譽資本,挑戰家庭倫理道德底線,并在通行的倫理道德中遭受懲罰,甚至失去親友群體這一可靠的社會資本,最終演化為“失道者寡助”。因此,農民家庭的地權遭受侵犯多源于村莊中的其他家族和非親友群體。由于非正式的行動秩序缺乏有效且有約束力的規則對其進行規范和懲戒,地權排他性的對象也主要為村社非親友群體。顯然,在地權穩定性缺位時期,抵御村內其他家族和非親友群體的地權侵犯、強化地權排他性是農民面臨的重要困局。(1)防范“公共領域”租值耗散的集體行動將在村社中形成“差序格局”、互為進退的人情“契約”關系,也造就了宗族、鄉族、村規民約等非正式制度的治理方式,通過約定俗成的基層規則來規范、約束農民的行為。由此,這不僅形成了一套依靠“鄉紳治鄉”“族長治村”“家長治家”的非正式治理模式,而且“家有家法”“族有族規”“鄉有鄉約”,進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且高度自治的村社運行體系[1]。這樣的一套村社運行體系是依靠村莊權威制定并對村莊整體具有較強的約束力,但真正能夠發揮作用且化解內部矛盾和糾紛的核心方式在于家族之間締結人情契約關系,欠了別人人情就得找機會回禮,循環往復的人情締結形成緊密的社會關系網絡,維持著家庭之間的和諧關系[8]。重要的是,人情關系隱性契約的構建實際上傳遞著地權不被相互侵犯的可信承諾。(2)獲得村莊社會認同是強化農民地權穩定強度的重要內容之一,構筑非正式的社會行動和村社通行的倫理與道德規范,以形成約定俗成的地權保護秩序是獲得社會認同的重要方式。實際上,農民家庭與村社其他家族和非親友之間的關系由于缺乏血緣、親緣等媒介進行維系,因此,關系強度較為脆弱且缺乏韌性。事實上,在缺少結構性力量維系、系統性規則聯結的非同一家族、非親友關系中,人情的往來和社會的交往更傾向于作為維護社會團結、和諧、降低互相侵犯攻訐的工具性手段和妥協性方法。因此,在地權穩定性缺位的村莊環境中,農民家庭通過構建、擴大和鞏固與其他家族、非親友群體之間的人情來往和交往密度,形成地權享益的“化干戈為玉帛”,可以成為減少地權侵犯,強化地權安全性、穩定性和排他性的有益選擇。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山大學社會科學調查中心2018年的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CLDS每兩年開展一次對中國城鄉的動態追蹤調查,樣本覆蓋了全國29個省份(不包括西藏、海南和港澳臺地區),對村莊社區結構、家庭狀況和勞動力特征進行系統監測,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代表性和穩定性。CLDS2018年數據集共包括368份村居社區問卷,13 501份家庭問卷,16 537份勞動力個體問卷。鑒于本文所關注的是農地產權與農村社會交往的研究主題,故截取農村樣本數據。由于CLDS 2018年數據對追蹤樣本僅統計了近一年發生的農地調整情況,且農地確權變量出現很大程度缺失,為獲得更為詳盡的地權穩定性數據,筆者與2016年數據進行匹配得到更為準確全面的農地產權數據,最終獲得全國161個村莊3 072個農戶4 596個農民樣本。在經驗分析中,由于存在各變量的數據缺失,因此,最終各個模型的觀測樣本會有所不同。
(二)變量設置及說明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農民村社交往頻率,主要考察農民親友間的圈內交往頻率和非親友間的圈外交往頻率,分別使用農民在村里親友和非親友辦喜事過程中的送禮頻率進行表征。禮尚往來的人情關系是農村社會交往的典型形式[20]。但村莊中農民的社會交往存在不同的頻率和強度,反映出農戶社會關系的可觸及位置及其嵌入性資源的可達性[21]。考慮到人情支出規模能在很大程度上度量社會關系網絡的緊密度[22],在穩健性檢驗中,使用農戶人情禮金支出重新刻畫被解釋變量。此外,本文還從經濟交易秩序的角度做進一步觀察。
2.解釋變量
本文解釋變量為地權穩定性,用農地調整衡量。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長期存在的農地調整是地權不穩定的核心觸發因素。本文根據CLDS2018年問卷中“2003年至今,村里的土地是否調整過”的問項結果刻畫地權穩定性(調整=1;未調整=0)。并采用2016年以來發生農地調整的情況表征村莊近年來的地權穩定性(調整=1;未調整=0)。此外,在穩健性檢驗中,根據土地調整的發生途徑從土地調整程度層面刻畫地權穩定性(具體賦值為:不調整=1;利用機動地調整=2;土地小調整=3;打亂重分=4)。
3.控制變量
本文控制了可能影響農戶村社交往頻率、人情往來的其他變量。主要包括農民個體層面、家庭層面和村莊層面的控制變量[23-25]。其中,農民個體層面控制了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等變量。家庭層面控制了家庭基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家庭經濟狀況特征和家庭社會保障水平等變量。中國家庭傳統的家長制決定了戶主在家庭社會交往中發揮主導作用[26],因此,本文控制了戶主特征的變量。人口統計學特征還包括家庭總人數、家庭男性比和家庭撫養比;家庭經濟狀況特征包括家庭收入、家庭是否從事工商業經營;家庭社會保障水平包括家中參加新農合成員占比和家中參加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成員占比。村莊層面控制了宗族狀況、村莊總戶數、村莊務農勞動力占比、村莊耕地面積、村莊非農經濟、村莊距縣城距離和村莊地形(以山地為參照)等變量。除此之外,還納入了省份虛擬變量。變量定義與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圈內交往頻率和圈外交往頻率的均值分別為3.153和2.362,表明親友間圈內交往頻率總體處于“大部分去”“全部去”之間,非親友間圈外交往頻率總體處于“少部分去”“大部分去”之間,這意味著村莊整體的親友間的圈內交往頻率要高于非親友間的圈外交往頻率,呈現“差序格局”特征。超過1/4的樣本所在村莊2003年以來發生過農地調整,少于1/5的樣本所在村莊2016年以來發生過農地調整,可見農地調整和重新分配在中國農村依然時有發生。
(三)描述性證據
基于CLDS2018年數據,表2描述了不同地權穩定性狀況下村莊農民的社會交往頻率、人情禮金支出和農地熟人交易情況的差異。由表2可知,首先,相比于未發生農地調整的村莊,發生農地調整的村莊農戶的圈內交往頻率和圈外交往頻率均更高。其次,發生農地調整的村莊農戶的人情禮金支出更多,平均高出590.808元。最后,發生地權調整的村莊內農地熟人交易更為盛行。以上表明,地權穩定性缺位可能是強化農民社會交往頻率、塑造村莊關系型社會形態和人格化交易秩序的重要誘因。
(四)模型構建與說明
本文旨在考察地權穩定性對村社成員交往關系和村莊社會形態的影響,為此構建如下模型:
[Yi=α0+α1Ci+αj=228α jXij+ρi+εi]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其中,[Yi]為農民圈內交往頻率和圈外交往頻率。[Ci]為農地調整,使用村莊農地調整發生及其發生程度共同衡量。[Xi]為所有控制變量,[j]為控制變量的個數。[ρi]為省份虛擬變量。[εi]為隨機擾動項,并假定其滿足正態分布。由于被解釋變量為排序變量,故本文采用有序 Probit模型進行估計。
四、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與分析
表3給出了有序Pr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匯報了村莊的農地調整發生情況對村莊內農民圈內交往頻率和圈外交往頻率的影響。由表3可知,農地調整均在1%顯著水平上正向影響村社農民圈內交往頻率和圈外交往頻率,這表明,在發生農地調整的村莊內,農民不僅會提升與親友的人情交往頻率,而且會構筑與村內非親友群體之間更為密切的人情互動關系。這也驗證了,農村地權穩定性的長期缺位是中國鄉村社會內部群體成員之間社會網絡關系、人情交往格局形成的重要誘因。村莊存在宗族會顯著弱化農民圈內交往頻率,強化農民圈外交往頻率。可能的原因是,血緣親情的基礎決定了宗族內部成員的權利糾紛往往可以遵循一套族規或秩序加以解決和處理,但對非親友間的利益競爭缺乏約束力。因此,宗族保護將減弱形式化的圈內交往頻率,而基于權利排他以提升圈外交往頻率。村莊務農勞動力占比越高的村莊會同時提升農民圈內交往頻率和圈外交往頻率,村莊務農勞動力占比較高往往意味著土地及其農事活動的重要性提升,而農民基于土地稟賦的競爭與排他關系決定了其開展并維系村社內的社會交往活動的頻率。此外還發現,村莊距縣城距離越遠,農民圈內交往頻率和圈外交往頻率越高,其原因在于,在偏遠村莊中往往非正式制度和可自我實施的村莊私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農民的社會交往活動發揮著保護權利、抵御侵犯,強化生活穩定性的重要功能。
考慮到有序Probit模型的參數只能從顯著性程度和影響方向上給出有限信息,因此,本文進一步計算出農地調整對農民村社交往頻率取值概率的邊際效應,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首先,發生農地調整的概率每增加1個單位,村莊親友辦喜事極少去、少部分去、大部分去送禮的概率分別平均減少1.2%、2.1%和3.6%,全部去送禮的概率平均增加6.9%。其次,發生農地調整的概率每增加1個單位,村莊非親友辦喜事極少去和少部分去送禮的概率分別平均減少8.7%和2.6%,大部分去和全部去送禮的概率平均增加3.8%和7.5%。由此可見,邊際效應的分析也驗證了上文分析的結論,雖然在兩類群體中地權穩定性影響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地權穩定性對強化圈內交往頻率的程度更大。
(二)穩健性檢驗
1.替換解釋變量
本部分從近一年來的地權調整情況刻畫地權穩定性,使用農地調整程度并加入全部控制變量重新刻畫被解釋變量。估計結果顯示,1無論是農民的圈內交往頻率還是圈外交往頻率,農地調整發生及其幅度越大的村莊,農民社會交往頻率越高,從而表明本文基準回歸結果穩健。
2.使用人情禮金支出重新刻畫被解釋變量
中國農村社會歷來被視為是關系型社會,也普遍被稱為熟人社會、人情社會。村社成員締結彼此熟識的關系網絡,共享村社生活的基本秩序、常識和彼此建構生存的運行系統,由此生成并存續人情關系的土壤[27]。中國傳統社會中維系感情、搭建人情關聯的重要媒介是節日或者婚喪嫁娶時互贈的禮品或金錢[28]。因此,村社關系網絡密度往往可以使用人情隨禮的金額進行表征[29-30]。本部分使用CLDS2018年問卷中“禮品和禮金支出總額”作為農民社會關系網絡密度的代理變量并加入家庭特征和村莊特征控制變量重新刻畫。估計結果顯示,農地調整均在5%的顯著水平上正向影響農戶人情禮金支出。這一估計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基本邏輯。
3.基于村社經濟交易活動的考察
村社中的經濟交易活動是中國農民生活的重要內容,其中,土地經營權的交易最具代表性。土地是農村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是農民的命根子,地權交易的首要準則是保障地權的安全性和收回的便利性。因此,以人情關系和聲譽機制維系的熟人交易成為農民化解地權風險的優選形式,人情規則成為農戶間經濟活動的重要規則,且血緣、地緣和親情關系較緊密的主體往往成為交易締約的首選對象[31]。本部分使用農地熟人流轉并加入村莊控制變量進一步考察地權穩定性的行為響應。估計結果顯示,農地調整會顯著增加村內熟人流轉主體數量和土地規模。從而表明地權穩定性不足是村莊社會熟人交易形態存續的重要誘因。
五、內生性問題討論和異質性分析
(一)內生性問題討論
1.基于工具變量法的檢驗
本文引入農地調整變量可能產生內生性問題。為有效解決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縣內其他村莊的農地調整率作為工具變量。理論上說,集聚層數據是合適的工具變量,同縣其他村莊農地調整的示范作用會影響到本村農地調整,但是,村莊是中國農民社會生活的基本組織單位,村莊組織文化在村社成員的行為決策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長期聚居生活形成了村莊的基本秩序。實際上,本村以外的村莊對于農民而言是不同的生活單位,并具有明顯的行為差異與生活界限。這意味著,本村農戶的行為觀念并不會直接受到其他村莊的影響,本村外其他村莊發生農地調整也并不會直接影響到本村農戶的行為預期。因此,滿足工具變量選擇標準。由表5可知,弱工具變量檢驗和識別不足檢驗表明,本文所采用的工具變量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和識別不足問題。工具變量法的估計結果表明,相比于地權較為穩定的村莊,地權穩定性不足的村莊農民具有更高程度的圈內交往頻率和圈外交往頻率。這一結果也與基準回歸的結果相一致。
2.基于PSM法的估計
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選擇問題,本文使用傾向得分匹配(PSM)法重新估計農地調整對農民交往頻率的影響。(1)將發生農地調整的村莊界定為實驗組,將未發生農地調整的村莊界定為控制組。(2)根據表1中控制變量,將農民的個體特征、家庭特征和村莊特征等因素納入模型,以保證可忽略性假設得到滿足,并使用Logit模型估計傾向得分值。(3)由于不同匹配方法無優劣之分且均會存在一定的測算誤差,若使用多種匹配方式后獲得的結果具有一致性,則意味著匹配結果穩健,樣本有效性良好[32]。因此,為增強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分別進行最近鄰匹配、半徑匹配和核匹配三種匹配策略,估計農地調整的平均處理效應(ATT)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農地調整會顯著提升圈內交往頻率和圈外交往頻率。由此進一步驗證上文估計結果穩健。
(二)異質性分析
1.基于農地調整發生機制的討論
在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框架內,農民成員權的天賦性和公平性決定了賦權均分的必然性,農地調整曾一度成為農村地區的普遍現象[33]。絕大多數農地調整是在人地關系發生變化后對要素分配不平等的響應。這意味著,隨著村莊新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的增加,農地調整的需求更為強烈,由此導致地權不穩定的潛在隱患。本部分仍沿用前文的估計模型,基于村莊人地關系變動,從地權調整發生機制的角度進一步識別地權穩定性對農民社會交往關系的影響。表7中村莊新生和死亡人口的估計系數均顯著為正,可見村莊人口變動確實提高了農民村社交往緊密度,并且在加入村莊新生和死亡人口變量之后,解釋變量依然具有正向顯著性且估計系數變大。可能的解釋是,農地調整是一種地權“均分”機制,相對于未發生人口變動的村莊,人口變動誘發的人地關系改變將提升農地調整發生的可能性,從而動搖村莊地權的穩定狀態,自然強化了地權調整對農民村社交往頻率的正向影響。
2.基于人地矛盾歷史遺產的社會關系效應的考察
從中國長期的歷史進程來看,中國農村地權不穩定問題一直存在。千百年來農村地權不穩定的歷史沉淀和制度遺產也必然成為形塑農民經濟社會交往秩序的核心因素。本文從經濟史學的角度,以中國歷史土地集中度刻畫人地矛盾以表征地區的地權穩定性。由表8可知,無論是按照6.670公頃農戶占比衡量土地集中度(集中度1)還是按照3.335公頃占比衡量土地集中度(集中度2),地權穩定性不足均會顯著提升農民村社交往頻率。
3.強化地權競爭性:知識資本和性別差異的力量
(1)知識資本在地權競爭中的力量強化功能。在中國傳統社會,通過教育進入國家體制內工作歷來被視為是主要的社會價值和鄉村追求的理想[34-35],具有體制內就業成員的農戶在農村社會中往往享有較高聲望、地位和權力,這不僅是一件榮耀的事,而且這種“炫耀性”的信號顯示能夠強化利益博弈中的談判優勢。本文基于“受訪者從事職業的類型”1的問項結果擬合出家庭成員中是否有在國家體制單位就業的成員,分別對兩類主體進行估計。由表9可知,在無體制內就業成員的農戶中,農地調整對農民村社交往頻率的影響與基準回歸一致,但是,在有體制內就業成員的農戶中,農地調整并未表現出提升圈內交往頻率的顯著影響。可能的解釋是,體制內就業所強化的地權競爭力量形成了對于村社交往以競爭地權的功能性替代。
(2)男性是傳統社會中力量和權力的象征。男性有著與生俱來的斗爭優勢,而且在傳統文化中,父系社會性質決定了男性在社會上具有較高地位、力量和權力,農戶家庭在村落經濟活動中的競爭能力也主要由男性表達[36]。因此,擁有更多男性的農戶家庭往往具有更強的地權競爭力量。本文按照村莊農戶家庭中成年男性的平均數將農戶家庭分為高成年男性組和低成年男性組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知,在高成年男性組中,農地調整并未表現出對圈內交往頻率的顯著強化作用,但依然會強化圈外交往頻率,從而刻畫出農村男性在地權競爭中的重要作用。
4.強化地權排他性:行政權威和法律賦權的力量
(1)行政權威強化地權排他性。中國農村不僅是充滿非正式制度的社會單元,也是國家基層治理的行政單元。隨著地方行政體制改革的推進,“鄉政”對“村治”的管制成為鄉村治理的重要導向。但是,就邏輯上而言,越是偏遠的村落,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可能越大[37]。本部分使用村莊是否在鄉鎮政府所在地來刻畫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強弱。由表11可知,距離鄉鎮政府所在地越遠的村莊,農業調整將顯著強化農民的村社交往頻率。但是,在鄉鎮政府所在地的村落中,農地調整甚至會抑制農民村社關系網絡的擴大。這是因為,基層行政權威不僅可以有效制約村莊地權侵犯,而且可以形成規范、有序且得以實施的正式規則和行動秩序。
(2)法治保護強化地權排他性。2009年試點并于2013年推廣的新一輪農地確權頒證政策被視為維護地權穩定與安全最為重要的政策舉措。農地確權通過法律賦權的方式,以法律證書的形式明確農戶與土地之間的關系。這意味著,地權的明晰與穩定將會弱化農民基于地權保護的非正式力量締結,尤其是基于強化地權排他性構筑的非親友關系社會網絡存續的基礎被解構。由表12可知,農地確權實施弱化了圈內交往頻率,會顯著降低圈外交往頻率。農地確權與農地調整是相對應的一組命題,表12的結果也進一步驗證本文基本邏輯的科學性。
六、主要結論、進一步討論和政策啟示
長期以來,鄉土中國的農村社會是一個以熟人網絡和人情關系為主要形態的生活單元,這樣的社會形態具有重要的土地情節和地權含義,其形成、存續和演化的根源與農民的地權關系緊密關聯。筆者認為,地權穩定性缺位內含的地權風險和生存風險將激發農民構建村社人情關系,強化家庭地權競爭力和排他性,這也是農村關系型社會形態得以形成的產權經濟學邏輯。
(一)主要結論
相比于未發生農地調整的村莊,發生農地調整的村莊內的農民具有更高的親友圈內交往頻率和非親友圈外交往頻率。隨著農地調整程度的加劇,農民將顯著強化村社親友和非親友的人情關系。進一步證據表明,地權穩定性不足的歷史遺產也將誘使農民與村社親友、非親友的人情往來。此外,筆者還發現,家中有體制內就業人員和家庭擁有更多成年男性是強化農戶地權競爭力量的重要砝碼,對農民開展的基于地權競爭的親友圈內社交具有功能性替代。村莊距離行政中心越近以及產權的法律保護可以有效強化農民地權排他性,從而弱化農民基于維護地權排他而構筑的圈外社交關系。筆者強調,中國農民村社交往格局及其形成的關系型村社形態隱含著深刻的產權經濟學邏輯。其中,村社圈內交往和圈外交往具有不同的產權意蘊。
(二)進一步討論
中國農村社會歷來被視為是一個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熟人社會與關系社會,其形成不僅是基于地理空間概念聚居而成的客觀形態,而且農村社會群體生存韌性不足也是農民主動締結關系的重要誘因。尤其是,土地作為中國農村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其穩定性與安全性狀態是影響農民生存安全與穩定的重要內容,也成為農民維系村社交往的重要制度邏輯。但是,農村的熟人社會形態并非截然二分,而表達為村莊內部的“差序格局”,村莊內部存在親友群體和非親友群體親疏遠近的“波紋”關系,農民的社交活動也包括親友間的圈內交往和非親友間的圈外交往。
從地權博弈的角度重新審視,兩類交往具有不同的產權邏輯。實際上,農村地權的調整與分配是基于村莊內部人地關系的存量分割,村社成員既是享益主體,也是競爭主體,還可能是地權侵犯的潛在主體。基于“差序格局”的特征而言,農民主要維系著親族和家族網絡的合作互助模式,實現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通過提升圈內交往頻率、密切親友交往關系,強化地權保護和競爭力量。雖然,親友在邏輯上也可能成為地權侵犯的主體,但家族內部的道德約束和群體性懲戒規則往往會形成剛性制約機制。但非親友就成為地權租值攫取的競爭對手和地權排他的主要對象。提升圈外交往頻率能夠達成地權不被侵犯的隱性契約,形成產權的社會認同,提升產權強度以強化地權排他性。因此,農民村社交往活動可能具有不同的產權意蘊。
基于農村土地產權競爭力量角度的觀察,值得強調的是,在非正式制度廣泛存在并發揮重要作用的中國傳統農村社會中,男性與生俱來的斗爭優勢和男權社會的權力賦予,使得成年男性家庭成員成為土地權利租值攫取及其保護的核心力量,這也打開了中國農村土地產權與農民生育性別偏好關聯性的邏輯密碼。此外,教育作為鄉土中國普遍的社會價值偏好,其具有的信號顯示功能也是強化地權保護力量的重要砝碼,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長期以來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學而優則仕”“讀書改變命運”等傳統教育觀念生成、存續和傳承的根源。
總之,農村社會的交往關系和內在邏輯是地權制度演化進程留給我們有益的社會資產和生存財富。明晰地權邊界、長期穩定地權已成為當前中國農村地權制度改革的核心線索。隨著村莊開放,農民日益獲得更為充分的非農就業機會和外部發展權利,且非農收入已經成為農民家庭的主要收入,農地的生存保障功能不斷弱化,由此可能帶來的是,農民基于農地產權所聯結的關系網絡將會出現不可避免的撕裂和瓦解趨勢。這些必須引起我們長期的觀察和重視。
(三)政策啟示
鄉土中國的廣大村莊在通常的研究中往往被定義為“熟人社會”或“人情社會”,其基本行為邏輯呈現出“差序格局”的特征。但是,中國的村莊一般由多個姓氏群體、不同宗族家族共同聚居而成,族親的邊界將圈內和圈外劃分為兩類群體并遵循不同的社會交往邏輯。探究村社內部不同群體的社會交往內含的聯系和差別,將有助于識別村莊交往出現的問題,制定有效的策略以實現鄉村善治。本文的政策啟示是:首先,穩定地權、明晰界定產權邊界已成為中國農村地權制度改革的核心線索。隨著時間漸遠、代際傳承,農地調整與再分配將逐步成為歷史,農地產權在從調整走向穩定、從模糊走向明晰,從羸弱走向強化的過程中,農村社會密切的交往關系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松動和撕裂,降低人情隱性契約的約束效率。這需要基層政府強化鄉風傳統管理和宣傳,開展村社集體活動以提升村民情感互動,維系并發揚村莊有益文化資源。其次,傳統農村社會成員的社會交往活動具有保護產權的行為邏輯,這也印證了推動地權法治化,提升農民產權強度的合理性和合意性,因此,政府應堅持地權法治治理、保障農民土地權利的改革方向,形成農村土地稟賦的國家法律賦權、村莊社會認同和農民行為能力相匹配的地權保障機制。最后,在鄉土中國中,讀書重教一直是普遍的社會價值偏好,教育具有重要的信號顯示作用,是強化農民家庭權利競爭力量的重要砝碼,因而國家應持續重視鄉村教育,尤其要維護教育公平。
參考文獻:
[1] 羅必良,耿鵬鵬.鄉村治理及其轉型的產權邏輯[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188-204.
[2] 仇童偉,羅必良.“好”的代理人抑或“壞”的合謀者:宗族如何影響農地調整?[J].管理世界,2019(8):97-109.
[3] 耿鵬鵬,羅必良.“競爭”抑或“繼承”:農地產權如何影響農民生育性別偏好[J].經濟評論,2021(6):34-48.
[4] HAN Y,ALTMAN Y. Supervisor and subordinate guanxi: a grounded investig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9,88(1): 91-104.
[5] 張櫻.社會資本對企業R&D投資的影響——基于GMM方法的動態面板數據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16(5):64-75.
[6] 易行健,張波,楊汝岱,等.家庭社會網絡與農戶儲蓄行為:基于中國農村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12(5):43-51.
[7] 張曙光.中國農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61.
[8]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82-83.
[9] 魯西奇.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400.
[10] 賀雪峰.公私觀念與農民行動的邏輯[J].廣東社會科學,2006(1):153-158.
[11] 羅必良.農地產權:調整、穩定與盤活[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9:31.
[12] SCOTT J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13] 賀雪峰,仝志輝.論村莊社會關聯——兼論村莊秩序的社會基礎[J].中國社會科學,2002(3):124-134.
[14] 耿鵬鵬,羅必良.“約束”與“補償”的平衡:農地調整如何影響確權的效率決定[J].中國農村觀察,2021(2):61-80.
[15] 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47-63.
[16] 馮必揚.人情社會與契約社會——基于社會交換理論的視角[J].社會科學,2011(9):67-75.
[17] HART O. Firms,contracts,and financial structure[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5.
[18] 李稻葵.轉型經濟中的模糊產權理論[J].經濟研究,1995(4):42-50.
[19] MA X,HEERINK N,VAN IERLAND E,et al. Land tenure security and land investments in northwest China[J].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2013,5(2) : 281-307.
[20] 章元,陸銘.社會網絡是否有助于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J].管理世界,2009(3):45-54.
[21] LIN N.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2] 趙劍治,陸銘.關系對農村收入差距的貢獻及其地區差異——一項基于回歸的分解分析[J].經濟學(季刊),2010(1):363-390.
[23] 周廣肅,樊綱,馬光榮.收入不平等對中國家庭可見性支出的影響[J].財貿經濟,2018(11):21-35.
[24] 朱月季,楊琦,劉玲.抑制或促進?勞動力外流對農村人情消費的影響研究[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5):136-147.
[25] 李江一,秦范.如何破解農地流轉的需求困境?——以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例[J].管理世界,2022(2):84-99.
[26] 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J].中國社會科學,2013(8):102-123.
[27] 宋麗娜.人情往來的社會機制——以公共性和私人性為分析框架[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119-124.
[28] 馬光榮,楊恩艷.社會網絡、非正規金融與創業[J].經濟研究,2011(3):83-94.
[29] 何軍,寧滿秀,史清華.農戶民間借貸需求及影響因素實證研究——基于江蘇省390戶農戶調查數據分析[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20-24.
[30] 楊汝岱,陳斌開,朱詩娥.基于社會網絡視角的農戶民間借貸需求行為研究[J].經濟研究,2011(11):116-129.
[31] 羅必良,劉茜.農地流轉糾紛:基于合約視角的分析——來自廣東省的農戶問卷[J].廣東社會科學,2013(1):35-44.
[32] 陳強.高級計量經濟學及Stata應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45.
[33] 李尚蒲,羅必良.農地調整的內在機理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5(3):18-33.
[34] KULP D H.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5.
[35] 蕭公權.中國鄉村:論十九世紀的帝國控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301.
[36] 朱文玨,羅必良.勞動力轉移、性別差異與農地流轉及合約選擇[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0(1):160-169.
[37] 仇童偉,羅必良.宗族結構、農地重要性與地權不平等——基于權力悖論的分析[J].江海學刊,2021(4):92-101.Social Relationship Effect of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 Micro Study on Soci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of Farmers
GENG Peng?peng1, LUO Bi?lia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2. National School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Summary:Understanding the basic logic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mong farmers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Land property rights are the core of rur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 Land property rights stability and safety are key element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farmers life, being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logic for farmers to maintain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villages.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mong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s extremely scarce, especially the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within villages.
Using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farmers from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this study adopts econometric models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on soci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of farmers.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farmers in villages where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s insufficient have a higher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family and friend circle, as well as in non?family and non?friend circle. As the in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ntensifies, farmers will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non?family members in villages. Further study suggests that historical heritage with insufficient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also stimulates farmers human relations. In addi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having family members within the system and the number of adult males in the household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farmers in competition for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have a functional substitute for farmers social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circle based on competition for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closer distance a village is to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and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can promote the exclusivity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so as to weaken the external social relationships built by farmers for maintaining exclusiv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innovations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it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shaping social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s among farm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exclusivity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righ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essential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within farmers family and friends circle and non?family and non?friend circle to reveal the logic and basic nature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within rural society. Second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s,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property rights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roots of the formation, survival, and evolution of the village for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in China.
Key words:property rights system;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social communication radius;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relationnal transactions; social relationship effect
(責任編輯:劉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