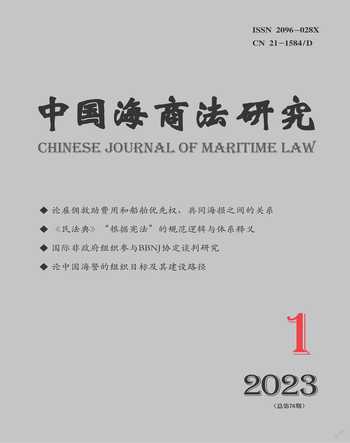《民法典》“根據憲法”的規范邏輯與體系釋義
摘要:在《民法典》編纂過程中,關于“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一表述始終存有爭議,并集中表現為民法獨立說、民憲平行說與憲法至上說這三種觀點。由于缺乏統一的方法論以及理論基礎,現有學說并未形成對“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融貫性的規范理解。“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本身具備來自規范層面、國家權力關系層面以及基本權利“客觀法”層面的正當性基礎。從憲法教義學的角度出發,可以系統探尋“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意涵,并將這一抽象的原則轉為在規范層面和技術層面可供操作的規則。一方面,在積極意義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要求《民法典》積極落實制度性保障功能、組織性保障功能以及國家保護義務功能;另一方面,在消極意義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要求《民法典》應始終恪守憲法框架秩序這一基本邊界,在解釋和適用過程中嚴格遵循合憲性解釋方法以及合憲性審查標準,以切實發揮“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指示作用。
關鍵詞:“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民法典》;規范意涵;制度性保障
中圖分類號:D923;D9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6-028X(2023)01-0025-11
Normative Logic and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Civil Code
WANG Zh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Legal Philosophy,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the Civil Code,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dispute about the expression of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which focuses on three views, including “the independent theory of civil law”,“the parallel theory of civil law and constitution” and “the supremacy of constitution”. Due to the lack of a unified methodology and theoretical basis, the existing theories have not yet formed a norm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istency of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has a legitimate basis from the normative level, the state power relationship level and the basic rights “objective law”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doctrine, the normative meaning of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can be explored, and this abstract principle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operational rules at the normative and technical levels. On the one hand, in a positive sense,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e Civil Code to actively implement the functions of systematic guarante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and national protection oblig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n a negative sense,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at the Civil Code always abide by its basic boundaries, that is, the order of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strictly follow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 criteria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thereby effectively playing the normative role of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Key words:“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the Civil Code; normative meaning; systematic guarantee
憲法是國家根本法,也是一國法律體系的法源和權源所在。因此,立法者在行使立法權、制定法典的過程中,理應積極從憲法中找尋合法性與正當性,即必須將憲法作為根本依據,以彰顯部門法的憲法淵源。【“法的淵源”包括四種含義:一是法的實質淵源,即法是根源于客觀物質條件還是主觀意志;二是法的形式淵源,即法的具體表現形式;三是法的效力淵源,即法由何種國家機關制定;四是法的材料淵源,即形成法的材料來源成文法還是來源政策、習慣、宗教、禮儀、道德、典章或理論、學說等。參見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頁。立法的權力淵源和內容淵源分別是在第三層和第四層意義上使用。】然而,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過程中,由于憲法學與部門法學缺乏深入互動和交流,各方關于“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一表述常常陷入爭論之中。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基本法》到原《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簡稱《物權法》),關于“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爭論就一直持續不斷,尤其是在原《物權法》的制定過程中,有關民法作為基本法與憲法作為根本法的討論更是始終牽動人心。此后,隨著原《物權法》正式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納入第1條,相關爭論也并未偃旗息鼓,依舊不時擦出火花。理論上的徘徊不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立法者時常陷入躊躇,據學者統計,截至2021年10月份,現行288件法律中,僅有97件明確吸收了“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參見張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蘊涵與立法表達》,載《政治與法律》2022年第3期,第109頁。】這就表明這一理論仍有厘清的必要。從事實角度來看,“根據憲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簡稱《民法典》)制定期間又一次引發了爭論,學界關于是否有必要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納入《民法典》,仍然是見仁見智。2020年5月份頒布的《民法典》在第1條明確規定了“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民法典》第1條規定:“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本款看似有著“定分止爭”的效果,但憲法和民法究竟是何種關系?當前爭論的焦點為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是否具備正當性基礎?更重要的是,“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是僅僅起到價值宣誓作用,還是具備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上的規范指向?顯然,厘清這些問題,對于建構起憲法與部門法之間的動態關系,推動部門憲法教義學的深化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王植:《民法典》“根據憲法”的規范邏輯與體系釋義
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理論爭議
在《民法典》的編撰過程中,關于民法和憲法的關系始終備受關注。民法學者與憲法學者延續2006年原《物權法》與憲法關系界分的討論,圍繞民法和憲法的關系展開了熱烈討論,并集中表現為民法獨立說、民憲平行說與憲法至上說三種觀點。
(一)民法獨立說
所謂民法獨立說,是指部分民法學者主張基于私法自治的需要,民法本身渾然一體,獨立于憲法之外,并呈現出一套涇渭分明的邏輯體系。
一方面,就歷史積淀而言,民法的歷史積淀要遠超過憲法。民法本身來源于市民社會,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并且經歷了習慣法、成文法、制定法、判例法等多種形式,不遺余力地調整著市民社會的關系演變,早在1804年就產生了著名的《法國民法典》,反觀憲法更多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后逐漸產生,直至1787年才形成了第一部明確的成文憲法,且1787年《美國憲法》,無論是篇幅、結構還是影響力都遠不如《法國民法典》那樣深遠。此時,如果強行將民法置于憲法之下,不僅會擾亂民法的邏輯體系,同時也會是憲法無法承受之重。
另一方面,就調整范圍而言,民法和憲法分別對應私法和公法這兩個維度。民法和憲法雖然都是一國重要的法律構成,但卻分別面向不同的法律關系抑或調整范圍,即民法更多是市民社會不斷發展的產物,反觀憲法則更多是政治國家逐漸成熟的法律外觀。申言之,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本身就是一套二元結構,早在自由資本主義期間,國家就扮演著“守夜人”的角色,這進一步表明,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本身是一個獨立的二元結構,因此,理應通過不同的法律加以調整,即民法調整市民社會領域的私權,憲法則調整政治國家領域的公權,基于“守夜人”的政治屬性,私權始終構成公權力的行為邊界。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法和憲法本應互不干擾,二者分別扮演著私法領域和公法領域的基本法角色。【參見趙萬一:《從民法與憲法關系的視角談我國民法典制訂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構》,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1期,第117-120頁。】
如此,如果秉承上述觀點,“根據憲法,制定民法”的邏輯仍然面臨著重大挑戰,正如郭道暉、梁慧星指出,公法優位主義并不可取,適度承認和確立私法優位主義,對于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更具創見性。【參見郭道暉、梁慧星、
摘要》,載《法學研究》1992年第6期,第2-3頁。】
(二)民憲平行說
所謂民憲平行說,是指民法和憲法分別對應不同的領域范圍和價值指涉,并無優劣和高低之說,而是表現為平行的法律關系。當然這種平行并不意味著法律效力的一致,而是指調整內容、規范方式以及目的價值的平行。在此意義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只能體現憲法在法律效力上優于民法,但卻并不意味著憲法在內容上相對于民法的優勢地位,更不能簡單以“母法”和“子法”的稱謂來回應憲法和民法之間的關系,相反,與其將二者的關系定位為“母子”,倒不如直接描述為相輔相成的平行樣態。畢竟,立足于社會主義法制統一性,憲法作為根本法無疑處于法律效力上的最頂端,法律在效力上當然要以憲法為依據,民法也不能例外,但這種效力上的優位更多指向形式意義,并不意味在內容設定上要將憲法定位為母法,民法只能將憲法予以具體化。【參見王利明:《何謂根據憲法制定民法?》,載《法治現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74-75頁。】事實上,憲法和民法在最初的設定上就呈現出迥異差別,前者更多對應“限制公權,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因此內容上自然以國家組織法和基本權利保障法為主,公權內部關系、公權與公民基本權利關系是重中之重。民法在設定上則更多是為了調適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從而最大程度上實現意思自治、私權自由,甚至民法的條款都以微觀的技術性規則呈現出來,與宏觀層面的“公權—私權”關系相去甚遠。【參見趙萬一:《從民法與憲法關系的視角談我國民法典制訂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構》,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1期,第122-123頁。】例如,民法的很多規則如無權代理、表見代理、善意取得等都是民法所特有的,并不涉及宏觀層面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此時,如果強行將憲法付諸民法領域的技術性規則,不僅會降低民法規則的明確性和可操作性,動輒憲法化的思維還會稀釋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存在“用大炮打小鳥”的嫌疑。一言以蔽之,“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特指法律效力抑或立法權來源,在內容設定上并不成立。有鑒于此,龍衛球等學者主張為避免憲法對民法的全面輻射,應該調整“根據憲法”的法律表述,以更明確的話語指出,從而全面彰顯憲法和民法的平行對等關系。【參見龍衛球:《民法典編纂要警惕“憲法依據”陷阱》,載財新網2015年4月22日,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4-22/100802509.html。】
值得注意的是,平行說和獨立說雖然在論證結論表述和具體論證方式上存在著不同,但在諸多方面的觀點都具有相同之處。具體來說,平行說和獨立說都以“民法相對于憲法具有相對獨立性”這一命題作為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礎的,都表達了對以憲法來統攝民法觀點的實質性抗拒,都強調民法與憲法在調整對象、調整范圍和功能層次上的不同,只不過平行說相對于獨立說而言承認憲法對民法具有形式上的效力優位地位。
(三)憲法至上說
上述民法獨立說以及民憲平行說更多以民法學者為代表。憲法學者對于這一問題同樣有所回應,并大多主張憲法作為根本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地位超然,因此,《民法典》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納入第1條并無不妥之處,理由如下。
首先,就民法和憲法的歷史積淀而言,僅僅從誕生的歷史長短來界定民法和憲法的關系未免過于武斷,如果理由正當,后來者居上也沒有任何不妥。當前,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愈發成熟,部門法法典化的呼聲愈發高漲,但晚近以來,民法典時代僅僅是法律化時代的一個側面,隨著現代憲法興起,后者業已逐步取代了民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并以根本法、基本法、框架秩序等多元形式呈現出來。【參見林來梵、龍衛球、王涌等:《對話一:民法典編纂的憲法問題》,載《交大法學》2016年第4期,第5-32頁。】在一定程度上,現有民法學說業已脫離了中國現有法秩序,將私法自治提升到自然法原則的高度,因此并不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
其次,就民法與憲法的調整對象而言,在當前語境下,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并非二元對立,彼此之間也并非絕對分離,而是呈現出相互交融之勢,此時,憲法并非僅僅調適政治國家,作為一種框架秩序,其業已成為整個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基礎,奠定了整個法律秩序的基本價值秩序。【參見韓大元、林來梵、白斌等:《行憲以法,馭法以憲:再談憲法與部門法的關系》,載《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2期,第7頁。】照此意義,憲法理應是“公法和私法的共同基礎”,【參見童之偉:《憲法司法適用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載《法學》2001年第11期,第8頁。】僅僅將憲法認定為公法規范,未免存在以偏概全的嫌疑。此外,現代憲法本身是一部權利保障法,無論其在內容上如何設定,保障公民基本權利都是其中的核心和關鍵所在。其中,基本權利的保障作為一個系統功能,不僅需要防止國家公權力的侵犯,在平等私主體之間實現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同樣至關重要。
最后,就民法和憲法的價值關系而言,相較于民法獨立說和民憲平行說,賦予憲法以優位地位更能夠在價值層面上樹立法制統一和權利保障的理念。通過在《民法典》中規定“根據憲法”,則不僅可以闡明民事部門法間立法權的邏輯關系,同時可以明確規范效力的來源,【參見鄭賢君:《作為憲法實施法的民法——兼議龍衛球教授所謂的“民法典制定的憲法陷阱”》,載《法學評論》2016年第1期,第6頁。】無疑更加符合現代憲法理念。
由此可知,當前無論是民法學界抑或是憲法學界,對于民法與憲法的關系界定似乎都存在一定主觀性和片面性,即更多是從本學科視角出發,帶有很強的學科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不僅是視角上缺乏一致,對于這對關系的解釋也缺乏方法上的統一。在筆者看來,“依據憲法,制定本法”本非一個系統問題,必須采取客觀、綜合且全面的態度來理性看待。
二、“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正當性基礎
(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基礎
“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在規范層面上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具備充分的形式正當性,且這一正當性能夠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簡稱《立法法》)以及憲法性法律層面得到充分回應。
一方面,就憲法層面而言,《憲法》第5條“社會主義法制統一”條款對于憲法與法律的關系予以了明確界定,【《憲法》第5條第1款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其中,享有立法權的主體的數量、權限以及行使立法權的方式等,都會或多或少影響到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在此,根據凱爾森的“規范等級理論”,國家法律并非位于同一位面之上,而是具有一定的階梯性質,并集中表現為“低級規范—高級規范—基礎規范”,其中,后者直接決定了前者的創設方式和創設內容,并最終形成一個富有凝聚力和體系性的法律組合。【參見[奧]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93-194頁。】憲法作為根本法,是中國的基礎規范,包括《民法典》在內的所有法規范,都必須在《憲法》的指引下在法秩序體系內實現融貫,以此來捍衛法制體系的統一性。
另一方面,“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作為《民法典》的立法依據和立法權限條款并非是獨存的,中國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都明確在第1條吸收了本款內容。其一,就組織法層面而言,包括《立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簡稱《監察法》)等都在一開始規定了“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部分在一開始未予規定的國家機構組織法,如2018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院組織法》也將本款納入了正式規定。其二,在部門法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簡稱《刑法》)、《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等都在第1條明確規定了“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即便是在制定期間充滿爭議的原《物權法》,最后也吸收了這一條款。作為部門法,民法獨立說、民憲平行說的觀點同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用于《刑法》和《監察法》,但這兩部法律最后選擇了妥協。正如葉海波所言,在法律中寫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不僅是立法者依憲立法的自我確證和事實陳述,也是立法權法定(包括權源法定和法源法定)原則的規范要求。【參見葉海波:《“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內涵》,載《法學家》2013年第5期,第20頁。】因此,通過對中國法律體系的整體觀察,《民法典》雖然同其他法律在規范領域和法律性質上存在不同,但是仍必須要在國家的統一法秩序中尋找到作為立法合法性與正當性基礎的立法依據。
(二)“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國家權力關系基礎
探討憲法與民法的關系,不能離開國家權力的配置關系。在中國,任何國家權力的行使都受到憲法的約束和限制,立法權亦不例外。
一方面,從制憲權理論角度,可以認識限制立法權的必要性。制憲權是指制定憲法的權力,又被西耶斯稱為原始的創造性權力,【參見[法]西耶斯:《論特權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56頁。】國內在憲法學研究早期,對于制憲權下了諸多定義,如許崇德認為,制憲權是指制定和修改國家根本法,即憲法的根本性權力。【參見許崇德:《憲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頁。】朱福惠認為應該從內容、主體和程序這三個維度來界定制憲權,即制憲權是指規定國家基本制度、調整國家基本關系的根本性權力,是特定主體通過特定程序和方式行使的,區別于普通立法性權力的始源性權力。【參見朱福惠:《憲法至上——法治之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頁。】徐秀義和韓大元認為,制憲權是一個綜合體系,既涵蓋制憲活動的事實,也包括憲法至上的政治權威。【參見徐秀義、韓大元:《現代憲法學基本原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頁。】盡管上述定義各有不同,但無一例外均強調制憲權的主權性、至上性和根本性。事實上,制憲權并非憑空產生,而是與立法活動和立法權具有緊密的聯系。換言之,雖然在制憲權概念出現之前,立法活動就已經在事實上存在了,但是制憲權概念得到承認之后,便呈現為主權性權力,立法權則成為制憲權所衍生、委托的下階權力,自始至終接受憲法的監督和約束。此時,盡管國家呈現出完整的法律體系,但在效力位階上卻等級分明,其中,憲法作為根本法,統領國家一切法律事項,調整國家法律關系,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權威,法律則負責將抽象的憲法原則具體化為可供操作的法律規則。在立法的過程中,必須有效約束和限制立法權來保障以憲法為核心的法秩序體系的融貫性和規范效力。“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有利于在民事立法中,依據憲法規范和限制國家立法權,保障民事立法維護公民基本權利。
另一方面,從對議會民主的理論反思角度,也可以認識限制立法權的必要性。當今時代下,僅僅依靠多數主義的議會民主原則并不足以防范立法權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害,畢竟議會行使立法權只能保障形式意義上的合法性,卻并不能保障立法內容的合憲性。同理,將《民法典》的合法性和正當性訴諸代議制民主看似合理,但受制于種種因素,代議制民主也并非始終具有可靠性。代表與選民之間的民主鏈條極有可能因為代表自身素質不夠、代表存在獨立利益、議會會期短暫、立法任務緊張等各種主客觀因素出現斷裂,并最終制定出不正義的法律。除此之外,根據社會契約理論,國家并非憑空產生,而是人民通過契約所締結的結果,其中,人民作為主權者,享有國家最高的權力,行使包括制憲權在內的主權性權力。立法權則是制憲權所派生的下階權力,即人民通過在憲法中設定立法權,委托特定機關從事國家立法活動。立法權是依據憲法而產生的權力,受憲法的約束,唯有國民擁有制憲權。【參見[法]西耶斯:《論特權第三等級是什么》,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56-64頁。】畢竟,法律很難完全反映每一個人的意志,而只能尋求其中的最大公約數。法治普遍性和權威性等品質在帶來積極價值的同時,本身也導致一定的消極代價,即人民對法律的絕對服從,對不正義的法律予以適當容忍。申言之,這種以“多數決”為特征的民主程序更多在于維護多數人的利益,并不能夠保障全體選民利益的實現,在這一過程中極有可能忽視甚至是犧牲少數選民的利益,此外,即便選民民意得以有效傳輸,也不能證明所立之法一定是良法。
因此,通過在《民法典》中引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可以有效監督議會立法權的行使,防止《民法典》對公民基本權利造成不必要的侵犯。
(三)“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客觀法”基礎
在《民法典》中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不僅具備形式正當性,而且還具備實質正當性,且這種正當性更多來源于基本權利保障。眾所周知,《憲法》第33條第3款的“尊重”和“保障”與主觀法和客觀法相互呼應,【《憲法》第33條第3款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輔之以《憲法》第二章所規定的具體基本權利,共同從根本法層面構筑了中國的基本權利保障體系,形成了一套基本權利的框架秩序。
事實上,在魏瑪憲法時期,憲法中的基本權利條款并無太大威懾力,對于國家機關而言,其更多被視為一種價值裁量空間,只具備一定程度上的目標導向作用。對于普通公民而言,其更不能以此為依據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只能被動地等待立法予以形成。但在二戰之后,這種空洞的基本權利條款逐漸開始演變為直接約束國家機關的“客觀規范”或者“客觀法”。所謂客觀法,是指憲法中的基本權利規范本身作為國家的框架秩序,包括立法者在內的國家機關必須積極遵從,即一切國家公權力都必須時刻接受這一“框架秩序”的約束,并盡一切可能去推動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參見張翔:《基本權利的雙重性質》,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3期,第25-26頁。】照此意義,立法者所有的立法行為都被賦予了這一使命,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更是有義務去將憲法中的權利規范加以具體化。因此,在《民法典》中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就可以被解釋為,在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始終將基本權利條款作為立法的考量因素,以推動基本權利的全面實現。立足于這一點,相對于憲法全方位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民法則僅僅是基本權利保障的一個側面,即是以保障財產權為核心的基本法。【參見趙萬一:《從民法與憲法關系的視角談我國民法典制訂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構》,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1期,第123-125頁。】申言之,面對憲法這一權利保障的框架秩序,民法僅僅面向私主體之間的權利保障,也僅僅是憲法民事權利的具體化,因此,在《民法典》中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不僅能夠彌補憲法私法化的不足,還能為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奠定基礎,使民事權利得到更為充分的訴訟法保障。【參見秦前紅:《民法典編纂中的憲法學難題》,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第11-26頁。】
此外,客觀法秩序還意味著國家面對基本權利,不僅需要消極不作為,同時還需要積極作為,在平等私主體之間承擔起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即保護公民免受平等“第三人”的侵害。畢竟,國家壟斷了公民私力救濟的權力,因此,當公民遭受平等第三方的侵害時,立法者當然負有義務來改善這一現狀。申言之,隨著公民社會的培育和發展,國家早已不是侵犯公民個人基本權利的唯一主體,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有可能遭受來自國家以外的第三人的侵害,【參見王進文:《基本權國家保護義務的疏釋與展開——理論溯源、規范實踐與本土化建構》,載《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4期,第107頁。】來自企業、行業等由私主體造成的威脅和災難較公權力更為嚴重地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權利,成為亟待解決的基本權利保障難題。【參見龔向和、劉耀輝:《論國家對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載《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5期,第59頁。】期間,以科技變革為主的社會變化對傳統權利格局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尤其是在互聯網、大數據、生物科技等現代技術的影響下,相關私主體之間的利益侵害現象也愈發頻繁。【參見侯學賓、鄭智航:《新興權利研究的理論提升與未來關注》,載《求是學刊》2018年第3期,第97-98頁。】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顯然有義務采取積極有效的保護措施。【參見陳征:《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功能》,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頁。】截至目前,無論是德國還是中國,都已經意識到了國家保護義務的重要性。基本權利保護義務在德國誕生于1974年德國聯邦法院
“第一次墮胎案”判決,此后,經歷了比較有代表性的“施萊爾綁架案”“航空噪聲污染案”“第二次墮胎案”以及“航空安全法案”而不斷豐富,【參見王進文:《基本權國家保護義務的疏釋與展開——理論溯源、規范實踐與本土化建構》,載《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4期,第107-109頁。】業已形成了一套與基本權利防御權相并列的理論體系。在中國,相關學者也紛紛發文對國家保護義務的基礎理論進行了闡釋。如陳征主要介紹了國家保護義務的基本框架,并初步預測了國家保護義務功能在中國的制度化;王鍇圍繞《憲法》第49條,系統論述了國家對母親和兒童的保護義務;龔向和則主要闡明了國家保護義務的層次以及國家保護義務與第三人效力的關系。【參見陳征:《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功能》,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1期,第53-60頁;龔向和、劉耀輝:《論國家對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載《政治與法律》2009年第5期,第62-65頁;王鍇:《婚姻、家庭的憲法保障——以我國憲法第49條為中心》,載《法學評論》2013年第2期,第8-9頁。】不同于防御權功能的雙方關系架構,在國家保護義務理論之下,則往往需要將視角置于國家、私人受害者、私人侵害者三方關系架構之下進行考量。此時,國家需要從基本權之敵轉變為基本權的保護者,對基本權主體之間互相沖突的利益進行調和:一方面,國家與受害者之間形成保護義務鏈條。國家通過完善立法,為受害者提供完善的權利保障框架,以此形成公法上的權利給付體系。另一方面,國家和加害者之間形成防御權鏈條。國家在對加害者行為進行規范和限制的同時,還需要恪守防御權的保障框架,以此避免形成對加害者自由權的不當限制。此時,基于上述國家保護義務理論,《民法典》作為私權領域的基本法,當然有必要在憲法指示下通過完善相關立法,進而改善不對等的私權結構,“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也就順理成章了。
三、“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積極規范意涵
民法和憲法縱然存在一定區別,但二者都蘊含著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價值指向,此時,面對憲法私法化的制度障礙,如何讓部門法承擔一定憲法功能,【參見謝鴻飛:《中國民法典的憲法功能——超越憲法施行法與民法帝國主義》,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年第6期,第40-47頁。】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一抽象的原則轉為在規范層面和技術層面可供操作的規則,就尤為重要。這不僅有利于建構民法與憲法的動態關系,還能夠突破憲法和民法各自的局限性,通過協同配合,最大程度上推動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畢竟,不同部門法之間的分殊僅是表面現象,但在價值層面卻是殊途同歸,即都是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此時,“根據憲法,制定民法”本身具有一定的積極指向,要求《民法典》積極落實制度性保障功能、組織性保障功能以及國家保護義務功能。
(一)《民法典》積極落實制度性保障功能
基本權利保障是一個系統工程,特定基本權利能否實現,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往往都需要依賴一定的制度。基本權利的客觀法功能要求各個權力機關理應積極建構各項制度,從而為基本權利奠定制度依托。期間,立法者作為制度形成的前端,往往負有重要使命,這意味著立法者面對憲法中規定的基本權利,必須積極通過立法建構各項基本權利制度,從而促使基本權利的內涵得以全面實現。在這一意義上,“根據憲法”首先意味著立法者積極完善立法,建構各項基本權利的保障制度。考慮到憲法與民法的關系,這些制度至少包括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財產權保障制度、勞動保障制度、個人信息保障制度等。在此,為了系統論證“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制度性保障功能,不妨以婚姻制度、財產權制度以及個人信息保障制度為例加以闡釋。
首先,就婚姻制度而言,《憲法》第49條的“婚姻家庭”條款與《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編存在密切關聯,【《憲法》第49條規定:“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父母有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后者通過在《民法典》中對憲法條款加以制度化,能夠和《憲法》形成完美呼應。此時,包括結婚自由制度、離婚自由制度、離婚冷靜期制度、繼承制度等,就構成了整個婚姻家庭條款的制度性保障。正如在施密特看來,制度性保障有著天然被國家立法限制的屬性,這些制度僅僅是在國家之內存在,是一種受到法律承認的制度,而非原則上不受限制的自由權。【參見[德]卡爾·施密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頁。】照此意義上,婚姻自由當然構成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部分,因此其并非可以主張之主觀權利,而是國家應予以保障的制度安排。“沒有法律,婚姻自由將無從談起。”【參見王鍇:《婚姻、家庭的憲法保障——以我國憲法第49條為中心》,載《法學評論》2013年第2期,第12-13頁。】顯然,《民法典》通過將憲法條款加以制度化,有效保障了婚姻制度的核心內容。
其次,就財產權保障制度而言,現行《憲法》明確將財產權納入“總綱”,并在第13條就財產權進行了系統規定,【《憲法》第13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這表明私有財產權保障業已成為一個憲法議題。但憲法財產權條款畢竟屬于憲法統領性規范,《民法典》有關其規范結構、保障范圍以及判斷標準的認知,在某種意義上直接影響了關于財產權的定性與保障。畢竟,立足于《憲法》第13條第1款“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只要公民財產符合“合法性”要件,就自然屬于憲法財產權的范疇,并受到憲法的積極保障。但“合法”一詞的外延極其廣泛,如果缺乏良好民法物權制度的“制度性保障”,憲法財產權規定就很容易陷入空中樓閣般的尷尬境地。基于此,《民法典》對財產權保障制度進行了系統規定,將抽象的憲法財產權條款通過代理制度、合同制度、侵權制度、繼承制度、產權制度、物權法制度等進行多個角度的細化,不僅如此,還緊緊追尋大數據時代的特質,在《民法典》第127條中設定了有關數據財產和虛擬財產的保障制度。【《民法典》第127條規定:“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尤其是將虛擬財產納入財產權的范圍之中,不僅增加了物的種類,促使財產權形態由有體化過渡為無體化,而且這種物質形態上的拓展,能在很大程度上適應社會變遷對現有財產權制度的沖擊。更重要的是,承認虛擬財產的價值,還可以為今后財產客體的變遷提供思路,即隨著科技和經濟的不斷發展,不僅是網絡虛擬財產,諸如其他形式的財產,如果具備憲法價值,同樣應該被納入憲法財產權的范疇之中。
最后,就個人信息保障制度而言,《憲法》在第38條和第40條分別就人格尊嚴和通信自由進行了規定。【《憲法》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憲法》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但權利的外延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的發展導致利益關系發生變化,在既有權利無法滿足利益訴求時,便自然產生了新的權利需求和權利主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數字經濟的高度繁榮,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據資源在國家生產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發重要。以科技變革為主的社會變化對公民個人信息保障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尤其是在互聯網、大數據、生物科技等現代技術的影響下,數據權需求隨之產生,【參見侯學賓、鄭智航:《新興權利研究的理論提升與未來關注》,載《求是學刊》2018年第3期,第91頁。】相關私主體之間的利益侵害現象也愈發頻繁,這些個人信息保障需求勢必會反映到立法層面中去。普通個人在享受大數據時代的紅利之時,也時常伴隨著個人信息和數據的公開與權利的讓渡。而互聯網企業作為數據資源的集散地,相對于普通公民而言,其在數據處理和使用方面往往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囿于上述憲法條款的抽象,如果缺乏相應的個人信息保護制度,那么公民的人格尊嚴和通信自由將始終無法落地。在這種情況下,《民法典》單獨設定一章“隱私權與個人信息保護”,并就數據信息的收集、處理、儲存、分析乃至交易進行系統規定,通過對信息交易制度、處理制度、責任制度的建構,較好地厘清了數據所有者與數據使用者的關系,使公民的個人信息保障具備了制度性依托,這也是制度性保障功能的鮮明體現。
總之,憲法和民法在基本權利保障領域殊途同歸,在憲法確立基本權利保障的事項和目標之后,基本權利的客觀法秩序要求立法者設定專門的基本權利保障制度,從而為特定基本權利的實現提供制度依托。【參見[德]卡爾·施密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頁。】
(二)《民法典》積極落實組織保障功能
除了制度性保障之外,“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同時意味著《民法典》必須為相關基本權利提供相應的組織與程序保障,這也是客觀法秩序下的另一重要功能。從歷史變遷角度來看,既然基本權利約束包括立法者在內的國家公權力,那么積極的組織和程序保障就構成了基本權利客觀法功能下課予立法者積極形成制度的義務,同樣是為追求基本權利本身的達成。【有關積極/消極的制度性保障這一說法在中國主要是由歐愛民引入,此外,許育典也認為制度性保障存在消極與積極之分,消極的制度性保障基本就是上文中施密特所說的制度核心不得侵犯,而積極的制度性保障是課予立法者積極形成制度的義務。參見歐愛民:《德國憲法制度性保障的二元結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載《法學評論》2008年第2期,第117-124頁;許育典:《憲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16-119頁。】
就組織性保障而言,在《民法典》提供制度性保障之后,還必須依賴特定的主體用以執行或者監督,如此才能讓制度性保障功能充分落地。事實上,現有《民法典》的很多規定都體現了組織性保障的功能。例如,就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權利保障而言,《民法典》考慮到這部分人智識不夠成熟,特別規定包括婦女聯合會、殘疾人聯合會、民政部門等在內的組織,保障其作為民事主體的資格。【《民法典》第24條規定:“……被人民法院認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經本人、利害關系人或者有關組織申請,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其智力、精神健康恢復的
狀況,認定該成年人恢復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本條規定的有關組織包括: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學校、醫療機構、婦女聯合會、殘疾人聯合會、依法設立的老年人組織、民政部門等。”】此時,如果缺乏這些組織的幫助,在必要情況下就很難實現自身的權益保障。此外,為了保障業主的權利,《民法典》還專門設置了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這些組織,用以制定特定組織章程、選定物業服務機構、管理小區維修資金等事項,不僅如此,為了強化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的權威,還賦予了其決定對于業主的法律約束力。再比如,為了保障特定公民的生命權和健康權,《民法典》規定,進行臨床試驗理應經過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和同意,從而有效改善公民與醫療機構的不對等地位。【《民法典》第1008條規定:“為研制新藥、醫療器械或者發展新的預防和治療方法,需要進行臨床試驗的,應當依法經相關主管部門批準并經倫理委員會審查同意,向受試者或者受試者的監護人告知試驗目的、用途和可能產生的風險等詳細情況,并經其書面同意。”】
(三)《民法典》積極落實基本權利國家保護義務
誠如上文所言,不同于傳統視閾下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簡單劃分,在大數據時代下,市民社會并非始終以對等私主體的形式呈現,其內部固有的社會權力結構已然發生變化,一些以企業和行業為代表的準權力機構開始愈發龐大起來,這些準權力機構的生成邏輯雖然不同于國家機關,但卻能產生出類似于國家機關的權力統治模式,時刻影響著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
此時,基本權利國家保護義務作為客觀價值秩序下的一種具體功能,不同于廣義上的組織性保障、制度性保障。國家保護義務由于僅僅面向來自私主體的侵害,因此保護義務首要約束立法機關,在內容的設定上也更多以立法保護為主,行政和司法保護為輔。畢竟,健全的立法體系是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的前提所在,立法者在前端審慎平衡不同權利主體的基本權利沖突,為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設定一個權利保障的基本框架,可以有效約束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以及司法機關的法律解釋權。此前,學界中張翔列舉了兩種典型的國家立法保護義務,即刑法上的保護和警察法上的保護,前者用以針對不法私主體的犯罪行為,后者則主要針對不法私主體的緊迫侵害行為,【參見張翔:《基本權利的雙重性質》,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3期,第28頁。】但隨著自由法治國向社會法治國過渡,當前僅僅通過刑法和警察法的立法保護已經遠遠不夠,唯有在憲法的指引下,建立起以民法、刑法、行政法、社會法以及基本權利專門法在內的法律體系,才能更好地保護基本權利主體免受私主體的侵害。需要注意的是,立法者的立法保護義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動態且持續的過程,申言之,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旦法律的適用環境發生了變化,立法者必須進行必要的修改和補充,必要時甚至要制定新的規范,否則同樣違反了保護義務。【參見陳征:《基本權利的國家保護義務功能》,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1期,第55頁。】
此外,《民法典》“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不僅是一種價值上的宣誓,本身還意味著立法者在履行保護義務的過程中應嚴格遵循一套明晰的、類似于比例原則的標準用于自我評估。國內外學術界雖然意識到了國家保護義務的重要性,但對于評估立法者履行保護義務是否達到憲法要求的研究則略顯不足。基于此,“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主張立法者履行保護義務需要遵循禁止保護不足原則,探尋該原則的正當性基礎并系統建構該原則的適用標準,以期為立法者更好地履行保護義務提供憲法指引。禁止保護不足原則,是指在合憲性審查過程中,判斷國家機關是否積極作為,是否達到了憲法所要求的基本權利保障標準。根據禁止保護不足原則,無論基于社會現實需求還是中國憲法給立法者提出的要求,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都應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適用禁止保護不足原則來判斷立法保護是否達到了憲法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不僅有助于推動合憲性審查理論的進一步完善,也有利于更好地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從某種意義上講,《民法典》在適用禁止保護不足原則時,既應當強調憲法對立法的指引,又應當認同憲法秩序要通過立法形成。將禁止保護不足原則作為憲法給立法者提出的最低保護要求,限于對被保護人期待可能性的審查,既能夠確保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功能發揮應有作用,又能充分尊重民主立法。
四、“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消極規范意涵
事實證明,法治蘊含的形式主義價值雖然有助于立法權的合法性,但卻并不能夠保障《民法典》本身合乎憲法秩序。與之相應,法律至上并不等同于《民法典》的合憲性,而只是實現這一價值秩序的重要手段,實質法治主張《民法典》要從根本上符合中國憲法框架秩序。基于此,“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不僅是合乎法律以及對法律的機械適用,立法者以及《民法典》本身也必須合乎憲法。畢竟,前述立法權的統一和法律體系的內部統一只是法制統一的理想狀態,一旦出現抵觸和違反,相應的糾偏機制就必須隨時出場。“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要求《民法典》在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應嚴格恪守憲法框架秩序的消極邊界,始終遵循合憲性解釋方法以及合憲性審查標準。
(一)《民法典》應嚴格遵循合憲性解釋方法
雖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是立法層面的規范要求,但是“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意義不僅限于立法過程之中。由于立法者理性的局限性和社會發展帶來的新問題,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漏洞,需要通過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法官的個案裁判來及時填補法律漏洞。這一過程不僅是法律適用的過程,更是立法過程的延續。
在《民法典》中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可以為法律漏洞填補中的合憲性解釋方法的運用提供法律依據。【參見王利明:《何謂根據憲法制定民法?》,載《法治現代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74-75頁。】憲法對于民法的解釋和適用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在采取司法審查制度的國家,法官甚至可以直接援引憲法來進行案件的審理,但就中國而言,則可以通過合憲性解釋來強化憲法在《民法典》中的適用。【中國司法實踐也已經逐步采用合憲性解釋的方法。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印發了《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書制作規范》,在其“裁判依據”部分,盡管依然規定裁判文書不得引用憲法,但也明確規定:“但其體現的原則和精神可以在說理部分予以闡述”,這在相當程度上應該被看作是對《民法典》合憲性解釋方法的認可。】合憲性解釋本就脫胎于基本權利的審查,健全的解釋規則得以確保《民法典》規范更加符合憲法,避免因為動輒出現違憲嫌疑而降低憲法的權威和尊嚴。
合憲性解釋作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本身是法律解釋而非憲法解釋,解釋對象也是法律而并非憲法。根據不同的適用目的,可被區分為解釋規則、沖突規則和保全規則三個層次。【其中,在解釋規則層面,合憲性解釋指憲法相關規定應在法律解釋時直接發生一定的影響;在沖突規則層面,指在數種可能的法律解釋中應優先選擇與憲法內容相符者;在保全規則層面,指當法律有違憲疑慮而有數種解釋可能性時,應選擇不違憲的解釋。參見蘇永欽:《合憲性控制的理論與實際》,臺灣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84頁;轉引自李海平:《合憲性解釋的功能》,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第44頁。】由于在不同層次適用合憲性解釋意在實現的目的有所差異,評價法律解釋是否具有合憲性的標準也不盡相同。事實上,《民法典》的法律解釋結論是否符合憲法的判斷標準與憲法所保護的價值息息相關,中國憲法的平等權條款、財產權保障條款、人格尊嚴條款等都可以折射到《民法典》的適用過程中,促使對《民法典》的理解和適用最符合憲法的精神指向。畢竟,對于權利規范而言,基本權利是憲法所期待實現的具體價值,符合憲法的法律解釋結論被具體化為符合基本權利的解釋結論,換言之,合憲性解釋就是合基本權利的解釋。
當解釋者適用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等解釋方法得出不同的法律解釋結論后,合憲性解釋要求解釋者在多個解釋結論中篩選出符合憲法的解釋結論,解釋者通常需要采取選擇或排除的方式確定《民法典》中法律文本的具體含義。【“這就是說,如果某個《民法典》解釋結論符合憲法,就應當選擇其作為解釋結論;如果所作的法律解釋違反了憲法,就應當予以排除。”參見王利明:《法學方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57頁。】申言之,解釋者需要對各法律解釋結論的合憲性逐一作出判斷,才能最終篩選出符合憲法的解釋結論,沖突規則層面的合憲性解釋有一定的合憲性審查意味。【參見李海平:《合憲性解釋的功能》,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2期,第51頁。】但需要注意的是,合憲性解釋并不是對《民法典》是否符合憲法的判斷,而是對《民法典》解釋是否符合憲法的判斷。合憲性審查的對象是解釋者根據傳統法律解釋方法對法律文本所作出的各法律解釋結論。解釋者對《民法典》權利規范的合憲性解釋涉及對公民法律層面權利限制程度的合憲性審查,故在對權利規范的合憲性解釋中向下融入整套法規范體系的價值秩序是憲法層面所設定的基本權利。與之相應,合憲性解釋意在規范解釋者的審查行為,避免公民基本權利受到違憲法律解釋結論的侵犯。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合憲性解釋并非完全杜絕了《民法典》的解釋和適用空間,尤其是對于立法者而言,憲法作為一種框架秩序而存在,立法者在這一框架內享有較大活動空間以及自主裁量權,合憲性審查主體在一定程度上也應當對其價值選擇和判斷予以充分的尊重。【參見陳征:《論比例原則對立法權的約束及其界限》,載《中國法學》2020年第3期,第151-152頁。】這就意味著當憲法層面的基本權利秩序被立法者合憲地具體化為法律秩序時,合憲性解釋主體應當遵守這一秩序,尊重《民法典》的規范基礎和價值意涵,進而選擇不超出立法者意志的解釋結論。
(二)《民法典》應嚴格恪守合憲性審查標準
“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本身具備授權與限權的雙重屬性,其在宣誓《民法典》合法性與正當性,賦予其法律效力的同時,也意味著《民法典》必須恪守憲法的邊界。畢竟,從憲法教義學的視角出發,憲法作為一種框架秩序,在框架秩序之內,立法者享有自主的活動空間,但在框架秩序之外,則是立法者的禁足之地,否則就是對憲法權威和尊嚴的褻瀆。申言之,“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雖然設定了《民法典》的形成空間,但也從側面劃定了其《民法典》規定事項的界限,一旦跨越這一界限,這就意味著其違反了憲法的不抵觸原則,侵蝕了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統一性。那么,《民法典》中“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要配套何種標準來進行合憲性審查呢?筆者認為至少應該包括主體合憲性標準、內容合憲性標準、方式合憲性標準以及價值合憲性標準。
首先,就主體合憲性標準而言,“基本法律”是《憲法》與《立法法》界定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民事立法權限的重要標準。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雖然共同作為立法權主體,但其民事立法權限卻存在迥然區別,根據《憲法》第62條第3項以及第67條第2項、第3項,【《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二)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發現“基本法律”是界定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民事立法權限的重要標準,不僅如此,這一法律術語背后還意味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民事立法權是存在邊界的。長期以來,我們更多將立法權局限于代議機關與政府之間進行討論,但代議機關不僅僅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存在,其內部往往有著不同的機構和職能劃分,在中國則總體上分為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但二者并非同一立法權主體,這集中表現為二者在立法代表性、立法權內容和立法程序上的重大差別,并由此決定二者民事立法權具有不同的憲法效果。對此,有必要轉換視角,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置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內部進行理解,即其不僅要求民法的各類構成要素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加以規定,還要求事關公民基本權利義務的民法基本構成要素必須且只能由全國人大制定民事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只能就非基本構成要素制定民事非基本法律,并在一定條件下享有對民事基本法律的部分修改權。
其次,就內容合憲性標準而言,立法權作為制憲權的延伸,其在內容上必須依照憲法設定的框架行使。事實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本身內含著對立法權的監督和防范。正如在孟德斯鳩看來,基于民主的立法權實際上更具擴張性,很容易僭越其他兩權的內容。【參見[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61頁。】
制憲者們尤為重視對國家立法權的防范,例如麥迪遜指出,在代議制的共和體制下,對行政長官的權力范圍和任期都有仔細的限制,反觀立法者則更有機會接近人民的錢袋,并通過其掌握的財政權迫使其他部門就范。有鑒于此,只有給予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主管人員以一定的手段來抵制立法部門的侵犯,才能更好地防范立法權。【參見[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91-294頁。】總體而言,分權制衡理論是消極權力觀的產物,對于國家權力的行使更多帶有防范和抵觸情緒。民事立法權作為立法權的基本形態,防止議會多數主義對少數公民基本權利的侵犯無疑至關重要。由此,“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意味著《民法典》在內容設定上需要遵循重要性法律保留理論,即以對基本權利的影響為標準,凡是對公民基本權利之實現有重要影響的立法事項,如國家任務之演變、國家權力結構的變化等都屬于憲法保留的范疇,理應由憲法進行調適,而不能放任《民法典》自由裁量。
再次,就方式合憲性標準而言,為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督促立法者積極履行立法義務,立法者的民主政治空間理應受到憲法的約束,即特定事項不僅在范圍上屬于立法者的保留空間,在方式上也必須由立法者制定法律,而不能隨意通過授權的形式制定行政法規。此前我們將法律保留理論完全視作立法者的民主政治空間,這并不利于從根本上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建構完善的國家民主法秩序,因為其忽視了法律保留理論對于立法者自身的約束,一旦立法者怠于立法,習慣性以授權的方式行使立法權,難免會架空對立法者的憲法委托,法律保留制度本身也就徒有虛表了。
最后,就價值合憲性標準而言,國家借助《民法典》實現“定分止爭”非是盲目狀態下的全方位回應,而必須跳出消耗與成果的比率關系,綜合考量立法權的功能邊界。這尤其適用于國家調控,即當國家試圖通過特定立法功能來完成國家任務時,必須綜合考量這一任務是否有必要,如果非完成不可,是否必須通過民事立法權這一形式,交由市場或者私人能否更好地完成國家任務。顯然,鑒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之時才能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故借助民事立法權僅僅是補充性和輔助性手段,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競爭機制始終是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最佳工具,它能使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社會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率。因此,為了不影響這種市場均衡,“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要求國家行使民事立法權時必須審慎考量,嚴格遵循立法中立性原則,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任務,以此避免因立法調控不當而改變有效率的經濟活動,進而對社會主義市場運行產生不良影響。
總之,通過在《民法典》中規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可以為合憲性審查制度提供直接有效的規范依據,即根據制憲權理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本身也要在憲法秩序內行使立法權,而不能以《民法典》形式外觀的合法性來豁免實質內容合憲性的要求,一旦其立法權行使偏離憲法設定的軌道,就必須適時啟動合憲性審查機制進行糾偏,【參見苗連營:《稅收法定視域中的地方稅收立法權》,載《中國法學》2016年第4期,第177頁。】以此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憲法權威,維護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統一性。
五、結語
在《民法典》編撰過程中,“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一表述始終存有爭議,并集中表現為民法獨立說、民憲平行說與憲法至上說三種觀點,但由于缺乏方法論的統一,這些認知或多或少存有不足。事實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在規范層面上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具備充分的形式正當性,且這一正當性不僅能夠從《憲法》《立法法》以及憲法性法律層面得到法制統一的證成,同時還能從基本權利客觀價值秩序層面得到積極回應。同時,相比于民法至上和憲法至上的地位之爭,筆者更傾向于立足于憲法教義學,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這一抽象的原則轉為在規范層面和技術層面可供操作的規則。畢竟,民法和憲法縱然存在一定區別,但二者都蘊含著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價值指向,此時,面對憲法私法化的制度障礙,讓部門法承擔一定憲法功能尤為重要。這不僅有利于建構民法與憲法的動態關系,還能夠突破憲法和民法各自的局限性,通過協同配合,最大程度上推動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畢竟,不同部門法之間的分殊僅是表面現象,但在價值層面上卻是殊途同歸,即都是為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在此基礎上,理應切實發揮“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效力,即一方面,在積極意義上,“根據憲法,制定民法”要求《民法典》積極落實制度性保障功能、組織性保障功能以及國家保護義務功能;另一方面,在消極意義上,“根據憲法,制定民法”要求《民法典》應始終恪守憲法框架秩序這一基本邊界,在解釋和適用過程中嚴格遵循合憲性解釋方法以及合憲性審查標準。總之,通過對“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進行憲法教義學的研究,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厘清憲法與民法的關系,同時還能切實發揮“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范指示作用,
今后理應拓寬研究樣本,繼續強化部門法憲法教義學的研究,唯其如此,才能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完善提供規范導向與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