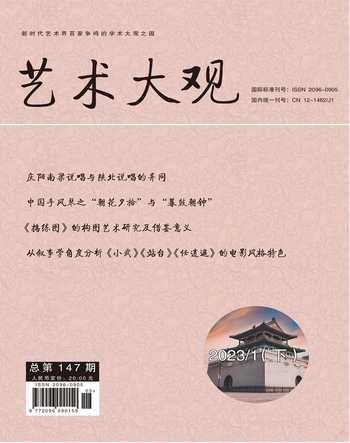慶陽南梁說唱與陜北說唱的異同
黃濤
摘 要:隨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發揚工作的迅速推進,社會各界對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與陜北說唱藝術的關注和研究與日俱增;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與陜北說唱藝術同為民間說唱藝術,具有許多共性和差異。基于此,本文著眼于多個視角,分析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與陜北說唱藝術的共性和差異,以期對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與陜北說唱藝術的傳承和發揚產生積極作用。
關鍵詞:慶陽南梁說唱;陜北說唱;共性;差異;多視野分析
中圖分類號:J6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03-00-03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延續歷史脈絡、樹立文化自信、弘揚和傳承民族精神、增強民族文化軟實力等方面具有關鍵價值。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極強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在此背景下,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與陜北說唱藝術備受關注。由此可見,針對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與陜北說唱藝術的共性和差異性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與陜北說唱藝術的共性分析
(一)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與百姓生活的關系方面具有共性
中國古人很早就意識到民風民俗在民間藝術形式起源、發展、傳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如孔子有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表現出其對音樂藝術與民風民俗關系的認知[1]。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與陜北說唱藝術同樣是民間說唱藝術,藝術表現的內容與百姓生活、市井文化密不可分;藝術表現者多是普通百姓、市井小眾;藝術欣賞和體驗者同樣多為市井群眾。因此,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與陜北說唱藝術同為起源于市井百姓的生活,并同在百姓生活中獲得發展、傳播和創新改進。
(二)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對百姓生活的影響方面具有共性
1.救贖精神的藝術形式
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同樣發源于黃土高原地區,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在作物的生長、百姓的交通、環境的改善等諸多方面產生限制作用。自然環境惡劣難耐以及出行交通不便為當地百姓的生活造成消極影響,有限的物質生活導致當地百姓很難尋求所謂高質量、高雅的精神享受。在這種情況下,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這樣的民間說唱藝術形式成為適合當地百姓的娛樂方式。因為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形式較為簡單,且對文化程度要求不高,因此,其操作實施較為方便,同時受眾的接受度較高甚至可能產生情感的共鳴。當地百姓受制于困苦的自然環境,但同時長期面朝黃土背朝天,勤于耕種的生活狀態塑造出不甘示弱、吃苦耐勞、踏實肯干、樸實無華的美好品格,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中蘊含著當地百姓的美好品質,為當地百姓困頓的生活提供精神慰藉。此外,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中也蘊藏著勸世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以說唱的方式展現,通過講述生活中的人和事,勸導人民勤勞、本分、善良、友愛,這些勸世的人文精神同時也體現出勞動群眾在生活和勞動中所獲得的人生哲理和處世之道。說唱藝人以加工渲染的方式將民眾生活中的哲理以生動形象的方式呈現,潛移默化中強調做人做事的美好品質,使民眾在艱難困頓的生活境況面前,積極勇敢地選擇勤勞做事,而非自暴自棄或怨天尤人。基于以上分析可見,慶陽南梁說唱和陜北說唱同樣通過說唱藝術塑造當地民眾勤勞、善良的美好品質,是為當地民眾提供深層次的精神救贖的藝術表達形式。
2.寄托情感的載體
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具有受眾廣泛的鮮明特點,這種集體形式的民間藝術表現形式能夠將一定的情感寄托在唱詞內容或者說唱表演中,實現通過說唱演繹和傳遞情感的作用,同時能夠在聽眾群體中得到共鳴,這種情感共鳴為說唱人和聽眾同時提供情感宣泄和寄托的機會。
(三)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樂器使用方面具有共性
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因其廣泛流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限、交通不便等因素的限制,表演時所用樂器較為簡單,如三弦、二胡、笛子、四葉瓦與麻喳喳等。三弦屬于彈撥樂器,是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表演中較為主要的樂器;二胡屬拉弦樂器,是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表演中主要的伴奏樂器;笛子同樣也是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表演中較為主要的伴奏樂器,一般出現在較為正式的舞臺演出中;四葉瓦多用竹板制成,屬于民眾自行創造的打擊樂器,按照曲譜內容的需要即興演奏時使用;麻喳喳多緊隨三弦出現,當停止彈奏三弦時,麻喳喳也立刻無聲。陜北說唱藝術同樣也是結合三弦、琵琶、梆子、二胡、笛子等多種樂器的綜合性民間說唱藝術。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同是在自身的創新演變過程中結合多種樂器進行表演,而且兩者所使用的樂器具有較大共性。
(四)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民風民俗方面具有共性
民風民俗是指在一定地區由廣大民眾群體創造、享用、傳承和發揚的生活文化。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同是黃土高原地區孕育產生,并同為當地民眾喜愛,在當地廣為流傳,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與當地民風民俗緊密結合并且相互影響。例如,“請干大”這種地區獨特的民風民俗形式,干大在古時多指與父親結拜的兄弟,演變至今則多指在進行請干大后給孩子掛鎖,保佑孩子平安健康的人。請干大以兩種方式為多見,一種是家長咨詢他人后,得知干大的姓氏。被請做干大的人通常也是同意祈福保佑孩子的平安健康,并于正月十五日到孩子家中向孩子表達平安健康的祝愿。另一種也被稱為撞干大,即家長在正月十五日抱著孩子朝著已確定的吉祥幸福的方向走去,碰到的第一個路人就是干大,干大同樣要向孩子表達平安健康的祝愿。在為孩子請干大時,父母除了擺酒席設宴招待眾人外,為了保佑孩子的平安健康或者助興,通常也會宴請說唱班子前來表演。由此可見,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已經與當地民眾布置紅白喜事、招福納祥等事情密不可分。又如當地的廟會,廟因人們寄托精神、宣泄情感以及祈求生活圓滿順利誕生,廟會也成為人們聚會、祈求美好生活的一種形式。現如今,因為人們寄托精神、宣泄情感的需求,廟會依然存在并與商業集市以及文化娛樂等行業結合成為一種綜合性的民風民俗活動,其作用在節日時展現得較為明顯。而廟會的產生和延續為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提供了發展機會,廟會在商業、娛樂、祈福等多方面的綜合性功能吸引了大量的民眾集中,為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表演提供了大量的聽眾,極大地促進了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受眾面的拓展。綜上所述,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發展過程中與民風民俗緊密結合并相互影響。
(五)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語音美方面具有共性
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語音方面同樣通過押韻、疊音等具體方式,使語句語音朗朗上口、節奏鮮明;形式多樣、富于變化;音律和諧、優美動聽。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獨特的語音美能夠提升其趣味性,增強對聽眾的吸引力;此外,還能夠有效拓展其影響和傳播的范圍。
二、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的差異分析
(一)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歷史起源方面具有差異
陜北說唱藝術大師韓起祥先生曾講述過其師傅親口所說的“三黃”傳說,這個傳說產生于“三皇”歷史時期,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陜北說唱藝術的悠久歷史。但這一傳說缺乏真實確切的歷史資料佐證,因此僅是為陜北說唱藝術的歷史起源提供一些參考。與陜北說唱相比,“慶陽南梁說唱”這一名稱的誕生就晚了許多。在當地有關文化部門收集和整理慶陽南梁說唱藝術有關資料時才發現,哪怕是當地百姓也只是知道當地有一種獨特的說唱形式,卻不清楚其具體名稱。后因其起源于南梁民間,是獨屬于南梁的民間藝術瑰寶,將其命名為“南梁說唱”[2]。此外,一方面由于慶陽南梁與陜北地理位置較近,兩地百姓之間的交流來往較為頻繁;另一方面,因為說唱藝術通過口授的方式傳播。因此,大多數人認為陜北說唱藝術為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塑造了雛形。綜上所述,慶陽南梁說唱藝術的歷史起源晚于陜北說唱藝術,同時受其影響較大。
(二)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影響區域方面具有差異
從說唱藝術的流行區域角度分析,慶陽南梁說唱藝術更多的只通行于慶陽市局部縣鄉;而陜北說唱藝術則是在陜西北部延安、榆林等地較為流傳的一種民間說唱藝術[3]。
(三)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曲調特征方面具有差異
慶陽南梁說唱藝術雖起源晚于陜北說唱藝術,且受其影響較大,但其在慶陽地區的流傳過程中,結合了當地的民俗民風,再加上說唱人的改造創新,慶陽南梁說唱藝術的曲調特征已與陜北說唱藝術產生較大差異。陜北說唱藝術具有九腔十八調的曲調特征,關于這一特征的形成大體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結合了三黃的民間傳說,認為三黃是最早開創陜北說唱藝術的藝人,后來他們將陜北說唱藝術的技法要點傳授給十八個徒弟,這十八位徒弟結合各自的特點又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風格,十八種曲調由此產生,因此陜北說唱藝術具有九腔十八調的曲調特征。第二種說法來源于楊景震先生的《韓起祥說書的故事》,說道:“九腔”是指胡胡腔、哈哈腔、梆子腔、影腔、咳咳腔、十三咳腔、迷子腔、二窩子腔、佛腔;“十八調”是指下盤棋、媽媽糊涂、茉莉花、小放牛、鋪地錦、叫面更、寡婦上墳、鴛鴦扣、姑娘、跑關東、打牙牌、莎金扇、茨山、放風箏、游寺、思凡、光棍哭妻、小上墳[4]。而第三種說法則認為九腔十八調僅僅是民間傳說而已,不具有歷史料佐證和事實依據。而慶陽南梁說唱藝術的曲調特征表現在其具有基本的連接方式,即:起板—正文—嘛簧—結尾。所謂起板,即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表演開始前,說唱藝人做好準備,提前演奏一段內容,作為說唱表演正式開始之前的起板,其作用就是吸引觀眾的興趣和關注點,使他們能夠全身心投入慶陽南梁說唱藝術的欣賞中;另外,能夠為說唱藝人提供緩沖時間,為正式的表演做好準備。正文是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表演的核心部分。在慶陽南梁說唱藝術中,說唱藝人往往將表現人內心高興、欣喜之情的,且曲調旋律上多為跳躍性的內容稱為歡音平調;相反,苦音平調是指表現悲傷、痛苦的內容,且曲調旋律低沉平穩。嘛簧是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吸收隴東道情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既有一問一答式的嘛簧,也有群體性的嘛簧。一問一答式的嘛簧通常是由主唱者發問,其他人回答。慶陽南梁說唱藝術的這種一問一答式的嘛簧在送簧方面沒有固定的句數限制,形式較為自由,且多出現在民間演出;群體性的嘛簧,是指多人合唱同一首民歌,選擇哪一首民歌往往根據唱詞的內容確定,多出現在舞臺表演中。群體性的嘛簧能夠輕松地將聽眾的關注點拉回到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表演中,同時也能夠將旋律轉換回原來的旋律上,維持表演旋律的穩定性。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表演的結尾表達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說唱藝人用簡短的語言干凈利索地收尾,二是以男女對唱民歌的形式結束整個說唱表演。兩種方式都是以一種減慢的拖腔,向聽眾表達說唱表演的結束[5]。結合以上分析可得,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曲調特征上各具特色。
(四)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唱詞特征方面具有差異
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在演變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與陜北說唱藝術略有差距的唱詞特征。表現為:慶陽南梁說唱藝術的唱詞多為七字句、十字句,八字句和九字句相對較少,同時多表現出對稱的上下句。慶陽南梁說唱藝術的唱詞多為七字句,具有押韻且朗朗上口的特點,另外,一些說唱藝人可能根據自己的說唱表演經驗和習慣在七字句中加入個別襯詞,但這本質上未改變七字句的形式,仍可歸類于七字句。七字句通常按照“二二三”的規律進行句子劃分。八字句相比于七字句,句子劃分方面較為靈活,通常是說唱藝人根據個人的表演經驗和習慣以及唱詞的內容構成進行劃分。十字句也是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出現較多的唱詞特點,其句子劃分同樣較為靈活自由,可根據唱詞內容進行確定[6]。此外,慶陽南梁說唱藝術表演過程中,并非以一種唱詞特點貫穿全程,通常是多種句式交叉使用。這種句式使用方式一方面能夠適應說唱藝術表演中的唱詞需要,減輕說唱藝人的表演壓力;另一方面,能夠增強說唱藝術表演的靈活性,更能吸引聽眾的興趣和關注[7]。相比之下,陜北說唱藝術的唱詞多為七言和十言,既能使音節和句式整齊對仗,又能增強唱詞的韻律感和節奏感,產生獨特的音樂美[8],但其句式形式較為單一。基于以上分析可見,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在傳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陜北說唱藝術略有差異的唱詞特點。
三、結束語
本文從多個視角對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的共性和差異性進行分析和闡述。綜合全文,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在與百姓生活的關系、對百姓生活的影響、樂器使用、民風民俗、語音美方面具有共性[9];在歷史起源、影響區域、曲調特征、唱詞特征方面具有差異。通過本文分析,為慶陽南梁說唱藝術和陜北說唱藝術的對比研究和傳承保護工作提供有效材料依據。
參考文獻:
[1]李永娟.《格薩爾》說唱傳統與陜北說書傳統的比較研究[J].文化學刊,2022(07):59-62.
[2]王茜.南梁說唱調查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2012.
[3].陜北說書[J].音樂天地,2022(03):64.
[4]汪東鋒,梁蕓霞.試論陜北說書的語言藝術[J].榆林學院學報,2020,30(01):25-29.
[5]賈勇宏,馬金龍.淺談陜北說書的語言特征[J].黃河之聲,2019(22):16.
[6]宋亞萍.陜北說書的文化變遷研究[D].西安工業大學,2013.
[7]王志峰,朱斌.“后非遺”時代紀實影像的文化書寫與省思——以非遺題材紀錄片為中心[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2(12):63-71.
[8]馬金龍,賈勇宏.南梁說唱的音樂特點[J].北極光,2019(08):41-42.
[9]王茜.甘肅省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南梁說唱初探[J].甘肅科技縱橫,2011,40(01):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