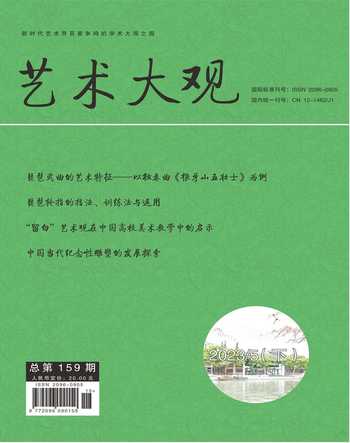母語音樂文化語境下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演唱研究
摘 要: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是中國古典文學與音樂有機結合的產物。而在如今重視民族文化和加強審美教育的當下,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仍因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在音樂中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同時,古典詩詞文化博大精深,廣泛凝結了中國漢語語言文化。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是集中體現母語音樂文化的一種表現體裁。其綜合了藝術性與文學性,在當下,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國際影響力的增加,如何傳承好以中華文化為母語的音樂文化成為重中之重。
關鍵詞: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母語音樂文化;《楓橋夜泊》
中圖分類號:J6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15-000-03
一、中國藝術歌曲與母語音樂文化的緊密聯系
藝術歌曲是一種興起于歐洲的聲樂藝術體裁,于19世紀初誕生,經過近幾個世紀的發展,在20世紀初傳入中國,藝術歌曲可以分為詞和曲,這兩者都成為藝術歌曲的組成,本文將從這兩個方面來簡述中國藝術歌曲與中華民族母語音樂文化之間的緊密關系。比如,從詞方面進行分析,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是中國藝術歌曲中,將傳統詩歌文化與藝術歌曲體裁融合最為人接受的。藝術歌曲本就以其鋼琴織體高度的藝術性,歌詞精致的文學性以及人聲的高品質而構成。藝術歌曲有其專屬的嚴謹性,不同于大眾歌曲的音樂氣質。而在中華民族母語文化中,中國古詩詞作品有著天然的優勢,如唐代詩人李白、杜甫,以及近代以來的詩人如艾青、徐志摩等。他們的詩歌創作兼具了文學性與藝術性,因此在藝術創作中,既繼承了中國傳統音樂的創作技法如“依聲填詞”,又吸收借鑒了西方作曲技法中時常使用的“因詞制樂”,這也造就了中國藝術歌曲獨特的音樂氣質。同時,由于這兩種不同的創作手法,我們需要同時了解中國傳統音樂中一些固定的調式含義及其特殊的情感表達,以及漢語中同一詞語在不同語境下的運用。[1]
“母語”即指一個人一出生后最早接觸到,并且掌握的一門語言,是代表一個人思維以及交流的工具。思考多是基于母語的語言邏輯思維為基礎的,而母語音樂則是指在學習過程中運用到的原生語言模式,其通過母語傳授,以中國傳統優秀音樂文化為內核。在我國的教育中普通話是重要的教學媒介,在進入學校后,普通話就成了學習過程中的“母語”,尤其是在聲樂的學習過程中。在這種意義上可以將母語音樂文化看作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保障中國優秀傳統音樂文化連綿不斷的紐帶。
長久以來,在美聲聲樂學習中,學生大量學習西方聲樂作品,由于美聲演唱是由西方傳入我國的,學習西方聲樂作品無可厚非,但在學習過程中甚至出現了“西方作品才正宗,中國作品不重要”的錯誤認知。在這個錯誤想法的影響下,有很多同學演唱中國作品時吐字有非常大的問題,導致聽眾在無字幕情況下完全不清楚演唱內容,這也突出體現了語言在演唱中的重要位置。除了語音以外,中文中一些特定詞語在不同情景中,有著不同的意義,在演唱時,尤其需要注意聯系全文理解該詞語的具體含義,這樣才能準確地把握歌曲具體表達的內涵。作為演唱者的我們只有不斷加強對民族傳統音樂文化的學習,才能增強傳承民族音樂文化的意識,了解傳統優秀文化的內涵。
二、以《楓橋夜泊》為例
(一)《楓橋夜泊》創作背景
《楓橋夜泊》這首作品是我國知名作曲家黎先生于20世紀80年代創作出的古詩類藝術歌曲,其中選取了唐代詩人的《春曉》《登鸛雀樓》以及《楓橋夜泊》。自2005年于北京公演后,《唐詩三首》在業內引起了熱烈反響,這其中《楓橋夜泊》尤為受到大家的廣泛追捧。[2]《楓橋夜泊》更是獲得了1988年全國高等藝術院校中國藝術歌曲創作比賽金獎。
(二)深度解析歌曲把握演唱情緒
黎先生創作的《楓橋夜泊》屬于近代較為常用的創作方法——“因詞制樂”,優美的詩詞配合著旋律使畫面具有層次,在旋律上鋼琴伴奏占據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不僅在烘托氛圍、奠定情感基調上作用明顯,更能夠與歌詞交相呼應。在樂曲的前奏中,前三個小節強度變化由pp到p再到mp由極弱到微弱,刻畫了一葉扁舟在江上緩緩駛來的畫面,第四小節一個mf力度的上行音階琶音,表現出船更近后波濤的漣漪。全曲中常出現以上行音階琶音指代江水的應用。同時低音區的柱式和弦也被應用于指代低沉的鐘聲。運用低音區的柱式和弦表示低沉的鐘聲上行音階輔以由弱到強的力度變化表示一葉輕舟由遠及近。這些聲音景觀可以使聽者即使在沒有歌詞的情況下,也能感受到詩中所描繪的畫面。原詩為“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3]通過寥寥28個字,移步易景,描繪出意境十足,又形象豐滿的泛舟江上圖。通過描寫遠與近、虛與實的對比將作者心中的孤寂生動地刻畫出來。只有中文才能做到如此精準凝練。這是多數讀者所感受到的意境之美,但這首詩,最成功的地方被隱藏在這生動的藝術形象之中,筆者通過查閱文獻,了解到早在唐代之前的樂府詩中“月”“烏啼”“霜”等意象就可以表達思親之情,在李白詩歌《靜夜思》中,“霜”與“月”的組合已經成為表達相思之情的經典意象。而為何《楓橋夜泊》中的“霜”“月”給人以陌生感,正是因為在這首詩中夾入“烏啼”,給人陌生感。而后半句的“江楓漁火對愁眠”,其中“愁眠”的主語也值得推敲,大多數讀者將“愁眠”的主語理解為作者張繼,這樣解釋自然可以做到行文通順,但仍然有兩個問題待解答,第一個問題是詩人“愁什么”,第二個問題是詩人選擇“江楓”和“漁火”作為寫景畫面入詩是否有著更深層的含義。根據記載作者當時所處位置屬于太湖流域,而“江”字在唐代可以代指長江,這里的“江楓”指的是作者眼前的楓樹是不大有可能的。而在《楚辭·招魂》中有詩句為“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自漢代起,“江楓”逐漸具有了女子盼夫歸來的意向,由此可以得出第二句的主語,并非作者張繼本人,而是望著悠悠漢江水在江邊徘徊等待丈夫歸來的張繼妻子。而“漁火”也大有妙用,漁火與詩人現狀姑蘇城外偏僻的環境與濕冷的天氣相對比,星星漁火也可以說是與妻子在一起時溫暖的回憶。詩句中的“夜半鐘聲”究竟有無,更一度是唐詩學案,據記載,唐代佛寺鳴鐘有特定章程,李咸詩中的“朝鐘暮鼓”指的是早晨寺廟先鳴鐘再擊鼓,夜幕降臨則是先擊鼓再鳴鐘,而且鳴鐘的鐘也有特殊的規格,是聲音沉悶扎實,但不能遠傳的梵鐘,而不是聲音清亮的執事鐘。“夜半”如無特殊情況也不會鳴鐘,只有在特定節日才會鳴鐘,而作者寫作的時期恰與蘇州一帶寺廟水陸法會日期相近,同時段再聯想到張繼的家鄉荊楚一帶,正在舉辦十分受重視的十月朝,更加反襯出詩人獨自在外無法參加家庭活動,不能向祖先獻祭的孤單與邊緣感。由此,通過詩歌原作以及該時代的寫作手法可以更明確解讀到詩歌的主要情感和深層含義,更能把握住所演唱歌曲的情感。在演唱時,除了準確把握原文,作者的情感更要依據作曲家在譜面上的記號依據自己的理解完成深度的二次創作,向聽眾傳達出具體的意境和內涵。[4]
(三)掌握漢字發音規則,高標準詮釋作品
漢語有其獨特的聲韻結構,在聲樂演唱過程中需要同時兼顧科學的發聲方法與規范的咬字發音,只有做到“依字行腔”,才能準確地傳遞出中國藝術歌曲的情韻和意境。以《楓橋夜泊》為例,筆者將結合自身演唱來分析“依字行腔”的具體應用,古詩詞具有押韻、平仄和句式等格律特點,這使得古詩詞本身就富有韻律、節奏和音樂感,《楓橋夜泊》是一首以“an”為韻腳的七言絕句,如第一句“天”字,第二句的“眠”字,第四句的“船”字。這個押韻也符合七言絕句的押韻特點。現代漢語把四聲調分為平仄兩類,其中平又可分為陰平和陽平,仄可分為陰仄陽仄,《楓橋夜泊》的節奏律動感也是來自詩詞的抑揚頓挫,其句式對仗工整。七言絕句是以七個字為一句,每一句的篇幅相當,句子的結構劃分也幾乎相同。這種作品十分具有韻律,朗讀起來朗朗上口,七言絕句的韻律一般為“上四下三”,其中“上四”又可分為“上二下二”,“下三”根據詞語可以具體劃分為“上一下二”或者“上二下一”,也就是說在前四個音節后可以有短暫停頓,結合到《楓橋夜泊》中詩句的節奏劃分應為: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節奏韻律只是廣闊漢語海洋中的滄海一粟,在演唱中更需要注意的是“依字行腔”,這就需要做到將漢語語音特色與演唱發聲方法相結合。順應漢語語音規則將演唱過程中的“情”“意”“聲”“韻”,充分表達做到字正腔圓。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在歌唱體系還未完善的情況下,就已經有了討論歌唱理論與歌唱語言的著作,在《樂記·詩乙》中提道:“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大致意思是,語言是歌唱的基礎,也是情感表達的延伸,從古人就已經意識到語言在歌唱中的重要基礎性地位了。在演唱《楓橋夜泊》這首歌曲時需要注意到其音域跨度較大,高音音域較多,如第一句中的“霜”字從f2起音,演唱時需強調字頭“sh”,將母音“a”飽滿地演唱出來,音色需要做到圓潤連貫,聲腔需保持穩定,然后快速歸韻到“ang”上。在該字的行腔過程中,容易因既要做到高位置又要快速吐出字頭而忽略行腔過程中的流暢,在歸韻過程中將“sh-u-ang”中“u”發音過長,從而影響了悠長緩慢的意境。“霜”字位于第一句的結尾,旋律在此處突高至#f2,情感也隨著旋律迸發,在演唱該字時氣息需沉下去,口腔要積極打開,從而使音色具有亮度和圓潤度。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楓橋夜泊》是一首一字多音較多,一字一音較少的歌曲。第一句強調的部分是“霜”字,在第二句中江“jiang”也有相似演唱方法,第二句中對“dui”語氣較重,在吐字時,應有力地咬住字頭,將口腔放松打開,最后在韻母“ui”上拖腔,在這個過程中,應當加強氣息支撐運用腰腹力量將氣勢表現出來。第三句“姑蘇城外寒山寺”中“姑蘇”二字一字一音,并且需要弱唱,這也要求演唱者身體打開放松,運用哼鳴的方法找到位置,輕盈地咬出字頭“g”,切忌咬字僵硬,腔體不打開。其中“蘇”是一個一字多音,音在“u”上延長,需將母音放入腔體內,放松下巴和嗓子,運用氣息將“u”音送出,這時起伏不要過大,運用平穩的氣息體現出寒夜深秋的肅寂。第四句“夜半鐘聲到客船”是全曲的高潮部分,演唱船“chuan”時應當在行腔過程中注意保持流暢,并且保證母音不變形,在演唱過程中聲音需要達到流動圓潤,只有張弛有度才能使作品更具有表現力。
在我國傳統聲樂理論著作中,將漢語的韻母按照相似的韻腹進行歸納整理出十三轍,每一個字都有屬于自身的行腔歸韻方式,掌握好十三轍可以幫助演唱者統一發音線條以及認識漢語發音過程的規律。在《楓橋夜泊》中以韻母“e”“ue”“ie”結尾的字屬于乜斜轍,如月“yue”在吐字時需要將“ue”看作一個整體不能分開行腔;以“e”“o”“uo”結尾的字屬于梭波轍,梭波轍又被稱為“歌波類”,如落“luo”,在演唱時要以舌尖著力輕咬字頭,在介母音“u”上快速略過,停留在主要發聲韻母“o”上;以韻母“u”結尾的字屬于姑蘇車轍,如姑蘇“gu”“su”二字,在演唱時,需保持喉部穩定舌根放松,將聲音集中傳出;以韻母“i”“u”結尾的字屬于一七轍,與姑蘇轍相似的是都屬于直出無收型,在咬好字頭的情況下,通過氣息帶動聲音;以韻母“ang”“iang”“uang”結尾的字屬于江陽轍,如霜“shuang”江“jiang”,其中“u”和“i”為介母音,在吐字時快速地帶過介母音,在“ang”上延長;以韻母“an”“ian”“uan”結尾的字屬于言前轍,如天“tian”眠“mian”船“chuan”,在吐字時需將舌位放置靠前,舌面保持低平,使用橫音豎唱的方法發聲。在演唱《楓橋夜泊》時要做到每一個字都仔細揣摩,力將一氣呵成地表達作品的意境。[5]
三、結束語
筆者希望通過此課題的研究,能為研究母語音樂文化提供一些參考依據,為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研究拓寬思考方向,但由于筆者自身水平有限以及參考文獻較少等局限性因素,對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研究還有不足之處,期待能有更多專家學者進一步研究廣博的母語音樂文化和精美的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
參考文獻:
[1]吳宇峰.古詩詞藝術歌曲的吟誦與演唱——以藝術歌曲《楓橋夜泊》為例[J].中小學音樂教育,2021(03):36-38.
[2]周學祿.古詩詞藝術歌曲的“情”與“聲”——以《楓橋夜泊》為例[J].藝術評鑒,2022(07):79-81.
[3]王提.藝術歌曲《楓橋夜泊》的藝術特征與演唱處理[J].黃河之聲,2022(03):119-121.
[4]林夢鈴.《楓橋夜泊》的思想意蘊和演唱分析[J].藝海,2022(12):44-48.
[5]曾興潤.古詩詞藝術歌曲《楓橋夜泊》中依字行腔的教學探究[D].四川音樂學院,2022.
基金項目:2022年度浙江音樂學院研究生科研及藝術實踐項目資助“母語音樂文化語境下中國古詩詞藝術歌曲的演唱研究”(項目編號:YXKY2022014)。
作者簡介:孫曼(1999-),女,安徽宣城人,碩士研究生,從事美聲演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