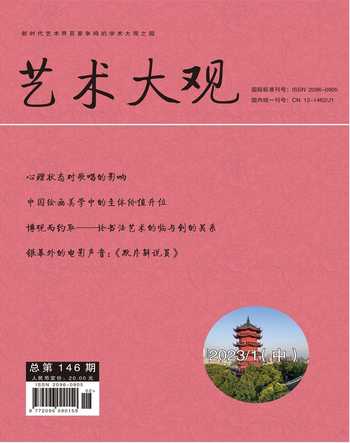以《夏山高隱圖》為例探析王蒙的隱逸思想



摘 要:以《夏山高隱圖》為例通過創(chuàng)作背景,構(gòu)圖形式所營造的氛圍,畫面各個要素,如人物、動物和山林小溪,以及筆墨的表現(xiàn)形式、在畫面中運(yùn)用到的皴法和筆墨經(jīng)營所營造出的氛圍,四個方面的研究來考證王蒙山水畫創(chuàng)作之中表達(dá)的隱逸思想。
關(guān)鍵詞:《夏山高隱圖》;王蒙;歸隱
中圖分類號:J205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02-00-03
一、《夏山高隱圖》背景介紹
該作品創(chuàng)作于1365年,是王蒙的晚期作品。這一時期正處于元朝動蕩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都處于衰敗的狀態(tài),繪畫作為一種表現(xiàn)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往往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精神風(fēng)貌。元代不像宋代繪畫那樣客觀地、寫實(shí)地描繪世界,更多的是表現(xiàn)畫家的主觀情感,是從“自然”到“自我”的變化。元朝很多文人士大夫官場失意,有的退隱山林、有的則是參禪入道,在元初趙孟頫掀起的文人畫風(fēng)潮也給了這些在官場上失意的士大夫們一個宣泄的空間。王蒙雖是入世,但他也同其他文人一樣,在這個動蕩的時代里想尋找一塊能過上安定平靜隱逸生活的凈土。翟坤在《王蒙山水畫藝術(shù)研究》中也提道:“他生平大部分時間是在元末戰(zhàn)亂紛爭的年代中度過的,他像大多數(shù)士人一樣仕途不順,郁郁不能得志,見形勢好了就下山做官,形勢不好就隱居山中以避世,官而隱,隱而官。”[1]這之中也說明王蒙所繪的情景也是他自己有真實(shí)體驗(yàn)的場景,但是這種長久的平靜只存在于畫面之中罷了。
《夏山高隱圖》中右上角題跋寫道,“夏山高隱圖至正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黃鶴山人王蒙為顏明征士畫于吳門之寓舍”。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胡雪琪在《元末明初政局中的王蒙——〈夏山高隱圖〉研究》[2]中認(rèn)為,該幅作品是王蒙在蘇州為官借畫來與官場之人結(jié)交拉近關(guān)系的作品。既如此,是不是此畫就不止含有歸隱山林這一個含義了。她還在文中引用陳基在《臥云軒記》中提到王蒙為張士誠手下官員“行中書省右丞吳陵王公”的新居臥云軒作畫之事,說:“黃鶴山人最善畫,凡卉木煙霞山光水色可以狀夫軒之勝者,慮無不曲盡其態(tài)。”陳基的筆記中記錄到王蒙的畫技也在官場之上結(jié)交官員所用。那么此圖中那個頭戴官帽,手中另握東西穿過重重山林深處探訪隱士的人想必便是慧眼識人的官場使者了。如此來講的話,“隱居”深山的畫面反而是表現(xiàn)出了王蒙想要被政府官員賞識“入世”為官的迫切愿望了。但是《夏山高隱圖》所創(chuàng)作的年份1368年他為官之地的上級張士誠已不在,這幅畫要作為王蒙仕途之路的鋪路石也很難實(shí)現(xiàn)。在如此紛爭的現(xiàn)世之中,王蒙也很難不想在這亂世找到一個安居之所,很難不有歸隱之心。沈晶也在《宗炳“以形媚道”的思想在元代山水畫中的踐行》中講道:“在1364年左右,王蒙出仕過張士誠幕下長史,后又不滿其政權(quán),再次歸隱,此次歸隱是王蒙山水畫藝術(shù)高度成熟之際,其傳世經(jīng)典之作《青卞隱居圖》就是此期間(1366年)所作,還有《夏山高隱圖》《花溪漁隱圖》等以隱逸為題的山水畫。”[3]她認(rèn)為《夏山高隱圖》乃是王蒙隱逸題材作品的代表。
或許王蒙正是因?yàn)樵诠賵錾弦淮斡忠淮蔚氖瑢?dǎo)致他一次又一次地“入世”“出世”,他作為一個有入世情懷的文人世家,出身名門,又有才華,在與其他文人雅士交往時,心中很難說是不想為官展現(xiàn)自己才華的,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讓他回到了自己的“桃源”之中。正如孔子所講:“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不如歸于山林,寄情于山水,在隱居生活中參禪悟道,與大自然和道友相互交流,在繪畫中尋找自己心靈的居所。
二、《夏山高隱圖》畫面分析
(一)構(gòu)圖形式
《夏山高隱圖》(見圖1)是山水畫常用的全景式構(gòu)圖,此畫長149厘米,寬63.5厘米,雖然尺寸上沒有那么大,但是整個畫面依然氣勢很強(qiáng),重重山脈,瀑布懸掛,草木茂盛,小流穿梭在山谷之中,沿著山腳蜿蜒曲折,流過寺廟,流過林間,穿過小橋,流向毛屋,從遠(yuǎn)到近順著水流一路看到茅草屋,從上到下貫穿畫面。繁密的構(gòu)圖中除了天空的空白和遠(yuǎn)山與中景山峰云霧之處有較大空白以外,畫面中幾乎都是對山石和樹木的繁密用筆,在水流處留白,利用山石樹木的繁密對比“擠”出水流來。但是整個畫面又秩序井然,層層遞進(jìn),這種布局讓畫面更具有觀看點(diǎn),讓人能更深入畫面中去。隨著山勢和溪流的指引,我們一步步地走向山林深處,雖是近景,但讓人感覺如同置身山間最隱秘的地方一般。近景中樹木繁茂,水流也比遠(yuǎn)處山谷中的水流看上去更加緩和,遠(yuǎn)處屹立的高山好像是阻斷了另一邊塵世一樣,近景所展現(xiàn)的環(huán)境如同適宜人居住的世外桃源一般。
整個山勢左邊和右邊都向中間聚攏,遠(yuǎn)山又屹立于中央將聚攏過來的氣沖散,一部分回旋在山谷里,另一部分順著山的左邊流走,被最后面的一座山一分為二,但是整個畫面因?yàn)橹虚g山勢的聚攏和遠(yuǎn)山的隔擋,顯得畫面中山林渾然一體,遠(yuǎn)山以及瀑布之后的山脈仿佛隔開了另一個世界。中景部分兩邊山勢明顯比遠(yuǎn)山要低很多,這些丘陵和垣坡、巨石上生長著苔蘚和樹木,碎石間流出一條小溪,說明此處地勢較為平緩。我們也能看到中景部分就開始有房屋了,再向前來在松柏叢中好像又蓋著幾間小觀。隨著水流再向前來就能看到這兩塊巨石后藏著的小茅草屋,茅草屋還被幾棵高高的樹木遮蔽著(見圖2)。在左側(cè)的畫面中左下角又是一間茅草屋而它右側(cè)偏上的地方有一個帶著官帽的男人(見圖3)。從整體上來看,第一眼會看到中景的房子和遠(yuǎn)山瀑布的地方,然后慢慢順著溪流往下看,給人逐漸進(jìn)入山林的感覺,畫面整體上渾然一體、氣勢磅礴,但是中景尤其是近景之處看點(diǎn)和細(xì)節(jié)就變得很多,需要仔細(xì)品味。
(二)畫面要素
1.人物
這幅作品中的人物分為三組(見圖4)。下方房舍兩區(qū),左側(cè)屋內(nèi)一婦人正在泡腳,庭中小犬靜臥,屋外男子正持盆在溪邊打水。林間小路上,有一個頭戴官帽的男子從山中而來,不知是不是前來歸隱山林的文人。中部山路曲折,溪水潺潺,茅屋隱于松蔭林木之間。右側(cè)屋內(nèi)男子手持羽扇踞坐榻上,童子捧盤前來侍奉,還有一只小犬跟隨其后,屋外一童子與鶴起舞,活潑天真,趣味十足。“山水面中點(diǎn)景人物雖小,卻涵蓋了畫家的主觀情感和理想寄托、現(xiàn)實(shí)生活狀況、社會道德思想及時代需求等多方面的因素。另外,元代畫家更加注重筆墨意趣,創(chuàng)作追求‘寫胸中逸氣。”[4]圖中每一個人的活動幾乎都應(yīng)對著“夏”這字,“鶴”在道家來看是仙界“接引的使者”,“鶴象”征著圣潔、清雅,某種意義上“鶴”已成為修仙的“圖騰”。那么不管從人物活動還是動物角色上,這一片安詳舒適的情景也正表現(xiàn)了整個畫面最為核心的“歸隱”主題,這些山間的生活無不是在展現(xiàn)山中隱逸生活的恬淡。
2.房屋
圖中我們能看到四處房子是有區(qū)別的,尤其是中景部分看到的這個屋子(見圖5)和前景中的茅草屋顯然是不同的。這種兩邊各有一間屋子,中間由一間廊道連接的結(jié)構(gòu)樣式就很像一座寺院了。根據(jù)當(dāng)時背景,元代統(tǒng)治者對老莊思想的推崇,在這樣的影響下,這些山林之中也不乏一些小型院廟。參考《營造法式》中的圖示(見圖6),這種建筑形式也在故宮午門有體現(xiàn)。宋代金明池也有中間是一座主殿,兩邊各一間殿院的形式。畫中屋檐的形式也像是宮殿一般的屋頂,但是山中畢竟狹小,不能建造大面積的宮殿,這種形制又與普通人所居住的茅草屋不同,很有可能就是朝廷支持打造的屋子,而且屋邊松柏聳立,《道觀園林植物景觀營造初探》中講道:“品《史記》:‘松柏為百木之長,古老的松柏一般為仙境的重要標(biāo)志。凡是中國古老的道觀,均為松柏摩天翳日,漪薈郁蔥。”[5]所以筆者判斷這大概是一間小型寺廟道觀。那么這正是因?yàn)橥趺墒艿搅死锨f思想的影響,他在隱居山林的同時也在自然中悟到一些道理,“清靜無為,反對斗爭,逍遙、自然”,這與他畫面的整個基調(diào)也是相符的,與《夏山高隱圖》這一題目也是相符的。王蒙在歸隱中實(shí)則已經(jīng)釋然了,他人是否要助“我”仕途,“我”已不在意了,只是順其自然,能為而為。在這亂世之中又何有順利的仕途,那“我”愿居于這世外桃源過逍遙自在的清凈生活。
(三)筆墨的表現(xiàn)形式
王蒙山水畫的繁密風(fēng)格我們在這幅作品中也能體會到。從樹木來看,整個畫面中樹為主要元素,繁密的樹木也體現(xiàn)出了“夏”的特點(diǎn)。山中樹種多樣,表現(xiàn)樹木的用筆方式也十分多樣,有“勾”有“點(diǎn)”,遠(yuǎn)處的樹木用“短勾”和“小點(diǎn)”來表現(xiàn)繁密的樹葉。近景的部分樹木樣貌較為清晰,能看到很多不同的樹種,有向下的尖葉子、“小混點(diǎn)”葉子、“聚散椿葉點(diǎn)”葉子、“大混點(diǎn)”葉子、圓葉子、柳樹葉子、大面積染成一片的葉子,這些種類不同的葉子一起營造出了山林景色。這其實(shí)就是“點(diǎn)”“線”“面”的組合,利用樹木的葉子相互組合,產(chǎn)生不一樣的黑白關(guān)系,讓畫面看起來不僅豐富,而且很透氣,能夠營造出幽靜空靈的氛圍。這種情況也說明了王蒙其實(shí)不僅是在主觀地創(chuàng)作繪畫,這也表現(xiàn)了他對自然的真實(shí)感受和長時間的認(rèn)識體會。他不僅師法前人,更是師法自然,對自然的理解。這種深刻的體會往往是久居山林之中才能體會到的,想必王蒙是時常居于山林之中的,這是不是意味著他心向自然,愿歸隱于此的內(nèi)心愿望呢。
從山石來看,王蒙師法董、巨“披麻皴”,在此基礎(chǔ)之上略微卷曲,形成其獨(dú)特的“牛毛皴”,我們從王蒙的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如《青卞隱居圖》《琴書自娛圖》《東山草堂圖》《松山書屋圖》中都有體現(xiàn)。山用披麻皴、牛毛皴、解索皴塑造出山體,邊緣塑造讓一整個山成為連綿不絕的山川。“就藝術(shù)表現(xiàn)來看,畫中所營造的林泉山川,無疑是畫家借畫言意的一種情感境象傳達(dá)”。[6]點(diǎn)子點(diǎn)于山頂和山中,在豐富畫面的同時,這些點(diǎn)子也化作了山中青苔象征著山的陰面。種種要素組合在一起,營造出了一幅夏日的山中景色。清代《夢幻居畫學(xué)簡明》中提道:“點(diǎn)苔之法,其意或作石上蘚苔,或作坡間蔓草,或作樹中薜蘿,或作山頂小樹,概其名曰點(diǎn)苔,不必泥為何物。”鄭安達(dá)在《王蒙〈夏山高隱圖〉密體形式在山水創(chuàng)作中的運(yùn)用》中描寫道:“《夏山高隱圖》密集的線條來皴染山石而用淡墨皴染出山體,同時運(yùn)用大量的點(diǎn)來對山的體積進(jìn)行深入的刻畫,而用的點(diǎn)并不均勻,給人一種豐富的想象。”[7]這也是這幅作品為什么尺寸不大,但是整個畫面不僅高遠(yuǎn)宏偉,而且畫面之中又十分細(xì)膩耐人尋味的原因。
三、結(jié)束語
《夏山高居圖》從其動蕩不安的背景來講,或者是從構(gòu)圖營造的氛圍,畫中人物的活動、鶴和房屋的象征意義,以及其筆法墨法所展現(xiàn)出的畫面來看,這幅作品已將王蒙“隱逸”思想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不論是他實(shí)際居所真實(shí)寫照還是心中所向的世外桃源,他的畫面中表現(xiàn)出的平淡的、恬靜的生活都是他所向往的歸隱山林的生活樣貌。
參考文獻(xiàn):
[1]翟坤.王蒙山水畫藝術(shù)研究[D].河北大學(xué),2010.
[2]胡雪琪.元末明初政局中的王蒙——《夏山高隱圖》研究[J].藝海,2016(02):73-75.
[3]沈晶.宗炳“以形媚道”的思想在元代山水畫中的踐行[D].湖南師范大學(xué),2020.
[4]張瑞娜.山水畫中點(diǎn)景人物與主題的互融互生——以王蒙《青卞隱居圖》和《秋山草堂圖》為例[J].藝海,2018(11):65-66.
[5]張麗麗,王立君,吳同強(qiáng),道觀園林植物景造初探[J].中國農(nóng)學(xué)通報(bào),2009,25(18):283-287.
[6]馬祥和.王蒙山水畫皴法形態(tài)特征研究[J].中國民族博覽,2019(14):151-152.
[7]鄭安達(dá).王蒙《夏山高隱圖》密體形式在山水創(chuàng)作中的運(yùn)用[D].上海師范大學(xué),2020.
作者簡介:馬小雨(1998-),女,陜西西安人,碩士研究生,畫家,從事山水畫創(chuàng)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