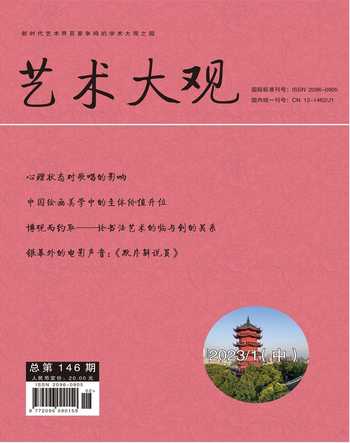以陳洪綬書畫作品展之所見談明朝人物畫的寫實方法
摘 要:當代中國人物畫的實踐者在各大展覽中直觀中國古代繪畫原作,是其接近、理解中國畫傳統,印證、辨析中國畫古論的最佳途徑。陳洪綬的繪畫對后世影響深遠,2022年的“高古奇駭——陳洪綬書畫作品展”中人物畫展陳密集,是一次很好的學習契機。當代寫實性中國人物畫的實踐發展方向問題一直是畫界討論的熱點,筆者通過觀看陳洪綬書畫作品展,對明朝中葉以后人物畫的寫實方法有了新的認識并深受啟發,因此想以陳洪綬書畫作品展觀展體會為入口,陳述筆者對明朝人物畫寫實方法的小結,以期對當代寫實性人物畫實踐的探索方向做出指導。
關鍵詞:寫實;肖像畫;陳洪綬;當代中國人物畫
中圖分類號:J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02-00-03
一、寫作緣起和觀展方式
當代中國高等藝術院校中國畫人物專業的教學中一直存在著諸多關于“人物畫寫實問題”的討論。筆者自己的創作和工作實踐方向在這個專業,所以也一直在面對和研究這個問題。2022年是陳洪綬逝世三百七十周年,紹興市徐渭藝術館舉辦了“高古奇駭——陳洪綬書畫作品展”。此次展覽展品豐富,尤其是人物畫作品展陳集中,筆者因此前往觀摩學習。仔細地觀看了展覽之后,聯想到筆者自身在創作實踐中遇到的具體問題以及幾年來參與教學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實際情況,想到應以此次觀展體會為契機,將筆者對“中國人物畫寫實問題”的一點看法整理出來,以便更好地明確自己創作和教學的方向。
展覽館展覽的特點就是所有展品的陳列排布相對集中,作品間的對比會自然形成。因此筆者在觀展前做了一個觀看準備,那就是此次展覽“只用眼睛看,不用腦袋看”。筆者作為實踐者也許會不自覺地攜有先前認知系統的偏見,但是當展品并列出現在觀眾眼前的時候,筆者想應當盡量單純地只用視覺去直觀地感受圖像帶給人身心的不同刺激,越是在所謂的“專業”中游走的人,越是應當時時提醒自己用所謂的“外行人”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專業感受這個專業。所以筆者聽從眼睛對心的指導,試著用這樣的觀察方式去分辨畫作的優劣高下。這樣做并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筆者被北齊顏之推的一段著述點醒,顏之推在《顏氏家訓論畫》中說:“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座上賓客隨宜點染,既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1]這段文字讓筆者重新思考觀眾與繪畫的關系,這也暗合了時下流行的學說“通感論”。所以這種觀看方式是筆者獲取此次展覽中人物畫相關信息的前提。
二、展覽中人物畫作品之比較以及寫實性人物畫的勝出
筆者將此次展覽中全部人物畫作品分為四個板塊:第一板塊是陳洪綬五世祖宗肖像畫軸原作2幅。第二板塊是陳洪綬繪制的紙本或絹本人物畫原作23幅以及《九歌圖》《水滸葉子》等幾部版畫作品的復制品。第三板塊是清代至民國受陳洪綬畫學畫風直接或間接影響的7位畫家的人物畫原作11幅。第四板塊是李公麟《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贊碑》拓片局部;展覽館為了輔助說明陳洪綬少時學習經歷所打印的李公麟《孝經圖》局部;以及敘述其生平信息中輔助性質的人物畫若干。
縱觀此次展覽中所有的人物畫資料,筆者以為2幅祖宗肖像畫《陳洪綬五世祖陳翰英肖像軸》和《陳洪綬五世祖母陳翰英夫人肖像軸》比其他人物畫更為動人,李公麟的《孝經圖》局部打印版雖然只是展覽中的輔助性資料,但是當圖像并置陳列的時候,其光芒真是難以遮掩。但因其是復制品,所以此文中不對其進行過多評論。反而相形之下,恕筆者直言,此次展覽的主角陳洪綬的人物畫有點黯然失色。總的來說,其失色在與2幅祖宗肖像畫和 《孝經圖》相比,陳洪綬擇取了以“虛構”為主的創造方式來表達人物以及人物和景物之間的關系。可以看出,其人物是陳洪綬從自然人身上提取強化進而創造出來的人物符號,景物的配備含有特定的內涵指向,最終呈現的畫面人物與景物的組合不是以自然再現為最高的審美取向,而是以虛構再現的表達方式實現表意言情的理想為宗。盡管這種創造方式被文人畫審美評定推演發展數代百年,盡管這種審美追求被冠以各種詩性和民族性的美名,盡管這種繪畫方式是陳洪綬影響后世畫學的主流脈絡,但是當真實的圖像并置陳列在一起的時候,“虛構的符號人”遠沒有“真實的自然人”動人,故意強化意向的人物和景物關系也并沒有再現客觀世界的人物景物關系高妙。
2幅祖宗肖像畫和《孝經圖》到底好在哪里呢?它們用什么觸動了觀眾的心弦?筆者暫且不想從它們的表現手法、繪畫風格等這些問題去談論,而是想先把直面畫面的觀感述諸紙面。這里筆者將重點談論2幅祖宗肖像畫軸。當筆者佇立在2幅畫作面前, 兩位四五百年前的陳家老祖正襟危坐,面容安詳,對視之下仿佛他們從未離世,他們坐在那里似乎正要將陳家的興衰榮辱家規綱常娓娓道之于后人。筆者雖是幾百年后一個與陳家毫無關聯的人,但是見到畫中人也是頓生慎敬之心瞬發強志之愿。相比于展廳中其他的人物畫作品,2幅肖像畫的優勢是其具有活性,其具有活性的原因在于繪者通過畫像把祖宗要傳達給后世子孫的心思十分清楚明確地表達出來,即使跨越時空,今天的觀眾也可以一眼辨識其義。而這“義”是通過真實的生命感十足的肖像傳遞的,是寫實的繪畫手法讓先祖對家族的威力不因其肉身的離世而煙消云散。與陳洪綬筆下的人物畫相比,2幅祖宗肖像畫軸的繪者不倚仗在畫面中故意強化弦外之音來表達先祖對后代的千言萬語和殷殷期待,同時他也沒有將后世子孫對先祖的特別敬仰或者對先祖的特別解讀用十分明顯的痕跡昭之于畫。他只是把先祖真實的自然人的儀容與姿態定格在那里,令人見畫如見面,見面如聞聲,聞聲則識心。然而識其心后莫關乎情,情之彌廣,難以言表,相比之下靜默樸素不露聲色的寫實性肖像畫比陳洪綬文人畫取向的人物畫格調要高出許多。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開宗名義之句“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1]與此刻眼前的2幅祖宗肖像畫構成了實證。如此細品,其著述本意的指向也應當是更傾向于為人物畫的寫實性確立審美的高度。其實我國年代較早的畫論中從來都不乏對“寫實”的肯定,對于寫實性繪畫的難度系數也很早就形成了認識。西漢劉安《淮南子論畫》:“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1]東漢張衡《平子論畫》:“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秦始皇兵馬俑出土以后,今人可以一睹兩千多年前秦朝雕塑的寫實高度,上述兩段畫論出自漢代,想必漢人當時對“寫實”有一定程度上的背棄,所以有識之士拿其筆來對其進行批判,而這些都能說明中國傳統人物畫審美取向中對寫實性繪畫的認同以及對寫實性繪畫技能的品評與追求。
一直以來,畫界同仁常常談到學習中國人物畫傳統精髓的問題,筆者認為對寫實性的認可與追求應是傳統中國人物畫的精髓所在。縱觀畫史,對人物的寫實性追求從先秦一路延續發展直至兩宋時期,人物的寫實性表達達到頂峰。兩宋以后文人畫審美理念逐漸成熟,文人畫繪畫構成規則法式逐漸興盛,人物畫寫實性品評系統與寫實性表達手法也隨之大勢逐漸式微。而至陳洪綬所在的明末清初,寫實性人物畫已經不再是人物畫審美評價的主流取向,自然于此方面發展的人物畫畫家也屈指可數。回顧展覽中陳洪綬的人物畫作品,文人畫風格明顯,反而是受西洋自然主義寫實風格影響下的2幅祖宗肖像畫更能讓人聯想起元以前人物畫審美與實踐的豐神。一個從視覺上而來的“像”字引發了時隔幾百年觀眾心靈間的通感與共情,也正是因這“通感與共情”使得一幅畫作得到了永恒于丹青的機會。故中國人物畫若想在新時代走出新境界,首先應當在寫實性人物畫傳統上多做研究,在寫實性人物畫表達上多做實踐,當代中國人物畫再創高峰則指日可待。
三、陳洪綬五世祖宗肖像畫軸的寫實方法
上文已經明確了寫實性當代中國人物畫的實踐大方向,接下來筆者想以陳洪綬書畫作品展中2幅祖宗肖像畫為例,談一談它們對當代寫實性人物畫實踐的具體指導所在。回顧《陳洪綬五世祖陳翰英肖像軸》和《陳洪綬五世祖母陳翰英夫人肖像軸》原畫,筆者主要想從其寫實性表達方式的兩個方面說明它們對當代寫實性人物畫的指導意義。
首先,畫作中人物要素本身的寫實性表達。明朝中葉,隨著西洋傳教士來到中土,隨之而來西方以自然主義再現為宗的一類寫實性繪畫技法也在中國大地悄然萌芽。雖然這種繪畫方式并未能在第一時間撼動當時主流的文人畫在畫壇中的領袖地位,但是它卻被中國當時的帝后、官僚階級所采納,通過結合傳統中國人物畫的繪制形式終將其改良為一種具有特殊功能用途的人物畫品類。展覽中2幅陳洪綬五世祖宗肖像畫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產生的, 南京博物院館藏的《明人十二相冊》與這兩幅畫的風格十分接近,同屬于這個時期此類肖像畫的代表之作。
其次,從這類肖像畫作中的人物本體要素來看,這類肖像畫呈現被畫人的真實屬性都采用了如下表現方式:1.人物面部的刻畫處理從直觀視覺上符合西方人體解剖學常識的基本規律,但是并沒有采用西方自然主義寫實性繪畫以光影塑造結構體積為主的表達方法。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有意識地降低中鋒線條勾勒強度與皴擦、暈染間的對比度來以期達到更為接近視覺真實的目的,傳統人物畫畫法中以線寫形的造型方式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繪者把傳統審美要求中線條的寫意成分降下來,以便把線性寫形調試到與被畫人真實樣貌更為匹配的狀態中去。2.人物手部的繪制是符合西方人體解剖學基本比例關系的,沒有做過特殊的變形處理。但是相較于面部手部的處理方式更趨于平面化,傳統人物畫畫法中以線寫形的造型特征更加明顯,加之古代顯貴階層因蓄留指甲習慣導致的超出日常范圍幾倍長的指甲,使整個手部的最終呈現看起來有一些傳統人物畫中程式化手部處理的味道。3.人物的衣冠服飾是使用了十分傳統的以線寫形的造型方法繪制而成的。衣冠服飾的處理并沒有因為要配合面部的輕微立體感就使用了和面部同樣的處理手法,相反繪者將整個衣冠服飾處理得極為平面化,粗線勾勒、色彩平施,但是他保留了被畫人真實的人體比例,故而使整個人物看起來和自然人十分接近,加之面部與手部的處理,肖像的寫實表達達到一個很高妙的境界,但這種境界又與西方自然主義寫實性繪畫的取境不同。最終畫面中人以一種非常得體的觀感呈現在觀眾面前,這種特殊的人物寫實方式不僅幫助繪者實現了他對這張畫最初的愿景,并且成就了一種新的視覺形式,開辟了一塊新的審美土壤。
最后,再看看繪者對畫面中人物、景物以及空間關系的寫實性是如何處理的。畫面中二位先祖在被繪制肖像時坐的是同一把椅子,但是不同的是,《陳洪綬五世祖陳翰英肖像軸》中陳翰英坐在椅子上時椅子靠背上披掛的是虎皮靠墊,《陳洪綬五世祖母陳翰英夫人肖像軸》中陳翰英夫人坐在椅子上時椅子靠背上披掛的是綢緞靠墊。同一把椅子與不同的靠墊作為道具輔助表達了一些具體的規制與含義,而這種處理手法將潛在的信息用十分自然的方式表達出來,加之對椅子與靠墊的寫實性描繪,椅子與人物之間真實的比例關系,三者結合成就了被畫人物的威儀,于不露聲色之間祖宗畫像的功能悄然宣之于眾。這里沒有其他的道具作為弦外之音出現在畫面當中,人物坐在有靠墊的椅子上是日常生活中真實的存在,而非虛擬,這也構成了一種寫實性的人物與景物組合關系,而這種寫實性的組合關系非但沒有阻礙畫面意圖的傳達,反而彰顯了畫作的功能與用途。2幅祖宗肖像畫中除了人物、椅子、椅子靠墊以外其余的畫面空間全是空白的,什么也沒有畫,這又與西洋以自然再現性質為宗的寫實畫有了不同之處。但仔細觀看就會發現,繪者在安排畫面構圖時將坐在椅子上的人物放置在了客觀世界透視中靠近近景的位置上,而椅子后方的中景以及更遠處的遠景才是繪者決定留取空白的地方。這樣做不僅可以增強人物本身的即視感真實,而且以近景的真實性可以幫助觀眾在腦海中建立起對整個環境空間的想象,這種處理方式是“不畫而畫,意向無限”的基石。回顧陳洪綬書畫作品展中李公麟的《孝經圖》打印版局部,小小的畫面中四個人物與景物道具以及背景空間關系的組合也是如此,所以盡管《孝經圖》是一幅長卷的繪制形式,并且帶有敘事性的功能,但因其寫實性的人物、景物、空間關系使之沒有變成一張大大的有如連環畫一般的插圖,而是成為一件無論在任何年代都能讓中國人產生共情的曠世之作。
雖說以2幅祖宗肖像畫的寫實方法辯說明朝的寫實性人物畫高度有點管中窺豹之意,但眼前實物引發的思考權可以當作開啟中國傳統寫實性人物畫研究的大門,當代寫實性人物畫的實踐者可以由此而入,探索學習中國古代更為廣闊的人物畫寫實表達空間,以便更好地為自己的實踐指明方向。
四、結束語
雖然說坐而論道易,起而行之難。但是方向總是要在坐而論道中漸漸地明晰起來,方向既已定,來日方可期。當代中國人物畫實踐應當在寫實性繪畫這條大路上前行,于中國畫傳統的研習應取其以寫實性為宗的畫學脈絡傳承發展,在寫實性的基礎上不斷探索當代中國人物畫發展的新可能。
參考文獻:
[1]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溫程媛(1987-),女,吉林吉林人,碩士研究生,從事中國畫人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