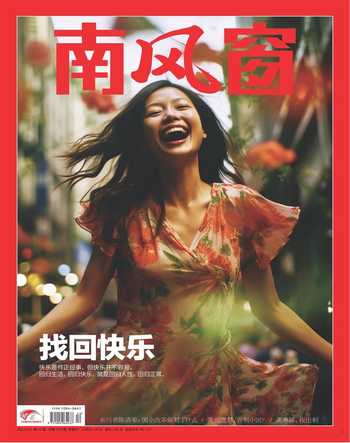素質加分淪為家長鉆營,中高考改不動
姚遠

上初一的女兒在繪畫比賽獲一等獎,本來可以在杭州中考“加分”,忽然,政策調整,“加分”取消,王冰反倒松了口氣:“沒有了是好事,就是我們自己有點可惜。”
2023年1月31日,杭州市教育局發布《關于進一步完善杭州市區普通高中名額分配招生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見稿)》,實行多年的分配推薦制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考生填報分配生志愿、高中學校按平行志愿錄取”。被取消的,還有5%的綜合素質評價分數,以后將僅作為前置性條件對學生進行考核。
這意味著,即將在1個月后舉行的2023年杭州中考,會是分配推薦制施行的最后一屆。
再往后,就將回歸“一考定乾坤”。
杭州原先施行的分配生政策,是根據95%(或以上)的學業成績,和5%(或以下)的綜合素質評分對學生進行綜合錄取。其中,學業成績包括初一、初二、初三各階段的六次考試,根據不同權重比例計算;綜合素質評價則包括課外活動參與和競賽榮譽。兩者的綜合成績將在初中校內進行排名,然后由學校根據分配名額向高中校選送。
制度設計的本意,是破除唯分數論,“堅持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需要”,卻在實踐不過幾年以后,在爭議中被推翻,最終還是回到以一場考試成績決定去向的原態。
無獨有偶,2019年在深圳,“初中生綜合素質評價制度”也曾招致反對,被質疑淪為形式主義,令學生和家長們疲于應對。
一直以來,“唯分數論”被當作應試教育的某種頑瘴痼疾,為人詬病。它催生了激烈的競爭、內卷和繁重的課業壓力,疲憊的學生和焦慮的家長,全被困在里面。人們一直在呼喚一種更多元、更靈活的升學機制,但當它以“綜合素質評價”的形式到來了,卻又陷進漩渦中。
為什么?
學生的素質,家長的能量
綜合素質評價分數即將調整,不再直接關系升學分配。“我身邊的家長都挺支持的。”生活在杭州的秦雨告訴南風窗。
盡管占比只有5%或3%,但在此前的分配招生中,素質評價分數關系重大,甚至有時決定著一個學生的去向。
秦雨曾以杭州部分學校的計算方法進行過一次模擬,假使A和B兩位同學初中3年6次考試成績每次相差20分,最后折算而成的學業總成績相差僅3.402分。也就是說,某種程度上,素質評分的這5分,比考試的20分來得更重要。
秦雨記得,前幾年在杭州家長中廣為流傳的一個例子是,某位學業成績排名全校第二的學生,加上素質分后變成第十;學業成績排名第三十八名的,加上素質分后排名第九。考試成績的第二名和第三十八名,只是因為素質評分的不同,最終去往同一檔次的高中—這讓家長們警鈴大作,同時嗅到一絲機會。
“競爭很激烈,想在學業成績上提高一兩分是很難的,如果素質評分能錦上添花,小朋友整個升學目標就完全不一樣了。”生活在杭州的李早安說,她完全理解家長們的重視,因為其中“是有操作空間的”。
只是操作起來,不那么輕松。
大部分杭州初中學校將綜合素質評價分成五類:德育類、體育類、藝術類、科技類和其他類。但其中,哪個項目、哪個比賽可以被認定,各個學校之間沒有統一標準。
“綜合素質評分是一校一政策,”秦雨說,“很多學校的標準并不公開透明,不是一入學就公布的,很多家長不知道哪個項目可以加分,哪個比賽不可以。”李早安也贊同:“想拿到加分,家長必須在信息收集上付出很大的努力。”她在教育行業工作了多年,對繁雜的素質加分項目尚且無法完全熟悉。“更何況普通家長呢?”
就這樣,綜合素質評分儼然成了一場信息競賽,誰掌握了更準確的信息,誰就掌握了比賽的主動權。
綜合素質評分儼然成了一場信息競賽,誰掌握了更準確的信息,誰就掌握了比賽的主動權。
學校擁有評分的自主裁量權,而離學校最近的在校教職工子女,成了這場信息競賽的天然贏家。“他們很早就知道哪些項目可以加分,哪些更容易加分,哪些可以找到對應的老師,”秦雨說,“所以教師子女的升學優勢就特別大。”
再者,當與升學成績掛鉤,課外活動和競賽的評選過程成了一個黑屋子。如剪紙、繪畫、手抄報等文藝作品類比賽,不要求學生到場限時創作,只需要提交作品即可,如此規則之下,為了取得更好的成績,花錢請人代勞成了一種獲獎捷徑、一種人人心知肚明的現象。
一位孩子即將升上初二的家長在“民呼我為”平臺寫道:“家長挖空心思去鉆營,甚至請人代做,素質分的獲得不全由學生個人努力,反而變成家長的能量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極大地違背了素質教育的初衷。”
她建議,素質評價分應由全市統一制定標準、降低在綜合評分中的比重、減少素質評價的考核項目、剔除非現場比賽的項目和人為評選項目。
2022年8月12日,她收到來自杭州教育局的回復,綜合素質評價評分的改革被官方提上了日程:“根據教育部相關文件要求,我市將從2024年開始調整普通高中名額分配招生方式,落實‘初中階段平時考試成績不得與高中招生掛鉤等規定。”
加分與公平
圍繞綜合素質評價的爭議,隨著一紙新政落下帷幕,但也有人抱有擔憂。一位自稱擁有近40年教齡的老師撰文稱,此次調整,“完全推翻了原本屬于杭州教育的優點”。
他認為,在公立初中學校,無論體育、藝術、科技還是思想品德等校園活動,“都是優等學生撐起了大頭,還有優等生家長在背后默默支持”。但當校園活動與升學不再有關后,“我的班主任經驗告訴我,這一切將失去有時間、有效率、有頭腦的優秀學生們的支持”。
他的觀點引來一些家長的認同。他們留言,以后“什么演講比賽、信息編程、陶藝繪畫,都靠邊吧,太浪費時間”,“也不必逼著孩子競選這競選那的了,她能管理好自己,但管理別人吃力不討好,還浪費時間”。
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專家組成員、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曾撰文指出,近年的教育評價與中高考招生考試改革上,不唯分數、綜合評價多元錄取一直是核心方向,而綜合素質評價是其中的重要一環,也是綜合評價錄取的重要依據。
“但無論中考還是高考,綜合素質評價與綜合評價多元錄取都走得很艱難,甚至很尷尬。”他寫道。
這種尷尬,來自對教育公平的傷害與擔憂。
此前,中高考加分政策被視作實現“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一種有效路徑,但另一面,它在高考恢復以來40余年的教育實踐中滋生了失范與腐敗。
一組令人震驚的數據是,據財新報道,2014年,在北京教育資源豐富的西城、東城、海淀三區中,中考加分考生占京籍考生比例超過20%。這其中,加分最多的一項是少數民族加分,其加分考生占考生人數比例分別超過8.7%、8.4%和6.3%,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少數民族占市常住人口4.1%的比例。
浙江師范大學田家炳教育科學研究院鮑嶸教授,2015年曾就浙江省高考加分政策開展過一項實證研究。研究發現,那些在學科競賽上獲得高考加分的考生,父母大都為社會中間階層、接受過高等教育,年收入較高。她分析:“能獲得學科競賽加分的考生,大都是家庭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厚實的小孩,經過中產家庭的培養,參加了一些培訓、通過了幾次考試,是否天賦異稟,真不見得。”
鮑嶸對南風窗說,學科競賽這一類針對特殊才能的鼓勵性加分項目,于憲無根,于法無據。“這種加分,屬于‘非補償性的錄取傾斜,無關教育的基本權利,無關高等教育機會的形式公平和實質公平。甚至于,與大學能不能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人才關系程度也很有限。”
她認為,后者是高校培養環節的課題,而加分與否是錄取環節的設計。“不能過度夸大選拔制度的功能,而忽略了高校內部對于學生的培養。”
鮑嶸舉了個例子:各地的外國語學校之所以被家長們追捧,只是因為它們有著相當大比例的保送生名額。當年,我國的外語人才稀缺,外語學科建設比較落后,在各地外語學校選拔人才的保送政策,初衷是重點培養、重點傾斜。
“但因為有這個政策,許多家長千方百計把孩子送去外國語學校,”鮑嶸說,“而被保送進大學語言系的學生,一部分會在大學選擇轉專業,扶持重點學科的實際目的并沒有達到,這就造成社會正義的一個扭曲。”
價值選擇
也是在2015年,時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接受采訪時表示,從當年起取消所有鼓勵性加分項目,僅保留扶持性加分。直至如今,中高考加分的“瘦身運動”一直小步快走、持續推進。2023年中高考即將來臨,其中一些扶持性加分項目也在不斷規范和完善。
“一種主張是正義的,即使效率較低,我們也應當堅持。”
申請加分的條件限制被進一步地細化了。以少數民族考生為例,在杭州,考生須有本市民族鄉、民族村戶籍,且在該民族鄉、民族村配套的公辦學校完整接受義務教育,才可以申請中考加分。
“這是在具體的政策上進一步精準化識別,體現憲法精神、落實法律的公平性。”鮑嶸說。
一些聲音擔心,取消加分會傷害人才選拔機制的運轉效率,鮑嶸認為,公平與效率不是教育系統的主要矛盾。“在教育的語境中,中高考加分政策涉及的更多是‘社會正義,當正義與效率放在一起,后者構不成對前者的價值制衡,”她說,“一種主張是正義的,即使效率較低,我們也應當堅持。”
鮑嶸認為,中高考的作用就是分流,公平地分流、準確地分流。而考試能承擔的功能是有限的,寄希望于讓它來實現多元評價的教育導向,是不切實際的。“即使我們給予了某些人群以錄取傾斜和分數優惠,也改變不了應試教育的本質,最終只會讓學生和家長們學會如何鉆營、如何討巧一些。”
多元與公平的難以兼容,不僅困擾著中國。
祝剛是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的副教授,長期關注歐美國家的教育改革。他告訴南風窗,2019年美國曾爆發過一則大學錄取賄賂丑聞,大約50名來自富裕家庭的子女通過違法違規手段獲得了美國著名大學的錄取機會。
還有一直以來爭議頗多的“遺贈優先”政策,美國常春藤等一些知名私立學校,在錄取時會根據申請人與該大學校友的家庭關系給予優先錄取考慮。“遺贈學生”在2014年至2019年間的錄取比例為33%,遠遠高于6%的正常錄取率,這在美國掀起過一陣抗議的浪潮。
或許,是綜合多元,還是公平正義,取決于不同文化語境和社會環境之下的價值選擇。而李早安覺得,作為一名普通的媽媽,她對中高考改革的主要訴求僅僅是:盡可能地公平。
“每個孩子確實能力有別,有些學習能力特別強,有些就是相對弱,人和人之間是有差別的。但只要保證足夠的公平,無論我的孩子有沒有在升學中取得好的結果,我都可以接受。”
李早安覺得,所謂的多元成長,不僅僅寄托于中高考。也可以去學一門藝術、學一手技能,或者早些規劃去留學。
“不只有中高考這一條路的。”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