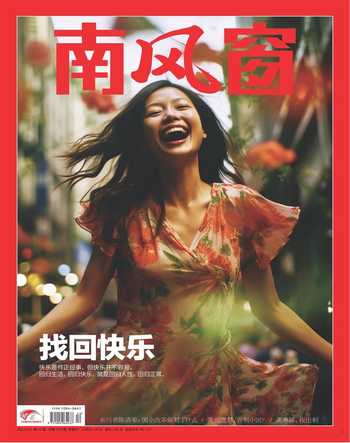經濟復蘇下的跨境并購
胡萬程

中國資本的出海并購活動,在去年降至了冰點。
根據普華永道的統計,2022年中國并購交易總額跌至4858億美元,為201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與2016年峰值相比預計減少80%以上,僅略高于金融危機過后交易活動銳減的2009年。
在新冠疫情持續蔓延、經濟增長放緩和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的大環境下,資金的出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使許多企業的海外并購步伐放緩。
但隨著疫情的結束,社會生活逐漸恢復正常。
在多重積極因素影響下,并購市場看到了穩步復蘇的曙光。行業人士預計,2023年中國并購交易短期內將以國內交易為主導,海外并購交易在下半年或出現觸底反彈,亞太地區、中東地區將成為首選目的地。
中國企業“出海”的歷史不長,僅有不到30年的時間。其間有苦有甜,有成果,有教訓,而在“后疫情時代”充分把握下一輪海外投資浪潮,需要投資者們在前人的肩膀上厘清方向、有的放矢。
貿易博弈的背景
畢德投資咨詢公司(BDA Partners,以下簡稱“BDA”)的合伙人兼中國區投行業務聯席主管蕭寅康,是活躍在中國跨境交易領域的“老兵”。
他所在的公司以跨境并購賣方顧問業務為主,2016年以來,穩居亞洲跨境并購交易數(企業價值10億美元以下)的榜首。
蕭寅康自2008年從香港來到上海,他接觸跨境交易項目的時間已超過15年。蕭寅康目睹過外資在中國投資的狂熱時期,也經歷過中國資本在全球并購的出海年代,如今又身處跨境交易的“相對冷冬”,他的感觸很深。
“對于我們從業者,這幾年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因為地緣政治的影響,中國企業在境外并購的數量有很大的縮減。疊加疫情的影響,受制于地理上的限制,項目難以促成,也直接影響了并購的交易量。”他說。
地緣政治的變化,給跨境交易帶來了一個直接障礙:監管審批。
在貿易保護主義言論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監管外國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跨境并購的關鍵因素之一。
美國是影響最大的一個地區。2020年1月,美國財政部基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公布了新法規,顯著擴大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管轄范圍。
“非美企業想要收購一家美國企業,就需要CFIUS的審查。如果這個行業比較敏感,涉及國家安全方面的話,這個審查時間就會很長。”蕭寅康說,“即便有很多交易最終沒有否決,但也未能給予承認,所以就無法交割。”
除此之外,以前一些傳統上被視為對外國投資持開放態度的國家,也走向了更嚴格的公共利益和外國直接投資交易審查。
比如德國,這個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里投資最多的國家,也在疫情期間,提前出臺了《對外貿易和支付法》,對非歐盟國家投資實施更加嚴格的審核的措施,將強制備案義務的投資范圍從“關鍵基礎設施”擴大到“關鍵技術”。
雖然確切數字難以統計,但從業者們表示,每年確實有相當數量的交易,因為某方感受到通過外資審查或反壟斷的希望渺茫而泡湯,甚至很多交易考慮到這點后未經討論便放棄了。
蕭寅康表示,監管審批是企業在參與跨境并購時會普遍關注的問題。“比如一家央企出境,就需要去國資委報批。交易一旦超過3億美金,就要去發改委報批。因為要走審核,這些在時間上都是不短的。”
而上述步驟只是中方的審批流程,每個國家的司法轄區都有其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和審批流程,這讓企業的交易變得更為復雜。
2005年,中海油欲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最終安全審查沒通過而交易受阻。
行業人士預計,2023年中國并購交易短期內將以國內交易為主導,海外并購交易在下半年或出現觸底反彈,亞太地區、中東地區將成為首選目的地。
2009年,中鋁公司計劃收購澳大利亞力拓,因為利益相關方認為交易條款過于偏向中鋁而終止交易。
2020年,山東黃金收購加拿大金礦商特麥克資源公司(TMAC)的交易,被加方出于國家安全的理由而叫停。
總之,中企要去海外買到好的資產,路途并不平坦。
錢,投到哪里?
盡管日趨嚴苛的審查變成“新常態”,但隨著疫情負面影響的消散,海外并購的活躍度也出現了復蘇的跡象。
一方面,全球各國的量化寬松和財政刺激措施,顯著提高了市場流動性和企業的可投資金。另一方面,受疫情沖擊最嚴重的行業,包括交通物流、旅游與酒店業、基礎材料以及非必需消費品,行業內的公司估值被“打折”,給了買家們掃貨的空間。
蕭寅康同樣看好未來的并購交易,他認為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被取消后,一些被抑制的并購需求反彈。“反壟斷”相關審查的告一段落,也使得國內的互聯網資本限制減少,有利于做正向突破。而IPO市場也會更活躍,公司估值的上升將有利于并購交易市場的恢復。
不過,接下來中國資本的并購方向會與以前有一些不同。以往中國買家專注于美國和歐洲市場,而現在對新興市場的投資會是一個趨勢,包括東南亞、中東、非洲。
“現在的中國買家,扮演的角色像是1990年代的美國。”蕭寅康說。
1990年代,美國企業在已有的市場趨于飽和,很多企業將重心放在海外,通過并購交易把自身的業務藍圖規劃到他國,在那里開拓市場。
而現在中國做的事也是如此。以前專注于收購歐洲的先進技術與產品,將其帶入國內,而現在是向外輸出國內的成熟技術和發達理念,與其在“已殺成紅海”的國內卷,不如積極出海,尋找額外的增長點。目前來看,互聯網經濟、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公司,具備這樣的潛力。
由于和中國在地緣上比較接近,投資環境相對成熟的東南亞就成為了不少企業的避風港。比如印尼,就是中國資本在東南亞最重要的出海目的地之一。
印尼的人口位居世界第四,達到2.74億,其中年輕人口占比高達58%。近年來,幾乎印尼互聯網所有垂類行業都經歷了兩位數百分比以上的增長,許多國際資本都想在印尼市場分得一杯羹。
2022年,中國企業對印尼直接投資額高達82.3億美元,中國位列印尼第二大外資來源國。在如今的印尼,電商市場、網約車業務、外賣市場、數字金融服務以及網絡游戲都有中國資本的身影。
“和早期出海的外貿、制造企業不同,現如今出海的中國高科技、智能制造等公司,一開始就會將東南亞作為首發市場。”蕭寅康告訴記者。
不過,挑戰也隨之而來。就和當年很多剛進中國的海外資本水土不服一樣,許多在東南亞的中國公司在本地化管理上遇到了不少挑戰。有的公司就因不了解東南亞國家本地宗教文化而觸犯禁忌,有的公司則是因為東南亞人受不了“996”、無法異地辦公、無薪加班等機制而吃了癟。
這其實也涉及許多中國買家在并購交易中常遇見的一個典型問題,即并購后不重視整合,文化差異妨礙執行。
比如,面對工會領導下的員工群體,中國企業往往缺乏管理經驗。如果中方高管試圖對原本平等的組織施加自上而下的威權文化,被收購企業的員工就會表示強烈不滿。
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收購企業的員工與取代了其長期領導位置的中方高管之間形成了日益加深的隔閡。這顯然會對并購交易的效果產生負面影響。
亟需全球化人才
做了十幾年的并購交易,蕭寅康見證了很多中資參與的案件。這其中有雙方一拍即合、順利交割的,也有過程異常曲折的;有交易后公司業務如虎添翼的,也有交易后表現平平甚至日益慘淡的。
他觀察到,中資企業在并購交易中是不愁資金的,它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常常集中于溝通層面。當中方作為標的公司控股股東的時候,外資常常會關注它會對企業文化和管理帶來怎樣的影響,而這點時常會被中方忽視。“如果這個問題處理不善,往往很多高級人才就會流失。”
“中國企業在做并購交易之前,最好在收購國有據點,有懂得當地社會制度、公司文化的人才。如果能把握住對方的痛點,就能與對方有更為高效的溝通,這也會有效提高交易的成功率。
BDA曾作為芬蘭公司Summa Equity的賣方顧問,在2021年幫助其以5.32億歐元的價格出售旗下的公司HyTest給中國的邁瑞醫療。
2022年,中國企業對印尼直接投資額高達82.3億美元,中國位列印尼第二大外資來源國。在如今的印尼,電商市場、網約車業務、外賣市場、數字金融服務以及網絡游戲都有中國資本的身影。
Hytest是全球知名的體外診斷原料供應商,擁有優質抗原抗體的原研和自產能力。這次收購對于邁瑞以及中國生物醫學界來說,填補了國內在體外診斷上游頂尖原料領域的眾多空白,助力解決了體外診斷上游原料供應“卡脖子”問題。
當時參與過此次收購案件,作為賣方顧問代表的BDA總監兼項目執行負責人張偲萌告訴記者,相較于一般企業,邁瑞的并購團隊非常專業,有很多在會計師事務所、高級律所、投行工作的高級人才,這讓邁瑞在前期的盡職調查、談判管理、臨場決策方面都更為順利。
她還表示,雙方因為本身就有業務往來,很早就建立了信賴關系。“過去幾年,公司的營收50%以上來自中國市場,加上邁瑞國際化的視野和思維,這些對于賣方都有著很強的吸引力。”
盡管,BDA經常作為賣方顧問參與并購業務,但如果買方是中國買家,他們就會主動做協調工作,傳達包括賣方的管理層有哪些隱藏顧慮、在條款上有什么在意的點,來幫助雙方進行更協調的溝通。
蕭寅康認為,未來中國買家想要吸引國際賣家,不應該單單局限于中國市場,因為很多跨國公司的業務是全球范圍的。中國買家還需要考慮去幫助賣家做更長遠的規劃,僅僅靠中國市場吸引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另外,我們也在積極配合我們在國內的客戶在全球范圍搜尋優質的投資標的,作為中資出海拓展業務的橋頭堡,支持實業的國際化腳步。”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告訴我們,優秀的并購交易能夠穿越經濟周期,創造較高的股東回報,也是全球領先企業不斷自我更新、保持基業常青的關鍵之一。
在前期經歷復雜環境的考驗后,一些企業的實力會更加穩固,而有些面臨經營挑戰的企業為謀求進一步發展也樂于被并購,中國的跨境并購在2023年有望迎來初級反彈。
“對于有實力的中國企業來說,現在就是并購最好的時機。”蕭寅康說。
但來自海外的競爭對手,并不會坐等中國買家趕上。如何把握好海外并購的黃金契機,在全球領先企業中占據寶貴的一席之地?它需要中國企業進一步培養和提升專業并購能力,以及吸引更多擁有國際化經驗和海外并購專識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