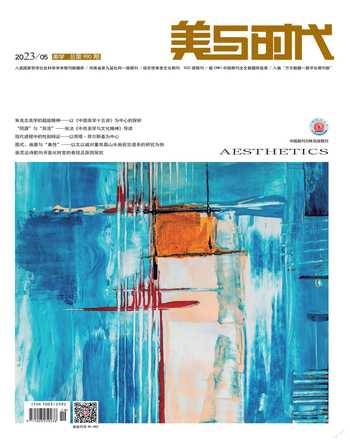和而不同不同而和



摘? 要:中西方復調思維有著本質的差異,“和而不同”體現中國復調思維的特點,“不同而和”反映了西方復調思維特性。中西方音樂文化相互借鑒學習,吸收優秀傳統文化。當代作曲家在吸納不同文化基因的基礎上創作具有民族化、個性化的音樂作品,體現了中西合璧、共通共融的思維形態。
關鍵詞:和而不同;不同而和;比較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系黑龍江省藝術科學規劃項目“中國當代復調曲集研究”(2022B114);黑龍江省教育科學規劃重點課題“中國當代復調音樂教學新理念與學科建設問題探究”(GJB1422665);哈爾濱音樂學院2022年研究生精品課程高質量建設項目“大型器樂作品分析”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西方文化歷史淵源有著很大的差異,中華民族以農耕為主的生活方式,群居的居住模式形成了“和睦相處”的文化氛圍。西方原始社會以狩獵生活為主,民族文化充滿探索精神,具有獵奇心理的思維模式。由于中西方民族文化與審美心理的差異,在藝術呈現方面表現出不同的形態,中國復調思維主要體現“和而不同”的和諧觀念,而西方復調思維主要體現為“不同而和”的審美追求。
“和而不同”出自《論語·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和而不同”是孔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君子可以與他周圍的人保持和諧融洽的關系。”“和而不同”顯示出孔子思想的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
“不同而和”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約公元前540-公元前480年)的著作中有所解釋,他曾說:“互相排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一切都是斗爭所產生的。”[1]19“自然追求對立的東西,它是從對立的東西產生和諧,而不是相同的東西產生和諧。……藝術也是這樣造成和諧的,音樂混合不同音調的高音和低音、長音和短音,從而造成一個和諧的曲調。結合物既是整個的,又不是整個的,既是協調的,又不是協調的,既是和諧的,又不是和諧的,從一切產生一,從一產生一切。”[1]19
朱世瑞教授從音樂的角度對上述兩個觀點進行總結,在其專著《中國音樂中復調思維的形成與發展》中曾寫道:“中國古人也說過‘君子和而不同,如果把‘君子比作美好的音樂,把‘和而不同比作音樂中不同因素的有機結合。那么,從廣義上說,東、西方的古代圣哲都曾預言,人類對‘和而不同——‘不同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的永恒追求,將會使廣義的復調永存于音樂的發展之中。”[2]
樊祖蔭教授曾在論文中這樣闡述:“中西多聲思維與多聲結構有著極大的差異,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學觀念的不同,借用‘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對此進行初步的闡析。”[3]
林華教授在其專著中從“和諧觀”角度論述相關的觀點,“由于不同的審美心理以及種種原因,中華民族的和諧觀強調和而不同,而西方民族的和諧觀追求的是不同而和,因此構成了西方音樂以縱向音響基本予以橫向運動的多聲格局,而中國傳統音樂追求以多樣化形式演奏同一旋律的支聲方式。這是兩種音樂織體觀念,各有自己的特色和韻味”[4]。
以上從哲學角度、音樂角度分別闡述了中西方“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的思維觀念,中國復調思維主要在相似的旋律中體現不同之處,而西方復調思維在不同旋律中尋找和諧的審美追求。
一、中國復調思維——“和而不同”
中國復調思維主要指傳統復調音樂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復調音樂的形成早于復調音樂理論的研究。中國藝術音樂專業化的發展模式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學習西方復調音樂理論,梳理傳統復調音樂思維的特征,表現為:線性思維、形象思維、群體思維。線性思維是中西方復調音樂的共性特征,但是,中國傳統音樂的線性思維與西方不同之處在于縱向的結合,西方復調音樂橫向旋律強調“線性”特征,縱向結合強調“對比”特征;而中國傳統復調音樂主要表現為同一旋律在多聲部以各種變體形態予以縱向結合。從整體上看,中國傳統復調音樂在縱橫方面都體現出“線性”特征。中國傳統的建筑,特別注意“流動的線條”,呈現出“線條化”的特征,例如,頤和園的長廊蜿蜒曲折,一眼望不到邊,“迂回”“婉轉”的線條蘊含著中國人傳統的審美原則。在傳統音樂方面,“線性”思維表現的最明顯特征為支聲復調。支聲復調是由同一旋律的各種變體形式縱向組合而成,依據縱向與橫向進行的不同方式,主要可分為:分合式、平行進行式支聲;裝飾性支聲、簡化式支聲、變化節奏式支聲、展開式支聲以及各種類型的綜合形式[5]。
在民族民間中廣泛地存在著支聲復調音樂,例如,廣西壯族民歌《環江米糯香》,主要是分合式支聲復調類型。第1-7小節,縱向音程關系主要由同度和其他度數組成,同度是“合”的主要特征,而其他度數是“分”的體現,表現為時分時合的織體組成方式(如譜例1)。
由樊祖蔭教授記譜的廣西德保縣民歌《唱相思》是二聲部分合式支聲復調的典型譜例,兩個聲部幾乎每小節都有同度匯合音,也有分開的音符(如譜例2)。
裝飾性、簡化式支聲復調更加突出不同聲部的同一“變體”形式,例如,江南絲竹《行街》,笛子、琵琶、小三弦等對主要聲部進行裝飾,縱向音為同度或八度的“交叉”,其他聲部對其他音進行裝飾,形成了裝飾性支聲復調(如譜例3)。
上例不同樂器組合演奏裝飾性支聲復調描繪了“邊走邊奏,婚嫁迎娶、廟會巡游”的音樂意象,中國傳統復調線性思維主要為描寫形象而服務。
中國傳統文化的“取象”思維,在于把“物”與“象”發生相關的聯想,明顯地表現為形象思維。中國畫藝術作品表現出“取象”思維,在“像與不像”之間達到平衡。中華民族的象形文字和單聲多調的語言是象形思維的文化體現。在傳統音樂作品中,《普安咒》形象地表現出“吟誦”的音調(如譜例4)。
中華民族“取象”的思維模式,決定了中國人不可能形成外向型的思維性格,而是內向型“自我反思”的行為表現,自我調節的思維能力來自“中庸”傳統文化,長期積累“自我體驗”意識便形成了“以和為貴”“中和之美”的審美理想[6]。
與人“和”,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中國人不突出個體思維,而是以團體為主的群體思維,達到“無我之境”。現實生活中的勞動號子、對歌等民俗性的音樂反映真實的人民生活,突出表現群體性音樂思維活動。例如,《搖櫓號子》領唱與合唱都是表現群體性勞動活動的具象聲音(如譜例5)。
中國傳統復調思維具有線條性、取象性、群體性特征,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為:支聲復調。傳統的復調思維強調“統一”,呈現“和而不同”特征,突出了中華民族中庸的審美情趣。中國音樂傳統復調思維繼續發展、深化演變為今天的復調音樂形態。
二、西方復調思維——“不同而和”
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突出個性化、思辨性、秩序性特征,個性化強調了個人的感官體驗,形成“二元性”的對立矛盾沖突,個性化的探索精神,從感官體驗中思考理性認知,突出分析與總結“形而上”的思辨性邏輯思維。理性思維多于感性思維的同時,強調規則,在對立中求得“統一”,復調音樂的賦格曲、賦格段都是表現思辨性、秩序性規則的典型范例。
西方“對立性”的思維傳統引導著早期復調音樂的形成。公元9世紀,以格里高利圣詠為固定旋律,在此基礎上附加平行聲部形成了奧爾加農,平行式奧爾加農逐漸發展為反向和斜向,華麗奧爾加農等。在奧爾加農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在已有的固定旋律上作即興對位形成了迪斯康特復調形式。與此同期的孔杜克圖斯復調形式由獨立寫作的新旋律取代了圣詠定旋律聲部,歌詞也不采用圣經經文,而是應用具有韻律的拉丁文詩歌。這一時期,教堂音樂用迪斯康特風格寫作的無詞復調短歌形成了克勞蘇拉復調形式,在克勞蘇拉無歌詞的上方聲部填上歌詞就形成了經文歌體裁。從西方早期復調音樂的演進歷史可以看出,格里高利圣詠作為固定旋律保持了幾個世紀的地位,它象征著教皇皇權,在多聲部音樂中,圣詠旋律的強勢聲部不可動搖,其他聲部作為附加聲部起到依附性作用,突出西方強調個性化的民族特征。
文藝復興時期,也就是嚴格復調黃金時代,個性化多聲部的對比,更突出二元性的矛盾沖突。帕萊斯特里那創作的《教皇馬切里》,每個聲部都是獨立的橫向旋律線條,縱向和弦構成了協和音響,形成了對立與統一的平衡(如譜例6)。
這一時期經典作品若斯坎創作的《圣母頌》,帕萊斯特里那的《如同小鹿》都運用了模仿復調對位技術。模仿復調對位技法,橫向進行表現為應句模仿主句,由于應句與主句縱向上錯位模仿并且同時結合,表現出縱向上的對比關系。自由復調發展過程中,繼續沿用對比復調與模仿復調的技術手段(如譜例7)。
自由復調時期,巴赫創作的《#f小調賦格曲》主題,兩個聲部為對比性旋律的縱向結合(如譜例8)。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傳統復調音樂強調“對比”思維,從格里高利圣詠單聲部音樂發展為奧爾加農,再過渡到經文歌等對比性質的多聲部音樂,早期復調音樂突出了個性化對立矛盾沖突。嚴格復調音樂時期與自由復調音樂時期的對比復調與模仿復調縱向疊置依然突出了對峙特點,因此西方復調音樂思維具有“不同而和”的形態特征。
三、中西方復調思維異同與融合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西復調音樂思維有著本質的差異,中國復調思維表現淡雅、中庸、散漫的“和而不同”的音樂性格,西方音樂追求張力、尋求個性化、思辨性、秩序性的思維模式。
近代以來,中西方復調思維呈現共融的發展趨勢。中國復調音樂作品融入對比性思維,西方復調音樂作品融合線性思維模式,運用支聲復調手法。中西方復調音樂思維融合,體現了對比性、統一性、個性化、規則性、民族化的共同特征。對比復調與模仿復調成為中西方復調音樂通用的規則,不斷尋求“統一”與“對立”的平衡點。20世紀以后,作曲家追求個性化、民族化的風格特征,復調音樂作品表現民族風格,彰顯個性化創作特征,在繼承傳統規則基礎上,創新發展,尋求突破。
例如,賀綠汀創作的中國經典復調音樂作品《牧童短笛》描繪了牧童悠閑地騎在牛背上吹笛子的畫面,上下方兩個聲部形成了對比鮮明的旋律線條,并列對置的線條在對比中融合統一(如譜例9)。
陳銘志先生創作的《小變奏曲》第1-8小節運用了二聲部對比復調織體,上方聲部是主要旋律,下方聲部為短句式呼應型織體呼應上方聲部(如譜例10)。
法國作曲家弗朗克創作的《交響變奏曲》運用了支聲復調織體。2-4小節,四個聲部形成兩個外聲部的持續音織體,內聲部隱伏線條演奏同一旋律形成支聲復調。第1小節上下方兩聲部各自形成平行八度(如譜例11)。
肖斯塔科維奇創作的《弦樂四重奏》OP.101,第一樂章主題的上、下聲部形成嚴格平行進行式的支聲復調織體(如譜例12)。
四、結語
當代,中西方相互學習,吸收各民族文化之所長。中國作品中運用西方復調技法,西方音樂作品融入中國傳統復調思維、五聲音階、民族音調等,中西方現代作曲家努力尋求個性化、民族化的創作風格,彰顯文化自信。
參考文獻:
[1]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古希臘羅馬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19.
[2]朱世瑞.中國音樂中復調思維的形成與發展[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2:237.
[3]樊祖蔭.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中國傳統多聲部音樂的思維特征與中西多聲結構差異原因之探究[J].中國音樂,2016(1):78-94,128.
[4]林華,葉思敏.復調藝術概論[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0:440.
[5]張磊.論支聲及其在西方現代音樂中的應用[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94-107.
[6]林華.音樂審美心理學教程[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335.
作者簡介:孫中華,哈爾濱音樂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