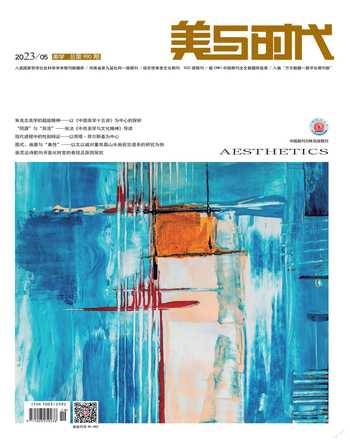淺析李國文《改選》中的干部形象
摘? 要:李國文的小說《改選》是“百花時代”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發表于《人民文學》1957年7月特大號。小說發表后,由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問題,在“反右運動”中遭到嚴厲批判,被打成“毒草”。在對小說中的工會主席與老郝兩個干部形象重新進行分析中,肯定“官僚主義”的存在在新時期有其歷史發展必然性的同時,指出在克服“官僚主義”的問題上,需要的是對替代其角色的新型管理者,即“干部”形象的重新想象。在這一過程中,又因工農干部其自身的局限性,使得塑造走進了一個困境。而遭到猛烈批判的悲劇性結局——“老郝之死”,在這一意義上,是作者在“寫真實”的指導思想下對于這一困境的回避性解決。
關鍵詞:李國文;改選;干部形象;老郝
1957年,是“百花文學”從盛開到凋謝的一年。在“百花時代”[1]1這一年多的時間里,《人民文學》作為國家重要刊物之一,“對倡導‘干預生活的創作,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1]110。甚至到了1957年中期,其主辦者還準備籌劃出更大膽的革新,預告7月號所準備增加篇幅出特大號的消息①。這時的《人民文學》主持者當然無法預知,形勢正在悄然地發生變化——毛澤東在5月一份當時沒有公開的文件中已開始指示:“幾個月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應當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條主義,許多錯事不能改正。現在應當開始注意批評修正主義。”[2]234而面對正如火如荼的“百花現象”,毛澤東認為:“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于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并不要釣。”[2]235-236
而對此毫不知情的《人民文學》繼續在7月號上準備了190頁的特大號。這一期中,小說刊登了李國文的《改選》、宗璞的《紅豆》、豐村的《美麗》。這三位作家在接下來的“反右運動”中無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右派”。孫秉富在其《批判“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毒草》一文中分別對這三篇小說進行了批判。孫秉富認為《改選》“是把老郝這位辛辛苦苦為群眾辦事的老工人,作為悲劇角色來描寫”,這篇作品“惡毒地把為群眾辦事的老工人和愛戴他的工人群眾跟共產黨和工會組織對立起來,把工廠的黨政領導、工會主席和委員們都寫成懶散、官僚的卑劣人物”;豐村的《美麗》則是歌頌了一個“偽君子”形象的秘書長與他和季玉潔之間的不正當情感;而《紅豆》“也是一株莠草”,作者居然將江玫 “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愛情至上的個人主義者”歌頌為“‘健康的黨的工作者”[3]。
《人民文學》的革新宣告失敗,并開始轉載其他報刊上的一些文章來承認錯誤,被轉載的除了上述提到的孫秉富的文章,還有李希凡的《從〈本報內部消息〉開始的一股創作上的逆流》。針對七月號的三篇小說的讀者反饋——有一百位多讀者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其中對‘改選的意見有四十四件;對‘美麗的意見有五十七件;對‘紅豆的意見有二十二件”[4]35,編輯部也公開做了自我檢討②。
與后兩篇因為愛情書寫問題而遭受批判的小說不同,李國文的《改選》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思潮”作品的原因,是在于他對小說中兩個干部的塑造——一個是官僚作風式的工會主席,一個是悲劇英雄式的老干部郝魁山(簡稱“老郝”),以及小說悲劇性結局的設定上。當時對小說的關注因為政治傾向等各方面因素,過多地集中在小說所敘述出來的干部特征上,認為《改選》是對黨的領導的攻擊,“是一支隱藏著敵意的向黨進攻的毒箭”[4]35。在這樣的政治認知限制下,潛藏在干部特征背后的其他表達訴求便被若有若無地忽略了。
小說雖然主要講述的是老工會委員老郝的個人故事,但這個圍繞“改選”主題展開的故事存在著兩條敘事線條:一條是以工會主席為敘事主體,一條是以老郝為敘述主體。在敘述過程中,它們并不彼此獨立,而是相互聯結的。這兩條主線上各有三個敘述情節——每一情節都有一個相同的因素,使兩條主線交叉、纏繞。這三個相關因素分別是“版(板)”的尋找、“職位”變動與“改選”現場。本文將從文本出發,分別對工會主席與老郝這兩個人物的“干部”身份進行分析,試圖從傳統、現實與想象來解讀《改選》中的“干部”塑造。
一、官僚形象的塑造前提:
存在的合法性與“反官僚”主題
正如蔡翔所說,如果當代文學通過塑造“好干部”“也即社會主義‘帶頭人的形象描述,表達了自己對‘革命中國的新型的‘官員的想象,并試圖以此來重新結構中國的基層社會。那么,它的另一個任務則必然是對現實中的另一類‘干部進行批評乃至批判。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反官僚、反特權的文學主題”[5]103-104。工會主席這一角色,就是小說《改選》中的另一類“干部”。在小說中,對這一人物形象的敘述與描寫,模糊而抽象——無名無姓,沒有具體的外貌描寫,也不涉及情感表露。他展現的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一類人,即官僚的集合形象。
主線的前兩個敘述情節各從不同的角度刻畫出工會主席的官僚風氣。在第一個部分中,是關于他為了連任所要求的“兩化一版”,即“工作概況要條理化,成績要數字化,特別需要的是生動的樣版”[6]352。為了完成這一“樣版”的設計,他沒有去參加工人老吳頭的葬禮,而之所以沒有派人去尋回因主持葬禮而缺席“樣版”討論會的老郝,則是因為心想著“得罪了死者倒不用怕的,反正他也不會提意見了,冒犯了群眾那可劃不來”[6]353。第二個部分,則是描寫他對上級的察言觀色與見風使舵,從而官運亨通、春風得意。這兩個部分的描述,將工會主席作為一個自私自利、曲意逢迎的小官僚形象展露無遺。但是,官僚形象的塑造, 并不是寫作的主要目的。這一形象的塑造,是為了揭露現實的陰暗面,為了通過反官僚的主題表達對未來國家的制度建設與政治生活的想象。而這一想象,在中國當代社會中,就是對“干部/群眾”這一關系的重新構建。為了完成這一想象,革命首先要摧毀的就是帶有傳統中國的政治或宗法等級制度的延續的官僚形象。因此,無論在寫作還是實踐中,在面對官僚主義時,就要注意到兩個特點——一是明確塑造這一形象的目的,二是認識到這一形象的存在其實是依托于中國傳統的制度觀念,而非某一種意識形態。姚文元在《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和創作傾向》中寫道:
官僚主義,當然也應當批評,我們從來就主張用自我批評的精神去揭露工作中的缺點,我們反對無沖突論。但官僚主義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也并不占主要地位或統治地位,因此,不能夠把犯有官僚主義錯誤的人都丑化成人民的敵人,或者把官僚主義描繪成統治一切的一種力量,仿佛現在我們社會中已經被官僚主義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了。——這種歪曲的描繪正是右派分子所衷心希望的。這是“清規戒律”嗎?不,這是生活的真實,在這個充滿朝氣的年青的如旭日才升的社會主義祖國里,不論在什么地方,官僚主義都沒有合法存在的權利,官僚主義不管在某個地方或某個時候如何厲害,它決不可能永久存在,而是被當作一種舊意識舊作風的殘余,被黨的領導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斷地克服下去,社會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保證著勞動人民有可能發揮著最大的民主同無限的創造性,因此也就有著不斷地克服官僚主義的社會條件。[7]437
在這里,姚文元認為“官僚主義并不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從而把官僚主義解釋成“一種舊意識舊作風的殘余”。在前文的分析,已經指出官僚主義的存在的確是一種歷史性的延續,但將這一現象全然歸咎于“舊”,就忽略了即使是“舊”的殘余, 也是借助于革命的機體與現行的制度而存活著的這一現實狀況。在此狀況之下,他的這一判斷就陷入了一種理論悖論之中——“如果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產生官僚主義,那么,所謂的‘繼續革命就將失去它的理論支持。”[5]105
從這一層面來說,李國文所塑造的工會主席這一小官僚形象的真實性,在理論與實踐方面都有其存在的依據,是可以從社會主義實踐中尋找到現實原型的。但同時我們應警惕地注意到,實際上工會主席這類的官僚形象,已經在由傳統的官僚逐漸進化成一種潛伏在社會主義內部的新型官僚——他對“樣版”的熟練運用,“善于察言觀色、領會上級意圖”[6]360,都體現出了官僚制度死灰復燃甚至異化的可能。正是為了摧毀傳統的官僚制度并防止新型官僚制度的出現,社會主義實踐“必須對‘干部進行重新的想象”,“而在這一過程中,文學也必須相應地重新編碼乃至進一步虛構”[5]100。
二、新型管理者的塑造:
“干部/群眾”的新關系搭建
在敘述這一部分之前,首先有必要對“干部”這一身份概念做一個基本的辨析。實際上,“干部”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所特有的,它本身是一個日本轉譯西方的詞匯。在孫中山的《革命原起》中就提到過“遂開乾亨行于香港,為干部,設農學會于羊城,為機關”。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黨章中,首次使用了“干部”這一詞。而毛澤東多次強調過培養干部的重要作用,如“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在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8]等。之后中國共產黨的十二大黨章更是明確指出:“黨的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
《改選》中的老郝就是這樣一個“公仆”形象的人物。關于他的敘述,同樣體現在“找‘板—職位—改選”這一敘事線條中。在工會主席忙著尋找“版”的時候,老郝也同樣為了“板”而忿忿。只不過,前者是為了自己的連任而尋找報告的“樣版”,而老郝則是想為去世的工友老吳頭要一副好的“棺材板”。第二部分主要講述了老郝的職位變動:原本是工會主席的老郝,因為念錯了官樣文稿而被上層領導認為犯了“政治上的原則錯誤”,降為副主席;為了盡快修繕工房,老郝冒雨堵在廠長家門口,最終迫使廠長下命令讓維修廠長、科長住宅的工人先去“老工房堵漏子”,因此在黨內受到了“不應該這樣對待領導”的批評;為了幫助工友解決最實際的早餐問題,主張盤下并改建小磨房,卻犯了“經濟主義”的錯誤,被降為勞保委員;休養所的選址出現問題,又是老郝莫名被背上黑鍋,而最終,他被排擠成了一個掛名委員。但是,“大家越來越尊敬他,親近他,信任他,在好多工友的心目中,老郝就是工會,工會就是老郝,有事都來找他。”[6]361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影響老郝政治身份變動的事件,既涉及工廠中的公共領域,又關涉到工友們的私人生活。“公共/私人”領域的重疊,使得老郝即便在“公權力”中被排擠成了一個掛名委員,依舊從工友們的認可中得到了辦事的合法性。而這一合法性正是首先建立在他對工友們的關心,并處處維護他們的利益之上。這樣的干部形象,在當代小說中并不少見,一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而在新中國初期的生產隊、合作社和工廠等這些單位中,并沒有公共/私人之間的絕對分治,兩者處在一種互動和轉化的關系之中。因此,干部不僅要在大的社會改革、運動中發揮作用,同時也要參與群眾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獲得群眾在認識和情感上的支持。
從這一角度來說,老郝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式的干部,在與群眾的關系互動中,他是合格的。但同樣是在“為人民服務”的過程中,老郝卻被迫從中心走向邊緣,甚至最后被踢出了工會委員的候選名單。這樣的遭遇,一方面顯示出了官僚主義對“干部/群眾”關系的破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這一關系對干部的嚴格要求暴露出了老郝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在這兩方面力的共同作用下,老郝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困境中。
三、“老郝式”干部的困境:
“老郝之死”的外因與內因
姚文元在提及《改選》時,曾經說過這是“一篇政治上有根本性的錯誤的小說,它的畫面不僅陰暗,而且帶著絕望的、冷漠的控訴的性質,仿佛生活中有一種無法抗拒的巨大的壓力,把正直的人都壓倒了,壓死了”[7]444。他特別提到《改選》的結局,稱之為“最后那個帶著恐怖色彩的死亡的場面”,這一結局“使人感到陰沉絕望”[7]445。因為“這好像在告訴人們:你們看,郝魁山就這樣死亡了,官僚主義的、壓制工人的工會不受絲毫影響,照樣地工作。生活還是老樣子,死的白白地死掉,作威作福的依舊在作威作福。”[7]445
但是從文本分析入手再來看這一問題,事實上,并不能把造成“老郝之死”的原因全然歸結于姚文元所謂的“官僚主義的、壓制工人的工會”。不能否認,這一點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正是因為工會主席將老郝剔除在名單之外,對老郝的刺激,催化了老郝之死。但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是在于老郝本身。在“干部/群眾”的關系搭建中,對“干部”本身是有著嚴格要求的——除了搞好與群眾的關系,具有高度的獻身精神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要求干部擁有較高的政治覺悟。這一政治覺悟,不僅在于政治信仰的堅定,也在于面對政治生活中的各種斗爭的態度。
同樣是在第二部分中,老郝為了群眾的利益,敢于與各種各樣的干部據理力爭。而在自己遭到不公正待遇,職位一降再降的時候,他卻選擇了接受,并且表現出了一種退讓的樂觀。除了最后當老郝知道他被排除在改選之外的第一次缺勤外,在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中,他都沒有去反抗。這就體現出了老郝這個人物身上同樣也帶有著的長時期受壓迫的中國農民的軟弱與忍讓。這樣的特性,使得他在面對不公正的待遇時,一方面不想去抗爭,另一方面也無力去反抗。關于老郝身上所體現的這種農民的特性書寫,可以追溯至魯迅當年所批判的國民劣根性。在新時期中,這樣的“劣根性”雖然隨著時代的轉變而逐漸消失,但是并未被徹底清除,正如老郝始終都沒有形成與官僚干部作斗爭的政治覺悟。雖然小說最后以工友們在會議上的抗爭與老郝獲得3405票的絕對優勢當選,但這一特性的存在,使得老郝無法成長為一個真正的新型管理者,無法達到“干部/群眾”關系中對干部的嚴格要求。
因此,作為干部的老郝實際上已經陷入了一種困境。他的死并不能被簡簡單單地解釋成一種反諷的手法,而更像是對于這一困境的一種消極反抗。有的研究者認為“他的死可以看作是一種逃脫,因為他實際上是承擔不起廣大人民群眾的重托”[9]——老郝并非沒有當過主席,而只要他沒有真正擺脫那種軟弱和忍讓的特性,只要類似工會主席這樣的小官僚繼續存在,他依舊沒有能夠與之斗爭的覺悟與能力。那么,他只能再次陷入不斷被降職、被邊緣化的循環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老郝之死”是作者在“寫真實”的思想指導下,對“老郝式”干部何去何從的一種回避性解決,他的死亡成為了他生命崇高的落幕。
而這樣的干部,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是大量存在的。因為“老郝式”人物的本質,是先進性與落后性在這一時期的農民身上的矛盾結合。而由于當代中國社會的需要,對基層的管理又必須大量依賴于這些思想覺悟相對更高的農民與工人,但同時,他們的思想覺悟又并未完全達到政治要求所需要的程度。這樣的尷尬處境,使得“老郝式”干部陷入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所以,《改選》借助老郝這一人物所想要處理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社會主義實踐在培養工農干部身上所面臨的問題。
四、結語
在小說的第三部分,除了結尾處老郝的直接死亡,還有一個地方同樣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即小孫女的感覺。從一開始有工友反映為什么名單沒有老郝,再有人就“休養所事件”為老郝喊冤,這時“小孫女覺得她爺爺在哆嗦”;而之后提到“老工房”與“老吳頭”的事情時,“小孫女覺得她爺爺平靜了”[6]363-364。為什么要借助于小孫女這樣一個孩童的視角來表達老郝的感受?這個問題或可另文再述。但這一角度使得“老郝之死”這一啟發性的悲劇結局,除了作為一種反諷手法和作為一種對待困境的回避性解決之外,值得被更深入的探討。
注釋:
①參見《人民文學》1957年第5、6期合刊“編后記”。
②《人民文學》的自我檢討,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關于七月號的傾向”“關于小說”和“關于雜文及其他”,因為本文涉及的是小說部分的內容,因此其他部分僅在注釋中簡要提及。
參考文獻:
[1]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C]//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M].北京: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
[3]孫秉富.批判“人民文學”七月號上的幾株毒草[N].中國青年報.1957-09-06(3).
[4]這是什么樣的“革新”?——讀者對本刊七月號的批評[J].人民文學,1957(1):34.
[5]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一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李國文.改選[C]//本社編.重放的鮮花[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
[7]姚文元.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和創作傾向[C]//郭冰茹,編選.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1949-2009(卷1).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12.
[8]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M]//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527.
[9]汪海鷗.軟弱的英雄:讀李國文《改選》[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86-87.
作者簡介:莫雨曦,復旦大學古籍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