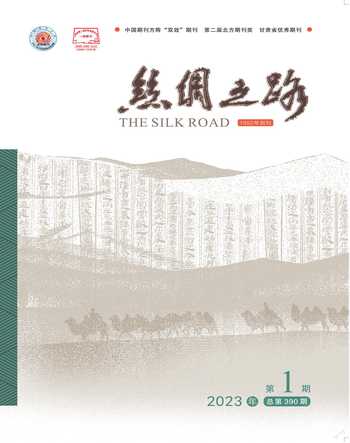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
石智勇 潘春輝
[摘要]研究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挖掘其歷史背景、內(nèi)容、成因及意義,可加深今人對近代國人地理認識活動的了解。本文通過分析相關(guān)史料,可知國人是在挽救邊疆危機、開發(fā)西北的背景下,認識到陜西礦產(chǎn)具有蘊量巨大、種類多樣、分布極廣、開發(fā)程度不高的特征。該認識的形成與陜西礦產(chǎn)地理實況和國人知識背景有關(guān),對地理知識生產(chǎn)、西北開發(fā)和陜西地位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關(guān)鍵詞]20世紀30年代;國人;陜西;礦產(chǎn)地理
[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3115(2023)01-0071-07
唐朝滅亡后,隨著政治中心的轉(zhuǎn)移,陜西失去了往日輝煌。進入近代,陜西已經(jīng)變成經(jīng)濟落后、社會發(fā)展緩慢的地區(qū)[1]。20世紀30年代,位于西北內(nèi)陸的陜西再次引起國人的關(guān)注,大家紛紛來到陜西考察,帶著好奇的眼光重新打量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化發(fā)源地,包括礦產(chǎn)資源在內(nèi)的一切地理事物成為他們認識的對象。“地理認識,就是人們對一定區(qū)域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現(xiàn)象,資源及特征的觀察、了解、熟悉與認知的過程。”[2]目前學(xué)術(shù)界涉及20世紀30年代國內(nèi)知識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的相關(guān)研究罕有。張用建曾在其文章中論述過抗戰(zhàn)前10年部分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情況[3];吳加峰亦在其文章中探討過顧執(zhí)中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4];劉平則在研究1932年上海銀行界人士來陜考察的文章中,提及過這段歷史,但卻未深入探討[5]。在學(xué)界前輩的已有研究基礎(chǔ)之上,力圖深入探究這段歷史,以期為學(xué)術(shù)界研究盡一份綿薄之力。
一、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認識的時代背景
20世紀30年代,陜西礦產(chǎn)資源成為國人地理認識的對象,與當(dāng)時特殊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依據(jù)史料分析,挽救邊疆危機和開發(fā)西北是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進行地理活動的主要時代背景。
(一)挽救邊疆危機
進入20世紀30年代后,中國依舊是貧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內(nèi)有腐敗無能、兇殘暴虐的國民黨反動政權(quán)欺壓民眾,外有侵略成性、嗜血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虎視眈眈。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按照蓄謀已久的計劃,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不久之后,東北軍執(zhí)行國民黨政權(quán)的“不抵抗”錯誤政策,大部撤進關(guān)內(nèi)。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先后淪陷。東北地區(qū)大片領(lǐng)土的丟失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邊疆危機的開端。日本的侵略野心顯然不止于侵占中國東北地區(qū),他們還將魔爪伸向內(nèi)蒙、西北各省。日本特務(wù)不僅誘使內(nèi)蒙部分王公前往長春去面見傀儡溥儀,“所以前年春間日人某氏介紹德王卓王等乘坐日機飛往長春,謁見溥儀”[6],還暗地里在內(nèi)蒙進行分裂中國的陰謀。“可是去年九月發(fā)動直至目前高唱的內(nèi)蒙自治運動,至少也是受了日偽的慫恿和煽動而起的。”[6]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者不僅派特務(wù)秘密來往西北各地[7]288,還派日僑到陜西獲取物產(chǎn)等方面的情報[8]。此時,中國的東北地區(qū)大部淪為日寇的殖民地,內(nèi)蒙、西北地區(qū)亦岌岌可危,中國北方的邊疆危機日益嚴峻。“國人始知西北之危機,不減于東北,而關(guān)系中國前途之重要,實較東北為甚”。[7]98部分國人為此來到陜甘等西北省份,進行實地考察,以達到“保護西北,使不至淪為東北之續(xù)”[9]7的目的。在當(dāng)時國人看來,礦產(chǎn)資源“關(guān)系國防軍事之命脈”[10]13,是不可忽視的了解對象。可見,挽救邊疆危機是國人針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進行認識活動的時代背景之一。
(二)開發(fā)西北
民國建立之后,便有國人提出開發(fā)西北的建議。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其著作《實業(yè)計劃》中便提出建設(shè)西北鐵路、開發(fā)西北資源的計劃。馮玉祥、楊增新亦提出過各自的開發(fā)西北計劃。1916-1917年,途經(jīng)陜西的謝曉鐘亦提出開發(fā)西北礦藏的意見。即“煤鐵諸礦,所在而有,急宜籌措資本,設(shè)立公司,依照新法從事采掘”[11]。1928年,國民政府確定開發(fā)西北為緊要政務(wù)。1930年,國民政府建設(shè)委員會制定《西北建設(shè)計劃》,民國時期開發(fā)西北活動緩緩拉開序幕。1931年,早已對中國垂涎已久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在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國民黨東北軍大部撤進關(guān)內(nèi),不久之后,東北地區(qū)落入敵手,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東北淪陷的情況下,國人開始關(guān)注西北地區(qū)。1932年,日寇在上海發(fā)動“一·二八”事變,南京受到威脅,國民政府遷至洛陽辦公。國難當(dāng)頭,開發(fā)西北不再只是少數(shù)人呼喊的口號,而成為大多數(shù)中國人關(guān)注的社會熱點問題。“開發(fā)西北問題,從前僅少數(shù)人呼喊,自政府遷洛以來,始為多數(shù)人所注意。”[7]72此時,開發(fā)西北活動已進入高潮階段,得到更多國人的支持。“時海內(nèi)新聞亦高傳開發(fā)西北之聲浪。”[10]2在一些國人眼中,開發(fā)西北已成為迫在眉睫之事。“西北之開發(fā)亦為當(dāng)務(wù)之急”。[12]在當(dāng)時國人看來,前往西北地區(qū)實地考察是西北實際開發(fā)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國民政府甚至出臺獎勵考察西北的政策[13]174。于是,大批國內(nèi)各界人士組成考察團,紛紛來到西北地區(qū)進行實地考察[14],礦產(chǎn)資源則是考察內(nèi)容之一[13]177。由此可見,正如陳賡雅所言“并促開發(fā)計劃之早日實現(xiàn)”[15]8,來到陜西的國人對當(dāng)?shù)氐V產(chǎn)資源進行地理認識活動本意在于為早日實現(xiàn)開發(fā)西北計劃提供幫助。
二、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認識的主要內(nèi)容
陜西地處我國西北內(nèi)陸,是我國的資源大省之一,礦產(chǎn)資源十分豐富,136種礦產(chǎn)已被知曉,27種礦產(chǎn)儲量位居全國前三,37種礦產(chǎn)儲量位居全國前十[16]3。陜西礦產(chǎn)資源具有蘊藏量巨大、種類豐富和分布特色明顯的特點。在挽救邊疆危機和開發(fā)西北的時代背景下,他們的認識側(cè)重于實用。數(shù)量、種類、分布和開采利用情況成為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認識的重點。
(一)陜西礦產(chǎn)資源的蘊藏量巨大
20世紀30年代來陜的國人通過對陜西礦產(chǎn)的了解,普遍意識到三秦大地蘊藏著數(shù)量巨大的礦產(chǎn)資源。顧執(zhí)中隨陜西實業(yè)考察團來陜后,發(fā)現(xiàn)陜西煤礦石蘊量巨大,“總共四千七百二十九兆噸”[9]55。這個數(shù)字是當(dāng)時陜西建設(shè)廳調(diào)查得出的官方數(shù)據(jù),顧執(zhí)中認為陜西蘊藏的煤礦石數(shù)量實際上多于官方統(tǒng)計數(shù)字,官方數(shù)據(jù)存在遺漏,并不準確。“此數(shù)系核減折中數(shù)目,遺漏甚多。”[9]55-56奉母命前往陜西考察的林鵬俠發(fā)現(xiàn)陜西的礦產(chǎn)資源在數(shù)量上極其豐富,“查陜省山脈縱橫,蘊藏極富”[10]12。林鵬俠認為從咸陽到榆林,這片區(qū)域蘊藏數(shù)量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石油資源是當(dāng)?shù)厮械V產(chǎn)中最豐富的。“沿線礦產(chǎn)豐富,尤以石油為最”[10]23,她甚至認為陜西蘊藏的石油可以滿足全世界的需求。“以陜省數(shù)百方里內(nèi)儲油之富,原可供全世界之需”。[10]23陳賡雅來到陜西后,也發(fā)現(xiàn)陜西蘊藏巨量礦產(chǎn)資源的情況。以石油為例,在陳賡雅眼中,陜西石油蘊量驚人,甚至多到從巖石里溢出,地面、水面到處是石油。“油泉先后涌現(xiàn)者,達四五十處,多自石巖流出,或由溝底、河邊,涌浮于水面。”[15]307陳賡雅甚至認為,開采陜北石油可以解決西北地區(qū)的燃料問題,“提煉良品,以解決西北燃料問題”[15]307。除此之外,陳賡雅還提到,陜西的藍田玉、鉛、銅、砂金、石棉、翡翠、汞、銀、水晶等礦石蘊量也十分巨大,只是缺少開采:“更不勝枚舉,惜多未開發(fā)。”[15]30720世紀30年代來陜考察的陜西實業(yè)考察團也認為陜西礦產(chǎn)蘊量豐富,開采礦產(chǎn)資源是考察團眼中未來陜西最有發(fā)展前途的事情。“吾人平日對于陜西實業(yè)之觀念,認為蘊藏最普遍而前途最有普遍而前途最有希望,厥為礦產(chǎn)。”[17]127何慶云和顧執(zhí)中一樣,都跟隨陜西實業(yè)考察團來陜考察。顧執(zhí)中考察的范圍主要在陜北地區(qū),何慶云與之不同,他主要考察陜南地區(qū)。何慶云在陜南考察時,發(fā)現(xiàn)陜南的礦產(chǎn)資源蘊量豐富的情況,“陜南礦產(chǎn)富饒,固不待言”[18]70。
(二)陜西礦產(chǎn)資源的種類多樣
陜西地跨不同的地質(zhì)構(gòu)造單元,成礦條件有利,礦產(chǎn)種類多樣[19]139。從部分旅陜游記中分析,20世紀30年代,一些國人認識到陜西礦產(chǎn)資源種類并不單一,種類多樣成為他們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之一。顧執(zhí)中曾經(jīng)在其游記里面,將其得知的所有種類陜西礦產(chǎn)歸納總結(jié)。顧執(zhí)中共發(fā)現(xiàn)金、銀、銅、鐵、錫、煤、石油、石棉等51種礦產(chǎn)[9]16-26。侯鴻鑒則在其游記中列出5種陜西礦產(chǎn):“有延長的石油、縣的鐵、平利的石棉、藍田之玉、大荔之鹽。”[20]132林鵬俠在其游記里,提到過陜西的7種礦產(chǎn)[10]12。陳賡雅來陜后,發(fā)現(xiàn)的陜西礦產(chǎn)有15種[15]307。何慶云在陜南地區(qū)考察時,發(fā)現(xiàn)光在南鄭縣境內(nèi),就有煤、銀、硫磺、銅、鐵、錫等6種以上礦產(chǎn)資源[18]46。可見陜西礦產(chǎn)資源種類之多樣。1936年,《旅行雜志》刊載李文一漫游關(guān)中和陜南地區(qū)的游記。李文一到達南鄭縣后,也發(fā)現(xiàn)陜西的一個縣域竟蘊藏多種礦產(chǎn)資源。他在游記中記述南鄭縣蘊藏銀、煤、石灰、金、鐵、銅、錫、青土、硫磺等9種以上的礦產(chǎn)資源[21]301。陜西實業(yè)考察團則在陜南地區(qū)發(fā)現(xiàn)煤、鐵、銅、金、銀、鉛、石棉、鹽、硫磺共9種礦產(chǎn)資源[17]109-124。
(三)陜西礦產(chǎn)資源分布極為廣泛
陜西是我國的資源大省之一。資源分布廣泛是陜西礦產(chǎn)資源的主要特點之一[22]。在20世紀30年代,分布極為廣泛,遍布全省是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內(nèi)容之一。林鵬俠認識到陜西礦產(chǎn)資源不僅蘊量巨大,部分還遍布陜西全境:“蘊藏極富,五金礦產(chǎn),布于全境。”[10]12就石油資源而言,林鵬俠認為陜西石油分布很廣泛,省境內(nèi)幾乎所有地方都有石油,“幾于無地不見”[10]12。她甚至在游記里,說明了石油在陜西分布范圍。“幾占全省之半”。[10]12顧執(zhí)中在陜期間,亦觀察到陜西的煤資源分布很廣泛的情況,陜北、關(guān)中和陜南都蘊藏有煤資源,“陜西產(chǎn)煤之地,共有三區(qū),即關(guān)中、漢中、榆林”[9]56。在顧執(zhí)中看來,陜西不光只有煤分布廣泛,石油資源的分布范圍也很廣闊:“陜西油礦之分布,大致在洛河、延河、無定河等流域,面積極廣。”[9]74陳賡雅旅陜期間,則認識到陜西煤資源在陜北、陜南都有分布,分布范圍可以稱得上寬闊,“煤礦,陜南北均產(chǎn)之”[15]307。1935年,侯鴻鑒來到陜西,在他留下的記述中,可以發(fā)現(xiàn)在他眼里,陜西礦產(chǎn)從北到南都有分布,范圍極廣,“有延長的石油、沔縣的鐵、平利的石棉、藍田之玉、大荔之鹽”[20]132。
(四)陜西礦產(chǎn)資源開發(fā)程度不高
陜西礦產(chǎn)資源豐富,然而開發(fā)程度不高,這是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資源較為普遍的看法。顧執(zhí)中在陜期間,實地調(diào)查陜西多處礦廠。在宜君縣,他發(fā)現(xiàn)宜君一些地區(qū)依舊采用落后的方法開采煤礦石,開采規(guī)模不大[9]47。抵達陜北甘泉縣后,顧執(zhí)中注意到當(dāng)?shù)靥N藏鐵礦資源,且質(zhì)量上乘,但未停止開發(fā)之前,當(dāng)?shù)夭扇÷浜蟮募夹g(shù)方法開發(fā)該鐵礦[9]64。不僅宜君、甘泉兩地,顧執(zhí)中甚至認為陜西全省的礦產(chǎn)開發(fā)程度都不高,“遂致貨棄于地,無人過問”[9]62。林鵬俠來陜之后,也發(fā)現(xiàn)陜北等地開采煤礦的技術(shù)落后,開采礦石數(shù)量不多的現(xiàn)狀。在她看來,當(dāng)?shù)孛旱V開發(fā)程度遠遠不夠,“系用土法開采,技術(shù)幼稚,所獲甚微”[10]12。李文一在陜西南鄭縣時,發(fā)現(xiàn)南鄭縣的天然富礦特別多,“南鄭的天然富源極多”[21]301。然而卻存在“但用土法開掘,生產(chǎn)量不多”[21]301的問題,甚至很多礦產(chǎn)都沒有經(jīng)過開發(fā)[21]301。李文一不禁發(fā)出“貨棄于地,殊屬可惜”[21]301的感嘆,這更反映出當(dāng)時陜西礦產(chǎn)資源開發(fā)程度低的史實。陳賡雅來到陜西之后,發(fā)現(xiàn)延長石油開發(fā)過程中,存在“資少機劣,未著大效”的情況[15]307。此時的延長石油仍掌握在國民黨政權(quán)手中。陜西其他礦產(chǎn)資源更是存在“惜多未開發(fā)”[15]307的問題。他還認為陜西全省都存在“礦產(chǎn)之待開發(fā)”[15]308的問題。何慶云在陜南調(diào)查時,發(fā)現(xiàn)已知陜南各礦甚至都沒有專業(yè)人士進行詳細勘探[18]70,有效開發(fā)更是無從談起。在他看來,陜南礦產(chǎn)資源開發(fā)程度明顯處于較低水平。
三、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認識形成的原因
蘊藏量巨大、種類多樣、分布極廣、開發(fā)程度不高是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形成的四點認識。國人之所以會形成這四點認識,與近代陜西礦產(chǎn)的實際情況和國人的知識背景有關(guān)。
(一)近代陜西礦產(chǎn)地理實況
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大都形成于其旅陜期間,結(jié)合有關(guān)近代陜西礦產(chǎn)的相關(guān)史實記載,基本可以斷定近代陜西礦產(chǎn)地理實況是他們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部分認識成因。今日的陜西是全國有名的礦產(chǎn)資源大省,礦產(chǎn)資源的蘊量十分豐富。煤、石棉、大理巖等24種礦產(chǎn)被探明儲量位居全國前三[19]3。在近代中國,一些隸屬于陜西省建設(shè)廳、中央地質(zhì)調(diào)查所和地質(zhì)研究所等官方機構(gòu)的專業(yè)人員曾經(jīng)對陜西礦產(chǎn)的蘊藏量進行過調(diào)查活動。從調(diào)查的結(jié)果來看,近代陜西礦產(chǎn)的蘊藏量是十分可觀的。1923年,王竹泉在考察陜北地區(qū)地質(zhì)礦產(chǎn)等情況后,提出陜北地區(qū)侏羅紀地層的煤礦石遠景儲量多達904億噸[19]71。1928年和1932年,趙國賓曾兩次前往渭北地區(qū)調(diào)查當(dāng)?shù)氐拿骸⒄惩梁褪規(guī)r,他認為陜西渭北地區(qū)蘊藏著25億噸煤礦石資源[19]71。1938年,陜西探礦人員呂翕聲對陜南地區(qū)的鐵礦石資源進行調(diào)查,他提出陜南七縣蘊藏著儲量達2800萬噸的鐵礦石[19]73。基于上述史實可知,礦產(chǎn)蘊量豐富是近代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實況之一。在解放前,被發(fā)現(xiàn)的陜西礦產(chǎn)種類并不多,根據(jù)官方史料記載,陜西被認為僅蘊藏著石油、煤、鐵、錳、銅、砂金、石墨和黏土這8種礦產(chǎn)資源[19]69。種類雖不豐富,卻也不能稱之為單一,種類多樣是近代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另一個實況。在近代中國,陜西被發(fā)現(xiàn)的礦產(chǎn)資源在陜北、關(guān)中和陜南均有分布[19]69-75,分布范圍亦是十分廣闊。根據(jù)史料記載,近代陜西礦業(yè)極其落后,除過延長石油外,其余的礦業(yè)都采用落后的土法生產(chǎn),還不時出現(xiàn)無法生產(chǎn)的情況[19]72。甚至在1949年以前,陜西基本沒有形成正規(guī)礦山[16]244,由此可見近代陜西礦產(chǎn)資源的開發(fā)利用程度極低。近代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實況與前文所述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大致相同,再加上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基本形成于其旅陜期間,意識是客觀存在的主觀印像,可見近代陜西礦產(chǎn)地理實況是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成因之一。
(二)國人的知識背景
根據(jù)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四點認識分析,他們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了解大多只是略知皮毛而已。之所以會形成這四點淺顯的認識,他們的知識背景是主因。顧執(zhí)中長期從事新聞行業(yè),是民國時期著名記者,掌握的知識多與新聞有關(guān)。林鵬俠早年曾在美國、英國等地求學(xué),在英國學(xué)習(xí)過軍事航空,是當(dāng)時中國著名女飛行員,她所掌握的專業(yè)知識集中在航空領(lǐng)域。陳賡雅與顧執(zhí)中知識背景相似,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所具備的知識大多與新聞專業(yè)有關(guān)。侯鴻鑒則是一位教育家,早年留學(xué)日本,研究東西方教育學(xué)說。根據(jù)顧執(zhí)中的記載,何慶云來自農(nóng)學(xué)院[9]7,其專業(yè)知識大多與農(nóng)學(xué)有關(guān)。李文一的知識背景不詳,陜西實業(yè)考察團當(dāng)中則有一些具備地質(zhì)礦產(chǎn)專業(yè)知識的成員[9]8。從這些20世紀30年代國人的知識背景來看,他們中大多數(shù)具備各自領(lǐng)域內(nèi)的專業(yè)知識,卻未從事過地質(zhì)礦產(chǎn)行業(yè),也未接受過地質(zhì)礦產(chǎn)類的專業(yè)教育,對地質(zhì)礦產(chǎn)類知識了解甚少。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能形成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四點淺顯認識。
四、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認識的意義
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是民國時期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重新認識和知識再生產(chǎn)行為,具有多重重要意義。
(一)加深當(dāng)時國人對陜西地理的了解
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實際上就是獲取相關(guān)地理知識,重新認識陜西地理的行為。在那個信息閉塞的時代,沒有來過陜西的國人對陜西等西北省份的地理情況知之甚少,且在認知方面存在誤解和偏見。當(dāng)時留學(xué)海外的中國學(xué)生對西北地理的了解程度甚至不及外國人。“習(xí)聞外人盛稱我西北為世界之天堂,又目為世界之秘密寶藏。間有西人同學(xué)詢余以西北地理氣候人情物產(chǎn),余乃瞠然無以應(yīng)。”[10]2不僅是在外中國留學(xué)生,就是生活在國內(nèi)其他地區(qū)的國人也對西北地理情況不甚了解,他們甚至“總覺西北是荒涼與苦寒,難宜人類生存”[23]。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隨著不斷有國人來到陜西,實地了解陜西礦產(chǎn)的相關(guān)地理知識,國人缺乏陜西地理知識的情況逐漸得到改善。在他們眼中的陜西已非荒涼之地,而是礦藏豐富的聚寶盆。隨著來到陜西了解礦產(chǎn)地理的國人不斷增多,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真實情況也漸漸傳播開來,為社會人士所周知。《南寧民國日報》曾報道過陜西實業(yè)考察團考察陜西后,得出的“陜北煤礦豐富”[24]等陜西的地理實況。重慶的《新蜀報》也有過相關(guān)報道,“故礦產(chǎn)豐富,尤以煤油、鹽、煤、石等礦,分布極廣”[25]。北京的《益世報》也根據(jù)調(diào)查結(jié)果,報道過陜西礦產(chǎn)蘊量、種類以及分布情況[26]。由此可知,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加深這一時期國人對陜西地理的了解。
(二)為民國開發(fā)西北提供了必要的知識支持
開發(fā)蘊藏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是民國時期開發(fā)西北的重要內(nèi)容。在當(dāng)時國人看來,開發(fā)西北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能夠滿足我國建設(shè)內(nèi)地工業(yè)的需求[27]。然而,當(dāng)時包括陜西在內(nèi)的廣大西北地區(qū)所蘊藏礦產(chǎn)資源是缺少勘探和調(diào)查的。何慶云在陜南調(diào)查當(dāng)?shù)氐V產(chǎn)資源時,便認識到這個問題,“但所知各礦均未有專門學(xué)識之人,詳為探勘”[18]70。實踐是認識的來源,獲取科學(xué)的地理學(xué)知識的最佳方式便是實地考察。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大都是通過親身到陜西考察獲取的,認識內(nèi)容可信度較高。根據(jù)相關(guān)學(xué)者的研究,對西北地區(qū)礦產(chǎn)情況的考察活動是開發(fā)西北活動的準備工作之一[28]。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內(nèi)容涵蓋蘊藏量、種類、分布和開發(fā)程度,較為詳細,為民國時期開發(fā)西北活動提供了知識支持。
(三)提高了陜西在國人心中的重要性
陜西是中國西北省份,而在民國時期,西北地區(qū)地處邊陲,遠離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處于被國人忽視的地位,甚至成為“秘密之土”[7]97。“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國人雖然開始注意西北地區(qū),但是西北地區(qū)在國人心中重要性依然不高[7]86。20世紀30年代之前,民國政府亦輕視陜西,并派貪暴殘酷的官員去管理陜西。外省人士也不大了解陜西實況,“為外人觀聽所不及”[29]。陜西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也被國人所忽視,“陜省天富獨厚,惜無人注意”[30]。國人考察陜西礦產(chǎn)地理之后,陜西蘊藏豐富礦產(chǎn)資源成為他們的普遍認識。在當(dāng)時很多人是從經(jīng)濟角度上去重視西北,寶貴的礦藏是他們重視西北的理由之一[31]。在他們得知陜西礦產(chǎn)資源等財富要多于東南地區(qū),“關(guān)中為我國腹地,財富之廣,甲于東南”[32],開發(fā)陜西便成為極其重要之事,“開發(fā)陜西,實為目前切要之圖”[32]。于是,陜西成為國人心中愈發(fā)得到重視的地區(qū)。
五、結(jié)語
地理認識是人們發(fā)現(xiàn)未知世界和獲取區(qū)域地理知識的有效途徑。發(fā)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活動,在中國地理發(fā)現(xiàn)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原因在于這次地理認識活動不但是一次重要的地理發(fā)現(xiàn)活動,而且還是一場偉大的愛國主義運動,國人藉此發(fā)現(xiàn)了陜西是蘊藏豐富礦產(chǎn)資源的聚寶盆。資源大省成為繼文化源地之后,國人對陜西的另一印象。救亡圖存、建設(shè)祖國的愛國信仰是20世紀30年代國人不畏艱險來到陜西,認識當(dāng)?shù)氐V產(chǎn)地理的思想動力。“我們的目的在:一方面要將東北以死力收回,一方面將西北以死力固守。”[9]7在了解陜西礦產(chǎn)資源情況后,這些國人還會給出相對合理的礦產(chǎn)開發(fā)建議,這些建議基本上都是從利國利民的角度出發(fā)的。例如林鵬俠提出開發(fā)延長石油的建議一經(jīng)實施,最大的受益者是國家。“年可得一萬萬元以上之國營產(chǎn)業(yè)收入利益,同時亦即減少一萬萬元金錢之流出”。[10]14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他們通過這次地理認識活動所獲得的陜西礦產(chǎn)資源的相關(guān)知識,為新中國開發(fā)陜西礦產(chǎn)資源打下知識基礎(chǔ)。他們不辭辛勞、不畏風(fēng)險,在那個動蕩的時代,毅然前往陜西進行礦產(chǎn)調(diào)查,不含私人利益,只為救亡圖存、建設(shè)祖國。然而,盡管20世紀30年代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資源地理的認識意義重大,但這場地理認識活動對推動開發(fā)西北而言卻收效甚微。與考察熱潮和決議熱潮相差甚大的是,國民黨政權(quán)在西北地區(qū)具體建設(shè)、開發(fā)等方面鮮有建樹[13]186。在國民黨政權(quán)的消極對待下,國人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活動所付出的努力大半付諸東流。他們對陜西礦產(chǎn)地理的認識并未實現(xiàn)最初的目的,這不得不說是一個由黑暗時代造成的巨大遺憾。
[參考文獻]
[1]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陜西省志·旅游志[M].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2008:43.
[2]馬強.唐宋時期中國西部地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
[3]張用建.抗戰(zhàn)前十年國人對西北開發(fā)問題的認識[J].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03,(02):94-103.
[4]吳加峰.一個“西北行”兩個“輿論場”——顧執(zhí)中和范長江“西北行”之比較研究[J].今傳媒,2016,(03):43-45.
[5]劉平.1932:上海銀行公會代表的陜西之行[J].中國銀行業(yè),2016,(07):114-116.
[6]因心.邊疆危機[J].求實,1934,(06):3.
[7]馬鶴天,劉鐵程,王志豪.萬里籌邊[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9.
[8]青島日僑[N].益世報,1935-01-12.
[9]顧執(zhí)中,范三畏.西行記[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10]林鵬俠,王福成.西北行[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
[11]謝彬.新疆游記[M].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23:34-35.
[12]周憲文.東北與西北[J].新中華,1933,(11):6.
[13]關(guān)連吉,趙艷林.西北開發(fā)思想史[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
[14]佚名.開發(fā)西北之研討[J].西北言論,1932,(04):8.
[15]陳賡雅,甄暾.西北視察記[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
[16]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陜西省志·地理志[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
[17]陜西實業(yè)考察團.陜西實業(yè)考察[M].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1933.
[18]何慶云.陜西實業(yè)考察記[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19]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陜西省志·地質(zhì)礦產(chǎn)志[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
[20]侯鴻鑒,馬鶴天,陶雪玲.西北漫游記·青海考察記[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21]李文一.從西安到漢中[A].楊博.長安道上:民國陜西游記[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
[22]曹明明,邱海軍.陜西地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8:62.
[23]范長江.中國西北角[M].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2010:57.
[24]如何開發(fā)陜西[N].南寧民國日報,1932-10-23.
[25]陜西礦產(chǎn)[N].新蜀報,1935-02-24. [26]陜西礦產(chǎn)調(diào)查[M].益世報,1933-08-14.
[27]張人鑒.開發(fā)西北實業(yè)計劃[M].北京:北平著者書店,1934:5.
[28]張克非,王勁.西北近代社會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26.
[29]孫幾伊.民國十年間之陜西[J].時事月刊,1921,(02):119.
[30]陜省建設(shè)計劃[N].新蜀報,1932-11-23.
[31]徐旭.西北建設(shè)論[M].上海:中華書局,1944:2.
[32]馬青菀.對開發(fā)陜省農(nóng)礦之建議書[N].西北文化日報,193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