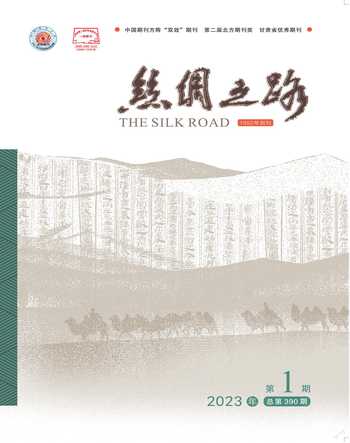趙時春《稽古緒論》的思想內容及其學術評價
[摘要]《稽古緒論》是明代學者、文人趙時春的思想性、史論性著作,其撰寫的目的是闡發儒學思想、發表歷史評論,同時也矯正士風、垂鑒當世。書中的儒學思想以“圣人”為核心,側重在傳統儒學和宋代理學命題,如圣人氣象、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吟風弄月等,其史論也以關涉儒學思想的歷史人物、事件為主,見解新銳。這些論述雖然其整體難以登上明代學術的一流水平,但于深化傳統儒學命題、深入認識歷史,都有明顯的借鑒、啟迪價值。趙時春的學術具有明代學術的普遍特點,他不訓釋經典字詞,不考辨儒學概念,而是一味的義理演繹和歷史評論;同時,因擅長于文章創作,所以,即便是在《稽古緒論》這樣的學術著作中,也處處體現出其縱橫不羈的文筆。
[關鍵詞]趙時春;《稽古緒論》;儒學思想;歷史評論
[中圖分類號] K8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3115(2023)01-0092-09
趙時春(1508-1567),字景仁,號浚谷,平涼(今甘肅平涼市)人,嘉靖五年(1526)進士,“嘉靖八才子”之一,歷任刑部主事、司經局校書、山東民兵僉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山西巡撫、都督雁門等地軍務,著作有《平涼府志》13卷、《趙浚谷集》16卷、《洗心亭詩余》1卷、《稽古緒論》2卷。趙時春為人堅持氣節、剛正不阿,他關心國政、心系民生,同時,又著文修史,闡發儒學思想,勤謹一生,孜孜以求。他曾率軍轉戰于山東、山西,為國效力,晚年定居平涼,低調著述,在去世前三年為平涼韓王府宗室所迫,移家至華亭硯峽的群山之中,郁郁以歿。他是一位有著崇高理想、高貴人格、淵博學識和較高文化成就的隴籍士大夫。在明代嘉靖年間的政壇和文壇上,他有著較大的影響,在隴右文化的發展歷程中,他更占據著重要地位。今天,整理趙時春的著作,表彰他在文學、史學、思想等方面的成績,批判地弘揚其文化遺產,對于整理傳統文化典籍、發揚地域文化、促進新時代的文化建設,都有積極的學術意義。目前,在趙時春的著作中,《趙浚谷集》《洗心亭詩余》已整理出版,《平涼府志》正在整理之中,《稽古緒論》未見整理。為此,本文研究《稽古緒論》的成書背景、思想內容,討論其學術評價問題,企圖為趙時春和地域文化研究貢獻一份綿薄之力①。
一、《稽古緒論》寫作的時代背景
在明代歷史上,嘉靖朝是一個有轉折意義的時段。北蒙南倭的邊患,是困擾朝廷的最大問題,頻繁的戰事導致財政緊困,人民賦稅沉重,軍人疲于奔命卻戰力低下。嘉靖皇帝在其統治的初期興“大禮議”之爭,中后期又很少臨朝,以致朝臣傾軋弄權,政局日漸衰落。可以說,從嘉靖后期開始,不僅明代政局,整個中國古代政局的走勢已經處于頹勢之中。此后萬歷間張居正的改革雖然能起到暫時的推遲、救急之用,但最終還是無法扭轉整體的頹勢。
面對頹廢的政局,明代中期的士大夫在思想、文學乃至個人氣節等方面,都做出了積極的、令人感動的努力。他們奮不顧身地與權臣抗爭,其風骨之烈,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少見的。如嘉靖初年“大禮議”事件中楊廷和、楊慎等抗爭張璁、方獻夫,嘉靖中期楊繼盛、馮恩、趙錦等彈劾嚴嵩,均風骨凜凜。在思想上,自明朝伊始尊奉的程朱理學,嚴重限制了思想的發展,所以,以王陽明為代表的思想家開始了對理學的叛逆和反思,他門闡發思想,聚眾講學,鼓蕩士風,并在嘉靖、隆慶、萬歷時期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心學思潮和流派,成為中國思想發展后期的一道亮光。在文學上,以李夢陽為代表的文學家反對臺閣體的匠氣,主張用秦漢文章的矯健古氣和盛唐詩歌的渾融氣象來矯正時代詩文的板滯之弊,而且也形成了廣泛而持久的文學復古思潮,開啟了明清文學中流派紛呈、輪流登場的大幕。應該說,以王陽明、李夢陽為代表的士大夫,分別從思想和文學的維度,為明中期的文化做著積極的努力。雖然這些努力許多都發端于嘉靖之前,但其真正形成廣泛、持久而深入的影響卻更多是在嘉靖時期。所以,嘉靖朝是明代歷史發展中具有轉折意義的時段。
趙時春是嘉靖時期一位積極有為的士大夫。在嘉靖初的“大禮議”事件中,他支持楊廷和,反對張璁,拒絕方獻夫的邀請,并因此而導致了初入仕途的失意,體現出士大夫的堅定立場。在“庚戌之變”中,居家的趙時春毅然赴任,訓練民兵,任山西巡撫、率軍轉戰于雁門一帶,后來又堅決支持好友唐順之出山抗倭,并撰寫《北虜紀略》,這是他對北蒙南倭的回應。他參與嘉靖初年“詩學初唐”的文學活動,反對“詩必盛唐”,是文學上與時代的接軌。在任東宮僚屬時,他以儒學自任,與唐順之、羅洪先并稱“三翰林”,體現出對學術的執著。他與王慎中討論“尊德性,道問學”的理學問題,撰寫《稽古緒論》以闡發思想,體現出對時代士風的憂慮和力圖匡扶思想的抱負。從這些角度來說,趙時春是深度地融入了時代政局與思想文化之中,走在主流文化的行列,他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都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
二、《稽古緒論》的寫作、刊刻時間
《稽古緒論》一書,趙時春未有序,其詩文中也未提及《稽古緒論》。趙時春的著作都沒有自撰序跋,如《稽古緒論》《趙浚谷集》《洗心亭詩余》均是,顯然,不自撰序跋是趙時春有意為之。這本無可厚非,不過也因此,我們今天要了解其著作的寫作時間、緣起、目的等,就只能通過其他文字來推理了。
(一)《稽古緒論》的寫作與刊刻時間
完成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孫應鰲序云:“得公所著《稽古緒論》,讀之,雖累日彌旬,余音遺味,猶不盡于口耳。”[1]689孫應鰲讀了《稽古緒論》,說明他是看到了全帙,因此,可以肯定,至少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稽古緒論》已完成,其刊刻時間也應在本年或略后。我們今天能見到的《稽古緒論》,也僅此一個版本。該本分上下卷,凡30篇,4萬余字。
完成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李開先《趙浚谷詩文集序》云:“浚谷子每寄聲,云詩、文、詞、論俱未有序,在交游知愛莫有如中麓者,四序幸勿退托。”[2]1言下之意,趙時春在書信中說,自己的詩、文、詞、論四部著作都尚未有序,故請李開先為之序。這與嘉靖四十一年(1562)孫應鰲作《稽古緒論序》的事實明顯相背。之所以這樣,應當是趙時春邀請作序的書信發出去較早,李開先因身體欠安,遲遲沒有寫序,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才寫成,這期間他也未見孫應鰲序,故敘述如此。
(二)《稽古緒論》的重刻
完成于萬歷八年(1580)的周鑒《重刻稽古緒論序》云:“因檢集中九篇,舊刻弗載,謀于學憲李君,并梓學宮。”②周鑒是趙時春的女婿、得意門生,時以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在開封,周鑒擬重刻《稽古緒論》,遂撰寫了這篇序言。作為方面大員,周鑒能調動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所以才有能力刻印趙時春著作。他精選趙時春詩文,刻印《趙浚谷詩文集》17卷,同時,他還擬重刻《稽古緒論》。從引文來看,周鑒是想把趙集中主題相近的其他9篇作品也收錄進來,以擴大《稽古緒論》的篇幅,但遺憾的是,周鑒刻本《稽古緒論》今已難覓其蹤。我們推測,周鑒并未完成《稽古緒論》的刻印工作,因為就在本年,他因被彈劾而離開河南,調入京城,任通議大夫、督察院右副都御史了。所以,周鑒刻本《稽古緒論》可能就不存在,但周鑒對趙時春的忠誠之情,是值得高度贊賞的。當然,另一種可能是,周鑒已經刻印完成,只不過我們尚未見到而已。
三、《稽古緒論》的寫作目的
(一)著書立說、留名青史是趙時春撰寫《稽古緒論》的根本目的
儒家自古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觀念,通過著述以垂不朽,是古代士大夫普遍的人生理想。趙時春固執地堅守儒學思想,因而,他必然地受其影響,在“立功”難以實現的情況下,埋頭著述以期傳諸久遠,就成為他理所當然的選擇。
嘉靖三十二年(1553)底,時年45歲的趙時春因戰敗罷官,三十三年(1554)初返鄉,從此開始了他余生14年的著述生涯。從返鄉初至《稽古緒論》的完成約九年時間,這期間他還作有380余首詩、70余篇文章,以及幾十首詞(趙時春的詞作時不明)。另外,趙時春從嘉靖三十五年(1556)開始纂修《平涼府志》,為此,他遍歷平涼各縣,歷時五年,完成《平涼府志》13卷,被譽為“西北名志”。一年之后,他完成《稽古緒論》。可以看出,在這九年間,趙時春創作欲旺盛,勤奮著書,可謂高產;而在此之前,他以寫詩作文為主,戰敗返鄉后,他才決心埋頭著述。
從前引李開先《趙浚谷詩文集序》的話來看,趙時春是一直在用心地收集著自己的詩文,“詩、文、詞、論”,再加上“史”(《平涼府志》),五類作品,詩、文還有清晰的編年,體現出對其作品的高度重視。再從這九年間趙時春文章創作來看,《趙浚谷集》中與《稽古緒論》主題相近的文章還有嘉靖三十五年(1556)完成的《諸儒》《儒學》《莊列諸子》《周漢君臣》《漢二帝》,三十六年(1557)完成的《雜劇談》17則,三十七年(1558)完成的《史論》33則,四十年(1561)完成的《〈詩〉論》,四十一年(1562)完成的《范曄史》《觀〈玄〉》等,這些文章或討論儒學問題,或評論歷史人物,說明這九年中趙時春思考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儒學思想和歷史思辨上。
綜合這些信息,我們能得出結論:立志著述是趙時春返鄉之后的首要任務。他在不斷地積累材料,完善思考,他想完成的,首先是立足儒學問題的思想性著作《稽古緒論》,其次應該是類似王夫之《讀通鑒論》的史論著作,他企圖藉此以傳諸久遠,垂名后世。遺憾的是,他執著于“述而不作”的傳統,大多闡發那些略顯陳舊的儒學命題,選題新意不夠,他的史論也顯得零散、不夠系統和集中,而且,他將這兩類問題的討論都匯集到《稽古緒論》中,使該書內容不夠純粹,當然也影響到他在思想史、學術史上的成就和影響(詳后)。但至少可以肯定,立志著述以垂名后世,是趙時春撰寫《稽古緒論》的根本動因。
(二)闡發思想、矯正士風是趙時春撰寫《稽古緒論》的直接目的
今天來看,《稽古緒論》是一部以闡發儒家思想為主的著作。趙時春平生以儒學自任,在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交替的嘉靖思想界,趙時春闡發儒家思想,必然有其深衷。我們首先要明確的是:對于陽明其人及其心學,趙時春從未有過明確評論,他為何不置一評?考慮到陽明心學的風行,我們以為,說趙時春不了解心學絕無可能;他之不置一評,本身就是對陽明心學的態度。趙時春的儒學思想,主體在先秦儒家思想、漢代賈誼、董仲舒以及程朱理學的范圍,對于陽明心學,趙時春不感興趣,也不認同,所以,他從不提陽明其人,也基本不提“心”的概念,至少從未以“心即理”“心外無物”的角度提“心”。明代儒者中,趙時春僅對河東學派的薛瑄給予了高度贊譽[1]179,因為薛瑄本來也是繼承和發展程朱理學的。由此推理,趙時春撰寫《稽古緒論》,繼承和闡發先秦儒學、程朱理學思想,其直接目的就是要在陽明學風行天下的時代,依然倡揚程朱理學,以消解陽明心學的影響。
如果再放寬視野來看,趙時春長期生活的平涼,屬于“關學”的影響范圍,而明中期的“關學”,本身也是對衡陽明心學的。比趙時春略早的隴籍著名學者胡纘宗也宗奉程朱理學,受薛瑄影響尤多。所以,無論趙時春贊譽薛瑄,還是受關學影響,都能反映出在明中期的山西和西北地區,認同或信奉心學思想的學者極少。
需要明確的第二個問題是,既然趙時春不認同心學,卻與陽明后學交往密切,該如何解釋?趙時春交往的陽明后學有徐階、聶豹、程文德、鄒守益、錢寬、羅洪先、唐順之等,其中徐階于趙時春有知遇之恩,鄒守益之子師事趙時春,羅洪先、唐順之與趙時春交往過從,尤為密切。而他們都是陽明后勁,羅洪先在《明儒學案》中享專傳專卷之尊,趙時春對羅洪先更是念茲在茲。在我們看來,趙時春與陽明后勁交往密切,但這并不妨礙他堅持立場、保持距離。事實上,嘉靖年間陽明學的興盛與徐階入閣關系莫大。嘉靖二十六年(1547),徐階入閣,以宰相身份聚眾講學,以致學徒云集,才為隆慶前后陽明心學的鼎盛奠定了基礎[3]。這期間,趙時春于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1550-1553)出仕,但主要任職于山東、山西,很少在京城,所以他無暇參與心學活動;罷官后,他長歸田園,活躍于京城、江南的心學講習也與他毫無干系。由此可定,趙時春與陽明后學的交往,主要是在心學大盛之前;心學大盛之后,他偏居西北一隅,無法預入其中。當然,這都是外部因素,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對程朱理學的認同和對陽明心學的排斥。
趙時春撰寫《稽古緒論》的另一目的是矯正士風。對于時下的士風,趙時春很不滿意,批評很多,這在《稽古緒論》中體現的很明確,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篇批評“竊名以自大,眩以自高”的欺世盜名之徒,《荷莜》篇批評“鄉愿”之徒,《學至圣人之道》篇批評“異端他岐之術”,《人主出治之本》篇批評“趨于文藝之習”之人等。其許多歷史評論也是在影射時代,如《項莊拔劍起舞》篇言:“人臣之事君,當先急其所急而后其所緩。”即作為大臣,就應該抓重點、解決緊要問題,如果聯系嘉靖時代宰相多靠“青詞”進身的現實,這頗具諷刺意味。《聞雞起舞》篇批評祖逖貌似忠勇、實則觀望的偽忠,《三者皆人杰》篇批評韓信、蕭何是茍幸富貴的“盜賊之雄”,這與趙時春激烈批評平虜大將軍仇鸞非常近似。《人之出治之本》《至誠治天下》兩篇討論君主修身以治理天下的問題,其核心落腳點不外仁義禮智信,這與嘉靖皇帝后期統治的偽善與一味修玄恰好形成鮮明對照。應該說,趙時春撰寫《稽古緒論》,是有著其鮮明的現實關懷,有著清晰的矯正士風的目的。
四、《稽古緒論》中以“圣人”為核心的儒家思想
(一)趙時春言必稱圣人
“圣人”是至為完善的人,是才德兼善的超越性的存在。但是,圣人到底該有如何氣象、如何品質,圣人有沒有情,如何去學做圣人,普通人能不能達到圣人的境界,這些歷來都眾說紛紜。在我們看來,古人所謂“圣人”,只不過是一個高懸著的、超越性的理想人格,各人有各人心目中的圣人,各家也有各自思想譜系中的圣人。
趙時春言必稱圣人。在《稽古緒論》中,直接以圣人名篇的有《圣人天地氣象》《學至圣人之道》《學者潛心圣人》《圣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圣人法天而不私》五篇,這些文章直接論述圣人之道及圣人的氣象、文章、品格等,最為醒目。所以說趙時春的儒家思想以圣人為核心是合理的。當然,擴展來看,則言必稱圣人也是許多儒家學者的基本風貌,符合古代儒家思想的基本傳統,王陽明《傳習錄》上卷絕大部分都是討論圣人的言論。由于圣人濃縮了儒家的最高理想,所以,圣人概念不僅包含著修齊治平的最佳方案,體現著忠孝倫理的最優水平,而且也包含著儒家解釋世界、認識社會、處理人際關系的根本準則。于是,我們就能看到,古代儒家學者在闡發思想時都對圣人念念不忘、三致其志,趙時春也不例外。
(二)圣人的本體性與超越性
趙時春的基本邏輯是:天是一切的根源,命出于天;因為命出于天,所以道出于天,圣人也出于天。圣人不僅是“道中之一人”,同時也是“道之宗主”(《道之大原出于天》),承道而行;承道而行,也即承天而行。正是在這個邏輯上,趙時春將天、道、圣人串聯起來,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等同起來,從而借天之權威性來賦予圣人承天而行的特權,讓圣人具有了高于常人的超越品性。
為什么只有圣人能承天而行,普通人就不能呢?因為在趙時春看來,只有圣人的行為才符合道,而普通人的行為與道有距離。道無處不在,變化萬千,但總能歸于一;圣人也能“通天下為一身”[1]696,正與道吻合。道之大,在簡易而無窮;圣人之杰特,在“無我”“無欲”,在“不獨擅”,在“以天下為公”[1]728,也就是說,圣人在其行為品性上完全合于道。基于此,他認為圣人具有“天地氣象”:“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圣人以其無私被天下。”[1]696這其實是在本體性上論述了圣人崇高的超越性地位。
(三)圣人是日常行為的典范和治國平天下的依據
為什么圣人不僅能成為人們日常行為的典范,而且能成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依據呢?趙時春還是從本體論起。“一陰一陽之謂道”,即陰陽成道;陰陽化五行,五行化萬物;“圣人因陰陽以驗天地”[1]702。于是,圣人本于道而制定五典、五禮、五刑、五服,以及仁、義、禮、智、信等人倫,而且都能顯仁藏用,體用無窮,“凡食息罅漏之間,鄙褻幽隱之地,無適而非道也”[1]716。因此,圣人才能成為人們日常行為的典范。由此推理,國君之治理天下也必然以此為終極依據。“天道,圣人且不之違,而況于有治之責求以安民乎?”[1]722言下之意,國君治理天下,必然以天道為依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理,莫不如是;孔孟之道,賈誼、董仲舒以及程朱理學,亦莫不如是;而如“文士高選”“詩酒不輟”的陳后主、隋煬帝則恰好相反,所以會敗不旋踵。
進而,趙時春指出,士子學習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達成或接近圣人之道,而且,還必須持之以恒。他說:“夫學者,非學為圣人乎?”“欲至圣人之道,必先學圣人之學;欲為圣人之學者,必不失可為之機;欲不失可為之機者,必先去‘吾姑待明日之心而后可。”[1]699
(四)《稽古緒論》中的程朱理學思想
《稽古緒論》中的《圣人天地氣象》《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吟風弄月》三篇,分別論述宋代理學中三個醒目的命題:圣賢氣象,五殊二實、二本則一,風月無邊。其中“圣賢氣象”是二程屢次申述,進而得到呂希哲、李侗、朱熹、真德秀等高度認同的概念,朱熹、呂祖謙編《近思錄》甚至以“圣賢氣象”來收束全書,真德秀《西山讀書記》也列專篇論析,逐漸地,“圣賢氣象”便成了理學家的口頭禪。“五殊二實,二本則一”與“風月無邊”均出自周敦頤,其中“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概括“理氣”問題,盡管各家對“理”“氣”關系的看法不盡相同,但其在程朱理學中的根本性位置則毫無疑問;“風月無邊”是表現理學家個人修養境界的詞語。
這些命題或是理學家語錄體的簡述,或是學者解釋《周易》《論語》時的發揮,或者是他們詩歌中的描述,而類似趙時春這樣的專篇論述并不多見(筆者未見到專篇論述,真德秀的論述也只是讀書札記)。所以,專文論述本身就是趙時春對這些命題的倡揚和推進。而且趙時春還將圣人氣象提高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覆載,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的高度,這與此前將圣賢氣象局限于“孔顏樂處”和“曾點氣象”相比,是明顯的提高,是理論貢獻。趙時春將“吟風弄月”解釋為理學家內心的“自然之天”,是“天然之機流動充滿,足乎己而無待于人”,是與顏回、虞舜境界相當的圣人之境,這與僅僅將“吟風弄月”(又作“風月無邊”“光風霽月”)解釋為胸襟坦蕩、灑落相比,也是明顯的發展和深化,增益了這些命題的價值與內涵,按照“述而不作”的古訓來看,趙時春的“述”確實是對傳統思想的擴展。這完全值得肯定。
(五)對異端思想的批判
在儒家思想中,孔、孟以楊、墨為異端,韓愈以佛、老為異端,朱熹以“非圣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為異端。顯然,所謂異端,其內涵也在不斷地豐富著。趙時春思想中“異端”內涵明顯繼承了這些傳統看法,即“不楊則墨,不佛則老”,其對異端的批判,也與孟子、韓愈等如出一轍:“辟異端者必倡道,倡道者必倡言,倡言者必先諸圣。”[1]706他將貶斥異端與道統、文章、圣人緊密聯系起來。這大體是韓愈做法的翻版,雖態度鮮明,但新意無多,不再贅述。
五、《稽古緒論》中的歷史評論
(一)《稽古緒論》中歷史評論的目的是闡揚儒家思想
趙時春曾任翰林院編修、司經局校書,受過嚴格的國史訓練,有著較高的史學素養,這從其《平涼府志》可見一斑。另外,從其文集中大量的史論文章來看,趙時春對歷史也有著強烈的興趣。所不同的是,其文集中的史論多是就史論史,而《稽古緒論》中的史論則有著鮮明的傾向性,即都集中在與儒家思想相關的人物或事件上。顯然,《稽古緒論》是借史論以闡發儒家思想,所以,書中《雋不疑引經斷獄》《雪夜微行》《武帝不冠不見黯》《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等文章,每篇有一個與儒家倫常相關的主題。如《雋不疑引經斷獄》贊揚雋不疑借《春秋》經義以果決應變的策略,批評那些膠著經義,而忽略當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之政局的說法,是膠柱鼓瑟的迂腐之談;《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分析求忠出孝的人性根源,進而對王祥臥冰求鯉的故事提出了有力的質疑,尤其是對王祥貌似誠孝卻助晉篡魏的偽孝進行了嚴厲批判。這樣的評論,都明顯關涉儒家學說和倫常,是借史論來倡揚儒家思想。
(二)《稽古緒論》中的歷史評論具有新銳特質
在史論中,趙時春無新不發,每篇必有新見。許多已有成論的觀點在趙時春的這里被否定了,而且這些否定也都有理有據。比如,向來被傳為美談的“聞雞起舞”與“雪夜微行”故事,在趙時春看來都不值得贊美。他認為,聞雞起舞固然勵志,祖逖固然忠勇可嘉,但因其守志不堅、心懷觀望,所以實在難稱純臣,祖逖的首鼠兩端也恰好成為其敗覆的根源;趙匡胤雪夜微服私訪趙普,并由此確定掃平天下之方略,但微服私訪置國君于不安之境,于國家有害,于禮不合,于經有違,他還引“公至自某”的春秋筆法以為證。這樣的論述,具有鮮明的新意。今天來看,趙時春雖然有刻意求新之嫌,但其立足點確實是在儒家思想與倫常之上,觀點鮮明,立論堅實,說服力較強。
(三)囿于固執的“圣人”觀念和忠孝倫理,其部分史論局限明顯
如前所述,趙時春言必稱圣人,他也以圣人的標準和忠孝倫理來衡量、評論歷史人物,在他看來,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才是古今完人,此后便質文更替,末世滋偽,道以代降,圣人遂不復見。基于這種觀點,他認為,如西漢高祖、武帝雖然雄才大略,但高祖本草昧之徒,興兵自利,開天下為私之先河;武帝重用刑名,巫蠱之禍中骨肉相殘,臨終時舍長立幼,留下了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的政局,因此,他對高祖、武帝均給予了苛評。他還從“知人以道”和“知人以術”的角度出發,認為堯、舜等知人以道,故君臣始終相睦,而劉邦則知人以術,故難與韓信善終,進而評韓信等人為盜賊之雄,甚至譏諷劉邦是“時來胡虜亦成功”。相應地,他對漢文帝這樣的溫和守成之君給予了高度評價。我們以為,這樣的評論囿于其固執的圣人觀念,局限明顯。歷史地看,高祖、武帝以及韓信等人,確實為推動歷史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趙時春的苛評難以令人信服。
六、《稽古緒論》的學術特點及評價
(一)《稽古緒論》的學術特點
對于明代學術,《明史·儒林傳》概括云:“有明諸儒,衍伊、洛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訛,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余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4]7222言下之意,明代學者沿襲邵雍、二程的理學,一味地探討性命之學,不訓釋經義,也不考究經學源流,因此,明人遺落了漢、唐經學的精華,僅繼承了宋元理學的糟粕。拋開《明史》的褒貶之外,其概括明人的學術特點為不考究經學源流、不訓釋經典字詞,是準確的。
趙時春的學術特點與明代學風一致,他從不考究經學的授受源流,從不訓釋經典的字詞含義,也從不考辨儒學概念。體現在《稽古緒論》中,便是一味的義理演繹和歷史評論。就其優點而言,這樣的義理演繹具有清晰的本體追問特色,體現出精致的思理、嚴密的邏輯,顯得理論水平較高;其歷史評論也都在是非褒貶之間隱寓著繼承往圣、垂鑒當世的深衷,具有鮮明的現實傾向。所以,趙時春以及明人學術是在務虛的表象中包蘊著關注時代、塑造思想的現實情懷。就其不足之處而言,因為一味的思想闡發和是非評論,故其立論的基礎時有不可靠之處,甚至偶有常識性疏漏,這就顯得明人似乎“讀書少”,甚至是“空疏不學”,以致招致清代學者“游談無根”“優孟衣冠”(多見于《四庫提要》)之譏。如果嚴格按照這一缺點來追蹤的話,《稽古緒論》也確有此之弊。
(二)縱橫不羈的文筆
趙時春在當時的影響主要是在文章創作上,徐階“其所為文章傳播海內,士相與口誦手抄,以為法式”的話[2]1,可以為證。黃宗羲《明文海》選錄趙時春文章18篇,也能體現出一代學術宗師對趙時春文章的肯定。凡是明人關于趙時春的傳記,基本都認為趙時春文章有司馬遷、李太白遺風,于是,“豪宕閎肆”“雄渾頓挫”就成為對趙時春文章的普遍評價。基于這樣的文風,盡管《稽古緒論》是學術著作,側重在思想闡發與歷史評論,但字里行間還是難以掩遏其縱橫不羈的文筆。趙時春散筆行文,卻又多用俳句,顯得文意浩蕩、氣暢神足,多數段落文采斐然,如:“文士高選,楊廣不足以取文士之首冠,而祇足以取智及之弒逆;詩酒不輟,長城不足取虜將之來朝,而祇足以取匿井之阨辱。”“大抵放肆于深宮大庭之中,而斂束于稠人廣眾之際;矯揉于親近君子之時,而狎近于昵幸小人之時;收拾于大道圣言之粗余,而肆意于言語文字之習。”[1]710趙時春在分析那些不誠意修身的國君,他列舉陳后主、楊廣為反面例證,分析他們貌恭心蕩、不習圣道的種種情形,散筆對句,確有賈誼、司馬遷之風。有意思的是,趙時春批評那些沉溺文辭之人,但其本人卻對于文辭極為在乎、在行,其身后也主要以文傳名。這表面看似矛盾,其實也完全可以理解,作家可以在價值層面貶低文學,但在具體創作中卻又含英咀華、研討文辭,以致文采斐然,似此情形,史上多見。
(三)《稽古緒論》的學術評價
我們以為,明人不考究源流、不訓釋字詞的特點,與其說是明人學術的不足,不如說是明人學術的時代特點。在漫長的歷史中,思想遞嬗,學以代變,到底哪一個時段學術是輝煌,哪一個時段衰落?一般來說,先秦諸子、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史上較有成就的段落,漢代經學、清代樸學也受到較多肯定,唯有明人學術,受到自清初以來學者的大力批判,遂成空疏不學的代表。明人真不學嗎?真空疏嗎?其實,明代學人的抱負、執著、熱情、純粹及其責任感、使命感,不比任何一個時代弱,只不過他們以另一種風貌表現出來而已,如趙時春好友薛應旗《宋元資治通鑒》,唐順之“六編”(左、右、文、武、儒、稗),以及晚明陳子龍的《皇明經世文編》,明末黃宗羲《明儒學案》《明文海》等,均是皇皇巨著,有著強烈的經世傾向,體現出明人的學術思想與應世方案。我們相信,隨著學術的不斷深入和推進,這些著作的價值必然會愈發凸顯和重要起來的。時至今日,歷時千年的漢宋之爭,不應該還延續在我們的學術評價中。
同理,趙時春《稽古緒論》所體現出來的學術特點,與其說是不足,不如說是時代學術風貌的映現,不容輕易貶低。趙時春對傳統儒家思想命題的闡發,雖然選題陳舊,但這也是古代儒學發展的基本特點,何況其論述大都細致深入,能對傳統儒學思理進行豐富和深化,體現出精致的理論水平;其史論多能別出心裁,眼光敏銳,議論尖新,對于我們更為深入地認識歷史無疑具有啟迪、借鑒價值。如果再從“理解之同情”的角度出發,我們能給趙時春給以較高評價,即他是一位正直、積極、有責任、有抱負的士大夫,其人其書都值得我們尊重,盡管他未能達到歷史一流水平。
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不完全同意司馬朝軍的評價。司馬朝軍言:“時春稽古未深,學問未成,《緒論》一編,龐雜無緒,卑之無甚高論,未能研精一理,亦未能自成家數。”[5]39其中“龐雜無緒”“未能研精一理”的評價,有一定道理,但要說趙時春“稽古未深,學問未成”,似嫌低評。我們的理解是,《稽古緒論》之所以成為“龐雜無緒”的面貌,有著特定原因。
《稽古緒論》之“龐雜無緒”,顯然不是趙時春的初衷。趙時春受過國史訓練,對他來說,認識這樣的不足不言而喻,但他還是匆匆地、“龐雜無緒”地將著作付梓了,什么原因?我們推理,嘉靖三十九年(1560)趙時春完成《平涼府志》,其中對平涼藩王韓王府的所作所為多有指責與揭露,從而引起了韓王的仇視,以致百般刁難。趙時春感到了嚴重的威脅與生之不易,所以,他將尚未完成的、體例未統一的思想性與史論性文章合編刊刻,兩年后(或許根本就不到兩年,因為刊刻費時很長)便舉家移至華亭硯峽的群山中。對這一變故,趙時春無法言說,也不欲向世人明言,所以,其著述中很少看到痕跡,唯有詩句云:“移家硯峽千層嶺,淚灑丘園三百年。”“念吾盧破碎,有國難投。為皇家力戰三關,與宗室何心一斗?”[6]874、972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居然拋棄300年歷史的故園,其心情之惡可想而知;這位曾為國力戰三關的斗士,為了避免與韓王府宗室的惡斗才舉家遷移,否則他有什么理由從平涼移至華亭群山之中安家?因此,趙時春之所以將《稽古緒論》匆匆付梓,韓王府的威脅是主因。《稽古緒論》呈現出來的這個面貌,并不能說明趙時春“稽古未深,學問未成”。
[注釋]
①關于趙時春生平、仕履、個性、文學創作、身后評價及目前的研究狀況等,筆者在《趙時春文集校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趙時春詩詞校注》(巴蜀書社2008年版)兩書前言中有分析,茲不贅述。
②王祖嫡《師竹堂集》卷9,《明人別集叢刊》第三輯,第87冊,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113頁。該文系周鑒所作,闌入《師竹堂集》無疑。王祖嫡與趙時春毫無關聯,不可能重刻《稽古緒論》;文中交代的作者行實,亦與王祖嫡生平完全不合。對此,筆者另有文章辨析,不贅。
[參考文獻]
[1]趙時春.稽古緒論[M].續修四庫全書[Z].第11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杜志強.趙時春文集校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3]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4]張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5]司馬朝軍.續修四庫全書雜家類提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6]杜志強.趙時春詩詞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