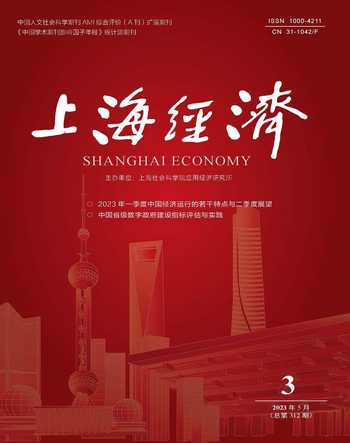中國省級數字政府建設指標評估與實踐
顧潔,王振



[摘要]數字政府建設是數字時代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和推進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路徑。當前,我國數字政府建設成果顯著,但距離高質量發展還存在差距。本研究構建數字政府建設指標體系, 借助熵權法和專家打分法構建綜合指標權重,全面評估了我國31個省市數字政府建設的現狀水平。國內31個省市根據數字政府建設總體水平和分級指標的分布特點可劃分為“引領型”、“特色型”和“追趕型”。分析發現,政府供給側分級指標內部的系統耦合協調度較好,但政府供給側與社會需求側之間存在耦合失調問題。從空間格局上來看,數字政府建設的“東-西”區域鴻溝明顯。通過局部莫蘭指數的分析發現,長三角范圍內上海、江蘇、浙江在空間上形成了數字政府建設“高-高”水平正向關聯。但安徽省與其他兩省一市的協調度較低,在長三角一體化建設中仍有提升空間。最后,本研究根據建設水平的領先性和治理模式的典型性,選擇上海、廣東兩省進行案例分析,總結先進的治理實踐經驗。
[關鍵詞] 數字政府,指標體系,系統耦合度,區域協調度,案例分析
[中圖分類號] 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211(2023)03-0014-20
一、引言
數字化浪潮中,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互聯網服務平臺等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帶來了社會生產率的顯著提高,同時還深刻影響著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江文路和張小勁,2021, Harrison et al. 2022)。數字政府是數字技術與政府創新相互融合的成果,強調以創新的政府治理思維,以數字化、平臺化、智慧化的方式,推動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管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政民互動信任化(孟天廣, 2021)。
數字政府建設是數字時代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和推進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路徑(Janowski, 2015)。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針對數字政府建設作出一系列戰略部署,將數字政府建設視為創新管理方式、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之應然。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推進數字政府建設”;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提出要“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優化,不斷提高決策科學性和服務效率”;2022年6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對數字政府建設水平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沈費偉和曹子薇,2022)。
我國的數字政府遵循“中央部署、地方探索”的建設模式,省級地方政府是推動實施數字政府建設的重要單元。在中央的頂層部署和努力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秉持技術賦能、數據賦權和為民服務的理念,從制度設計、能力建設、數據治理、治理效能等多方面著手,根據自身資源稟賦推動數字政府本地化建設,涌現出了以上海“一網通辦”、廣東“管運分離”數字改革、浙江“數字化轉型”、貴州省“一云一網一平臺”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數字政府創新實踐。
總體來看,我國數字政府建設成果顯著。《2022年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數據顯示,我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EGDI)得分從2020年的0.7948提高到2022年的0.8119,全球排名第43位,是該報告自發布以來排名最高的一次。在城市在線服務指數排名中,上海作為中國城市的代表在全球193個城市中排名第10,位于第一梯隊(“非常高”水平)。
盡管我國數字政府建設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距離高質量發展還存在差距,實踐中表現的頂層設計不完善、建設能力不足、數據利用效率低、網絡安全保障存在短板、治理成效有待提升等問題還較為突出;地方之間數字政府發展水平不平衡,跨區域、跨部門協同存在壁壘的問題依然嚴峻,部分省域范圍內省-市縱向整合存在障礙;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更是對地方政府數字化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鑒于此,有必要對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現狀和問題進行系統的梳理和評估。
省思當下方能展望未來。數字政府的建設是一項系統性、耦合性工程,呈現出制度設計、技術能力、治理成效等層面的相互影響和漸序深化。本研究立足于數字政府的復雜意涵和中國的本土探索實踐,基于“戰略-技術-成效”的分析框架提出數字政府建設的“五度”綜合評估模型——即制度就緒度、能力支撐度、數據利用度、安全保障度、治理成效度,以客觀數據為基礎,梳理分析中國31個省級地方政府數字政府建設情況,從系統耦合度、區域協調度等方向指出目前國內數字政府建設的痛點問題,通過科學系統的指標評價和分析過程,為未來數字政府建設提供參考和建議。
二、數字政府的概念與內涵
數字政府作為數字經濟時代涌現的新型政府模式,其思想來源于英國社會學家佩里·希克斯(2003)提出的“整體政府”、美國數字政府中心創始人簡芳汀(2002)提出的“虛擬政府”等創新理念,之后又衍生出 “協同政府”、“全觀型政府”、“網絡政府”等概念。盡管這些概念各有側重,但所指向的“數字政府”的核心意涵都是通過借助數字技術促進政府治理方式的變革,引發政府治理形態的結構性重組與功能性轉變(劉祺, 2022),即從傳統的以職能為中心的治理模式提升為以公民為中心的新型治理模式,最終形成更加高效的政府治理形態。
數字政府并沒有統一而明確的概念,根據研究者所選擇的理論視角不同,數字政府的內涵界定存在差異(劉祺, 2022; 胡稅根和楊競楠, 2021)。從新型政府形態視角出發,有研究者將數字政府定義為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為促進經濟社會運行全面數字化而建立的一種新型政府形態(胡稅根和楊競楠, 2021)。從技術轉型視角出發,學者們強調數字政府需要技術賦能,通過采納先進的信息技術驅動政府行政流程優化和治理方式改革(張成福和謝侃侃, 2020)。另一批學者立足于新公共管理視角,認為數字政府并非政府治理工具的技術化替代,而是一次深刻的政府治理模式變革,其重點并不在于技術本身,而是如何利用現代數字技術促使政府自身的改革(鮑靜等, 2020)。
數字政府意涵的復雜性不僅表現為理論解讀的多面性,也體現為概念內涵的動態變化性——數字政府會隨著新型數字技術在政府中的應用和滲透而不斷豐富、拓展和延伸,其概念和內涵是隨著技術不斷演進的(趙金旭等, 2022)。20 世紀70年代末,數據庫、微機等新技術在公共部門中開始應用,推動了“政府信息化”和“辦公自動化”(劉祺, 2022)。90 年代末,互聯網和大型辦公軟件開始普及。作為數字政府的前身,“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傳遞信息和公共服務給公眾”的“電子政務”概念開始興起。隨著數字技術的更新迭代,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互聯網服務平臺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開始滲透到政務管理的各個領域,促進了政府數字化轉型。
當前,數字政府的概念和內涵發生了兩個重大的變化。第一、數字政府的意涵更加豐富。數字政府的意涵已經超越了早期計算機、互聯網時期工具主義的范疇,而是包含了制度、技術、治理等多方面的內容。第二、數字政府所以來的信息技術更加先進,數字化、平臺化、智慧化成為數字政府新型基礎設施。同時,伴隨著數字技術的廣泛運用,網絡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聚焦國內數字政府的發展特點,并著眼于數字政府概念的多面性、技術的領先性,本研究采納新型政府形態的理論視角,將數字政府的概念定義為:政府借助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互聯網服務平臺等新一代數字技術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從而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支撐的新型政府形態。從內涵和構成出發,數字政府包含制度賦責、技術賦能、治理增效三個維度:從制度的角度出發,通過頂層設計推動自上而下的治理變革;從技術的角度出發,借助新一代數字技術建立政府數字化服務能力,包括技術支撐能力、數據利用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從效果角度出發,數字政府建設最終要體現為公共價值增益。
當前,研究界存在多種數字政府評估指標體系,主要可以分為三類:(1)政策分析類。研究者從公共政策角度出發,利用政策工具分析的方法對數字政府文件進行解構,分析和比較政策文本的制度邏輯、內容框架和治理形態等特征。(2)技術工具評價類。研究者聚焦特定技術形態的數字政府業務,對政府網站、移動客戶端、開放數據等建設情況進行針對性評估。(3)服務價值評價類。研究者從政務系統設計合理性、科學性、用戶滿意度等角度,對政務服務效果進行評估和分析。
總體上看,已有的評估體系相對單一,或著眼于政策文件,或聚焦特定技術形態的數字政府業務,尚缺乏切合我國本土實際的數字政府綜合性調查評估。
三、數字政府評估的指標設計
(一)總體指標框架
數字政府的建設是一項系統性、耦合性工程,呈現出制度設計、技術能力、治理成效等層面的相互影響和漸序深化。本研究立足于數字政府的復雜意涵和中國的本土探索實踐,基于“戰略-技術-成效”的分析框架提出數字政府建設的“五度”綜合評估模型——即制度就緒度、能力支撐度、數據利用度、安全保障度、治理成效度。
本研究通過文獻扎根、專家訪談、專家問卷、數據研判多輪指標修正過程,確保最終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合理性。
(二)數據來源與指標權重
評估分析主要數據來源有:省級政策信息庫、地方標準數據庫、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系統、工信部、科技部等官方網站公布的相關統計數據、第三方研究機構發布數據,以及本研究自采集的政府招投標數據、政務app相關數據等等。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均為以上來源截止至2022年11月的最新公布數據。
1. 制度就緒度
數字政府轉型是一項綜合性的、自上而下的治理變革,地方政府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做好系統謀劃與戰略布局。本研究從政策設計、標準體系、組織機構等多個方面量化測度省級政府在數字政府建設方面的制度就緒度。
第一、省級政府出臺的數字政府政策文件數。根據地方政府表述的不同,既包括數字政府文件,也包括一網通辦文件。為保證政策針對性,不考慮地方“十四五”規劃、數字經濟規劃等綜合性文件。
第二、從標準規范方面,計算本地區出臺的數字政府方面的地方標準數量。
第三、從政策工具評估的角度,對政策協同性和連貫性進行評價。其中政策協同性測算本地區是否同時出臺了數據條例、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等相關文件數量;政策連貫性測算本地區前期出臺的電子政務相關文件數量。
第四、組織機構方面包含兩個子維度:(1)省級地方政府是否建立大數據管理機構;(2)地方智庫為數字政府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咨詢建議,因此還測算了省域范圍內國家級智庫數量。
2. 能力支撐度
數字政府建設需要技術能力的支撐。與其他指標體系著重考察固網和移動網絡覆蓋度相比,本研究強調技術前沿性,補充考慮人工智能、云平臺和先導技術的技術支撐能力。能力支撐度具體包含以下內容:
第一、網絡能力。包括政務網建設項目投入金額(萬元)、5G基站數、10G PON及以上光纖接入端口數、移動互聯網普及率、固定帶寬普及率。
第二、算力能力。算力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重要的基礎性資源。本研究通過三個維度綜合測算地區算力能力:(1)省域范圍內設立的國家級算力樞紐數量;(2)省級人工智能算力規模;(3)國家級綠色數據中心數量。
第三、平臺能力。英國提出“數字政府即平臺”的建設理念,國內數字政府業務架構也日益趨向平臺化模式。本研究通過四個維度測算地區數字政府平臺能力:(1)政務云平臺項目建設投入資金;(2)政府網絡門戶平臺上的可線上辦理業務比例;(3)跨區域服務支撐,即可跨區域辦理的業務數;(4)跨部門服務支撐。跨部門服務的核心是將已建系統中相對獨立的重要功能模塊“沉淀”下來變成通用“能力”,包括統一身份認證、電子證照共享服務體系、統一電子印章、共享電子檔案、統一電子票據應用等。
第四、先導創新。數字技術快速更迭,數字政府建設也應該與時俱進。通過地方政府對元宇宙等先導技術的創新布局,測算地方政府的先導創新水平。
3. 數據利用度
作為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的核心主體,政務數據的共享、開放和運用,均與數字政府建設密切相關。換言之,政府對政務數據的管理和利用效果,既是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體現,也決定了數字政府的建設質量。本研究采用三個維度測量數據利用度:(1)數據共享,即政府數據跨地區、跨部門的共享情況。由于數據共享發生在政府內部,無法對其進行直接測算。本研究采用了間接測算方式,使用包含政府數據共享的文件數與政府數據共享標準數進行綜合計算。(2-3)借鑒復旦大學發布的《2021中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報告》,采用數據層和利用層的二級指數進行測算。
4. 安全保障度
網絡安全事關國家安全,數字政府網絡安全保障更是重中之重。圍繞數字政府安全保障度,本研究設計了4個二級指標進行測算:(1)省級地方政府出臺的有關信息安全、網絡安全、數據安全的政策數量;(2)信息安全、網絡安全、數據安全相關的地方標準數量;(3)省域范圍內信息安全、網絡安全、數據安全相關的發明專利數;(4)通過政府招投標數據,分析政務網絡、系統、信息及數據安全投入(萬元)。
5. 治理成效度
數字政府治理的核心價值在于以公眾為中心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務,公共服務的可達性、滿意度、包容度、透明度等成為衡量治理成效的關鍵因素。本研究設計了4個分級指標衡量數字政府治理成效度:(1)多渠道:支持政務服務獲取的渠道數,渠道越豐富、公共服務的可達性越高。測算中計算了省級地方政府政務app(安卓和蘋果操作系統)、小程序(支付寶、微信小程序)、在線網站等。(2)滿意度:使用政務app評分計算。(3)包容性:政務服務網站是否設計了長者版和無障礙版。(4)透明度:數字政府透明度是指公眾通過互聯網獲取各類政府信息,與行政主體聯系與交流,通過政府行政主體或者重要公務人員的網絡行為、政府應付突發事件的網絡表現等,采用政府網絡透明度指數結果進行測算。
在確定指標權重的優化模型的指導下,通過運用熵值法和專家法這兩種分析法對各指標進行了主客觀權重分析,再使用均值法獲得均衡權重(詳見表1)。其中,熵權法利用信息熵理論,通過計算各指標之間的相對熵值,得出各指標的權重。在熵權法中,首先將原始指標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然后計算各指標的熵值,熵值反映了數據中客觀呈現的指標信息量。而專家打分法則是基于領域專家的經驗知識,對各指標進行打分和權重分配。本研究邀請了6名從事數字政府實務工作和研究工作的政府、高校和科研單位專家對指標集合進行評分和權重分配,并通過加權平均方法得出專家打分法下各指標權重。最終權重采用熵權法和專家打分法的權重平均值,用于最終的指標評估。采用綜合權重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出現指標賦權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以達到各指標賦權的主客觀的平衡性。
四、評估結果與指標分析
評估結果見表2:
(一)總排名及其分析
結合總指數自然間斷點分級法與分級指數特征研究,將31個省級行政區數字政府建設分為三個層次。分層結果見下:
引領型(71.68以上):包括上海、北京、廣東、浙江、江蘇五個省市。這五個省市在綜合排名中位居前五,在分級指標方面也各具優勢。其中上海在制度就緒度、數據利用度和治理成效度方面均排名第一;北京在安全保障度維度排名第一;廣東在能力支撐度方面位居第一;浙江在數據利用度和治理成效度方面均位居第二;江蘇在能力支撐度和安全保障度上均位居第二。
特色型(41.83~71.68):包括山東、貴州、四川、福建、重慶、安徽、廣西、河北、江西、河南、天津11個省市。這11個省市在綜合排名中位于第六至第16區間。在分級指標上,11個省市在特定維度上相對具有長板,如山東、貴州在數據利用度方面較為突出(第四、第三),四川在治理成效度方面成果突出(第四),福建在制度就緒度方面表現亮眼(第三)。
追趕型(41.83以下):包括黑龍江、寧夏、甘肅、陜西、內蒙古、吉林、湖南、山西、湖北、遼寧、海南、新疆、云南、青海、西藏15個省。相比于前兩組,這些省綜合排名靠后,同時各項分級指標沒有特別突出的,處于追隨者的地位。
(二)分級指標結果及分析
1.制度就緒度
上海在制度就緒度維度上位居第一,且評估分值遠超過其他省市。在總排名位于第二層級的福建、安徽、貴州進入制度就緒排名前五。
制度就緒度體現在政策、標準和組織三個維度。政策文件是數字政府建設的根本遵循,各地由政策文件為切入,引領指導地方“一盤棋”開展數字政府建設。上海自2018年開始就啟動了系統性的數字政府建設的戰略布局,隨后繼續優化完善相應的制度設計。截至2022年12月,上海共公開了60份“數字政府”、“一網通辦”政策文件,其政策的豐富度遠高于其他省市。除了政策數量所體現的制度豐富度具備優勢外,上海在政策協同性方面也表現突出,出臺了15份數據條例、公共數據運營方面的文件,體現了政策具有較高的系統性。
福建因其在政策連貫性方面的優勢進入制度就緒度前五名。國內數字政府建設并非從零開始,有前期建設電子政務的積累,政府數字化進程更快。福建省級政府前期共出臺71份電子政務文件,在政策連貫性維度表現突出。
安徽、貴州在制度就緒度方面的優勢來源于標準優勢,截至2022年,安徽、貴州分別出臺數字政府相關地方標準46項和43項,位居全國前兩位。
在組織機構方面,全國目前共有18個省市設立了省級大數據管理機構。在地方智庫方面,北京占據絕對優勢,全國30家國家高端智庫中有24家位于北京。
2.能力支撐度
在能力支撐度方面,排名前五的分別為廣東、江蘇、北京、浙江、上海。
(1)網絡能力
從政府招投標項目中獲取政務網絡建設項目投入金額(萬元)。31個省市中對政務網絡建設投入力度最大的為北京,隨后為廣東、重慶、河北和黑龍江。
根據工信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22年9月,廣東省在5G基站數和10G PON及以上光纖端口數上居于全國首位。
在移動網絡滲透率方面,北京、上海、廣東為前三名。在固網滲透率方面排名前三的分別為浙江、江蘇、福建。
(2) 算力能力
算力是大數據和智能時代的核心生產力。根據《2020全球計算力指數評估報告》的分析結果顯示,2015-2019年,計算力指數平均每提高1點,國家的數字經濟和GDP將分別增長3.3‰和1.8‰。本研究采用三個維度測算省市算力能力:
·省域范圍內設立的國家級算力樞紐數量。《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協同創新體系算力樞紐實施方案》同意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內蒙古、貴州、甘肅、寧夏啟動建設8個國家算力樞紐,并圍繞這8個算力樞紐,規劃了張家口、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蕪湖、韶關、天府、重慶、貴安、和林格爾、慶陽、中衛10個數據中心集群。課題按照10個數據中心集群位置鎖定省域范圍內的國家級算力樞紐數量。
·省級人工智能算力規模。北京、廣東、上海位居全國省市算力規模前三名。
·國家級綠色數據中心數量。自2019年起,我國已創建三批共153家國家級綠色數據中心。按照數據中心所在位置進行分省統計,廣東省數量最多,共18家,緊隨其后的是北京(13家)、江蘇(13家)和上海(10家)。
(3)平臺能力
從政府招投標項目中剝離政務云平臺建設項目投入金額(萬元)。31個省市中對政務網絡建設投入力度最大的為北京,隨后為貴州、江蘇和福建。
業務上云率方面來看,上海完成了政務服務100%上云。全國范圍來看,有18個省市業務上云率達到90%以上,青海、云南、江西的政務上云率有待提升。
面對日益紛繁復雜的跨域公共事務、人員大規模跨地區工作生活以及各類生產要素加速流動,“一畝三分地”的單一主體治理模式已然難以有效應對,亟需打破部門壁壘和區域壁壘,加強業務跨部門和跨地區的協同辦理。其中,跨部門服務支撐的核心是將已建系統中相對獨立的重要功能模塊“沉淀”下來變成通用能力,包括統一身份認證、電子證照共享服務體系、統一電子印章、共享電子檔案、統一電子票據應用等。在中央的推動下,全國省市基本上都已經啟動全國統一的身份認證、電子證照體系等的建立和應用,甘肅、西藏、吉林等省在電子檔案共享方面還需補位。
在跨區域協同辦理方面,廣東走在了全國前列,全省共有3066項業務可以跨省通辦,緊隨其后的是河北(1142)、天津(1102)和上海(478)。
(4)先導創新
數字技術快速更迭,數字政府建設也需與時俱進。元宇宙是未來虛擬世界和現實社會交互的重要平臺,是數字經濟新的表現形態,潛力巨大。目前國內上海、北京、武漢、廈門等發布了元宇宙相關的文件。2022年7月8日,上海市政府發布了《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賽道行動方案(2022—2025年)》,提出將堅持虛實結合、以虛強實價值導向,發揮上海在5G、數據要素、應用場景、在線新經濟等方面優勢,推動元宇宙更好賦能經濟、生活、治理數字化轉型;力爭打造10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頭部企業、100家“專精特新”企業,推出50+示范場景、100+標桿性產品和服務,到2025年產業規模達到3500億。
3.數據利用度
數據利用度方面,排名前三的為上海、浙江、貴州。
在政府數據內部共享方面,采用政府數據內部共享的文件和地方標準數量作為替代變量進行測算。在31個省市中,福建對政府數據共享極為重視,共有124份省級文件提及政府數據共享,其次為上海(108)、廣西(74)和廣東(70)。貴州是全國最早啟動政務大數據建設的省份,在地方標準方面也走在全國前列,共出臺28項政務數據共享相關的地方標準,其次是安徽(15)和北京(10)。
公共數據開放與數據應用方面,本研究采用了復旦地方政府開放森林指數的二級指標。浙江、上海、廣東在數據開放方面居于全國第一梯隊,山東、浙江和上海在數據創新應用方面有突出表現。
4.安全保障度
數字時代,網絡安全事關國家安全。十三五以來,我國網絡安全治理體系逐步完善,國家層面出臺了《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數字政府與經濟社會的正常運轉密切相關,倘若出現重大安全問題,則可能導致治理失靈抑或引發嚴重的安全問題,威脅國家總體安全。因此,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的安全保障成為關注重點。
安全保障度方面排名前五的省市分別為北京、江蘇、廣東、上海、浙江。安全法規方面,上海出臺的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法律法規數量最多,共有58項。緊隨其后的是浙江(51)、陜西(49)和福建(48)。安全標準方面,遼寧出臺的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方面的地方標準數量最多,為23項。緊隨其后的是江蘇(16)、湖南(14)和北京(10)。陜西、吉林、寧夏、天津、甘肅、青海、四川、海南、西藏等省未出臺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方面的地方標準。安全專利方面,排名前五的省市分別為北京(1741)、廣東(1386)、江蘇(790)、浙江(495)和上海(446)。安全投入方面,從政府招投標數據中剝離政務網絡、系統、信息及數據安全方面的資金投入。北京在政務網絡、系統、信息及數據安全方面的資金投入力度最大。緊隨其后的是山西、廣東、江蘇和山東。
5.治理成效度
治理成效方面,上海、浙江、北京、四川、吉林位居治理成效前五強。四川、吉林因其較高的政務服務一體化能力和政務app評分而進入第一梯隊。
治理成效度采用服務多渠道、服務滿意度、數字服務包容度和政務透明度四個維度進行衡量。
(1)服務多渠道
在服務多渠道方面,大部分省市在線政務方面做到了全渠道覆蓋,即包括在線網站、安卓應用、蘋果應用、支付寶和微信小程序,但部分省市渠道覆蓋方面存在短板。例如,黑龍江的政務app“全省事”僅有安卓市場可以下載,湖南的政務app“新湘事成”在安卓和蘋果市場齊齊下架。
(2)服務滿意度
在服務滿意度方面,采用了政務一體化好差評分值和政務app評分兩個分級指標予以測量。對兩個分級指標進行機制標準化后進行加權平均獲得服務滿意度分值。
2022年國務院政務一體化“好差評”,評分中將31個省市按照政務一體化分值分為非常高、高和中三個層次。
政務app評分計算時,計算各省級政務app在蘋果app store和安卓多個應用市場用戶評分的均值。若一省有多個省級政務app,則再對多個app分值進行平均。
從評分情況來看,上海的“隨申辦”評分最高,為3.8分,遼寧評分最低,為1.9分。全國政務app評分的均值僅為2.72(滿分為5分)。總體來看,政務app在用戶評價還普遍較低,用戶滿意度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3)數字服務包容度
當不同群體在獲取數字服務存在機會和能力不均等時,就會出現數字鴻溝。為彌合數字鴻溝、提升數字政府服務包容度,幾乎全部省級政務app均開發了長者版和無障礙語音模塊,但部分省市存在功能上線但不可用的情況。例如天津政務網站長者版無法辦理業務,貴州、內蒙古無障礙語音版無聲音,海南省無障礙模塊進入后無內容顯示等問題。數字政務包容度需要從用戶出發,切實提升功能的有用性和易用性。
(4)透明度
數字政府透明度是指公眾通過互聯網獲取各類政府信息,與行政主體聯系與交流,通過政府行政主體或者重要公務人員的網絡行為、政府應付突發事件的網絡表現等,采用政府網絡透明度指數結果進行測算。根據《2021年中國政府透明度指數報告》,政務透明度排名前三的省份為浙江、廣東、江蘇,而青海、新疆、西藏的政務透明度評分較低。
(三)系統耦合度分析
理想狀態下,數字政府在各個子維度應該存在正向關聯,即各個子系統之間是耦合協調、相互促進的關系。為評估目前國內數字政府建設的耦合協調性,采用相關系數的方法簡單測算數字政府評估模型中制度就緒度、能力支撐度、數據利用度、安全保障度和治理成效度“五度”之間的相關關系。
從表4結果來看,目前數字政府“五度”子系統之間存在一定耦合失調問題。五個分級指標按照性質可以分為政府供給側指標(制度就緒度、能力支撐度、數據利用度、安全保障度)和社會需求側指標(治理成效度)。從表4結果來看,政府供給側的四個分級指標內部存在顯著的正向關聯性,系統耦合協調度較好。然而,政府供給側與社會需求側兩類指標之間,僅有能力支撐度與治理成效度呈現顯著的正向相關性,供需之間存在耦合失調問題。這說明目前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存在“投入-產出”失調問題,政府投入的治理成效顯示度不高,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四)區域協調性分析
國務院要求各地依托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和各級政務服務機構,打通業務鏈條和數據共享堵點,推動更多事項“跨省通辦”。但因行政區劃壁壘由來已久,相關制度尚不健全,跨界治理的開放式治理理念與地方本位主義存在沖突,各地系統互不聯通且數據標準不一、地方數字化能力差距較大等等原因,各省市數字政府建設水平存在較大差異,表現為數字政府建設方面的“區域數字鴻溝”。通過指標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各省之間的數字政府建設有著明顯的差距,東部沿海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程度整體高于中西部地區。區域層面,長三角、京津冀和泛珠九省區的數字政府水平相對較高。
為進一步分析數字政府建設的跨區域耦合性,引入局部空間莫蘭指數,分析特定省市與鄰近區域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空間關聯性。
式中,Lmi表示省市i的局部莫蘭指數,,,其中Fi為省市i的數字政府綜合水平值,wij為空間權重值。Lmi的統計指標顯著,表示省市i與臨近區域形成顯著的空間關聯。結果見表5。結果表明,上海、江蘇、浙江三省市在空間上形成了區域數字政府建設“高-高”水平正向關聯,安徽省在長三角數字政府一體化建設中還屬于“旁聽生”。我國西部的新疆、西藏地區數字政府建設呈現“低-低”的空間關聯。
五、地方數字政府建設案例
本研究根據建設水平的領先性和治理模式的典型性,選擇上海、廣東兩省進行案例分析,總結先進的治理實踐經驗。
(一)上海超大型城市數字政府建設經驗
超大型城市治理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科層制治理結構中的條塊分割、信息盲點、反應遲鈍與治理梗阻問題。如何實現對社情民意的極速感知、快速決策與高效處理,是超大型城市數字政府建設需要突破的治理難題。
上海作為總面積63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2487萬的超大型城市,在數字城市建設方面成為全國標桿,打響了上海“一網通辦”服務品牌。《2022年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中,上海作為中國城市的代表在全球193個城市在線服務指數排名中位列第10,位于第一梯隊(“非常高”水平)。本研究評估結果中,上海不僅在全國31個省市數字政府建設總體水平中排名第一,在制度就緒度、數據利用度、治理成效度等多個分級指標中也位居第一。
上海是全國最早啟動數字政府建設的城市。根據建設進程中的關鍵節點,大致分為三個主要的發展階段(孟子龍, 2022)。
初步探索期(2001—2011):2001年9月,“中國上海”門戶網站開通試運行,2002年1月該網站正式上線運行,標志著上海市數字政府建設的正式開啟。在初步探索期,電子政務的治理理念開始浮現,但從政策內容和重點任務上看,政府對電子政務的理解主要聚焦對內的“無紙化辦公”和對外的“政府門戶網建設”,其中政務門戶網站主要服務于政務信息公開化的管理要求,搭建由政府向社會公眾的單向信息傳遞通道。在這一階段,上海數字政府的治理理念還比較模糊,對電子政務的探索也在比較初期的階段。上海雖然在政府信息公開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但實際效果來看尚未形成較強影響力。
積極發展期(2012—2017):2012年4月,上海出臺《上海市政府電子政務“十二五”發展規劃》,標志著上海數字政府建設進入了新的階段。2012年5月,上海市出臺《上海市電子政務管理辦法》,其中將電子政務定義為“政府機構應用信息與網絡技術,將管理和服務集成,實現政務與技術的有機融合,向政府內部和社會公眾提供更加規范、透明、高效、便捷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活動”。這一定義已經具備“數字政府”核心理念的雛形,但仍然聚焦在具體業務(即“活動”),而非政府治理形態的整體轉型。
深化拓展期(2018—2022): 2018年以來,上海數字政府建設走向深化,圍繞“一網通辦”、“一網統管”、“公共數據開放”等工作打響了上海數字政府品牌。2018年3月,上海市政府出臺《全面推進“一網通辦”加快建設智慧政府工作方案》,確立了未來三年間數字政府建設的基本內容。2018年9月,上海發布《上海市公共數據和一網通辦管理辦法》,提出“依托全流程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臺和線下辦事窗口,整合公共數據資源,加強業務協同辦理,優化政務服務流程,群眾和企業辦事線上一個總門戶、一次登錄、全網通辦,線下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次”的工作任務。為推進數字政府建設,上海市政府成立以市長為組長的專項領導小組,組建上海市大數據中心,統籌全市“一網通辦”相關工作。2019年,“一網通辦”移動端“隨申辦”上線。根據2021年7月的政府公開數據,“隨申辦”的月活峰值已經超過1517萬,實際辦件的網辦比例超過70%。2020年,上海市政府出臺《2020年上海市深化“一網通辦”改革工作要點》,在已有建設成果上進一步“攻堅提升”,著力實現從“側重行政權力事項”到“行政權力和公共服務并重”轉變,從“能辦”到“好辦”轉變。
上海數字政府建設為國內其他省市提供了實踐經驗。
數字政府建設涉及政府部門全方位的變革,意味著需要有充足的權威資源保障和自頂向下的制度安排方能順利推行。在建設前通過充分研究形成科學合理的政策內容框架,以及在建設中高位領導充分的支持和重視,能夠為數字政府建設的有序開展提供保障(陳子韜等, 2022)。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時要求抓好“一網通辦”等“牛鼻子”工程,并提出“實戰中管用、基層干部愛用、群眾感到受用”的建設要求。為推進數字政府建設,上海市政府成立以市長為組長的專項領導小組,組建上海市大數據中心,統籌全市“一網通辦”相關工作。有力的上級支持和良好的制度設計上海數字政府相關舉措有序推進的重要原因。在頂層推進下,上海各部門以核心業務為主線、以數據融合為核心、以資源協同為支撐,按照業務閉環管理要求對部門業務流程進行全面梳理和優化重構,通過簡化流程和理順機制來推動數字政府理念的落地生根(陳志宏和姚元, 2021)。根據本研究統計,上海自2018年起在“數字政府”、“一網通辦”方面共出臺60項政策法規,政策工具具有良好的橫向協調性和縱向連貫性,這表明上海充分重視數字政府建設工作,結合前期電子政務實踐經驗和地方資源特征,認真規劃符合上海實際的數字政府建設路徑。
上海以數據治理為核心的整體政府理念形成“用數據認知、循數據決策、依數據施策”的治理思維。上海數字政府包括多方面的創新舉措,而這些舉措并非零散的應用,而是要打破部門壁壘造成的數據孤島,通過對數據的統一規劃來優化流程。在諸如“最多跑一次”、“不見面辦事”等創新中,用戶只需要一次提交全部數據,然后由系統根據用戶辦理的事項來組織業務流程,以數據的“流動”牽引分布在不同空間中的管理和服務主體為同一個事件而相互協作。在決策上,數據匯聚所建立的關聯性可以提供更多的事實或隱藏價值,循數據決策在上海應對新冠疫情危機下發揮了重要價值。上海不僅重視政府內部數據的共享,還跨越政府邊界,強調通過公共數據開放充分發揮數據價值,實現向市場、向社會賦能。2022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品的《2022全球重要城市開放數據指數》中,上海在全球重要城市數據開放評估中位列第四,在入選的30個中國城市中位居第一。
上海利用“以用戶為中心”的核心思路串聯起數字政府建設的諸多議題。上海“一網通辦”從實踐早期就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數字政府建設導向,提出了“讓政府辦事像‘網購一樣方便”、“群眾感到受用”等發展目標。以“一網通辦”為改革切口,上海數字政府建設強調將過往以部門為中心、以職能為中心轉變為“辦好一件事”為中心的邏輯(王孟嘉, 2021)。作為“一網通辦”的移動端,“隨申辦”從設計之初就制定了公平普惠、隨時可用的目標。
(二)廣東數字政府建設模式的探索與創新
廣東秉持“敢為人先、理念先行”的改革傳統,以先行先試的理念推動數字政府建設(吳磊, 2020)。廣東省數字政府建設取得良好成效。在本研究數字政府“五度”評估中,廣東在綜合指數中全國排名第三,在能力支撐度方面位列全國第一。
廣東省數字政府建設的最大特征,唯“改革”二字。
1.領改革風起之先,大刀闊斧開展頂層設計改革。
在吸收借鑒國內外主流建設思想的基礎上,廣東分別將互聯網思維、整體發展思維有效融合到政府數字化轉型改革中,提出“政務互聯網思維”,并以此來指導“數字政府”的改革建設。《廣東省“數字政府建設”總體規劃( 2018-2020年) 》中指出: “數字政府”是對傳統政務信息化模式的改革。相較于改革前的建設狀態,當前廣東省數字政府建設充分體現了全省“一盤棋”的改革發展思路。
為破除中國矩陣式管理造成的部門相互掣肘、省-市上下分割的問題,廣東從數字政府建設的頂層設計端著手推進政府治理改革,將數字政府改革作為“一把手工程”,成立了由省長擔任組長的改革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并系統編制“數字政府”建設規劃,以“數字政府”頂層規劃、實施方案以及考核指標為牽引,加強政府各部門的改革意識和創新思維。
一方面,廣東省將“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列為全省全面深化改革的18 項重點任務之首,將數字政府建設提到全省戰略高度不僅可以在更高層面掃清數字政府建設中遇到的跨部門、跨層級障礙,也保證了數字政府改革建設的資金投入。
另一方面,廣東省大刀闊斧進行機構改革。為明確管理職責,廣東省撤并和調整了省和省直各部門44個內設信息化機構,組建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隸屬于廣東省政府辦公廳) 作為“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的行政主管機構,負責政策規劃、統籌協調,從體制機制源頭上革新組織保障。
2.創新性開展“政企合作、管運分離”的建設模式。
“數字政府”建設過程對技術、人才、資源、資金等需求越來越大,政府部門囿于自身能力和資源限制,不得不借助于市場力量和企業技術優勢來實現政府數字化轉型,“政企合作”也成為數字政府建設的必然途徑。和全國其他省市主要采用的“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模式相比,廣東省在“政企合作”模式方面的改革力度最大,直接選擇管運分離模式,政府不再承擔建設者的職責,而是轉為使用者、評價者和監督者。2017年,廣東省發揮省內運營商優勢,與騰訊、華為和三大基礎運營商合作,成立數字廣東網絡有限公司作為數字政府的運營中心,形成“政企合作、管運分離”的運營模式,在較短時間內成功打造了“粵省事”移動應用和“廣東政務服務網”一體化在線政務服務平臺,充分發揮了政府與企業間優勢互補(王張華等, 2021)。
廣東省的數字政府建設模式改革體現了一種協同治理的思路。一方面,“管運分離”的模式轉型有利于減輕政府的建設壓力。另一方面,這種協同治理的模式還能充分發揮企業參與數字政府建設的市場化優勢,彌補政府在運營經驗和技術設施方面存在的不足。從用戶角度出發,相比于政府,科技企業和互聯網公司依靠技術能力和行業經驗能夠更加精準靈活地把握用戶需求。
3.推動全省“縱橫一體化”跨層級、跨部門協調改革。
與直轄市相比,省級行政單位還面臨“省-市”數字政府縱向整合的問題。目前國內部分省級行政單位未能充分利用省市兩級建設成果,“縱向聯建”進展緩慢。在某些省域范圍內由于各地市之間資源稟賦差異較大,數字政府建設改革進度不一、地級市之間信息數據未打通、辦事標準不統一等問題,省級政府對地級市政府的統籌領導能力較弱,造成較為嚴重的省市割裂、各自為政的現象。
為解決這一問題,廣東省在組織機構、平臺建設、標準體系、數據共享等方面發力,推動全省“縱橫一體化”跨層級、跨部門協調改革。在組織機構方面,廣東省除了成立省級大數據管理局作為“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的行政主管機構,同時在市縣成立相應的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從而形成了上下貫通、技術與業務融合的集約化管理體制。
在平臺建設方面,廣東省確定“一體化”的建設思路。在政務平臺層面,廣東對內統一規劃建設全省政務云平臺,落實“集約共享”平臺建設思維,形成“1+N+M”的政務云平臺,包括1 個省級政務云平臺、N 個特色行業云平臺、M 個地市級政務云平臺。為解決各地級市數字政府建設能力不平衡的問題,廣東采取“省統市建共推”的策略,即各地市可根據自身經濟發展和信息化水平分類推進,但最低要求依然包括運用全省統一技術標準的基礎設施數據平臺。
在標準體系方面,廣東省深度完成政務服務事項標準化工程,在省、市、縣的跨層級、跨部門共享提供了基礎技術標準、數據共享標準等條件。
在數據資源方面,廣東省建設全省統一的政務大數據中心,開展政務數據治理,實現數據匯聚共享。全省政務大數據中心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統籌資源,各部門不需要重復建設機房和數據中心,降低了建設成本,還通過一體化流程辦理服務推動了部門間的數據自主流轉(吳磊, 2020)。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數字政府建設是數字時代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和推進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路徑。當前,我國數字政府建設成果顯著,但距離高質量發展還存在差距。本研究構建數字政府建設指標體系, 借助熵權法和專家打分法構建綜合指標權重,全面評估了我國31個省市數字政府建設的現狀水平。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一)國內31個省市根據數字政府建設總體水平和分級指標的分布特點可劃分為“引領型”、“特色型”和“追趕型”。其中上海、北京、廣東、浙江、江蘇五個省市數字政府建設總體水平較高,分級指標方面各有優勢,屬于“引領型”;山東、貴州、四川、福建、重慶、安徽、廣西、河北、江西、河南、天津11個省市分級維度上各具特色,屬于“特色型”;黑龍江、寧夏、甘肅、陜西、內蒙古、吉林、湖南、山西、湖北、遼寧、海南、新疆、云南、青海、西藏15個省數字政府建設還有較大提升空間,屬于“追趕型”。
(二)指標內部系統耦合度分析發現,政府供給側分級指標(制度就緒度、能力支撐度、數據利用度、安全保障度)內部的系統耦合協調度較好。然而,政府供給側與社會需求側(治理成效度)之間存在耦合失調問題。
(三)數字政府建設的區域鴻溝明顯,東部沿海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程度整體高于中西部地區。全國一體化數字政府建設與跨區域協調發展成為未來關注重點。從局部莫蘭指數的分析結果上看,上海、江蘇、浙江三省市在空間上形成了區域數字政府建設“高-高”水平正向關聯,安徽省與其他兩省一市的協調度較低,在長三角一體化建設中仍有提升空間。
數字政府的建設是一項復雜工程,需要政策、技術、管理、資金等方面的大量投入,其建設天然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共同合作。在對數字政府建設的案例分析中發現,上海和廣東表現為兩種不同類型的政企合作治理方式,在決策層、運營層和治理模式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政企合作是數字政府建設的必然要求,如何根據自身的資源條件和環境因素設計公私合作模式,從而推動數字政府建設績效的最大化,體現了地方在政府數字化方面的治理智慧。上海技術、人才豐富,且廣泛分布于企業、科研院所、社會機構等多元主體。為充分吸收多元主體的技術資源和治理智慧,上海采取了“多邊決策結構+服務靈活交付”的多元治理模式,發揮“政產學研”協作倍增效應。與之相比,廣東借助本地科技企業和運營商的總部優勢,大膽采用“管運分離”的建設模式,政府退居幕后,主要承擔規劃引導、資源協調的作用。
上海、廣東在數字政府建設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反映了政企合作在數字政府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同時也說明數字政府建設模式不存在唯一的最優解。政府需要根據自身條件因地制宜設計數字政府建設模式,并根據不同的推進階段特點進行動態調整,從而不斷提升數字政府服務水平。
參考文獻:
[1]David R. Perri, D. Leat, K. Seltzer and G. Stoker,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J]. Parliamentary Affairs, 2003(02).
[2]Harrison TM, Luna-Reyes LF. Cultivating trustwort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igital government[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22 Apr;40(2):494-511.
[3]Hoetker G, Fountain J E. Building the Virtual St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 Management, 2002(4).
[4]Janowski T. Digital government evolution: From transformation to contextualization[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15 Jul 1;32(3):221-36.
[5]鮑靜,范梓騰,賈開.數字政府治理形態研究:概念辨析與層次框架[J].電子政務,2020(11):2-13.
[6]陳子韜, 李哲與吳建南, 作為組合式創新的數字政府建設——基于上海“一網通辦”的案例分析[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22(02): 133-144.
[7]陳志宏, 姚元, 基于云計算的政務信息系統整合研究[J]. 電信科學, 2021. 37(09): 118-128.
[8]胡稅根, 楊競楠, 發達國家數字政府建設的探索與經驗借鑒[J]. 探索, 2021(1): 77-86.
[9]江文路, 張小勁, 以數字政府突圍科層制政府——比較視野下的數字政府建設與演化圖景[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21(06): 102-130.
[10]李雪妮, 秦書鍇. 數據安全治理能力評估框架構建研究[J]. 信息通信技術與政策. 2022 Feb 15;48(2):37-41.
[11]劉祺, 從數智賦能到跨界創新:數字政府的治理邏輯與路徑[J]. 社會科學文摘, 2022: 73-80.
[12]孟天廣, 政府數字化轉型的要素, 機制與路徑——兼論 “技術賦能” 與 “技術賦權” 的雙向驅動[J]. 治理研究, 2021, 37(1): 5-14
[13]孟子龍, 超大城市數字政府建設的演進路徑與變遷邏輯[J]. 城市問題, 2022(06): 88-103.
[14]沈費偉, 曹子薇, 社會質量視角下數字政府發展的現實困境與優化路徑[J]. 電子政務, 2022(07): 76-87.
[15]王孟嘉, 數字政府建設的價值、困境與出路[J]. 改革, 2021(04): 136-145.
[16]王張華, 周夢婷與顏佳華, 互聯網企業參與數字政府建設:角色定位與制度安排——基于角色理論的分析[J]. 電子政務, 2021(11): 45-55.
[17]吳磊, 政府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探索與創新——以廣東數字政府建設為例[J]. 學術研究, 2020(11): 56-60.
[18]張成福, 謝侃侃. 數字化時代的政府轉型與數字政府[J]. 行政論壇. 2020;27(6):34-41.
[19]趙金旭, 趙娟與孟天廣, 數字政府發展的理論框架與評估體系研究——基于31個省級行政單位和101個大中城市的實證分析[J]. 中國行政管理, 2022(06): 49-58.
[20]鄭躍平, 楊學敏, 甘泉, 劉佳怡, 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主要模式:基于公私合作視角的對比研究[J]. 治理研究, 2021. 37(04): 38-50.
Assessment and Practice of Provincial Digital Government?Construction Indicators in China
Gu Jie, Wang Zhen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235)
Abstract: This study develops an indicator system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mbining the entropy weight and expert scoring to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government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wa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Based on the overall level and distribution features of the grading indicators,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were classified into "leading type", "typical type" and "catching-up type". Furth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coordination within the government supply side grading indicators was good, but there was a coupling mismatch between the indicators between government supply side and the social demand s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attern, there was a clear gap between the "East-West" regions in terms of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leve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ocal Moran index, we found that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Shanghai, Jiangsu, and Zhejiang formed a "high-high" level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regional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while Anhui Province was still in the periphery posi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leading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typical governance mode, Shanghai and Guangdong were selected for cas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and advanced governance practice experience was summarized.
Key words: Digital Government, Indicator System, System Coordination, Spatial Coordination, Case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