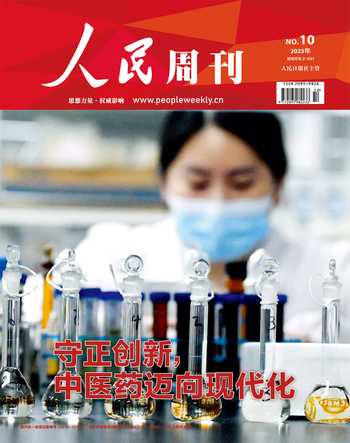中醫發展正迎來最好的時代
錢敏
新冠疫情防治中,中醫藥大放異彩。兩年前的5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專門去了醫圣祠,了解張仲景的生平和對中醫藥發展的貢獻。
“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中醫科學院成立60周年賀信中明確指出,要切實把中醫藥這一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在建設健康中國、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譜寫新的篇章。
就中醫藥傳承和發展,本刊記者專訪了首屆全國優秀中醫臨床人才優秀獎獲得者、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東直門醫院腎病內分泌科主任趙進喜教授。
中醫具有鮮明文化特質
“中國有兩套醫學體系,一個是中醫,一個是西醫。”趙進喜說,中醫是相對西醫而言的,是在西方現代醫學傳入中國以后才被提出來的。在西醫傳入中國以前,中醫就叫醫學,而不是中醫學。
“中醫強調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強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強調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認識全身的五臟六腑、經絡氣血,也是強調整體觀的。”趙進喜說,中醫認識疾病,強調不同的季節、不同的地域,因為時間和地點不同,常發病、多發病不同,還強調不同的體質,因為即使同一種病,針對不同體質的處置方法也會不同。
“司外揣內”是中醫的基本思維方式,即根據外在臨床表現推測一個人的健康狀況。趙進喜介紹,主要方法是通過癥狀、體征、舌苔、脈象等進行診斷。“就像挑西瓜一樣,看看皮色、聽聽聲音,判斷西瓜成熟了沒有。如果換作西方現代醫學,則是直接用探針取出一點瓜瓤,用化學分析的方法分析糖分含量,進而判斷是否已經成熟。”與西醫認識病因通過分析細菌、病毒不同,中醫是根據臨床癥狀,推測病人的風寒、暑濕、燥火等疾病。
趙進喜介紹,中醫治療疾病的藥物主要是天然藥物,包括植物藥、動物藥和礦物藥,其中以植物藥為主體,所以中藥又稱“本草”;治療的手段主要是自然手段,比如針灸、按摩、推拿等,雖然中醫也會進行一些小手術,但總體來說,創傷性的手術比較少。
在趙進喜看來,中醫不僅能治病,具有科學內涵,還具有鮮明的文化特質。“如陰虛火旺、心腎不交、木火刑經等,這些描述病情的語言并不是現代醫學詞匯,而是具有顯著東方文化色彩的語言。”
什么是中醫學?基于上述闡釋,趙進喜總結道:“中醫學是中華民族先人發明創造的,基于天人相應整體觀,采用‘司外揣內的基本思維方式,運用天然藥物和自然手段,針對人體的各種疾病,進行個體化防治的一門知識體系。它既有科學內涵,又有文化特質;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傳統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
中醫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
2015年,在給中國中醫科學院成立60周年的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把中醫稱為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趙進喜認為,這回答了“中醫到底是不是科學”這一問題。
趙進喜說,中醫不僅在古代是一門科學,而且是古代最寶貴的科學。但是,它和建構于數理化基礎之上的現代科學又完全不同。“中醫的產生和發展主要來源于臨床實踐,包括一些修身養性的個人體驗,中醫也有解剖學的基礎,但是它又受到傳統哲學的巨大影響,比如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趙進喜說。
“在跟疾病作斗爭的過程中,歷代醫家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趙進喜首先提到的是張仲景。張仲景生逢漢末亂世,建安政權建立不到10年,他的宗族200多人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多數都是外感熱病去世的。大災之后的大疫綿綿不絕。曹植在《說疫氣》中寫道:“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傳染病肆虐,人們的生命健康遭到巨大威脅,出現“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慘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仲景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寫成中醫經典《傷寒雜病論》。
后來歷代醫家中,也不乏張仲景這樣的醫之大者。李東垣生活的金元時期同樣戰亂頻發,中原地區尤甚。“為何在金元四大家里,三人都出自河北?因為那時候宋金元交戰的核心區域就是今天的河北地區。”趙進喜說,元太和二年,汴梁城瘟疫流行,李東垣發明普濟消毒飲,并把處方寫在木牌上,在十字路口等人員聚集之地將木牌釘在墻上,供大家抄用,救人無數。
明末崇禎年間再遇瘟疫流行,吳又可寫就《瘟疫論》。他認為瘟疫不光關乎風寒濕熱,還在于天地間獨有一種雜氣存在,它非寒非熱非濕,人一旦感染了這種雜氣就會傳染。于是,他提出邪伏膜原理論,并發明處方達元飲。趙進喜說:“在2003年抗擊非典和這3年抗疫中,達元飲依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處方。在治療流感等多種傳染性疾病中,達元飲也都很有療效。”
中醫的保護和傳承
中醫傳承發展至今,并非一片坦途。清朝末年,隨著西學東漸的影響,中醫學受到巨大沖擊。到了國民黨汪偽政權時代,還曾提出廢除中醫的建議。當時,以北京四大名醫為首的中醫前輩們奮力抗爭,譜寫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趙進喜提到前段時間上映的《老中醫》,他認為該劇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但也存在一定不足,最大的問題是著重講師傅帶徒弟,沒有反映出近代中醫的精髓。“實際上,近代中醫最值得稱道的行為并不是行醫,而是辦學,這才是近代中醫抗爭的精髓。”
1916年,孟河醫派傳人丁甘仁首創上海中醫專門學校(后改名上海中醫學院),該校是中國第一家經政府備案的中醫院校。之后,北京四大名醫在興辦中醫院校方面也頗有建樹。
“這幅畫是蔣兆和畫的張仲景,在上面題字的就是蔣兆和的岳父蕭龍友。”指著辦公室墻上的一幅掛畫,趙進喜告訴記者,蕭龍友是北京四大名醫之首,他和北京四大名醫中的另兩位孔伯華、施今墨共同創辦了北平中醫學校。后因辦學理念不同,施今墨又開辦了華北國醫學院。
據介紹,華北國醫學院培養了諸多中醫人才,施今墨學派也人才輩出,前三屆國醫大師中每屆都有施今墨學派的醫家,比如第一屆的李輔仁、第二屆的呂景山和第三屆的呂仁和。
呂仁和是趙進喜的導師,曾直接師從施今墨。談到師祖施今墨,趙進喜滔滔不絕。他說,施今墨有著開放的胸懷,是最早運用血壓儀、體溫計的醫家,在《施今墨醫案》中,他把西醫病名引入中醫診斷。施今墨的學生中,祝諶予很有名氣,出師后,施今墨將他和女兒一起送去日本學習西醫。新中國成立前,施今墨是當時中醫研究院的專家之一,他全心致力于中醫現代化和中醫科學化。“施今墨既是中醫臨床家,又是中醫教育家,也是中醫改革家。”趙進喜說,在近代中國,中醫學校人才培養是事關中醫存亡的關鍵,是保護、傳承和發展中醫最重要的舉措。
1956年,在北京、南京、成都、上海、廣州,五大中醫院校成立,中醫學開始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60多年來,這些院校已經培養出大量優秀的中醫人才。
進入新時代,中醫在疫病防治和慢性病防治方面的優勢被越來越多人熟知和認可,中醫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黨和國家一系列利好中醫的政策法規相繼出臺,中醫發展正迎來最好的時代。趙進喜說,全中國人民的健康需要中醫,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也需要中醫。政策好,落實也很關鍵。要想辦法打通“最后一公里”,讓中醫真正惠及百姓,實現更好的保護、傳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