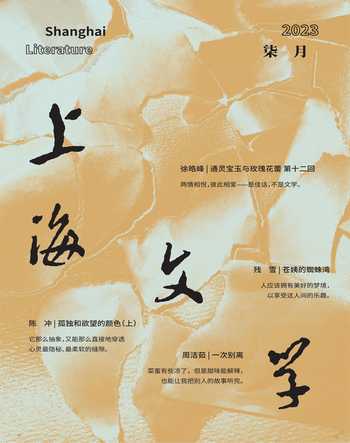歷史意識、詩人做派以及“當代性”的魅惑
李章斌
題記:
論詩之文字有很多種,有的論題適宜層層推進、步步為營,成為長篇學術論文;而有的問題與現象,或許并不適宜逐一舉例嚴密論證,而輕拿輕放、點到即止反而妥當,是謂“零札”。
關于“歷史意識”與“歷史性”
詩人、批評家T.S.艾略特所謂的“歷史意識”一直在詩人與批評家的言說中反復出現,不過,很多人似乎對這個詞有誤解,往往“顧名思義”,以為這是要把寫作與歷史現實關聯起來,強調寫作中的“歷史感”,甚至有人把它當作是“歷史決定論”的一種變相的表達。這顯然是一個牛頭不對馬嘴的誤會。重讀這個說法的來源,即著名的《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可以發現艾略特所謂“歷史意識”強調的重點顯然不是寫作與社會背景、歷史經驗的關聯性,那他想說的是什么呢?艾略特所針對的問題(之一),乃是浪漫派以來對于個人之“獨創性”與“獨異性”的崇拜,即“作品中那些最不像別人的地方”,但是艾略特意識到,這種求“新”求“異”的沖動帶有欺騙性,因為那些所謂“獨異”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往往在偉大的已故詩人那里就已經有了。因此,“歷史意識”首先是一種辯證的批判眼光,它“既是對于永久的意識,也是對于暫時的意識,也是對于永久和暫時的合起來的意識”,這個歷史意識不是指平常所說的“歷史觀”或者“歷史性”,而有點接近我國古人所謂的“常”與“變”的關系。進化論式的史觀已經根深蒂固地植入我們的文學史書寫中,似乎文學發展像是芯片更新換代似的,不停推陳出新、技術換代。然而這更多是現代性所造成的“神話”或者“陷阱”,對于寫作者而言更是一個相當有害的圈套,因為只知求“新”求“變”往往會新無可新、變無可變,反得其“舊”。如果用這種眼光來看當代詩歌,就會看到一些看起來頗為悖論的事實:每個人都堅信自己的特異性,當代詩人看起來像是一些“研發人員”,各自在實驗室里發明詩歌寫作的“新技法”,然而從旁觀者的角度,他們彼此相似到令人驚訝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意識”是一個有益的提醒,它實則是認識到一種文學乃至文化的“共時體”的存在,“常”與“變”并非只是簡單的取代與更替關系,若不知“常”,亦難以知“變”。
說完“歷史意識”再來說“歷史性”或者歷史關聯。在當下的學術研究與批評語境中,把詩人創作與歷史、社會、思想乃至個人經驗等背景聯合起來闡釋已經是一個頗受歡迎的“方向”,我本人也做過類似的嘗試。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收益與危險都同樣大的批評方法。首先,細細端詳具體詩人與歷史的“關聯”時,不難發現,與具體詩人所“關聯”的歷史絕非鐵板一塊。每個詩人所感受到的“歷史”都是如此的各自有別,甚至像“九葉詩人”這樣的同時代詩人之間也不例外,各自的歷史感知和書寫歷史的方式有鮮明的差異。“歷史”像是一大片土地,從不同地塊長出的樹又是如此不同。因此,“歷史”也不是“決定論式”的存在,它是寫作的出發點(之一),但絕非終點,終點往往是人各有別的,何況“出發點”本身也在不停漂移。對于現代歷史,其實我們所知有限,因為其中存在太多的禁忌與空白,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也只能去關聯部分“歷史”和部分“思想”,因此,這種做法很有可能變成柏拉圖所言“洞穴偏見”的反復加強。再者,很多結合歷史背景和思想史動向的研究固然會帶來批評之思想性與層次感的加強,但是也存在一種風險,即以一些常用的“慣見”來代替解詩的苦難,抹去文本的曖昧不明和深不可測之處。我們在把詩歌與歷史、思想、個人傳記關聯時,容易只談寫作之“原材料”而忘記寫作不僅僅是原材料的堆砌,很多時候,“成品”與“原料”看起來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否則,我們直接去研究歷史、思想或者社會學就行了,為什么還需要去讀詩呢?
當代詩歌的語言與倫理
在前兩年的文章里我曾屢次談到當代詩歌的語言與倫理,這里再補充幾句,也消除一些誤解。我們所謂的“語言與倫理”,并不是要給詩人的寫作加上一套道德律條的緊箍咒,不是指如何讓詩人遵紀守法,懲惡揚善,做一個“好人”,而是更多指向“語言中的倫理”。我那些文章卑之無甚高論,無非是在說一條常識,即語言的發生與創造并不是一個僅僅與自身相關的孤立的“定點”,而是一項涉及到自我與他人、他物之關系的“動勢”①——這里的“關系”更多是認知意義上的,而非“人際關系”“搞關系”意義上的“關系”——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人”與“他物”的存在,便是語言更新的開始;而他人與他物,都是深不可測而動向未知的,需要持續探索才能略知一二。討論這個問題主要是源于對先鋒詩歌中的過度膨脹的“自我中心主義”的觀察與反思。當然,這并不是在生硬地劃分“有倫理”的寫作和“無倫理”的寫作,在現實中不存在這種截然的對立。哪怕最“自我中心主義”的寫作,也無一例外地處于前述的“關系”和“動勢”當中,只是寫作者往往處其“動”而不自覺,誤以為是凝固的“定點”,因而也就容易自設牢籠,刻舟求劍。簡言之,語言往往是“倫理中的語言”,借用列維納斯的話并偷換幾個字來說:真正意義上的語言是能夠容忍“他(人)”或“它(物)”從它面前通過的語言。
關于寫作路徑的爭執
在當代漢語詩壇中經常可以見到寫作路徑或者詩歌立場的爭執,這些爭執不僅經常使得詩壇熱鬧不凡,還成為有的詩人獲得知名度和文學史“地位”的捷徑。在我們看來,有的詩人似乎陷入一種對寫作路徑的執迷。寫作并非是打游戲,不是說找到一個巧妙的新方法,就可以一路過關斬將,寫出有意義的新作品,包治百病。所以,也不存在一種方法就一定優于另一種方法這樣簡單的對比,比如一種倫理主義的方法就一定優于自我中心主義的方法,或者那種與政治、歷史、社群“聯動”的方法便優于純詩式的寫法,又或者“非歷史主義”式的寫法就優于“歷史主義”的寫法。就“方法”這個問題而言,更恰當的比喻是走鋼絲繩,寫作就像走在鋼絲繩上,充分意識到自身的邊界與每一個行動的后果或者危險,每走一步都或許需要重估一下自己的“方法”。帶著“一招鮮吃遍天”的執念,往往會一腳踏空而進入飄飄然的狀態,自我重復而不自知。在當下詩壇中,我們已經看到相當多頗有建樹的詩人進入到這種幾乎無節制的自我重復當中。因此,我們與其擔心“沒有方法”或者方法“落后”,不如去擔心“方法”的過度膨脹。如果一種方法無法帶來持續的想象力的擴展與詩語的更新,那么無論它是如何“正確”的,它也沒有凌駕于其他寫作路徑之上的權力。更何況,政治上、倫理上或者藝術上的“正確”是一個危險的論域,在此時此地“正確”的理念到了彼時彼刻很可能就是“錯誤”的。
“當代性”的魅惑
在當代文學批評領域,“當代性”經常成為了一個不證自明的力量之源和合法性標準,在數量龐大的批評文字、作家訪談、對話以及文學會議之中,可以看到“當代性”顯然是一個褒義詞,似乎文學作品好與壞的標準就是是否具有“當代性”,甚至批評家也被要求具有“當代性”或者“現場感”。這樣一來,仿佛不和作家喝上幾杯,不去深入了解他們的八卦、酒后牢騷、生活處境、說粗話的風格、他們對其他同行的私下非議,就根本不具備批評當代文學的資格。在這樣的壓力中,我偶爾讀到海倫·文德勒《看不見的傾聽者》書中的一段話,頓覺大快人心:“抒情詩人對看不見的傾聽者的想象……顯示了生活中有些情境下,可見的對話者(一個朋友,一個愛人,一個同行詩人)不足以滿足詩人的要求。”正因為不滿足,所以有的詩人要去和幾個世紀之前的畫家對話(如阿什貝利),有的詩人則想象和未來讀者的親密交談(如惠特曼),有的詩人則想象和上帝對話,等等。讀到此忽然想起孟子的所謂“知人論世”:“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下》)夫子實際上也是在告誡我們,不要只和一“村”的人做朋友,甚至也不要滿足于只和一國之人或者同代之人做朋友,要去上溯古人,跟古人做朋友,去讀其書而且知其人,這才叫“尚友”。
依我愚見,這個道理對于文學批評而言也成立,與同時代人交流固然有利于增強“參與感”,但是交流多了也會像是在泥坑里打滾,或者說在澡堂里一起泡澡吧,赤裸相對,親密無間,對對方身上幾顆痣幾處胎記都了如指掌。細節是清晰了,但是“對話”的主題與境界卻總是有限,缺乏時間的“穿透性”,而且,話術和問題還容易彼此重復。與來自過去、未來或者永恒的“傾聽者”對話之所以必要,其實是認識到很多問題并不能在“同時代人”或者“多數人”那里得到答案——話說回來,迷戀“同時代人”似乎像是一種羊群心理,在同伴那里更安全——也是為了給自己更大的自由和空間。
關于“詩人做派”
在讀到西默斯·希尼那首樸實的詩歌《警察來訪》(黃燦然譯)時,我突然想到這些話:我們稱之為文明或者人性的東西是如此脆弱,隨便哪個狂人或者瘋子就可以把它一腳踩在地上變成爛泥。這種寫真實場景下真實的恐懼的詩歌,不那么張揚自己的詩人主體,不那么有“詩人性”或者“詩人做派”,反而令人感懷觸動。說實話,我很不喜歡那種自居為瘋子、先知、旁觀者、批判者或者語言的守護人之類的“詩人做派”,實際上,大部分詩人什么也沒預言出來,至少在社會公共事務上是如此,他們和普通人一樣,談不上更聰明也談不上更愚蠢。很多詩人的裝瘋賣傻更像是一種欺騙或者掩蓋自己的興奮劑,而到了利益攸關的時刻,有的又成了徹徹底底的機會主義者或者變節者。在很多動不動把“詞語”“語言”“歌”直接寫進詩歌里宣揚自己的技術自覺的文本中,其中的語言才能并不高明,甚至談不上敏銳。我有時很不明白,寫作者為什么不能僅僅將自己當作一個手藝人(和裝修工人一樣)?或者說,一個簡單的“社會人”?在這種時候,我倒很喜歡拉金那句詩(米沃什也寫過),就是不要忘記自己身上住著的那只丑陋的癩蛤蟆,這樣或許會少一些放肆和自我張揚,多一些寬容。
語言與民族文學的統一性
說到當下學者(包括海外漢學家)討論的現代文學的“中國性”議題,我的直接的看法就是這是一個有問題的概念,甚至是個“偽概念”,它被很多關懷在于文學之外的學者塞進了太多的意識形態爭執。對于民族文學之統一性的問題,俄羅斯大詩人曼德爾斯塔姆的見解值得引述:“回到俄羅斯文學是不是一個統一體,以及如果是,其統一性原則建立在哪里的問題,我們就必須立即消除進步論。”“唯獨語言本身可以用作某一特定民族文學之統一性的標準,用作該民族有條件的統一性的標準,其他標準都是次要的、短暫的和任意的。”(《曼德爾斯塔姆》,黃燦然譯)很多放在“中國性”名義下討論的問題,其本質實際上屬于“漢語性”的范疇。如果我們要討論中國文學的統一性,必須以漢語本身作為主要的標準,而且有必要區分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有的“中國性”論者不作這種區別,甚至以古代漢語/古代詩歌為準繩,將現代漢語、現代漢詩的雜合性質當作一種非法特性,企圖將漢語、新詩“凈化”,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
現代漢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民族試圖仰望并且融入世界文化的渠道而出現的,它與其時的古代漢語的重要區別就是它對外來文化、語言的開放態度——而且本身就是這種態度的一個結果。這一點與曼德爾斯塔姆所說的俄羅斯語言對西方文化的“眷念”是頗為相似的,他說:“俄羅斯語言就像俄羅斯民族精神一樣,是通過不斷的混合、雜交、嫁接和外部影響形成的。然而它將在一件事情上忠于自己,直到我們的洋涇浜拉丁語為我們發出回聲,直到我們生活的蒼白小芽開始在我們語言的強大軀體上開始抽芽……”(《曼德爾斯塔姆》,黃燦然譯)而曼德爾斯塔姆所說的唯一忠于俄羅斯語言自身的一件事情,就是“俄語是一種希臘化語言”。在我看來,任何企圖以“凈化”漢語的名義排除外來影響的做法本質上是在閹割這一門語言,也就是閹割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一種可能性前景。
附帶說一句,當代學界對于諸如“中國性”“華語語系文學”這些宏大、空洞概念的熱衷是我所不能理解的,這些概念對于我們認識文學本身其實并沒有太多助益,對于讀者或者學生接近文學更是毫無益處。
漢語詩律學的自我調整
在我看來,“聲情”或者“音樂性”維度的薄弱是當代新詩研究以及批評的一大缺憾。雖然,零星的探索還偶或出現,但是系統性的理論突破與范式更新仍是一個有待完成的任務。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一直到九十年代,漢語詩律學的主流依然是著意于構建種種節奏模式、結構范式,比如“音步”“頓”以及“韻”的程式和規律,而大部分當代詩人卻對此毫無興趣,這是頗為尷尬的現象。可以說,漢語詩律學或者說韻律學(prosody)在當代幾乎完全與新詩創作實踐脫軌,要對此現象負責的首先是研究者。在新詩寫作中處于核心的技術手段在傳統的詩律學中幾乎沒有重要的地位:語調的控制,詩情之抑揚起伏的實現手段,分行、停頓、標點等90形式的作用已經很難在傳統詩律學的框架下討論,它們很少是用來制造整齊的節奏感或者所謂和諧、悅耳的“音樂性”的,而是變成了詩之時間性、“肌理”乃至意義的關鍵。在這方面,目前筆者所見最有說服力、也最為深刻的論述是伽達默爾對策蘭《呼吸結晶》這組詩中的分行、停頓等細節的分析,還有海倫·文德勒對于格雷厄姆詩歌分行以及長度的分析,他們出色地展現了,詩的分行、節奏是如何與文本的整體脈絡和意義融為一體的,而不僅僅是一個聲音或者節奏層面的現象。②它們或許也會為漢語學界如何處理詩歌的語言細節問題帶來深遠的影響。
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是,要么把節奏的變化與起伏、語調的高低抑揚、分行、停頓、標點等形式排除于詩律學之外,要么對詩律學本身的范圍乃至方法論進行急劇地更新——這有可能導致這門學科喪失邊界乃至意義——變成一門關涉到詩歌文本之整體性的學問,至少是從時間的角度理解這一整體性的學問。過去的詩律學似乎傾向于將自身定義為一門規范性的學科——其核心是如何定義“節奏”以及如何評判“好的”(和諧的)節奏——它在對規則與結構的沉迷中喪失了進入現代詩歌之內核與肌理的意愿和能力,而又因固守“聲音”這一維度而在詩歌意義的理解中自我設限,因此退化為一門漠視詩之動力機制的機械的修辭學,這是它在當代陷于停滯狀態的根源。擺在詩律學面前的問題包括(但不限于):如何分析變動不拘的自由詩的節奏?節奏是一種單一的“程式”還是一個“眾聲喧嘩”的體系?節奏與時間的關系如何實現于具體的語言之中?排版、分行、標點等與詩之時間性是什么關系,它們又如何構建詩之整體意義和“靈韻”?已多少陷入停滯的漢語“韻律學”或者“詩律學”必須面對這些問題,才能開始“自我調整”,重新觸及到詩人寫作的內在“動力”以及意義的“內核”,而不是停留在對舊有格律范式的迷戀以及對當下靈動、豐富的寫作狀況的“全盤否定”式批判之中。
① “定點”“動勢”二詞借用自駱一禾的詩論《美神》,見《駱一禾詩全編》,張玞編,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版。
② 參見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保羅·策蘭:《誰是我,誰是你》,陳早譯,上海文藝出版社二○二三年版;海倫·文德勒:《打破風格》,李博婷譯,廣西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