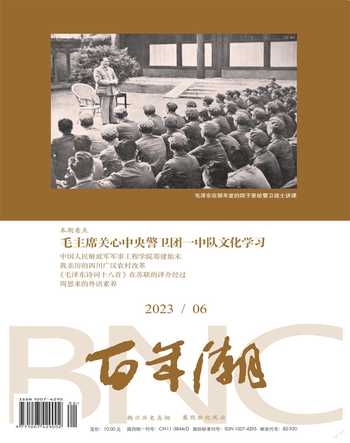天人合一:中華文明的精神追求
楊家剛
人生于天地宇宙之間,對于人自身的渺小和宇宙的浩瀚總難免產生好奇。對于天與人關系的認知與探索,自人類誕生之日起即未嘗停歇。綜觀人類早期文明,大都有對于天人關系的神話或宗教性解釋。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前5世紀,幾大早期文明則更從思想與哲學高度嘗試予以解答。兩千多年前的汨羅江畔,屈原更以詩歌《天問》對天與人的各種困惑發出一系列追問。作為中國紀傳體史書的開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表達了通過撰史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天人之際”,或天人關系問題,成為中國古代思想與哲學中一直嘗試解答的一個核心性論題。
先秦時期,雖有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天人相分主張,但大多也落在“制天命而用之”,從而在利用天命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作用層面,后世進入中國哲學主流的還是在基于天人貫通視域下的“天人合一”理論。
“天人合一”,作為一個固定成語出現比較晚,出自北宋大儒張載的《正蒙·乾稱》篇,原文為:“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遺人。”然而,這也是張載對之前哲學思想的概括總結。追根溯源,“天人合一”觀念在先秦時期已露端倪。其直接經典來源是《周易》。《周易·賁·彖傳》有“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種基于天象與天時的天人貫通觀念可謂直接影響中華文明幾千年。《周易·系辭》則指明《周易》一書的性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周易·說卦》則說:“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作為經學體系的易學因而成為古代講述天人關系的重要經典,且經由孔子贊《易》,具有了經綸天人的哲學屬性,這與作為數術范疇的卜筮之書是不同的,《周易》揭示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因而成為中國傳統對宇宙與道德中天人關系的普遍認識。
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道”的概念作為宇宙本體,并以“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概括了天、地、人相效法的宇宙觀。其后,莊子沿續老子無為、自然的觀念,在《莊子·齊物論》中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成為“天人合一”的重要思想淵源。
作為漢代天人之學的確立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將萌芽于殷周,完善于戰國末期的天人感應思想與戰國末期陰陽家鄒衍的“五德終始”說發展為一整套天人感應論,包含“天人同類”“人副天數”“同類相動”等,他在《春秋繁露·陰陽義》中提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這是古書中最早提出的“天人一”,然而與后世“天人合一”有所不同,董仲舒是在天與人相似的比較層面強調天和人具有同質性,以類而言,天和人是一樣的,實際是他的“天人同類”說。
至宋代理學的哲學重構時期,北宋大儒張載基于易學與氣化宇宙論,同時闡演《中庸》“天命之謂性”與“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等思想,強調天命與人性的貫通,最終提出“天人合一”這一哲學命題,同時也是對中國古代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與道德觀的經典概括。在“天人合一”的視域下,張載進而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民胞物與”社會觀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道德人格追求,廣為傳誦,激勵著一代又一代讀書人超越自身、效法天道、追跡圣賢。由此,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提出:“‘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的最大貢獻。”
一、“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和道德觀的底色
“天人合一”觀,脫胎于中國上古對宇宙和人世的觀察,在基于天文歷象的觀測和人世各方面的總結基礎上,形成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和道德觀,尤其體現為易學哲學。
作為中國傳統五經之一,《周易》被贊為“群經之首”。根據傳說,易學源自伏羲“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而畫八卦,用八種卦畫統括天、地、水、火、風、雷、山、澤等八種事物,用來解釋人間各類事物的變化法則。《周易》直接來源則是商末周初的占筮之書,經由周文王、周公等進行編訂,至孔子贊《易》,作《易傳》,則為其注入了理性色彩,使其脫離了原有的占筮性質,從而為儒家學說貫注了天人哲學視角,儒家道德觀因而有了“形而上”的宇宙觀來源。
《周易》的思維方式是取象比類,或者叫比物象異,通過取象把萬世萬物都統合到一整套六十四卦的符號系統中,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統合天人的思維方式和符號系統,因此《周易·系辭上》說:“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這就開啟了“萬物一體”的天人觀念。
宋明理學為了回應佛教與道家,利用先秦儒家資源建構了一套哲學的天道觀,其中很重要的是利用了《周易》的資源,將天道和人道統合到一起。王陽明在《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中說道:“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與北宋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民胞物與”理念遙相呼應。
除了“萬物一體”觀念之外,中國古代一直有“三才之道”的論述。三才,即天、地、人,這一觀念最早也源自《周易》。《周易·說卦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概括了天、地、人三才的不同屬性。天道的根本,在于陰陽二氣的運行變化;地道的根本,在于世間萬物的剛柔交錯;人道的根本,在于道德仁義的修養遵循。在這些屬性中,天、地、人也是互相呼應的。
世界是在天、地、人的交互作用中才得以成立。因而,古代又有“天人相參”的說法。春秋時期,越王勾踐的相國范蠡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后乃可以成功。”(《國語·越語》)《中庸》也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即便是戰國時期主張“天人相分”的荀子,在天人相互作用中,也強調君子在“天人相參”中的重要作用。《荀子·王制》說:“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可以說,中國自古以來就在尊重天地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加入人的主觀能動性,參與到天地萬物的造化之中,這就是《中庸》所表達的“參贊化育”理念。
二、“天人合一”最重要的是“天人合德”
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在敬天的基礎上轉向了對人生及人倫社會關系的思考,進而運用于政治學說之中,尤以道家對天道與人生關系的認知與儒家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及孟子“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的天人學說最為典型。
同樣也是《周易》最早提出了“天人合德”的思想,《周易·乾·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這里的“大人”即是指具有崇高道德品性的圣人君子,這種人的德行是可以上合天道、明昭日月、普照四方的。《周易·乾·象傳》與《坤·象傳》進而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也即君子效法天道而剛健不息,效法地道而寬厚包容,在德行上不僅縱向層面天、地、人具有同質屬性,橫向層面又兼具乾坤剛柔的兩面,從而達成天、地、人同德的道德境界,“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因而成為中國最典型的民族特征。
作為與《周易》同等地位的另一部中國早期哲學經典,老子在《道德經》中則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結構層次,與《周易》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相似,也是“人—地—天—道”的天人貫通視域,通過“道”這一核心命題將天、地、人統括為一體,融于“天人一體”的大道之中。
在道德修養方法上,《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即人的性來自上天,人遵循天道而行,按照上天的“誠”來實現人的“誠”,這個修養過程就是遵循和踐行天道,而修學天道的過程就是教化,圣人是能做到不用強求而從容中道的,因而是踐行天道的表率,圣人通過教化使人遵循天道而行,從而實現人人行為符合天道的理想狀態,其實就是道德教化層面的“天人合一”,也可以說是“天人合德”。
相傳《中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孔伋)所作,孟子受學于子思的門人,在道德教化與踐行天道方面,孟子繼承了子思的思想并發揚光大,成就了后來成為儒學主流的思孟學派。在回答人與天的關系方面,孟子提出了“盡心、知性、知天”和“存心、養性、事天”的道德修養方法論,《孟子·盡心上》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方面是君子通過“盡心、知性”來了知天道,通過“存心、養性”來侍奉天道;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修身來達到安身立命、順應天道,從而推動了儒家由心性論的修養了知天道及侍奉天道的修養方法論,從而成就君子人格,在心性層面實現天人貫通,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此外,與《中庸》一同被朱熹列為“四書”的《大學》則通過“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三綱領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建構了一整套由個人推及家、國、天下的修養與治國理論。個人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明了光明的德行,這一德行來自天道。個人修養完善后,進而推己及人,由家到國再到天下,從而影響更多的人,安頓全天下人,最終達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而“至善”,就是與天道相合。這是在具體實踐層面藉由“天人合德”最終達至“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三、“天人合一”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恰當追求
“天人合一”除了作為傳統道德觀的“形而上”的理論來源之外,在社會觀方面主要表現為中國傳統生態觀念與養生思想。中國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態觀由來已久。在與“五經”中《尚書》具有同等性質的古籍《逸周書》中就記載了周朝對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態追求與規定,《逸周書·文傳》中說:“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卵不?,以成鳥獸之長;畋獵唯時,不殺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不騖,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谷,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谷,樹之葛木,以為絺绤,以為材用。故凡土地之閑者,圣人裁之,并為民利,是以魚鱉歸其淵,鳥獸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林以遂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而戰國時代的孟子則繼承了這一思想,用來勸諫梁惠王施行仁政,從而在保證生態協調的前提下維護民生,實現其民本與仁政主張。《孟子·梁惠王上》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近些年來,粗放工業生產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所產生的惡果已經凸顯,南北極冰川融化、物種滅絕、氣候異常等生態惡果對人類生產生活產生的影響逐漸顯露,有人稱之為“大自然的報復”,或者稱為“天人相感”。這不得不說是大自然給人類的一種提示,應該在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基礎上考慮轉變人類舊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從而實現天與人和諧共存。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生態文明建設發表重要論述,2018年5月18日,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他就引用了《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經典語句,指出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這也是古老文明對現代生態發展的重要啟示。
作為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的中醫及其養生思想,也在醫學理念上貫穿了“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中國古代樸素觀念認為整個世界都是由“氣”推動運行的,具體又可歸納為陰陽二氣的交互運行。人由陰陽二氣所推動,人體本身就是一個小宇宙,人的體內循環依循外在時空而變換,因而人身具有與外界相合的生物節律與生命周期。人體治病與養生都不能脫離外在時空和節律而存在,因而中醫理論除了提出五行辯證的觀念外,還有五運六氣的身體運行理論與養生觀念。這實際體現了基于天、地、人同構的身體觀念。對于天地時空的強調貫穿了中國“天人合一”的醫學思想與養生觀念的始終。
四、“天人合一”體現中國文化的審美意趣
基于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和思想理念,中國傳統藝術無不貫注著“師法自然”的精神理念,為中國傳統藝術注入了精神活力與審美滋養。
與西方古典藝術傾向于具象寫實有所差異,中國古典藝術以“尚意”為先,尤其表達天人和諧的審美意趣與思想意旨。與西方傳統上以宗教畫或人物畫為大宗的寫實性繪畫不同,中國的水墨畫尤以表達人與自然和諧的山水畫為代表。
在居住環境上,中國的“天人合一”理念尤其體現在中國古代建筑與古典園林意趣上。由于哲學理念與審美意趣的差別,西方古典園林大多視自然為不完美的,因而強調通過人工設計加以改造,從而以幾何設計和對稱性為主要表現形式。與之相比,雖然中國傳統禮制建筑通過人工規劃突出禮制的威嚴,如紫禁城、天壇,而在園林這樣的非禮制性建筑中,中國古典園林卻以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造園意趣表達“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以蘇州園林、圓明園、頤和園等為代表,善于運用借景、框景等手法將自然景物納入生活空間之中,運用裝飾和植物點綴表達田園意味與思想品位,從而達到了中國古典造園藝術的巔峰,并進而反映到文人山水畫的水墨意趣之中。可以說,中國古代建筑和園林藝術將“天人合一”的生態理念與審美意趣合而為一。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北京大學,在師生座談會上列舉中華文化中的優秀思想和理念,就提到了“天人合一”。2014年5月15日,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首次提出闡釋中國和平發展基因的“四觀”,其中就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2021年4月,總書記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的講話指出:“中華文明歷來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可以說,“天人合一”既是中華文明的精神追求,也是新時代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追求。“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傳統宇宙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因子,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觀念、道德規范,也是我們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智慧源泉。我們應汲取“天人合一”的文明智慧,推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使這一久遠智慧在新時代展現出更加璀璨的時代風采。
(責任編輯?黃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