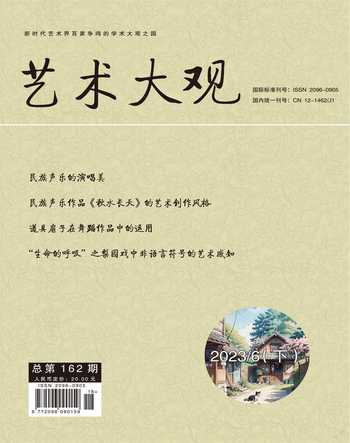俄羅斯作曲家斯克里亞賓《第四奏鳴曲》研究
張徵靜


摘 要: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斯克里亞賓的音樂誕生于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俄羅斯。他的“神秘主義”觀念、創作手法和審美情趣都與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相結合。本文將重點論述斯克里亞賓中期作品《第四奏鳴曲》,從這部奏鳴曲的曲式結構、和聲分析入手,去解讀這一部作品,發現隱藏其中的尚處于萌芽階段的“神秘和弦”。
關鍵詞:斯克里亞賓;第四奏鳴曲
中圖分類號:J6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18-00-03
一、斯克里亞賓時代背景
斯克里亞賓出生于1871年,他生活的這短短的43年,正處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紀歷史轉折時期,屬于世界現代前期。對于俄羅斯來說,此時的俄羅斯經歷著農奴制改革,農民獲得平等權利成為自由人,人們對自由的渴望、對個性的追求以及戰爭帶來的動蕩,都使得各種文化思潮在這個時期瘋狂興起。斯克里亞賓繼承了19世紀歐洲音樂的觀念和創作技法,又借由節奏、調式、調性、和聲等元素打破了傳統,形成了神秘而獨具個性化的音樂語言。獨特的風格使他的音樂成為連接浪漫主義音樂時期和近代音樂時期的橋梁。
二、斯克里亞賓人物背景
俄羅斯作曲家、 鋼琴家亞歷山大·斯克里亞賓(Alexander Skriabin),出生于1872年1月6日俄羅斯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母親是一位優秀的鋼琴家,從小在此家庭氛圍中的他,顯露出非凡的鋼琴演奏天分。但斯克里亞賓自幼與他的祖母生活在阿姨家。由于上一代的溺愛,以及他的敏感,好幻想和沖動的性格,導致他變得情緒脆弱。這一切都為日后逐步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埋下隱患。由此不難理解,多年后,他宣稱世界是“我的世界,我的創造,我的欲望”。而這種意識極大地影響了他音樂風格的形成與發展。斯克里亞賓游歷歐洲各國,他不斷吸取各個國家音樂的不同之處,更是受到了詩歌、戲劇乃至神學的影響,建立起了具有他自己獨特個人特色的神秘絢麗的音色風格。
三、《第四奏鳴曲》曲式結構
(一)第一樂章
第一樂章屬于單三部結構。A段(1-16小節),一小節的連接后接展開性的段落,又回到A主題的變形(35-50小節),最后以尾聲的變形來與第二樂章進行緊密的銜接,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單從曲式中不難看出,作曲家已經一點點嘗試打破傳統。在奏鳴曲的第一樂章采用其他的曲式結構,而不是使用奏鳴曲式。相比于第二樂章,第一樂章所占全曲三分之一,且在第一與第二樂章不論是作曲家本身的標示或是作曲家所特別譜寫的與第一樂章前面部分所不同的織體,以及缺失對比調性的主題,使第一樂章成為第二樂章高潮部分的鋪墊,在結構上我們甚至可以將這兩個樂章的奏鳴曲視為一個帶引子的奏鳴曲。在一定程度上暗示著斯克里亞賓之后創作的風格,由多樂章(傳統奏鳴曲基本為四樂章形式)轉向單樂章創作。在這一點上受到李斯特“交響詩”的影響,如《第七奏鳴曲——白色彌撒》和《第九奏鳴曲——黑色彌撒》,強調了詩意、神秘、哲理乃至神學的表現。
第一樂部呈示了樂曲的主題旋律(該旋律貫徹兩個樂章全曲)。這一樂部仍是使用八加八的規整形式,音型主要是上行四度音的進行,而旋律則出現了升D—升G—升C的四度音走向,在橫向的結構中可以看到,這個三全音和弦算得上是斯克里亞賓作為“神秘和弦”的嘗試和實驗。這個音程的聽覺效果極度不穩定,甚至是詭異的,音樂之父巴赫曾用“魔鬼、地獄、痛苦”等來形容,在以前的教會音樂中是被嚴禁使用的。但這并不影響它在斯克里亞賓的音樂創作中利用它來描繪出一種迷幻神秘的色彩。第二樂段基本為第一樂段的重復,但在接入過渡的時候有一小節的疊入,使整個銜接圓滑而統一。
展開部在第一樂部的基礎上加上了裝飾音、顫音,在節奏不變的基礎上由八分音擴展到十六分音,使得音樂在聽覺效果上更加具有流暢前進的感覺,偶然出現的切分音型,又以一種不平衡的推動感使音樂在奇異而美妙的變化中前進著。長顫音的推動接著一個帶裝飾音的上方四度音,猶如清晨鳴唱的鳥兒那般生機勃勃。左手也從單純的柱式和弦演變為四連音的琶音形式,在動力上為右手做了支撐,在音域上對之前進行了擴充,充分應用了低音區泛音的音響效果,使其雖然是琶音,但卻能讓聽者感受到音與音之間相互疊加相互融合的色彩感。在各種音型變化后,漸漸回到中心調,為再現做屬準備。
再現部將主題完整地再現了,但與主題呈現不同的是,在伴奏上出現了新的變化。第一句在旋律上方加入四連音為基礎的伴奏音型,雖為和弦,卻要求以PP的力度,宛如云朵一般烘托著主題旋律的起伏,在伴奏音型上,采用主持續的手法,使得之前一直游離的調性有了歸屬的感覺。第二句在第一句的基礎上,伴奏音型繼續加花,從四連音再一次增加音符的密度,變成一個小節由六個三連音構成,由原來的云朵一般朦朧的音色轉變為更為流動的效果,一直將樂曲不斷地向前推動著。這種在譜面上節奏不變但實際音效卻有所增加的手法,暗示著第二樂章的速度,并為其做好了鋪墊,使其能更為自然地銜接。
尾聲運用了主題材料,但不同的是,它并不是完全的引用,而是將材料的后半部分五連音上行的句子改為下行,意指即將到達這一樂章的結尾,似嘆息一般。但隨后很快又回歸積極而又充滿堅定力量的幾個和弦上,以一組未解決的和聲,使人無法不接著繼續去尋找解決的答案,以此將音樂順其自然地引入了第二樂章,使得兩個樂章連接得好像不曾有斷開樂章的感覺。
(二)第二樂章
第二樂章使用了一個完整的奏鳴曲式。呈示部一開始的主部主題就是由兩段規整的樂句所構成的復樂段。在主題音樂上,作曲家使用了8/12的節奏,并標示prestissimo volando(急速的),這種不平穩的節奏加上大量切分音符,使其產生一種沖動不安的情緒,從第一小節開始,音樂的走向一直不斷向上進行,先是由上行四五度跨越到半音階級進的音型,而音程的緊縮也不斷為這一作品帶來緊張的氣氛。之后,作曲家又將主部主題中的b材料抽出來,利用其將調性轉為副部主題所想要的#C調做出準備,這一部分為呈示部的連接部(17-20小節)。而主部主題的#F調與副部主題的#C調使其具備了奏鳴曲主副部調性必須是不同的這一特點。副部主題中使用了主部主題的旋律和節奏型,但卻將其隱藏在中間聲部,從音區上來看,直接從高聲部下降到了中低聲部區域,這也使得這兩個主題之間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系,兩者之間不僅僅是對比,更是對作曲家思想表達的一種陳述。在音區中那種隱約深重的感覺,更是使的音樂線條的張力得到擴充。
展開部有三段基本展開部分。展開部Ⅰ,使用了主部主題中的第一種材料進行展開,但只使用主部主題富有動力的連續上行四度的音樂形態,刪去了原主部主題的下行補充部分,并將旋律進行疊入。展開部Ⅱ,使用的是主部主題中第二種材料進行展開。此時音樂的調性主要落在#f小調上,這種由調性改變所產生的色彩將樂曲渲染得更為朦朧迷幻。展開部Ⅲ,則更為大膽地使用了第一樂章中的主題材料進行展開,并在主旋的每一個音上標記有重音記號,再次強調了第一樂章與第二樂章的內在聯系性。而且此處高音旋律的時值被拉寬了,也是為了在速度上與第一樂章有所對稱。最后用主部主題的第三種材料進行展開的屬準備部分,將之前游移不定的調性重新穩定下來,引申至再現部。縱觀整個展開部,其音區的大幅度跨越,強弱起伏呈現波浪式的巡回,伴奏織體流動的琶音,更是渲染了主題“恍惚飛翔”的特性。
再現部與呈示部的結構基本相同,都是由主部、連接部、副部和結束部構成的完整結構。但主題的再現與呈示部相比顯得更加緊湊,主旋律聲部和伴奏聲部時常會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奇妙的混響效果,而原本呈示部那種不安的音樂情緒在此處變得更為活潑。副部主題從102小節開始,此時調性已經回歸到主調的調性,主副部調性沖突得到解決。副部左手的伴奏音型主要以琶音為主,音區跨越中、低兩個音區,主旋律聲部高高漂浮于上端,這種創作手法在這首作品前面也曾出現過,我們也可以從側面判斷出斯克里亞賓在此時已經將這種飛翔式的創作手法逐漸融入個人創作風格中。結束部再次將主題材料加以變化地展開,運用重復和模進的方式一點點將力度和氣氛推向全曲的最高點,最后樂曲以fff最強的力度進入全曲的尾聲。
尾聲的主題旋律同樣是使用了第一樂章的音樂主題,但與之前不同的是,由dolciss(柔和的情緒)轉變為focosamente,giubiloso(熱情如火的)。這種轉變不僅突出了主題旋律的重要性,更是獲得了首尾呼應的效果。尾聲的伴奏織體達到了全曲中最為強大飽滿的組合形式,以柱式和弦為織體的伴奏聲部貫穿了鋼琴的高、中、低三個音區,六個音同時落下加上厚重的力度,聲勢浩大,如雷鳴滾滾一般,音樂熱情而激昂。同時,尾聲與之前其他部分不同的是,它使用了對稱的樂句寫法,為了達到最強的音想效果,音與音之間相互對齊,基本不再使用切分等不穩定的節奏型音。在和聲上,為了強調和鞏固#F大調的調性感,在和弦的使用上重復出現主、屬和弦,以明確中心調性。從之前作品中的調性游移,非傳統和聲以及樂句的結構來看,斯克里亞賓將這些不穩定的因素轉換為穩定,并將這種穩定推到了全曲高潮的頂點,可以看出作曲家對于樂曲的精心安排,使得音樂在最后獲得了圓滿的效果。
四、“神秘和弦”的萌芽
對于“神秘和弦”有多種解釋和說法。《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記載:斯克里亞賓從1910年到1915年的晚期作品,不是由主題而是由和聲的因素構成,通常是由神秘和弦變化而來,盡管它很少用基本原形來呈現。《牛津簡明音樂詞典》寫道:“其和弦往往建立在四度疊置之上,有時甚至是二度疊置。它由一系列的四度——C、#F、bB、E、A構成,有時甚至還加上D。”[1]《第四奏鳴曲》作于1903年,基本可以定位為斯克里亞賓中期作品中的第一首。其中開始的第九小節便已使用這個和弦(見譜例1)。這首作品與早期創作中主要是模仿肖邦、李斯特等人的風格不同,是逐漸顯露出斯克里亞賓個人風格的轉折點。若仔細觀察,可從他的十部奏鳴曲中發現,《第四奏鳴曲》是他最后一首多樂章奏鳴曲,也是最后一首在曲尾會有明確調性的奏鳴曲。在后期的六部奏鳴曲中都是以單樂章形式表現,且在調性的使用上越來越模糊,對于和聲色彩要求也越來越絢麗,最后甚至拋棄了傳統的大小調體系,只為追求音樂中的神秘性,以及運用音樂向人類傳達出某種真理。1904年,斯克里亞賓通過接觸通神論者,獲得神秘的概念,這種特殊的情感融入他的精神中乃至音樂中,在創作上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音樂風格。而相傳《第四奏鳴曲》僅用了兩天的時間便完成了,在這首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其中已經有了宗教神秘主義的突顯。首先,在奏鳴曲的結構上打破了傳統奏鳴曲第一樂章為奏鳴曲式的特點,將第一樂章寫成單三部曲式作品;其次,在節奏上,出現大連復合型節拍,左右兩手并不是對仗工整的,而是相互交織、相互烘托營造氣氛(見譜例2);高難度的分解和弦和復雜的織體,將鋼琴的表現力發揮到極致。在當時文化大爆炸的時代以及俄國不斷出現的革命背景下,不難感受到這部奏鳴曲中那種對于認識新的知識事物的愉悅之情,也能感受到在革命的動蕩中爆發的猶如風暴一般的音樂形象。《第四奏鳴曲》標題的引語是:“快樂像是我的翅膀一般,帶我不停地向上飛……為了追求那最美的心,不斷努力飛翔!”其中,星星所指的就是本曲中的主題材料。斯克里亞賓是這樣形容的:“這些美麗的星星閃爍著迷人的光芒,一會兒在深邃奧妙的宇宙中隱藏得只剩下隱約的亮光,一會兒那炫耀的光芒如炬,如一輪驕陽,把人們從一個境界領向另一個奇妙的世界。”全曲演奏一氣呵成,兩個樂章之間不做停頓。
五、結束語
斯克里亞賓是跨越歐洲晚期浪漫主義到近現代音樂的重要作曲家,他的音樂獨具魅力,在其背后還與他復雜的人格有著緊密的聯系。他的這些對于音樂的突破打開了通往近現代音樂的大門。縱觀20世紀近現代音樂,個性化是主流的思想。斯克里亞賓的個性化創作正是這種思想的先驅。在音樂的長河中,只有獨樹一幟,具有自己的風格才能被歷史所銘記。在斯克里亞賓的作品中,《第四奏鳴曲》又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他轉型期的第一部作品,傳統與創新都可以在這部作品中找到痕跡。通過分析比對,能讓人們更好地理解音樂中的無調性、復雜節奏、序列主義等,這對于進一步去理解20世紀音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宋莉莉.橫看成嶺側成峰——對斯克里亞賓“神秘和弦”的歷史審視[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5(01):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