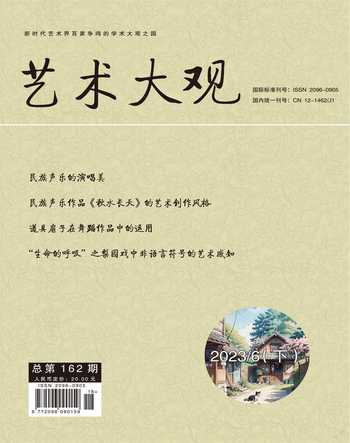奧馬爾·法斯特作品中的真實與虛構
徐文祺
摘 要:在這個數字真實侵入虛構領域的時代,一些藝術家的展覽引發了人們對于現實與虛構、真實與幻覺之間關系的反思。雖然電影被視為映射世界的一面鏡子,但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其始終無法完全替代現實,因為電影本身就是建立在虛構的概念之上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現實和虛構非常接近,這也導致兩者會被混淆:鏡頭越是中和,現實似乎越能自然地呈現,我們也越能體驗到有意識的虛構。本文將圍繞藝術家奧馬爾·法斯特的幾件影像裝置作品,探討“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真實;虛構;紀實
中圖分類號:J9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3)18-00-03
一、虛構和現實之間的關系——以《The Casting》為例
如果沒有現實,虛構就不可能存在;但如果沒有了虛構,真正的現實也難以呈現出來。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藝術家們一直在探索報紙、電視和電影如何使用圖像作為證據,同時也用于模糊事實和虛構的界限從而形成具有影響力的敘事,并從本質上重構了現實。影像藝術家奧馬爾·法斯特以影像為基礎,對現實和虛構的關系重新進行了界定,并有意地混淆回憶與真實事件的重現。他的影像作品穿梭于各種類型與形式之間,以現實和非現實的方式呈現特定主題,并探討影像作為真實和制造真實的工具在信息傳播中的作用和地位。他的作品往往通過重復、循環和重現等方式來操縱時間,在真實和虛構之間建立一種對話和關系,旨在將關于最近引起共鳴的事件的敘述與其背后的生活經歷重新聯系起來,讓觀眾在藝術的世界中體驗到現實和歷史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靜態電影又稱靜像電影,就是用靜態的圖像講述故事,例如新浪潮左岸派代表人物克里斯·馬克爾執導的科幻先鋒派短片《La Jetée》(1962年)全片僅有28分鐘,幾乎全部由完全靜止的畫面組成,在形式上使用靜態圖像來表現畫面,故事的主要敘述則來自旁白,而旁白的敘述者更像是一個旁觀者,以一種講故事的態度向觀眾敘述著,突破電影的限制,直接用語言向觀眾展示人物的心理。奧馬爾·法斯特的一件裝置作品《The Casting》便采用了這種形式,通過采訪的方式講述了美軍士兵的經歷和圣誕節期間與一個自殘女孩第一次約會的故事,影像中的圖像似乎是靜止的照片,而對話則是以畫外音的形式傳遞,這并不是靜態蒙太奇,而是演員們試圖保持僵硬姿勢的一系列鏡頭,這些畫面的組成遵循著一定的邏輯:當一個角色通過畫外音說話時,圖像軌道便切入一個用于描述對話的特寫鏡頭,短片中的試鏡被重新設定為采訪,虛構與真實相遇,相同的詞由于伴隨著不同的圖像而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含義。
《The Casting》運用電影元素作為虛構的幻想,來審視記憶、敘述和場景之間的關系。當觀眾在作品中四處走動時,由一個人的證詞引起的復雜情感,使紀錄片采訪與其戲劇化融合在一起,將這兩種表現模式混合,這種紀實和虛構的混合體與幾乎靜止的畫面的混合視覺形式相似,在運動圖像中使用近乎靜止的畫面,表現出媒介的交融。盡管這件作品具有四重投影和隨處走動的觀眾,與傳統電影有很大不同,但它仍然具有觀影視角、鏡頭語言和場景調度等電影元素,作品以紀實證詞為基礎,將其可視化,模仿主流新聞媒體的表現模式,將真實的形象和虛構的形象一起建構,使得虛構與現實不可區分,在經過一系列的處理后,士兵的話語中沒有任何真實的證明,所謂的非虛構意象在功能上等同于虛構,它基于非虛構的采訪,通過大量編輯和可視化進行雙重虛構,暗示了當代的真實逐漸衰退,被虛構所取代。
《The Casting》強調了兩個關鍵概念:“講述虛構的故事”和“紀錄片的證詞”。這兩種概念被建立在將電影視為一種虛擬技術的觀點之上,一直存在于藝術家對動態影像的運用中,且一直是電影史上的關鍵。該作品探討了電影參照性和再現性之間的張力,以及世界的真實和虛構之間的張力。從私人事件到公共事件的轉變,與我們由媒體構建的“集體記憶”融為一體。在當今社會,現實已經成為媒體圖像的形式,虛構和事實占據了相同的表現層面。讓·鮑德里亞認為:“我們今天世界的基礎不再是一種現實存在,而是建立在多重擬像偽相之上的幻覺,處于一個擬像的社會里面,我們所有看到的符號性和象征性的這些擬像的東西才是我們所感覺到的真實。”[1]擬像的超現實支配著視覺文化,它是沒有來源的復制品,在現實中沒有錨定,圖像不是指真實的,而是彼此之間沿著一條不同的符號鏈連接在一起的。傳統意義上的客觀真實,已經被預先設定好的符號模擬出來的“仿真”真實所取代。真實世界和擬像世界的界限在逐漸模糊,真實逐步消失,而影像逐步取代物質世界的真實,成為更加真實的世界。[2]用鮑德里亞的話來說:“虛構展現了一個更高級的階段,在這個范圍內,它消除了現實的東西與想象的東西之間的對立。非現實的東西不再留存于夢幻或超越之物中,它就在現實的幻覺相似物之中。”[3]其結果是真假難辨難分,進一步導致了“假的比真的更真實”,媒介正在構建一個比現實更現實的“擬象”社會,真實比虛構更令人陌生,這是因為虛構已經無處不在。
二、真實與虛構的混合形式——以《Nostalgia》為例
紀錄片與虛構電影似乎是對立的,一種強調未經處理的客觀真實,重現現實,還原生活的本相,而另一種則暗示著脫離現實進入虛構的領域,紀實影像和虛構影像在所有與動態影像的接觸中都發揮著作用,虛構電影試圖盡量減少電影元素以強化其故事世界的現實印象,而紀錄片則將必要未實現的電影形象和介入現實之間的因素囊括起來,以便更好地傳達即時性和真實性。然而,也有人認為,相對于真實的現實世界而言,電影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虛構,紀錄片本身就存在于虛構之下,因此電影能夠穿透這些虛構達到“真實”的通道。在《The Casting》中,因無法接近真實本身,法斯特通過將紀實和虛構相結合,打破圖像參照和認識論地位的傳統觀念,使紀錄片創作呈現出虛構與紀實相融的混沌狀態。當代藝術家在不斷地探索現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將圖像的參考地位轉向紀錄片和虛構的混合形式,旨在探索在真實和圖像之間的多重關系,而不是斷言它們的可互換性。他們認為,運動圖像可以在圖像的參照力受到質疑的時候表現出真實的痕跡,數字媒體的普及使非虛構圖像的傳播能力大大提高,因此觀眾對這些圖像“真實性”深信不疑,藝術家并沒有將這種情況視為消除任何紀錄片的可能性,而是強調參照性和再現性的共存,以便同時質疑紀錄片的真實性,并通過虛構產生的真相,引發更深層次的思考。
自1990年以來,各界對現實與虛構之間關系的質疑成為動態影像藝術的一個普遍現象。此時紀實和虛構的雙重轉向,標志著人們開始接受運動影像作為一種虛擬技術,高質量的電影和視頻被廣泛應用在早期藝術家對運動影像和電影理論的探索中。繪畫主義、虛擬主義以及敘事被認為是電影吸引觀眾的關鍵手段。福斯特指出:“從物質現實到虛擬的轉變是概念化藝術家如何使用運動圖像的一個重要因素。”
奧馬爾·法斯特的《Nostalgia》是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視頻裝置,通過敘事和電影結構、紀錄片和戲劇化的交織模式探索事實和虛構的關系,集畫外音、電影、紀錄片等多種元素于一身,將過去、現在、將來編織在一起。其中兩個超現實的場景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個是嘔吐的女孩,隨著鏡頭的平移嘔吐物變成了新鮮水果和花朵,這一鏡頭形象地概括了關于現實與再現之間關系的命題,同時也說明了再現也會背叛真實。
紀錄片和虛構之間存在深刻的本體論差異。法斯特堅持將紀實影像融入虛構,這表明《Nostalgia》和《The Casting》同樣強調了當代視覺文化標志著一種指涉性危機,其中,虛擬已經真正超越了現實。然而,法斯特并沒有抵觸這種情況,相反,他將其重新組合起來,要想使紀實圖像發揮作用,它們需要觀眾來評判,而制作者則需要對其進行情境化。維維安·索布查克(Vivian Sobchack)說:“死亡、再現和紀錄片的結合,預示著所有的視覺都是真實的,因為它涉及一個世界和其他世界。”[4]因為死亡和再現都是現實生活中的元素,而紀錄片則通常被視為揭示真實的方式。因此,當這些元素相互結合時,它們可以提醒我們,所有的視覺都是真實的,因為它們都在某種程度上涉及現實世界。此外,它也暗示著現實世界和其他世界之間的聯系,因為它們的交匯點可以通過這些元素的結合來表達。另一個場景是在一個廢棄地鐵站的椅子上,一名男子所觀看的《Sans soleil》中關于長頸鹿的片段。當它被擊中,它先是在灌木中掙扎,然后它開始顯得虛弱、無法站立,到最后痛苦地倒在地上。這個場景呈現出的氛圍是非常壓抑和真實的,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它體現出紀錄片的表現力以及觀眾與影像之間的關系。與之前女孩的表現方式不同,長頸鹿凸顯出真實的表現力。雖然長頸鹿的場景是存在于電影中的影像,并不是直觀的表達,而是間隔了一層媒介,但它同時也表現了真實的場景,這種真實性和影像之間的關系,代表著我們對于真實和虛構的認知和理解。在電影中,作者將人的視覺和記憶與攝像機和影像之間的關系相比較,強調了影像作為表達記憶和時間的媒介的能力。而長頸鹿的死亡場景則讓我們反思影像作為表達真實性和虛構之間的界限。它證明了在模擬中的持久性。圖像可能與其他媒介相關,但它們仍然可以與真實相關。長頸鹿的死亡場景打破了《Nostalgia》的代表性結構,并重申了紀錄片圖像可以漸近現實的方式,因此,可以將其視為一種紀錄片的虛構混合體。
作為一種記憶另一個時代的方式,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引發全球重組,使這個世界與我們所知的世界不同,或許這是為了在面對死亡時更好地理解生命。盡管世界已經被媒介重新編組,但這已經成為一個既成事實,長頸鹿的形象可能只是另一個時代的殘影,通過技術與世界建立聯系的符號,這在所描繪的未來社會中可能已經不再可能存在。紀錄片影像的觀眾渴望脫離現實,并通過電影尋求恢復的路徑,這種技術自相矛盾,不符合實際,從而創造出一種缺失并用同樣的方式來彌補它的方法。但是所有關于這個角色的心理和情感狀態的猜測都與虛構世界有關。與此同時,長頸鹿的形象已經超越了這個未來的科幻虛構情節,并將其形象重新塑造為單純的擬像。精心制造的“現實印象”因《Sans soleil》出現的真實回歸而變得不穩定。《Nostalgia》的整個敘事陷入了危機,長頸鹿的形象間接地指向了所有被排除在尼日利亞難民故事之外的東西,它已被引導到虛構的代碼中。動物死亡的呈現代表了真實,它開始侵蝕法斯特精心制作的虛構,暗示它的不公正,這表明只要有旁觀者關注,參照性確實會持續存在。
盡管《Nostalgia》與《Sans soleil》有共同點,兩個死亡場景都是象征性的符號,代表著作者對于時間、記憶、生命和死亡的反思,引入了對其自身策略的懷疑,而這在早期的裝置中是不存在的。它從簡單地拆除電影和電視中的現實主義慣例,轉變為質疑所有紀實影像現在都與虛構密不可分的這一概念本身,包含其自身的一些虛假設定。嘔吐物變成花朵的女人的形象可能表明了虛構電影中處理暴力的方式,但長頸鹿之死暗示了一種不安,人們對這兩部作品中出現的指涉性提出質疑。正如希托·斯特耶爾所說的:“書面證詞可能不可靠,可能撒謊,也不一定以任何透明的方式傳遞事件”,但它“可以表達難以想象的、已經沉默的、未知的、拯救的,甚至是可怕的東西——從而創造了變化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存在不確定性和不可靠性,書面證詞仍然具有潛力創造變化和產生重大影響。人們關注紀實影像,在其中既看不到事件的真相,也看不到擬像,而是要面對、質疑和考慮物質圖像[5]。
三、結束語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觀眾需求的變化,影像的形式和功能也在不斷地發展和改變。在當前的數字時代,影像已經成為一種極其重要的文化形態,它不僅承載了人類的歷史和記憶,而且已經成為能夠引起觀眾情感共鳴的重要藝術形式。影像將紀錄片和虛構模式結合到不確定的關系中,形成了一個微妙的美學建構。通過重新構想紀實影像和虛構影像之間的關系,我們承認它們的重疊而不是斷言它們在本體論上的對等,在這里,影像不再作為一種舊媒體,而是作為一種將藝術帶入與存在對話的新方式而受到歡迎和思考,使觀眾與另一個地點和時間的啟示性虛擬相遇。接受電影作為一種虛擬技術的力量并不一定意味著停止質疑媒介在物理現實與其表現之間的干預方式。奧馬爾·法斯特的作品并沒有將虛構和非虛構視為對立或分離的,而是將“混淆美學”加倍,并進一步混淆了虛構和參考之間的劃分,將這兩種概念結合起來,接受影像作為一種虛擬技術的力量并不一定意味著停止質疑媒介在物理現實與其表現之間的干預方式,運動圖像可以呈現給觀看的內容具有一定的規模和意義。在法斯特的作品中,真實通常是基于現實的素材。他使用真實的故事、場景、人物等來構建作品,但是在這些真實的素材上,他又加入了虛構的元素,這些虛構的元素可能改變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添加新的情節,或者是讓人物以不同的方式行動和表現,這種真實和虛構交織的方式,讓法斯特的作品更加有趣且引人入勝,同時也讓觀眾對真實和虛構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和理解。
參考文獻:
[1]孫冬,Man-Wah Luke Chan.論當代西方戲劇中的“在場”[J].外國文學研究,2010,32(05):145-153.
[2]周強.仿真與后現代表達:鮑德里亞擬像理論中的中國科幻電影解碼[J].電影評介,2019(15):48-52.
[3]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4]維維安·索布切克,范蓓.銀幕場景:想象電影化與電子化的“在場”[J].電影藝術,2010(05):95-102.
[5]孫晗迪.真實與虛構的雜糅——偽紀錄片的倫理考量[J].電影文學,2021(02):136-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