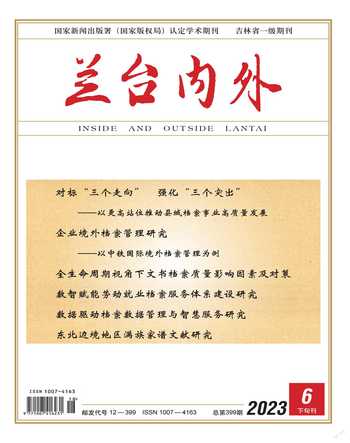“華亭周氏圖書”述略
摘 要:周大烈所藏“華亭周氏圖書”被其后人從20世紀90年代起,分三批捐贈給上海市圖書館、靜安區圖書館和金山區圖書館。捐給靜安區圖書館的藏書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對其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為深入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部署要求,近年來靜安區圖書館對周大烈“華亭周氏圖書”進行了認真的整理和研究,包括古籍版本鑒定,破損情況調查,編寫善本書目、善本書志和善本書錄等,揭示善本的存世價值。本文旨在呈現“華亭周氏圖書”的整理研究成果,展示靜安區圖書館在古籍保護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關鍵詞:華亭周氏圖書;古籍;藏書
引言
“華亭周氏圖書”是上海市靜安區圖書館所藏古籍的重要部分,為周大烈先生舊藏[1]。
周大烈(1901—1976),字迪前,號述廬,松江縣亭林鎮(今屬上海市金山區)人,中國學會發起人之一,中華圖書館協會首批會員,藏書家、國學家,有藏書樓名“后來雨樓”。周大烈是清代江南著名藏書家周厚堉之后。周厚堉“來雨樓”藏有歷代古籍善本。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向民間征書,周厚堉進呈的藏書逾百冊被錄用。周大烈的藏書室命名“后來雨樓”,有承繼祖輩藏書之志之用意。周大烈喜歡藏書,也勤于著述,著有《松江文鈔》《松江詩鈔》《南齊書校注》《南史藝文志》《四庫附存簡明目錄》《后來雨樓書目》《知見輯佚書目補》《清代校勘學書目》《述廬文錄》等。1937年冬,日寇從金山衛悍然登陸,周大烈與家人到上海躲避。一年后將劫余的藏書運到上海靜安區一處公寓,從此再沒有回家鄉。1976年,年事已高的周大烈逝世。20世紀90年代,周大烈七位子女將劫后幸存的近萬冊圖書捐贈上海市圖書館。1994年6月,周大烈七位子女再將1288冊藏書捐贈靜安區圖書館。2016年11月,周大烈之子周東壁先生作為子女代表又將1197冊藏書捐贈給金山區圖書館。關于捐贈靜安區圖書館的藏書,筆者協同文獻專家進行整理和研究,以便學界對周大烈及其“華亭周氏圖書”有一個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1 靜安區圖書館與“華亭周氏圖書”的淵源
周大烈先生從避居上海到去世,一直住在靜安區。其子周東壁就住在靜安區圖書館附近,愛閱讀的他經常到圖書館看書、參加活動和做志愿者。基于對靜安區圖書館的深厚感情和信任,周東壁先生提出將父親周大烈先生的1288冊藏書捐贈給靜安區圖書館,得到了兄妹們的一致支持。1994年6月,周氏兄妹將其父親藏書的一部分捐贈給靜安區圖書館。靜安區文化局和靜安區圖書館舉辦捐贈儀式,并向周氏兄妹頒發捐贈榮譽證書。證書寫道:“周迪前先生收藏之古籍,經子女周東序、周東垣、周東塾、周東壁、周孟繁、周梅詫、周季蘋七位,將1288冊藏書捐贈靜安區圖書館。使這些古籍為更多讀者所用,是為造福后人,功德無量。”同年11月,靜安區圖書館聘請周東壁先生為榮譽館員。2020年4月,圖書館領導登門拜訪耄耋之年的周東壁先生,向他介紹捐贈古籍的整理情況,提出將把整理成果陸續予以出版的設想,以此種方式致敬周大烈先生及后人捐書之大義[2]。同時,為了使這些古籍得到更好的傳承和利用,圖書館將通過舉辦周大烈藏書展覽、論壇、研討會、影印出版等形式,使更多的讀者了解藏書的內容和價值。周東壁先生對此表示支持,并深感欣慰。
2 館藏“華亭周氏圖書”整理情況
2.1 整理背景
自1994年至2018年,“華亭周氏圖書”作為鎮館之寶一直保存在靜安區圖書館專門定制的書櫥里,考慮到古籍的珍貴性及破損情況,沒有向公眾開放。為了完成周大烈先生子女捐書的心愿,繼承和發揚周大烈先生對傳統文化典籍的愛護精神,靜安區圖書館于2018年開始與復旦大學古籍保護專家一起,對這批藏書進行整理和研究,一方面響應國家號召,另一方面對這些古籍進行有效的開發和利用,使之走出書櫥,走向社會,真正服務讀者。
2.2 整理過程與成果
2.2.1對“華亭周氏圖書”進行梳理和書目編纂。靜安區圖書館將獲贈的“華亭周氏圖書”收藏于原中華民國海關圖書館,即如今的海關樓版本主題館。圖書館收錄時制成館藏古籍資產登錄簿,但未對這些古籍從文獻專業的角度進行編目整理、系統分析與研究。圖書館邀請文獻專家對全部藏書進行清點,共梳理出屬于線裝書藏書245部1167冊,并按照國家《古籍著錄規則》(GB/T3792.7-2008)標準,從題名、卷數、著者、版本、冊數、存卷、內封、卷端、藏印等款目內容方面對古籍進行著錄,最后編纂完成《靜安區圖書館海關樓藏古籍書目》。書目按照經、史、子、集、叢五部進行分類,其中經部29部148冊;史部52部323冊;子部74部202冊;集部87部464冊;叢書部3部30冊。
2.2.2對“華亭周氏圖書”古籍破損情況進行調查。“華亭周氏圖書”歷經戰火和多次轉運,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損。加之年代久遠等原因,紙張存在酸化、老化等現象。此次整理,不但對每冊古籍的尺寸和厚度進行測量,還對其破損情況開展調查登記。包括各冊的裝具、書衣、題簽、訂線、霉蝕、蟲蝕、鼠嚙、斷裂、書口開裂、水漬等內容,共完成破損調查記錄6000余項,形成《靜安區圖書館海關樓古籍尺寸測量與破損調查清單》,為今后制訂古籍修復保護方案提供了基礎數據。
2.2.3版本鑒定和編纂善本書錄。區圖書館邀請復旦大學圖書館文獻專家對“華亭周氏圖書”進行版本鑒定。在245部古籍中,清代乾隆六十年及以前的刻本、稿本、抄本、批校題跋本,以及乾隆六十年以后的稿本、抄本、校本及稀見刻本等可以列入善本的,有69部361冊,其中明刻本就有27部。專家調查了69部善本在國內外各收藏機構存藏情況,發現有的僅見于國內外幾家圖書館。例如《論語義疏》十卷本,是三國時魏國大臣何晏所做的集解,唐朝時傳到日本,并有手抄本流傳。到清代時,日本的足利學校還收藏有手抄本,第三任駐日公使徐承祖等人經過多方努力,才獲得足利學校同意,對該手抄本進行抄錄。帶回國后,由于各種原因沒有付諸刻錄。陳捷《關于清駐日公使館借抄日本足利學校藏<論語義疏>古鈔本的交涉》詳細介紹此事經過,并感慨一直找不到此抄本的下落。
2.2.4撰寫善本書志。在編纂《靜安區圖書館海關樓藏古籍善本書錄》之后,通過各書的序跋、識語、牌記、批校題跋、藏書印、版式、刻工等信息,參考《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叢書綜錄》、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高校古文獻資源庫、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等工具書和網上數據庫[3],選擇《南華真經》《論語義疏》《嵇中散集》《林屋全集》等重要善本撰寫書志,向讀者揭示這些善本的存世價值。
在此試舉一例,《南華真經十卷》書志:戰國莊子撰,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明刻《六子全書》本。六冊。半葉八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白魚尾,四周雙邊,版心鐫題名、卷次及頁次。框高十九點七厘米,寬十三點五厘米。前有郭象序。《南華真經》即《莊子》。唐玄宗天寶元年,莊子被封為南華真人,其著作亦被尊為《南華真經》。此書《中國古籍總目》著錄的最早版本為宋刻本,另有明嘉靖十二年顧春世德堂刻《六子全書》本、桐陰書屋刻本、萬歷十一年金陵胡東塘重刻顧氏《六子全書》本,清嘉慶九年姑蘇王氏聚文堂刻《十子全書》本、寶慶經綸堂刻本、愛日堂刻本、清劉履芬抄本等。其中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徐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上海圖書館藏明桐陰書屋刻《六子全書》本(袁廷梼跋并錄顧之逵校,葉景葵跋)分別入選第二批和第五批。此本乃據明嘉靖十二年顧春世德堂《六子全書》本翻刻。顧春字符卿,號東滄居士,江蘇吳郡人。有“世德堂”以刻書聞名。《六子全書》為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包括《老子道德經》《南華真經》《沖虛至德真經》《荀子》《揚子法言》和《中說》六種。其始刻于明嘉靖九年,竣于明嘉靖十二年,因校刻精良,后來多有仿刻、翻刻。前述明桐陰書屋刻本,《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有著錄,并認為乃“翻刻嘉靖十二年顧春世德堂《六子全書》本零種”。此本不避“玄”諱,版式、行款、字體均與顧春世德堂本同,惟版心上未鐫“世德堂刊”。哈佛燕京圖書館有收藏,并著錄為“明刻《六子書》本”。《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稱其“乃據明嘉靖十二年顧春世德堂刻《六子書》本重刻。顧春世德堂本書口上有‘世德堂刊四字,此重刻本則無”。此本通篇有沈大成錄惠棟紅豆齋校并跋。《南華真經序》題名下有沈大成綠筆跋語:“乾隆丙子中冬,借紅豆齋本錄,其《音義》則以陸氏《釋文》校正。小寒日大雪,云間沈大成記。”卷端題名下有朱筆識語:“乾隆丙子歲莫,大雪累日,借紅豆齋本校讀于廣陵客舍。沈大成記。”卷二眉端有朱筆批點:“莊生知道,實開予心。壬申九月二十一日識。”鈐有“學子”朱文連珠方、“有華書塾珍藏”朱方、“徐暎玉印”白方、“鹿樵”白方、“桐城蕭穆經籍圖記”朱方、“曾植私印”白方、“灊庸”朱方、“蘧傳”白方、“嘉禾姚埭沈氏金石圖史”朱方、“宋戉”朱文連珠方、“婁邨宋肎堂珍藏”朱方、“肎堂”朱方、“宋鉞私印”白方、“臣鉞之印”白方、“宋鉞之印”白方、“長宜子孫”朱方、“羲皇侶”朱方、“?鋒”朱方、“華亭周氏圖書”朱方印。
3 “華亭周氏圖書”的藏印情況
“華亭周氏圖書”的最大特征是鈐有“華亭周氏圖書”的朱文方印。靜安區圖書館的周大烈藏書幾乎都蓋有此印章。除“華亭周氏圖書”藏印外,許多書還蓋有歷任主人的藏印,如明崇禎刻本《翰海》十二卷鈐有“光風霽月”“俠膽傲骨”藏印,清康熙錢唐龔氏玉玲瓏閣刻本《浙西六家詞》鈐有“澹淵真賞”“王澹淵審定”“華亭王慶麟字畤祥一字澹淵印章”藏印[4]。更難得的是,“華亭周氏圖書”有很多是名家舊藏,如明刻六子全書本《南華真經》十卷鈐有沈大成、張大鏞、沈曾植等人的藏印,他們都是清代著名的藏書家、學者;明萬歷徐氏刻清康熙二十年徐佺重修本《世經堂集》二十六卷鈐有鄧汝功、吳引孫等人藏印,鄧汝功是清乾隆四十年進士,吳引孫是晚清官員和著名藏書家;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富順官廨刻本《六書音均表》五卷鈐有溫葆淳藏印,溫保淳后改名溫保深,做過咸豐、同治兩任皇帝的老師,官至福建學政、太子少保等職。
4 施蟄存與“華亭周氏圖書”
現代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學者施蟄存先生多次借閱周大烈先生藏書。這些藏書對施蟄存先生在校勘學、詞學、金石學、地方文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很大幫助。據《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收錄的施蟄存日記、信件中的記載,僅在1963年至1965年三年間,施蟄存先后21次到周大烈家中借閱研究所需要的珍貴書籍。這些書籍有《杜詩闡》《釋柯集》《葩廬詩經書目》《松江詩鈔》《湘瑟詞》《谷水舊聞》《金石莂》《封蔭甫傳》。施蟄存每次從周大烈處借到所需藏書都欣喜萬分,常在日記中記錄下興奮難已的心情,如:借到《云間文獻》八冊,回家后從早讀到晚;借到《萍因蕉夢閣題辭》《熙朝詠物雅詞》《金石莂》《猶得住樓詩選》等書,說這都是自己好長時間就想得到的。其中就有捐贈給靜安區圖書館的《金石莂》。此書為清代馮承輝撰,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云間馮氏刻本,內封題有“金石莂,云間馮少眉影摹金石拓本上版,刊者金陵鎦貢九,時嘉慶戊寅春日印行”,并蓋有“華亭周氏圖書”朱方印。
“華亭周氏圖書” 使施蟄存先生與周大烈先生成為學問上的知己。周大烈去世后,施蟄存親自為其撰寫《處士周迪前先生誄》,稱其“藝征七略,文律兩京”,“知其學樸茂淵渟,真儒士也[5]”,“失我益友,滋可痛也”。可見二人感情之深厚。
結語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中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6]該意見要求:“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加強古籍搶救保護、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進古籍事業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力量。”為此,靜安區圖書館將繼續做好“華亭周氏圖書”整理研究工作,通過推動古籍數字化、開展古籍專題展覽展示[7]、編輯出版、開發文創產品等方式[8],加強“華亭周氏圖書”古籍的保護、傳承和利用。
參考文獻
[1]周大烈選輯,張青云整理.清百家詞錄[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1-3.
[2]周大烈,姚竹修著,張青云點校.述廬文錄·惠風簃剩稿[M].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7.
[3]沈建中編撰.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陳捷.關于清駐日公使館借抄日本足利學校藏《論語義疏》古鈔本的交涉[J].版本目錄學研究,2010(10):375-408.
[5]周東壁,戴群.亭林周迪前先生紀念冊[J].都會遺蹤,2021(1):71-86.
[6]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J].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22(12):30-33.
[7]黃瑾.古籍的保護與利用分析——以南京圖書館為例[J].收藏與投資,2023(3):100-103.
[8]林立濤,王東波.古籍文本挖掘技術綜述[J].科技情報研究,2023(1):78-91.
作者簡介:韓怡星(1971— ),研究生,上海市靜安區圖書館館員,研究方向:文獻保護與傳承,文獻整理研究。
檔案史話
“清檔”——清代檔案的匯抄制度
在清代,軍機處建有一種檔案匯抄制度,稱為“清檔”。據《樞垣紀略》一書載:“凡本日所奉諭旨及所遞片單,抄訂成冊,按日遞添,按月一換,謂之清檔。”由于“清檔”系軍機處日常之事,故匯抄的范圍非常廣泛,數量繁多。諸如凡軍機處擬定的諭旨,經送交皇帝審定以后,均發還軍機處,由軍機處值日章京逐日逐條地謄錄在特別的簿冊之上,每月一冊,名曰“現月檔”。每年的“現月檔”均需另修一副本,按季分別命名為“春季檔”“夏季檔”“秋季檔”“冬季檔”總稱為“四季檔”。此外,軍機處還根據具體需要,按專題或事件匯抄檔案。例如在清乾隆朝以后將鎮壓農民起義的有關上諭和奏折匯抄而成的“剿捕檔”;抄錄有關西藏的各種檔案而成的“西藏擋”;記載皇帝出巡各地的“巡幸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