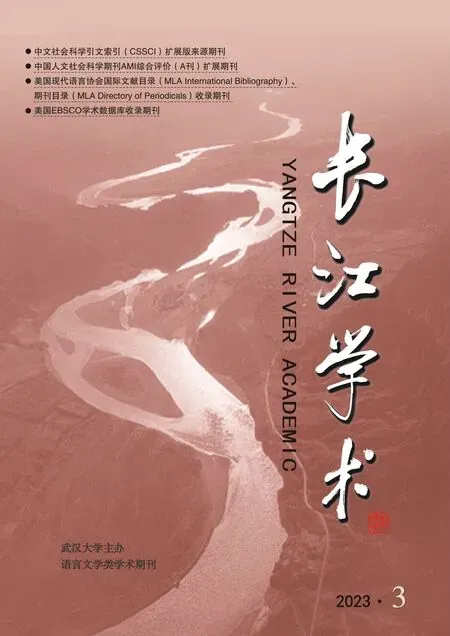意境化與知性化:現代派新詩意象與唐宋詩詞
陳學祖
(杭州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派詩人們在意象的選擇與運用上始而趨同,繼而分化乃至最終趨異。一部分現代派詩人追求意象意境化,呈現出朦朧空靈之美感色彩;另一部分現代派詩人則逐漸趨向于玄學化、思辨化詩風,并將其與唐宋詩詞的理趣美因素相融合,從而造成濃厚而獨特的知性特征。
一、現代派新詩意象意境化與唐宋詩詞
一大批現代派詩人在意象運用上受到唐宋詩詞的深刻影響,同時融合了西方現代派意象藝術,致力于意象意境化,其詩歌在整體上呈現出含蓄蘊藉的詩意結構,顯現出空靈幽晦的美感色彩。






受到新月派、象征派以及20 世紀30 年代現代派潤澤而成長起來的更年輕的一代青年詩人,如何其芳、林庚、程千帆、孫望、林英強、侯汝華、朱英誕等,均為唐宋詩詞行家里手,一方面迷戀于唐宋詩詞那種惝恍迷離的意境,另一方面熱衷于以分行書寫的新詩來表達自我內心的情思。因在調和與融通中西詩藝上所做的努力,其新詩構成因素極其復雜,作品呈現出別樣格調,其中的唐宋詩詞因素非常鮮明,甚至可稱為詩作中最重要的色調。換言之,他們的新詩亦多用唐宋詩詞的意象與語言,在詩風上呈現出強烈的意象意境化色彩,甚至將新詩寫得如同唐宋詩詞一般。


何其芳對唐詩有精細的閱讀和精深的研究,對李白、杜甫、白居易、溫庭筠、李商隱、李賀等人感興趣,尤其是對李商隱可謂達到癡迷程度。不但早期新詩中滲透了李商隱的詩美因素,而且直到晚年的舊體詩詞仍多模仿杜甫、李商隱之作,前者有《效杜甫戲為六絕句》,后者有《有人索書因戲集李商隱詩為七絕句》,其晚年創作的58 首舊體詩,竟有38首“無題”詩。此外,其《杜甫草堂》乃是歌詠杜甫之作,其14 首《憶昔》詩明顯受到杜甫《憶昔》詩的啟發,而《錦瑟——戲效玉溪生體》二首亦啟思于李商隱《錦瑟》詩。



二、現代派新詩意象知性化與唐宋詩詞
如果說戴望舒、梁宗岱、何其芳、林庚、吳興華、程千帆、孫望、林英強、侯汝華、朱英誕等人的詩歌更傾向于情緒與情感的表現,對唐宋詩詞意象的借鑒與沿襲主要是晚唐五代詩歌與唐宋詞“興象玲瓏”之美,那么,廢名、卞之琳、金克木、路易士、徐遲、南星則既重視“興象玲瓏”之美,又較為偏重與突出唐宋詩詞意象的獨特運用——善于以理性與智慧選擇富有差異性的意象,并將這種差異性予以突出與強調,因而其詩歌意象與意象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異質與背離,但這些看似相互之間背離的意象,卻在情感指向與藝術功能上具有驚人的一致性與統一性。換言之,他們善于以其獨特的理性與智慧,在意象選擇與藝術營構上體現出驚人的冷靜與克制,因此,在他們的詩歌中,本為感性意味的意象,卻因經過了理性與智慧的冶煉而展現出別樣的知性之美,其詩歌的意象藝術,可以說是唐詩之“興象”、宋詩之“理趣”、唐宋詞之“婉約”與西方現代派詩歌之“知性”的有機融合。








這正是卞之琳詩“智慧之美”的典型體現,也是其早期詩歌與唐宋詩詞之重要關聯。卞之琳最喜愛的唐宋詩詞家如李商隱、溫庭筠、姜夔,以及外國現代派詩人波德萊爾、魏爾倫、艾略特、里爾克、瓦萊里等,其詩詞作品也最能體現上述兩個特征。這是上述中外詩人相通之處,也正是卞之琳看重與取法之處。






《斷章》中的意象經由一般語詞的連接,構成了四個意義完整的句子,第一節是虛擬的情境,尚屬寫實層面,第二節則轉為由實入虛,由具體到抽象,由清晰到朦朧,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層次。從第一節到第二節,無論是句法結構還是語義結構,均發生了本質變化。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是,其一,第一節與第二節的“你”是否同一個人?其二,第二節中的“別人”是否就是第一節中的“看風景的人”?其三,既然“你站在橋上看風景”,怎么又說“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其中的“窗子”指的是什么?詞語語義的模糊造成了此詩眾說紛紜的解釋,也造成了巨大的闡釋空間與審美蘊涵。詩作語言形式的安排與內容的暗示多義,顯然得益于唐宋詩詞的類似詩歌結構,如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江畔何年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李商隱《子初郊宿》“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在句子結構與語義結構上整飭中有變化,相互對立又相互聯系,以這種詩歌結構來融合莊禪相對與相合的辯證思想,卞之琳于此可謂深得唐詩精髓。
與卞之琳不同,前期的馮至所崇尚的是浪漫主義的詩歌,受歌德詩歌影響較深,但他所接受的歌德與郭沫若所接受的歌德存在著本質的差別。較之于郭沫若詩歌強調激情的宣泄,馮至的詩歌較多現實的關懷,可以說,郭沫若所接受的乃是歌德詩歌中李白詩式的瀟灑飄逸,而馮至所接受的歌德則是杜甫式的沉郁頓挫。換言之,郭沫若是以李白、老莊去契接歌德詩歌,而馮至則是以杜甫、孔孟去契接歌德詩歌的。正因如此,馮至詩歌中自始至終保持著深沉的冷靜與克制。尤其是在抗戰期間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涯中,馮至自身的生命體驗與里爾克對于生命存在與現實擔當的深沉思考達到了高度契合,最終創作出了標志其詩歌創作頂峰的《十四行集》。






三、現代派新詩意象意境化與知性化分野之根源
中國現代新詩意象意境化或知性化,其根本成因取決于新詩詩人之詩歌閱讀經驗與詩歌審美心理結構,其中的某些核心因素,往往成為制約其新詩創作重要的“潛意識”,或自然而然滲透到其創作之中,或因詩人的刻意追求而使得某些詩美因素得以凸顯與強化。中國現代新詩詩人對唐宋詩詞意象的選擇、熔鑄與轉化也是如此。唐宋詩詞的意象有意無意地滲透詩人的詩歌思維之中,不僅成為其情感表達的重要載體,還制約其對整首詩歌意象的選擇與營構。戴望舒、梁宗岱、何其芳、林庚、吳興華、程千帆、孫望、林英強、侯汝華等詩人迷戀與崇尚唐宋詩詞,某些沉淀于其詩美心理結構深層的意象便自然而然地進入其新詩之中,同時,契合唐宋詩詞意象所奠定的基本情調,這些詩人也偏重于選擇富有情感內涵的西方詩歌意象;而以廢名、卞之琳、金克木、路易士、徐遲、南星為代表的另一部分現代派詩人,雖然也崇尚唐宋詩詞中那種惝恍迷離的意象類型,但因其偏重于佛禪道儒之哲學玄思而逐漸趨向于對艾略特、奧登以及玄學派多恩等詩人那種玄學化、思辨化詩風的體悟與追隨。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現代新詩對唐宋詩詞意象選擇、熔鑄與轉化的兩類基本形態。

同樣是對唐宋詩詞藝術資源的選擇與吸納,中國現代新詩在意象形態及審美特征上卻出現如此巨大的差異,其根源不僅在于新詩詩人不同的詩歌經驗結構,而且還取決于對這種經驗結構的擴展與轉化。詩美經驗擴展的基本途徑是經由已有詩美心理結構對于新的詩歌資源的選擇、接受與轉化而實現的。那些追求新詩意象意境化的新詩詩人,因其對于唐宋詩詞中注重情趣與興象玲瓏之美質的一路詩風的吸納,決定了其詩美經驗擴展的基本方向,必然走向瓦雷里、魏爾倫、馬拉美、蘭波等突顯情感內質與感性形式的詩風。情感因素的突顯必然導致意象類型化的要求,于是,以那種富有感性內涵的唐宋詩詞意象去契接西方詩歌同類意象,便成為其新詩意象營構的基本途徑。而那些注重融合杜甫詩歌及宋詩理趣詩風的詩人,則往往傾向于以唐宋詩詞意象去契接與融合艾略特、奧登等現代派詩人之詩歌意象,其意象體系呈現出玄學思辨的知性化特征。
不同審美趣味的新詩詩人,不僅在意象選擇上存在著巨大分野,而且在意象組接與營構方式上也呈現出較大差異。傾向于唐宋詩詞意象的新詩詩人,往往呈現出意象的密度與并置特征;而那些熱衷于意象知性化的新詩詩人,其詩歌意象往往較為稀疏,意象之間的組接往往穿插較多的修飾性語詞。這種意象疏密的形成及其組接方式的設置便秉承了漢語詩歌,尤其是唐宋詩詞依據情感特性及精神指向所形成的文體特性。意象的類型化、意象的疏密以及意象的組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中國現代新詩意象意境化與知性化之分野。


上述兩類詩人對唐宋詩詞之宗尚,同中有異,既有共同宗尚之詩人詩風,又在對同一宗法對象之具體因素的選擇、接受與轉化上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因而其新詩創作在遵循現代主義詩歌整體風格的同時,在詩美品質上呈現出較大差異。其中最明顯的便是20 世紀30 年代出現的“晚唐詩熱”。無論是傾向于意象意境化的詩人,還是追求意象知性化的詩人,均熱衷甚至迷醉于晚唐詩風,但在其選擇具體詩人詩風的時候,卻各有偏重。前者著意于晚唐詩歌之含隱蓄秀、深情綿邈;后者則偏重于晚唐詩風中的奧僻幽邃、冷峻鐫刻。



同樣是迷戀溫庭筠詩詞并受其影響,廢名與何其芳因詩學淵源、審美趣味之差異,而導致了在意象選擇與運用上的知性化、意境化之分野。雖然這只是個案的對比,但若對現代派詩人均熱衷于迷戀的李商隱做具體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將會是一致的。這充分表明,造成現代派詩人對唐宋詩詞意象借鑒、接受與轉化中意境化與知性化分野的根源,不但在于對意象類型的選擇運用,也取決于他們所吸取的與這些意象進行組合的另外一些因素。換言之,唐宋詩詞只是影響詩風的重要因素,而非決定因素。

綜上所述,20 世紀30 年代的中國現代派詩人從內心深處秉持著對唐宋詩詞的熱愛之情,使之成為其詩歌審美心理的“前結構”,換言之,唐宋詩詞成為現代派詩人詩歌知識與詩學觀念結構的構成因素,因而其詩歌創作大量吸取與運用唐宋詩詞意象。部分現代派詩人沿襲了唐宋詩詞的意象意境化追求,并融合西方現代派詩歌意象藝術,其詩歌呈現出含蓄蘊藉空靈幽晦的審美特征。而另外一部分詩人則將唐宋詩詞意象中的知性化特質以及中國傳統的儒釋道思想,與西方以艾略特等為代表的知性化詩歌傳統相融合,其意象藝術呈現出鮮明的智慧美感特征。現代派詩人的這種意象藝術的分野,既是個體詩人個性特質及詩學觀念的具體呈現,更是其師法的詩學淵源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