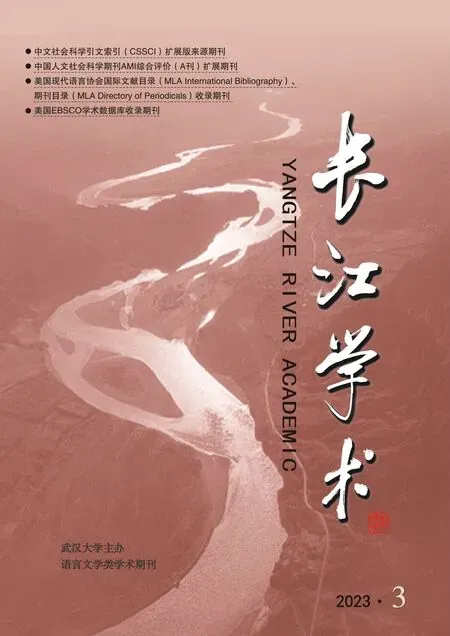論“雜史”“傳記”摻雜之“小說”
——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
王慶華
(華東師范大學 中文系,上海 200241)

一、近代以來學界忽略“雜史”“傳記”摻雜“小說”之成因

近現代以來,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比較突出的局限性表現為“以今律古”“以西律中”,在一定程



上述人文學科研究范式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形成的突出影響就是小說觀念的“以今律古”“以西律中”。這種研究思路造成了古代小說研究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其寄身其中的原有文類體系,對“小說”與“雜史”“傳記”之間的關聯互動關系論述較少,更是缺乏對未納入“小說”范圍的比較純粹的“雜史”“傳記”作品中的“小說”成分的關注。
二、“雜史”“傳記”摻雜“小說”之存在形態
“雜史”“傳記”“小說”雖然有著各自相對獨立的文類規定性,但也具有鮮明的同源共生、相互影響、互為補充的關系,三者都屬野史之流,多由記載見聞、傳聞或鈔撮眾書而成,率爾而作、內容駁雜,不少內容真虛莫測。除了因內容性質相近而被歷代官私書目混雜著錄于“雜史”“傳記”“小說”的著作之外,一些歷代官私書目普遍著錄于“雜史”“傳記”類的作品內容繁雜,也會收錄一些志怪志異、瑣細軼事、荒誕傳說等“小說”性質的作品,甚至個別著作整體上都與“小說”比較接近,古人對此亦有著清晰的認知。



此類“雜史”“傳記”作品中雜糅“小說”成分,存在形態多種多樣,可主要概括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雜史”“傳記”之作的編撰體例、題材性質及旨趣整體上與“小說”比較接近。


(二)“雜史”“傳記”之作采錄史傳、野史雜糅而成,各部分內容或多或少普遍摻雜了一些“小說”成分。


(三)“雜史”“傳記”之作僅有局部內容在著述體例、題材性質上與“小說”接近或摻雜了“小說”成分。

三、“雜史”“傳記”摻雜“小說”之題材性質



《四庫全書總目》對“雜史”“傳記”摻雜“小說”的評判,也主要沿著上述“小說”題材意識而展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雜史”“傳記”中“小說”成分的評述,從一個側面集中反映了古人對“小說”文類規定性的認知,實際上在相互比較中回答了何謂“小說”之問。
四、“雜史”“傳記”摻雜之“小說”應納入古代小說研究





上述現象對我們研究古代小說有著重要啟示。“小說”作為古代敘事文類、文體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史部之“雜史”“傳記”等相關敘事文類、文體存在著同源共生、文類混雜、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等種種難以割斷的密切聯系。因此,只有將文言小說起源和發展演化置于整個古代敘事文類、文體體系及其敘事觀念體系中加以觀照,特別是全面深入地把握文言小說與相關敘事文類的共生、聯系、混雜、區分、影響等相互關系,才能超越文學研究與史學研究之藩籬,更好地還原和把握其文類規定性及其發展演化。這不僅有助于將“小說”文類、文體放在整個古代敘事性文類、文體譜系背景下以更宏闊的視野來理解,而且有助于從相關文類、文體的相互聯系和區分的比較中,更深入地把握其文類、文體獨特的規定性。同時,只有回歸其原有文化語境,從文言小說與相關敘事文類、文體的具體關系中探討其起源過程和發展邏輯線索,才能超越就文言小說而研究文言小說之局限,進而深入揭示文言小說及文言小說觀念發生起源和發展演化的具體歷史過程和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