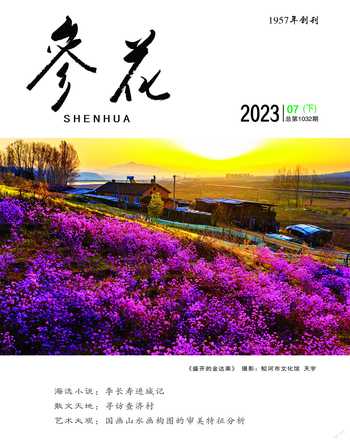山雪記憶(組章)
山里人的手推車
小嘎子時,第一次見到山里人用的手推車,感覺有些怪怪的。怪在哪呢?怪在車廂里到處是大窟窿,外加上那么一對長長的轅子。
城里人用的板車,有后堵、有車廂、有密不透風的底板。而山里人用的手推車,沒有后堵、底板,就四個大橫撐。車廂的兩個翅膀子,是兩個木方鉚上一塊橫板。從車廂里,能看到兩個車轱轆。
手推車雖然樣子簡單,結構卻是用標準的柞木榫卯連接而成,周身不用一根釘,牤實抗造。拉起柴火來,是長轅子爬犁的兩到三倍。比城里板車裝載量大多了。此乃山里人的發明創造,體現了山里人的智慧。
通過實踐,使我懂得了手推車大窟窿與長轅子的作用和價值。大窟窿不光綁繩方便,裝柴火靈活實用。長轅子有利于駕馭,能加大裝載量。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林區人,都燒大柈子。一節柈子六十厘米長。拉燒柴的人,在家里就在鋸把上做個標記。上山截木材,不用帶尺。四節柈子,用鋸量四下,快捷方便。兩米四長的圓木,在手推車里擺放得齊刷刷的,駕轅子的人,“坐坡”時,后背靠到擺放齊整整的木材時,能使上勁,且不會被木頭戳傷。
有更長一些的木材,就隨車轅子擺放,一直擺放得挺高,木材擺放時,把手臂活動的地方留出來,長轅子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些,都是板車做不到的。城里人到山里來居住,用板車拉燒柴,會遭到山里人嘲笑的……板車裝載量少,不得不入鄉隨俗,將車型改造成手推車。
手推車底的大窟窿,可以隨彎擺放有大癤包的木材。癤包朝下,上邊還是平平展展的。
上山拉燒柴,那可是個艱苦的活。人多,柴火越來越少,路途越來越遠。一出去就是七八個小時。出發時,兜里揣個發面餅子,貼在胸口上。幾個小時后,拿出來吃,還是溫乎的。渴了,抓把雪塞嘴里。
在山里,連爬犁都不敢用,陡峭山坡上,用繩將木材一趟一趟牽引下來,裝爬犁;再用爬犁把木材倒到手推車處,裝車。在凹凸不平的山野里,人像老牛一樣牽引,鼻尖都快碰到地面了,汗珠掉地下摔八瓣兒。那汗出的,三九天帽子都不戴。稍一停下來,耳朵“滋兒”的一下,就凍壞了。手腳凍壞了,是常事。凍壞了手腳怎么辦?山里人用冬天樹上結的“冬青”洗腳。或者用煙梗子、干茄子秧放到開鍋的水里煮,然后用煮茄子秧水洗腳。煙梗子也是一樣……
手推車放坡時,相當危險,要把車轅子?起來,必要時兩邊一面一個護轅子的。還有的在車后,栓個“擼死狗”,即一截圓木,或一捆柴火。車轅子短了,怎能行呢?
手推車還分“大軸”的和“小軸”的。大軸的也叫“通軸”。通軸粗。小軸細。大軸的拆卸方便。還可以當杠鈴舉。
有“通軸”的 車,在那個貧瘠的年代,也是一種驕傲,不起眼的手推車,不是家家都能買得起的。
山里人的柈子,用“溜”或“平”計算。“一溜”即一米高,六十厘米寬,四米長。“一平”即一米高,六十厘米寬,十二米長。
誰家要是買柈子,就問:“買多少?”
或曰買“一溜”還是買“一平”……
那個年代,誰家要是有個齊嶄嶄的大柈子垛,外加一圈齊刷刷的大杖子,和一個像樣的大門,往往會受到人們的夸獎。這才是正經過日子的人家……
消失的柈子垛
通往山里的雪路,經人馬牛爬犁碾壓,打磨得油光錚亮,兩條并行的爬犁道,在太陽的照射下,閃閃發光。
仨一伙兒、倆一串兒的人們,拽著長轅子爬犁,爬犁上綁著繩斧鋸,進山拉燒柴。夫妻、老少爺們兒齊上陣。
滿載而歸絡繹不絕的爬犁,一路吱吱啦啦,碾壓往日不平凡的歲月;多少辛酸多少無奈,都在歲月中耗去。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有手推車的人家微乎其微,家家使用一臺長轅子爬犁,蹶跶蹶跶費勁巴力,像牛一樣往家拽運燒柴。
表面上看,拉個小爬犁,挺浪漫挺刺激。實際干上三天您試試,那才真叫體力活。沒挨過那種累,實難體會其中之苦。
零下三十來度的嚴寒,帽子撇在爬犁上,背繩的后背,一條明顯黑乎乎的汗印,身上頭上蒸蒸冒著熱氣,那爬犁不拽,一步也不走,它不像手推車有慣.性,能跑起來,拉爬犁不注意身體貪載能累吐血。
當年拉燒柴,漫山遍野都有林業工人采伐過的樹頭,用鋸截成段隨便裝揀,快捷省勁。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柴火越來越不好找。林業部門開始限制。十二厘米以上的干樹頭,不許隨便拉。否則,罰款,嚴重者拘留……
靠山吃山,住在林區,得燒火做飯,茅草榛柴沒人燒,家家燒大柈子。哪家沒有一個大柈子垛?
高兩米、長五六米,小一點的,高一米多,長三四米。正面齊刷刷戳在院子里。那就是一面墻。柈子垛的大小,能看出當年家里日子過得怎么樣。
人口少的,一冬天下來,燒一小垛,人口多點的,燒一大垛。經過一冬一夏,一年到頭燒一垛柴火。人們就這樣在年復一年拉柴火的歲月中度日。
冬去春來,一垛柴火燒光了,再費勁巴力地組織人力去拉。十幾年下來,柴火越來越難找。拉燒柴要往返三十里山路,近處柴火都被人們揀絕了。
頭幾年上山不用帶飯。幾年后,再拉燒柴,帶一個發面餅子,揣在暗兜里,渴了,抓把雪就發面餅子吃。
一車柴火拉到家,耗費好幾個小時,來回要走二十多里路。
雪大路滑天冷,棉烏拉呱呱濕,一冬天一套棉襖棉褲,家窮孩子成堆,沒有換洗的,晚上,把棉鞋墊、棉烏拉放在火墻上烤。腳底下,炕棉褲。屋里散發著一股酸臭的鞋墊子氣味兒。否則,濕乎乎的穿在身上,只能用自己的體溫溻干。那滋味不好受。
放爬犁時更驚險,面對陡橛子——既高又陡的坡,一爬犁柴火,從上邊放下來,兩手死死地抓著爬犁轅子,人在坡下跐溜,就是人倒了,兩手也不要撒開,撒手,非傷即亡。爬犁要是敗道跑偏了,腳底下樹橛子,樹,撞上頭部還有好啊!多大的慣性啊!
膽小的,不敢放,干脆撒手叫爬犁自己“穿箭”,一旦扎到樹空里,一個人甭想弄出去,只好等山上人下來,或者接山人過來幫忙,把敗道的爬犁重新弄上軌道。山里人,民風淳樸,沒人看笑話。
小嘎子時候,有一個美好的夢,非常羨慕這樣的人家:蓋一座一面青的磚房,房蓋上,苫上一種整齊的、叫小葉樟的草,大板皮障子齊刷刷地排到大門口,兩扇漆黑的對開木制大門,上面有個雨搭。對開的大門中間,鐐吊子門閂,一拽嚓嚓響。外面對開的大門中間,吊著兩個錚亮的銅環。院子里,打掃得一干二凈。甬道邊,擺著一排齊整整的大柈子垛,這才是正經過日子人家!
我兒時的夢,就是自己將來找一個干凈、知書達理的媳婦,把家里的環境,布置成那樣,這輩子就沒白活!
時光飛逝,人已經變老,當年那美好的夢,已經成為塵封的往事。幾十年過去,生活水平今非昔比。我不但脫離了那種環境,還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居然住上了八十多平的樓房。自己不但成了作家,還把自己故鄉消失了的人和事,寫在電腦里,拿出去發表。
現在,再也不用為拉燒柴而犯愁。也不再向往那家家門口擺放的大柈子垛是如何壯觀好看。
再回首,重游故鄉西林,都住進了樓房。山里人,也不再拉燒火柴,拉燒柴那又苦又累的往事,已經成為過往。
黨的環保政策,不許亂砍濫伐,山野林區經過多年的修整,各種動物增多,又出現了一派勃勃生機!
打陀螺
“嘎”“嘎”,悠遠之處,傳來兩聲清脆炸裂的響聲,也許是寒凝大地的緣故,聲音傳播得格外遠,隔著三十來米距離,就能聽到聲音。等走到近處一瞧,才發現,好嘛!是幾個成年人,在揮動馬鞭一樣的大鞭,抽陀螺。
陀螺是書面用語,我們老家都把陀螺習慣性叫冰尜,打尜也是我曾經的最愛。
五十年前故鄉的冬天,家住在一個林區小站,街道上沒有汽車,只有馬爬犁、牛爬犁、人爬犁,路面被這幾種爬犁,碾壓得又光又滑。我們小嘎子,可以在路面上,盡情地打冰尜。
七八歲正是“討狗嫌”的年齡,有了打冰尜這個好玩的游戲,再冷的冬天也無所畏懼,嫻靜的冬日不再寂寞。
久居林區,尜源隨處可覓,隨手削一個木頭疙瘩,就是一個不錯的尜。家家都有大柈子垛,軟木、硬雜木、中性木質,隨便選。
有時候,三五個小嘎子,聚在一起,比誰的尜好,在抽同樣鞭數的情況下,看誰旋轉的時間長。比尜與尜相撞,看把誰撞歪,撞倒、撞滅。勝者找到了極大的快樂。敗者不服輸,不行重來。
有一年,班主任高興了,突發奇想,組織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比賽:男同學打尜,女同學踢毽子。
打尜比賽的規則,就像我前面寫的那樣,比誰旋轉時間長,比誰的尜能把其他同學的撞翻。那次比賽,我斬獲冠軍,得了一個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小日記本。至于比賽的勝利,是我贏在“武器”上了。
六十年代,我父親就是六級鉗工。是父親幫我制作了一個“鋼珠螺母尜。”
鋼珠螺母尜,體積小、底盤穩、鋼珠著地面光滑,別的木質尜,沒法比。這就像“叫花子和龍王爺比寶”,轎車和面包車賽跑。
那次比賽之后,小朋友都紅了眼,木質尜都淘汰了,都在四處踅摸鋼珠螺母……鋼珠是軸承潤滑旋轉,螺母是固定螺栓,想不到,它倆鑲嵌在一起,成了最佳組合。
鋼珠螺母尜旋轉到達極速的時候,釘在那里一動不動,能把雪軋過的路面,碾出一個小坑。
我現在,在城里看見打尜的,都是退休的成年人,春夏秋都在廣場水泥地面上打尜;冬天,在冰場上。
成年人玩的尜特別大,粗有十多厘米,高有二十多厘米,大鞭子也大。眼見幾位,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嚴寒中,把帽子脫了,一只手拿著帽子,一只手輪著大鞭子。“啪、啪”抽幾下之后,抱著膀欣賞自己的作品。有時扎堆閑侃,他們在快樂中游戲,在游戲中鍛煉身體,美哉!
小嘎子打尜,是單純游戲,不知道何為鍛煉身體,只知道玩樂,在玩樂中逐漸長大成人。
閑聊中,認識了修配廠的老徐,他原來是個車工,退休了沒事,五冬六夏打尜,夏天在廣場上抽尜,冬天在冰場玩,他不但右手會抽尜,左手也學會了抽鞭子。身體全方位得到鍛煉。他使用的尜,都是自己制作的,這為他節省了好幾百塊錢。有的尜還帶“發光體”,晚間也能玩。
市政府公園,有一個比較大的人工湖,夏天是水,里面有荷花、噴泉、小魚,供流動的人們觀賞。冬天,凍成了冰,供冰刀愛好者滑冰、打尜。冰場分成兩塊,大處滑冰,小地方打尜。
小冰場,自己維護,下大雪了,主動清除。冰面不光滑處,從公共廁所取來水,澆冰。等冰面像大鏡子一樣,便是打尜愛好者的旋轉世界。
時光煮雪,轉眼就是百年,好想重新回到童年。
作者簡介:聶孝明,系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會員,綏化市作家協會理事。出版散文集《行徑山野》。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