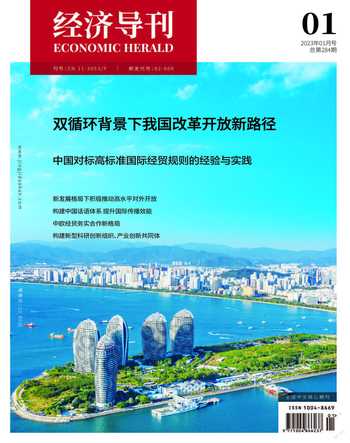推動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落實落地
呂建中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營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的良好環境,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
2022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有力統籌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布局,實施一批國家重大技術項目,完善新型舉國體制,發揮好政府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組織作用,突出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
過去曾說企業是技術創新主體,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提出企業是科技創新主體,更加突出了企業在未來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特別是對大型骨干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業應該是創新活動的主要承擔者
深圳為什么具有很強創新能力?它是一個典型的由企業作為主要創新主體的體系,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搭臺子、提供服務和一些必要的組織功能。深圳的市場化程度、國際化程度比較強,企業自主創新的動力和活力,來自于市場競爭的推動。
企業是純粹的市場競爭主體。和大學、科研院所相比,企業直接面向市場,它的產品首先要被市場承認;企業組織生產要有嚴格的質量和財務控制,因而必須掌握相關知識和生產要素,企業是新科技知識的主要需求者,也應該是創新實踐活動的主要承擔者,包括創新項目的選擇和決策、科研投入和組織、成果的鑒定、受益與推廣;同時承擔相應的風險。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依靠創新,創新是企業競爭力的關鍵要素。
過去,國有企業管理機構對企業的考核,強調企業的當期收益和利潤,而淡化了企業科研投入和技術創新的累積效應,導致企業技術儲備不足。當前我國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形成短板、被“卡脖子”等一系列問題,這和之前管理體制和政策的失誤不無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歷次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文件都強調,要推動企業加強科技創新、成為創新主體。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大力加強企業的技術吸收與開發能力和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中間環節,促進產學研的合作。1988年,《國務院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企業的技術開發和吸收能力。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使企業成為技術開發的主體。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提出,要讓企業成為科技投入的主體。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全面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的意見》明確提出,建立健全企業主導產業技術研發創新的體制機制。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提出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四個維度,即自主創新的“決策主體、研發投入主體、科研組織主體、成果轉化主體”。
2020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要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促進各種創新要素向企業聚集。
所以,現在判斷企業是不是創新主體的標準很明確,就是看它在技術決策、研發投入、組織科研、成果轉化方面,是不是有積極作為。
從1985年到2020年,我國企業的科技經費投入、研發人員在全國科技投入和科技人員總量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設立研發機構的企業的比例不斷增加。在成果轉化和科技決策方面,企業的自主性也不斷增加。例如,企業所屬研發機構在國家研發機構總數的占比,1996年超過50%,2020年達到82%。發明專利的申請量來自企業的占比,1996年超過50%,2020年達到將近70%;發明專利授權量占比2004年超過50%,2020年為63%。研發經費的占比,1998年超過50%,2020年達到77%。企業研發人員占全國科技人員的比重,2000年超過50%,2020年達到77%。技術市場貿易額占比,2004年超過了50%,2020年達到91%。
近年來我國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不斷提升。國有大型企業擁有5000多個科研機構、200多名兩院院士,學科配套齊全,具備國家實驗室、科研機構甚至大學的部分科研功能。特別是1999-2000年,轉制為國有企業的200多家科研院所,多數是部委直屬的從事產業基礎共性、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以中央企業為例,最近10年先后建成了700多個國家級的研發平臺,7個創新聯合體,其中5G、高鐵、大飛機、發動機、工業母機、能源領域,攻克了一批“卡脖子”的核心技術難題。
落實企業創新主體地位面臨的主要障礙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總體在逐步提升,但仍存在企業創新主體地位落實不到位的問題。
從國家創新體系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經濟主戰場,在各個應用技術領域也紛紛面向市場,進行自主研發和轉化,以及自辦企業。而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協同合作、政產學研用的合作效果則不盡如人意。企業在國家重大科研計劃中的話語權不足,大量科研成果不能及時有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從企業角度看,改革之初,企業的創新活動主要為已有技術成果的轉化,較少做基礎工作。很長一個時期,大部分企業偏好引進國外成熟技術,偏好“短平快”,導致在獲得新技術方面基本處于短期行為,缺乏立足于長遠考慮企業技術戰略構想。
2006年以來,中央大力倡導自主創新和增強企業創新能力,重點依靠“引進吸收再創新”或者“集成創新”,有很大進步,但由于缺乏深厚的自主科研基礎能力,產品的更新換代主要建立在別人科技成果的基礎上,原始的核心技術還在人家手里,在總體上還處于追趕或跟隨技術先進國家的階段。
我們企業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比較薄弱。中小企業基礎研究人才、科研能力和財力不足,一些大型企業缺乏基礎研究的動力。1999-2000年期間,200多家改制的科研院所,原來都是部委或者行業的基礎研究與共性應用基礎研究的“老大”,有很好的基礎研究力量。現實中,這些企業的基礎研究能力在企業改制后就開始“坐冷板凳”,這一代人退休之后,人才青黃不接。現在這一類轉制研究院所的主營業務是技術服務和技術推廣。
中央非常重視科技自立自強,要求大力加強企業科技創新能力,但是在實踐中還存著一些阻礙。
首先,國家科技布局中大企業的地位偏弱。國家安排企業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時,強調企業在技術成果商業化推廣和示范工程方面的作用,而企業在政產學研用合作中處于被動地位,在國家重大科技決策中更加缺乏話語權,國家重大攻關項目和重大科技決策的專家組構成,企業科研人員所占比重很小。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對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的認識不足。長期以來,政府主導的國家創新體系中,科研院所和高校占據主體地位,企業主要被視為生產經營主體,重點承擔技術成果的轉化,在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決策中,企業的話語權和研發主導權不足。
其次是企業自身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有企業現行管理規制約束了企業創新。這點是最需要關注的,也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轉換新舊動因的必要性之一。
國資部門對國有企業的干預比較多,限制了企業的創新動力和活力。在企業的人事管理上,國企領導的行政任命和有限任期,導致企業缺乏長期、系統的創新戰略規劃,不利于有潛力的企業家人才的培養和能力的持久發揮;在企業考核上,比較偏向財務指標,且過分強調保值增值,對企業創新投入形成硬性約束;定期的巡視審計,也限制了企業科技創新的積極性。盡管規定允許試錯,但容錯機制很難落地。這導致企業領導對待技術創新更多基于規避風險。
最后,科研成果轉化的人員激勵政策難以到位。由此,有競爭力的創新生態環境還沒有建立起來,一些國家法律法規還不完善。
相關的思考與建議
(一)從國家和政府層面看。一是把國家關于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的一系列政策落實。建議多出一些可操作、可考核、可監督的實施細則。二是明確企業參與國家科技決策的常態化機制,要多征詢企業的意見。三是鼓勵和支持企業根據國家戰略需求,牽頭組織相關重大攻關項目,包括通過創新聯合體、創新中心等組織形式;企業既可以當出題人,也可以當閱卷人,還可以當答題人。四是支持有條件的科技領軍企業加強基礎或應用基礎研究。五是發揮好大型中央企業成建制科研力量的作用,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
(二)企業要加強自身的創新能力建設。一是進一步加大企業的研發投入,特別是增加立足長遠的應用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二是要使企業成為研發主體,形成研發能力體系。三是加強國際合作,打破行業“圍欄”。四是在產學研合作中,企業要主動作為。五是大企業要當好鏈長、鏈主,要與中小企業協同創新。
(三)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創新生態。
一是切實落實企業家精神。一個企業要想成為創新主體,充滿創新活力和動力,必須要有企業家精神。要支持企業家做創新發展的探索者、引領者,鼓勵企業家與科學家深度合作。
二是要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要把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三是強化科技金融、科技市場、中介服務的作用。由于科研人員缺乏市場、缺乏資金、缺乏發展計劃等,會出現“死亡谷”。而依靠企業家,依靠科技金融、科技市場、中介服務等,可以幫助我們跨越“死亡谷”,使科技人員真正能夠安心科研,科技成果能夠順利進入市場、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從而真正使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編輯 宋斌斌)